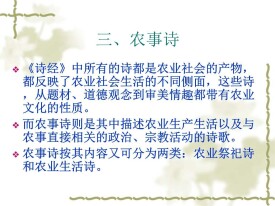農事詩
農事詩
《農事詩》四卷(約成於公元前37-30),每卷五百餘行,分別寫種穀物、種橄欖和葡萄、畜牧、養蜂等農事,屬於赫希俄德的教諭詩的類型。維吉爾此詩是應麥凱納斯之約而寫的,為屋大維吸引農民回到農村的政策服務。
詩人雖未描寫大田莊制度下奴隸的勞動生活,但他同情並肯定勞動,認為“勞動戰勝了一切”;他對照戰亂生活與和平寧靜的農村生活,歌頌義大利豐饒的自然資源,表達了奴隸主階層的愛國情感;他描寫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和動植物的習性(如蜂群的勞動和戰鬥),保存了當時的一些農業知識。詩中也有些神話插曲(如俄耳甫斯下冥土尋找妻子)。在對自然的看法上,他和盧克萊修不同,他仍然相信神的主宰力量。這部作品的風格特點在於詩人對種種自然現象很敏感,賦予生產勞動以詩意,表達了獨立小農的情趣。
作為一個泱泱大國,農業是中國幾千年的頂梁業,其歷史源遠流長。而由此衍生的關於農事的詩更是耐人尋味,延至後世的田園詩已是春花爛漫的詩壇一景。當陶淵明以清新明凈的詩體樹立了一個范型,成為田園詩的正統,開闢了田園詩的疆域時,田園詩便在詩壇蓬勃生長,然索田園詩之源,陶淵明並非第一人,最早的田園詩稚形應推《詩經》中的農事詩。其中人們熟知的《七月》固然是《詩經》中的優秀作品,但除它之外,雅頌中的十首農事詩,國風中的採集之歌與牧人之詩,也可視作中期的田園詩。田園與農事是分不開的,即使是後世文人大夫的田園詩也離不開農事的內容。由於後世寫田園詩的人能真正接觸農事的不多,所以他們筆下的農事往往變了味。在這種情況下,《詩經》中的農事詩更顯出了它獨特的價值。
現存《詩經》中的周代農事詩約有十一首,這十一首農事詩即是園詩的先驅。
周禮將這十一首農事詩分為《豳詩》、《豳雅》、《豳頌》三類。《豳風》中的七月為《豳詩》;《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為《豳雅》;《周頌》中的《思文》、《臣工》、《噫噫》、《豐年》、《載芟》、《良耜》為六篇《豳頌》。
據《周禮。春官》記載,上面這十多篇農事詩有明顯的祭祀祈年的目的:“中(仲)春,晝擊土鼓,籥(吹)《豳詩》以逆(迎)署。中秋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籥(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祀蠟則籥(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可見,這些作品是周人祭祀所用的樂歌,在每年的寒暑交易之際,要舉行儀式,在這個儀式上,眾人相聚,吹豳籥,擊土鼓,歌《豳詩》,祈求節序分明,風調雨順。而在祭祀田祖,或逢蜡祭時,也以此儀式來祈求豐年,勞送萬物,使其休息。因此,這些以農事為內容的樂歌,實際上是在特定的場合用來祈求豐年的祭歌。
由於周代的這些農事詩帶有明顯的宗教目的,所以這十一首農事詩實際上是宗教活動和農家生活的混合物——祭祀與農事的混合;宗教精神與田園風情的混合;祈年的目的和描摹勞動場面的混合;這種混合,不是個別的現象,它不同程度地存在於這十一首農事詩中。(關於《七月》,留在下面談)。對於雅頌中的十首農事詩,過去的評價不高,原因是它沒有更多地表現下層農人的生活和情感,其實這些作品為提供了另一種視角,即為了祈年的目的,如何去敘述農事活動,以求得神靈的庇佑。這些詩當然是以上層人物的觀念去觀照農村生活,而且還要達到祈年的目的,這就不能不使這類詩有一些虛飾的成分,但它畢竟還是反映了一些周代社會的真實情況:
這些詩大多首先是敘述農人的墾荒耕植: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今適南田,或耘或籽,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甫田》)
太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萬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大田》)
類似的敘述還見之於《楚茨》、《噫噫》、《豐年》等詩中,這些詩自然沒有反映下層農人的勞累和貧困生活,它表現的是作為農場主或高層統治者對農事的觀感。大規模的墾植,莊稼長勢良好,農官與農人克守厥職,詩中洋溢著一種土地所有者對生活的滿足感。這種滿足感還延伸到了秋收以後谷糧滿倉與祈求富足的場景:
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稷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庚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楚茨》)
豐年多黍多徐,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豐年》)
在統治者眼中,農業興旺,五穀豐登,自然是誘人的景色,但他們所希望的是神靈庇佑,萬世永享福酢。於是,這些詩無例地又將筆鋒轉向祈求萬世基業的祭祀場面:
執爨躇躇,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景福,萬壽攸酢。(《楚茨》)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大田》)
雅頌中這些農事詩的敘述程式,一般從開荒墾殖寫到五穀豐登,再到祭祀求福,表明了這類農事詩具有鮮明的功利目的,即祈求神靈保佑來年風調雨順,永享景福。猜想這類詩應起源於遠古部落的祭祀活動,通過敘述族人的活動,詠唱部落的成長狀大,以求得神靈的庇佑,雅頌中的這類農事詩,將農事與祭祀相結合,其淵源也應該是上古的祈年風習。
這些作品的價值在於它與《七月》可以形成互補,它所展現的一些場景是《七月》中所沒有的。譬如周代大規模的墾荒活動,周初五穀豐登的社會狀況,祈年的風俗等等。把它與《七月》相結合,才能夠較為全面地了解周人的田園與農事生活。故而對它的評價,也不能拘泥於是否表現下層百姓的生活,因為這類詩所表現的內容,畢竟也是周代社會的一種真實現象。並且它藝術上的平和雅正,在《詩經》中自然也能獨樹一幟。
若要說到能表現下層百姓的田園生活和農事情感的,首推《豳風》的《七月》為代表。
《七月》是豳風中也是十五國風中篇幅最長的作品。全詩共八章,每一章十一句,共八十八句。首章概述從歲寒至春耕期間,農夫們的生活與生產情況;第二章寫農家女子春天的採桑活動,及她們擔心被貴族公子侮辱的心情;第三章寫勞動者修剪桑枝,紡織染布和為貴族公子縫製衣裳的情形;第四章寫田間勞動結束后的打獵活動,以及把大部分獵物交給領主,忍受殘酷的剝削的情景;第五章寫秋盡冬來,農夫們為抵寒而修整破敗不堪的屋舍的慘象;第六章著意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寫出農夫們以野果、野菜充饑的痛苦生活;第七章寫秋後的緊張和勞累;末章寫冬季鑿冰、貯冰,並描寫了年終的祭祀和宴飲。
《七月》的可貴,在於它歷敘周人一年四季的農事活動,從中可以看到雅頌中所不易見到的景象。諸如從正月到臘月,農耕打獵、採桑織布、鑿冰春谷、索茅修屋、無不一一畢現。清人方玉潤說:“《豳》僅《七月》一篇,所言皆農桑稼穡之事,非躬親隴畝,久於其道者,不能言之親切有味也如是。”(《詩經原始》)詩中所敘述的浸滿了農民血汗的勞動生活,是雅頌中的農事詩和後代田園詩所難以企及的。雖然《七月》的作者不一定是農民自己,但從他對農村生活的熟悉程度看,當是一位非常接近下層百姓生活的人。
《七月》的可貴,還有在於它是一篇以農民的眼光去寫農民生活的作品,這一點尤其為後世田園詩所難能。在《七月》里,農人耕作的辛勞、物質的貧困和精神的創傷得到清晰的再現。其中有農人不得喘息的勞累:“八月剝棗,十月獲稻。”“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可以聽到家婦在隆冬臘月無衣避寒的憂慮:“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還可以看到寒風呼嘯,陋室棲身的慘況:“穹窒熏鼠,寒向瑾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這種沾滿泥土與血汗的描寫,不是後世士大夫過膩了官場或城市生活,到田園去尋覓新鮮感受的文人田園詩;也不是政治家站在高處,以憂國憂民的情懷去俯視農家辛勞的田園詩;而是以平視的角度,以農民的眼光觀照農民生活的、充滿了泥土血汗氣的田園詩。
《七月》的藝術手法也是獨特的,它通篇採用“賦”的表現方法,全靠如實敘述,以事實訴讀者,彷彿一個飽受辛酸的農夫在有條不紊地講述他年復一年的痛苦生活,長而不亂。詩的各章都是按季節時令的變化來安排結構,讀來親切自然。此外,為了更鮮明地揭示出剝削的本質,採用了對比的手法,從衣食住等幾方面加以對比,給人具體感受,語言樸實,如泣如訴。
此外,《七月》還是一篇農業百科全書似的作品,它全面地反映了周代農家生活的全貌。其中不僅有農家一年四季農耕打獵、採桑、織布等勞動場景,還涉及到節令氣候、飲食起居、倉儲納陰、築場修屋、春灑賀壽、羔韭祀神、衣著分配等到周人生活中各個方面的情景,因此說它是一篇百科全書似的作品毫不過分。清人姚際恆《詩經通論》評《七月》說:
鳥語蟲鳴,草榮木實,似《月令》;婦子如實,茅綯升屋,似風俗書;流火寒風,似《五行志》;養老慈幼,躋堂稱觥,似庠序禮;田官染職,狩獵藏冰,祭獻執宮,似國典制書。其中又有似《採桑圖》、《田家樂園》、《食譜》、《谷譜》、《酒經》,一詩之中,無不具備,詢天下之至文也。
所說雖然有些誇張,但他《七月》百科全書似的生活場景的概括還是準確。《七月》在對周代農家生活現實性的描寫上,既是空前的,也是後世罕見。清人方玉潤還從藝術上指出具卓絕處:“今玩其辭,有樸拙出,有疏落處,有風華處,有典核處,有蕭散處,有精處......無體不務.晉、唐后,陶、謝、王、孟、韋、柳田家諸,從未見臻此境界。“《詩經原始》這一評價,從其手法的多樣化來說也是準確的。
詩經中還有不少的作品也涉及農人的生活場景,但都不如《七月》祥盡而完備,價值取向上也有所不及,所以就不再補述。
在上述的詩里,聽到了農事與祭祀的交響,看到了生活似的畫卷,在田園牧場,還可以聆聽婦女的採集之歌、牧人的放牧之歌、獵人的狩獵之歌。這一切,構成了後世田園詩所少見的景象。
是一首非常有味的採集歌,那是來自一群婦女的吟唱:
采采苤苢,薄言采之。采采苤苢,薄言有之。
采采苤苢,薄言掇之。采采苤苢,薄言捋之。
采采苤苢,薄言禧之。采采苤苢,薄言襭之。
全詩共三章,雖然中間只更換了六個動詞,卻生動地描繪出一群姑娘採集車前子的勞動場面和全過程:始則相呼而采之,中間掇捋而采之,最後禧而歸之。這首詩所寫的內容,本來只用一句話就可以明白,如若不採用重疊唱的形式,反覆詠唱,必然會索然無味。正因為採用了復沓的形式,再加上語助詞的反覆出現,才準確地傳達出那種歡快的勞動節奏。隨著反覆詠唱,讀者也就逐步體味和感受到詩的優美意境。正如清人方玉潤說的那樣:“讀者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誘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詩經原始》)。
寫宮女為王宮的祭祀之事而到野外採摘白蒿:
於以采蘩?於沼於沚。於以用之?公候之事。
於以采蘩?於澗之中。於以用之?公候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宮女為公候之事(指祭祀),在沼澤沙諸山澗繁忙地採擷,直到光亮的發散亂如蓬方才回歸。詩人的敘述在表面是平靜的,但也透露出採集女的辛勞。
在牧場上,牧童的聲聲歌唱,引人入勝: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於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於嗟乎騶虞!(《召南。騶虞》)
從詩中所寫“葭”“蓬”的茁壯之貌以及對“騶虞”(畜牧官)之官的讚美來看,這無疑是一首牧業興旺的讚歌。彷彿看到牧童站在一望無際的草場邊上,不時發現突於蘆叢蓬草之中的大小野豬群,不禁發出對畜牧官的讚歎!再如《小雅》中的《無羊》更是首富有生活情趣的牧人之歌。全詩共四章。首章以兩個設問句作起,總寫牛羊較多,后四句描繪牛羊的情態,動靜結合;細緻地描繪出牧場上特有的景物氣氛。第二章開頭三句寫牛羊的各種形態。中間三句由牧及人引出牧人,他們披著蓑衣,戴著斗笠;有的還背著乾糧,寥寥幾筆,便勾勒出風裡來雨里去還辭勞苦的牧人形象。后兩句則寫了牧人對牛羊繁盛的讚美,流露出喜悅與欣慰之情。第三章寫牧人的飼養,放牧活動:精選飼料,交配及時,牛羊肥壯。詩人用簡潔的筆墨敘寫了牧人的生活,表現了他們勤勞樸實的品質和對勞動生活的熱愛。末章以以牧人做夢與卜人釋夢作結。牧人夢見眾多的魚和無數畫著膺的旗,卜人說這是豐年到來,家室興旺之兆。這個富有喜劇色彩的結尾,為牧人的生活增添了吉慶的氣氛,也表達了古老的民俗風情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全詩以工筆描寫和動態刻畫顯示了牧人形貌與牛羊的活動,像一幅民俗畫,逼真、傳神,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所以前人讚美這首詩“真化工之筆也”(方世潤《詩經原始》)。
此外,像《采蘋》、《十畝之間》、《吉日》等,也是《詩經》中採集畜牧的優美音符。採集與畜牧,是《詩經》中田園農事詩不可缺少的補充,也是後世田園詩自然超詣的風味最為接近的種類,它們雖然數量不多,但與雅頌中的農事與祭祀混合描述,與《豳風。七月》的泥土血汗有著不同的面目和風格,在莊重濃郁之外,體現出明快的色彩。由以上介紹可以看出,農事與祭祀、生活的場景、採集畜牧,這些不同內容和風俗的農事詩,構成了《詩經》農事詩的動人樂章,真實地再現了周代田園生活的場景。這些醞釀於早期詩歌中的尚顯稚嫩的田園詩稚形,具有後世文人田園詩中所不具備的古樸和農人自己真實感受。後代的田園詩可以寫得更敏感、更細膩、更潤澤,但也同時失去了許多原本就屬於田園的東西,比如泥土味、血汗氣、渾樸的風格等,這也是《詩經》農事田園的可貴和不可替代的地方,它值得一代又一代的嘆詠。
《農事詩》描寫了一九四〇年春法軍大潰敗中士兵及人民悲慘的境況,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期間一個貴族家庭發生的悲劇,以及一個年輕的美國人在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時參加巴塞羅那爭奪戰的感受。戰爭和革命密切交織的題材,使小說富有濃郁的史詩色彩。小說採用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長詩《農事詩》為名,因為小說主人公不論是在大革命的驚濤駭浪中或南北征戰的炮火震天、硝煙瀰漫中,念念不忘家園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的農事,同時也寓寄維吉爾詩中蘊含的哲理:世事紛紜,複雜多變,只有四季恆常更迭,有秩有序,人也僅能在田園耕作中享受樂趣,在大自然中獲得安寧與慰藉。
西蒙嘗試用無與倫比的貼近重現物質現實,也許他未能成為一個畫家,但是他以畫家特有的敏感描繪接踵而至的場景,栩栩如生,令人難忘。西蒙沉醉於細枝末節、精雕細刻,勝過其他所有所知的作家。他運用電影式的表現手法,在一個鏡頭到下一個鏡頭之間沒有明顯的過渡,視覺聯想使意象此起彼伏,連綿不絕。在他的小說中紛至沓來的事件並非按照實際發生,而是根據敘述者講述的順序進入讀者的視野,突破常規,新穎別緻。當社會秩序的形式和協議消解為致命的混亂時,戰爭成為描述普遍人類狀況最恰當的隱喻。西蒙提供了一種暫時的藝術秩序——也只能是暫時的,堅定地接受現實,意圖抵擋這混亂轟轟隆隆向前進發的腳步。西蒙的哲學是堅忍的,禁慾主義的,他也的確在現實中身體力行:不起眼、嚴肅、寡言,更適於葡萄園,而不是沙龍。——《衛報》
作者: [法]克勞德·西蒙 譯者: 林秀清
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08年10月
頁數: 393
定價: 27.00
裝幀: 平裝
叢書: 現當代外國文學·上譯
ISBN: 9787532746057
克勞德·西蒙(1913-2005),法國新小說派作家。一九一三年出生於馬達加斯加,一九三六年參加西班牙內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參加地下抵抗運動。戰爭的經歷對他的小說創作產生了重大影響。代表作有《弗蘭德公路》、《農事詩》和《歷史》等,一九八五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