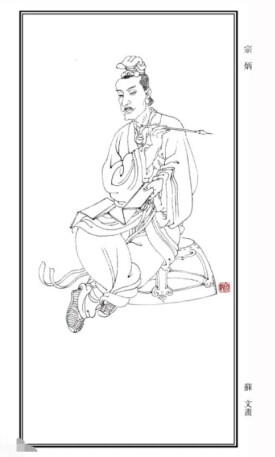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宗炳的結果 展開
- 宗炳
- 宋宗炳
宗炳
宗炳
宗炳(公元375年-公元443年)字少文,南陽郡涅陽(今河南鎮平)人,南朝宋畫家。家居江陵(今屬湖北)。士族。東晉末至宋元嘉中,當局屢次徵他作官,俱不就。擅長書法、繪畫和彈琴。信仰佛教,曾參加廬山僧慧遠主持的“白蓮社”,作有《明佛論》。漫遊山川,西涉荊巫,南登衡岳,后以老病,才回江陵。曾將遊歷所見景物,繪於居室之壁,自稱:“澄懷觀道,卧以游之”。著有《畫山水序》。
人物關係

宗炳
他遊山玩水,達到了狂熱的程度,他徜徉山水,飲溪棲谷30餘年,可謂終老山林了。由於他經歷過無數的美麗的山川景物,發掘出山水美的真諦,因而畫山水時,能夠“以形媚道”,暢其神韻。他除畫山水,又善彈琴,還信佛教,在廬山參加慧遠憎的“白蓮社”,曾作《明佛論》。他漫遊山川,西涉荊、巫,南登衡、岳,后以老病,才回到江陵。自稱“澄懷觀道,卧以游之”。
著有《畫山水序》,內中云:“豎划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論述了遠近法中形體透視的基本原理和驗證方法,比義大利畫家勃呂奈萊斯克(Pmilippe Brunlles co,1377一1446年)創立的遠近法的年代約早一千年。並主張“神暢”之說,強調山水畫創作是畫家藉助自然形象,以抒寫意境的一個過程,使中國畫“以形寫神”的理論,又前進了一步。
王微的山水畫與宗炳相近,放情丘壑。亦有畫論,意遠跡高,與宗炳均為文人畫之先驅。他提出畫畫應“以神明降之”,並以整煉的語言說:“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均是講畫山水畫不是自然主觀的死板摹畫,而是應抒寫自己的感情,才具有生命力。
根據文獻記載,六朝山水畫名作甚多,如顧愷之畫過《雪霽望五老峰圖》、《廬山圖》、《山水》六幅,夏侯瞻畫過《吳山圖》,戴逵畫過《剡山圖卷》,徐麟畫過《山水圖》、宗炳畫過《秋山圖》,謝約畫過《大山圖》,陶宏景畫過《山居圖》,張僧繇畫過《雪山紅樹圖》等。就表現技巧看,都能很好處理空間結構,把紛繁複雜的自然景物。加以概括、提煉和集中;就創作思想上看,均能以主觀思想感情對待自然景物,做到了比自然更真實,更完美,更集中。
宗炳一生好游觀山水,不論遠近,他都要前往登臨,晚年因病居於江陵,不能再涉足山水,常常感嘆不已。然而他將平生所游之地用他的畫筆繪於室內的牆上,雖然足不出戶,卻也似置身於山水之間,時而撫琴彈奏一曲,興趣盎然,不減當年。六十九歲時辭世。
廬山東林寺自宋代起設有“遠公影堂”暨“十八高賢影堂”。十八高賢,也就是慧遠和他的最得意的17位信徒。十八高賢,宗炳排在倒數第二。他入“白蓮社”僅僅50天,便無可奈何地離開了廬山。儘管如此,信息並不靈便的古人還把他放在“十八高賢影堂”里,足見他的價值份量。蓮社,首批“社員”有123人呀。那個時代也怪,有些專門逃避做官者,偏偏要往冷清寂寞、虎狼成群的廬山裡竄。他們把廬山當作了自己人生設計的最佳試驗地。其實也不怪。王羲之主持的蘭亭詩會,不就是把中國的儒家革命者或在政治失意之時,或在追求個體生命的價值的旅途所選擇的傳統方式——隱逸,以一種詩意的表達,讓它高高地放在了歷史的坐標之上了么?
宗炳出生於晉孝武帝寧康三年(375),字少文,祖父是“宜都太守”,父親是“湘鄉令”。由於他家庭經濟條件尚佳,父母課子有方,他又聰明,青年時代就能寫會畫,頗有些名氣。他的人生設計便與繪畫緊密相連了。北府將領劉毅、劉道憐等先後召征,都被他拒絕。皇帝是白痴,這是個爭奪皇權,戰爭頻繁的亂世。如此亂世,對他的心理壓力太大,他便以為“佛國最偉”。作為一個酷愛繪畫的藝術家,宗炳十分重視自己文化視野的開闊。他誠摯地吸取著外來文化——佛教的營養。
元興元年(402),他由老家南陽涅陽(今河南省鄧縣的漢水流域),逃之千里入廬山,更是因為崇尚佛教、仰慕佛學大師慧遠。那年,他27歲,慧遠69歲。他拜慧遠為師,參加“白蓮社”,奉信佛教,向慧遠學習佛、儒、老莊哲學及文學。這年七月二十八日,慧遠率門徒123人,在阿彌陀佛像前建齋立誓死後一同再投生於彌陀凈土,宗炳便列其中。
上年末,在江陵的七州都督兼兩州刺史桓玄帳下任職的陶淵明,回到廬山東南麓故里度歲。這年七月,他銷假返回江陵。或許正是這緣由,37歲的陶淵明與小他10歲、在廬山西麓東林寺里的宗炳沒有交往。這次宗炳來廬山,成了生死記憶。“昔遠和尚澄業廬山,余往憩五旬,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他還說,慧遠從“靈德自奇”的名僧道安為師,而後在廬山獨樹一幟了,“是以神明之化,邃於岩林。”他回憶了在廬山時,慧遠屢次在那秀美的山水之中為他開課,大師的講解像舒捲的行雲那般流暢,卻又很嚴謹莊重地引據佛經典籍:“驟與余言於岩樹澗壑之間,曖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尚據經之旨雲爾。”
元嘉十二年(435),他年及花甲,在江陵故宅寫作《明佛論》,作了上述回憶。當年,宗炳在廬山學佛不到兩個月,他的哥哥、南平太守宗臧找來了,堅決反對他加入蓮社,逼他回老家。宗臧就在江陵給他建造了房子,要他就在那裡閑居。他在廬山才50天,又大體活動在東林寺。如此一來,他成了廬山文化圈子的邊緣人物了。這是宗炳第一次和廬山結緣。然而,這次結緣卻修改了他的人生設計——他在廬山短短的50天里,染上了遊山玩水的癖好。自此,對自然美的探尋便成了他生命的強大推動力,成了他造就自己生命光輝的起點。慧遠作為一個佛教領袖,游廬山時常常是門徒成群,浩浩蕩蕩。而宗炳卻喜歡隻身遠遊,天馬行空,獨來獨往,這種旅遊方式是最個人化的,是老莊式的,最能釋放他個人的潛能。他多次沿長江東下去廬山,往西去荊山、長江三峽里的巫山,南往洞庭湖、衡山,北往嵩山、華山,遊歷了許多名山大川。他曾在衡山建別墅,“欲懷尚平之志。”
這中間,宗炳還與恩師慧遠保持著聯繫。義熙元年(405),他第二次來到廬山。這時候,蓮社成員、隱士雷次宗也由豫章來到了廬山東林寺,就儒學佛學向慧遠求教。慧遠為宗炳和雷次宗單獨開課,講解了儒家的《喪服經》。正在從事佛教中國化的慧遠,不但多次邀請西域的著名佛經翻譯家,還直接請古印度、尼伯爾一帶的外國法師來作正本清源的翻譯佛經的工作。他還十分重視對中國本土文化的研究。那時的廬山,不但是中國南方的第二個佛教中心,而且是慧遠與門生宗炳、周續之、雷次宗等共同研究孔儒、老莊、文學的學術重鎮。這正如北宋人李覯評論說:
噫!漢代初傳佛道,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當是時,謂之何哉?處國之神而已。及東晉、宋氏,其法乃大。蓋慧遠居廬山,名雖為釋,實挾儒術,故宗少文就之考尋文學,周續之通《五經》、《五紼》而事之,雷次宗亦從而明《三禮》、《毛詩》。儒者嘗為弟子,其人得不尊乎?
那年月,去廬山求學了,那殊榮可厲害呢!比宗炳出生晚幾十年的南朝名詩人江淹的《從冠軍建平王登香爐峰》云:“此山具鸞鶴,來往盡仙靈。”這不但是對廬山形態美生態美的抒寫,更是對文化巨子云集廬山的禮讚。後來,宗炳的兩個哥哥都不幸去世了,侄子們都由他撫養,生活越來越困難,他回到江陵故宅親自從事農業生產。
義熙七年(411),宗炳36歲了。那時,劉毅兼任荊州剌史。執掌朝權的太尉、中書監劉裕,採納了部下的建議,召宗炳任荊州府的主薄,要他輔佐劉毅。劉裕深知劉毅心底對他是不服的,是有可能背叛他的,是他奪取全國政權的最大隱患。他召宗炳去任荊州主薄,是對宗炳的高度信任,是要派他“卧底”監視劉毅。然而,宗炳不就此職。劉裕問他什麼理由?他說:“棲丘飲谷三十餘年。”也就是說,他在大山裡自由自在地活到了30多歲了,寧願就這麼從身體到精神皆與山巒融為一體地隱居下去,不願再去當什麼官兒了。劉裕倒覺得他的志向是對的,並不去勉強他,更不以為這使他的政治權威以及面子受到了嘲弄而怪罪他整他。劉裕愛才,仍派征西長史王敬弘關照他的生活。宗炳呢,有官府的接待與經濟支撐,更可以放蕩形骸于山水之中,“每游山水,往輒忘歸”。王敬弘雖然是個級別也很可以擺臉的官,卻對宗炳“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王敬弘總是很隨他的性情,由他怎麼的,不曾哪一回不讓他游個盡興而半途終止他的旅遊。
對於劉裕給予官位,宗炳很禮貌地拒絕了。他就是那麼個山野文人的德性,很有自知之明,對政治對當官不感興趣。他從來沒有幻想自己成為一個政治優化大師,他的人生設計從來沒有把自己列為儒家革命者。這在那個年月,除了宗教徒,很少有這樣的知識分子。這倒成全了他,讓他冥冥之中繼續往文化大師的高位上奔。他後來又跑到廬山去了,隱居於東林寺。次年,劉裕先發制人,親自率兵剷除劉毅,迅速猛攻江陵。劉毅在逃亡中自縊。假如宗炳接受了劉裕的任命,去荊州當了什麼主薄。劉毅當然不是傻瓜,定然看出了他來的真正使命。那麼,在劉裕發動進攻時,劉毅極可能先殺了宗炳。那樣呀,在官多如牛毛的中國政壇,僅僅多了一個其光如螢火蟲,瞬間即逝,絕對不能載入史冊的“六品官”而已,卻少了一位至少必須載入中國文化史,甚至必須載入世界美學史的大師。宗炳那篇《畫山水序》是世界上最早的山水畫論。歷史想到這裡,必定哎呀呀大叫三聲:好險啊!一個尊重自己的精神追求與個性的人,是笑在最後的。不適合做官,有著精神創造的志向與才華的人,就萬不能聽從官本位者們的大歌大頌,尤其是“龍恩浩蕩”之時,頭腦的清醒,意志的堅毅,放鬆的心態,就成了他的生命放出異彩的決定性的因素了。而人性的本能,社會對人性中的卑微、醜惡基因的煸情力量,又決定了自己是最沒有解剖自己的勇氣或者是最不了解自己的。自己是自己的哈哈鏡,自己又是自己的敵人。如此決定生命意義的生死存亡的關口,真要有“閱盡人間春色,風景這邊獨好”的高屋建瓴的自審能力,又要有“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死守精神家園的蠻勁狠心。
正是在這義熙八年(412)秋,太尉劉裕由荊州東征江州刺史劉毅經過廬山,又來找宗炳了,要宗炳出山做他的高參。宗炳是出於對他有幾度“知遇之恩”的劉裕的回報,還是為了保護東林寺的佛教事業的平安?還是因為85歲的法顯西行求法15年,遊歷了30餘國,終於越洋歸國,激發了他對佛教事業更加強烈的摯愛?他獻給劉裕一幅人物畫,這畫為“一筆畫一百事”。我想,可能是連筆畫,涉及故事一百個吧。“一百事”乃泛指,言涉及歷史故事何其多也。這畫可要功夫,考他的想象力。作為還禮,劉裕送給他“犀柄塵尾”(犀牛骨作長柄的宗教用具“拂塵”)。劉裕並沒有勉強宗炳出山。這年,宗炳才37歲,又回到江陵故宅,好年華用在或耕作,或漫遊,或作畫,或操琴,或撰文的逍遙自在之中。
唐代李延壽撰的《南史》把宗炳列入《隱逸傳》之中。《南史》的《宗炳傳》說:“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他構建的精神家園是豐富多彩的。他畫了不少山水畫、人物畫、動物畫,可惜,歷史把他定位於中國第一位山水美學家,卻恰恰連一幅山水畫都沒有留傳下來。是不是那時代,從政壇到文壇,大抵沒有朝更寬容的審美意識中覺悟過來,看輕了山水畫呢,仍然以為只有以人物為主體的畫兒才偉大呢?那時,前有顧愷之開闢了山水畫作為一個獨特的畫種的道路,然而,山水畫也沒有留傳下來。宗炳的人物畫題材廣泛,留傳下來的有:《嵇中散白畫》、《孔子弟子像》、《永嘉邑屋圖》、《周禮圖》、《惠特師像》等。他的動物畫有《獅子擊象圖》。他晚年著有佛學論文《明佛論》、《答何衡陽書》、《又答何衡陽書》。他還寫了具有中國第一篇山水美學理論性質的《畫山水序》與繪畫技法探討的《獅子擊象圖序》。
據《隋書·經籍志》,他有著作16卷。然而,卻只有7篇作品流傳至今。義熙十一年(415)春,太尉劉裕率東征軍,討伐劉毅的余部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兼江州刺史魯宗之。三月,劉裕軍至江陵,殺敗了司馬休之。硝煙初散,劉裕記起在此地山野隱居、才華出眾的宗炳,徵召他以及在廬山隱居的周續之,均任命為“太尉掾”,即太尉劉裕身邊的佐官。這確實是劉裕很器重他倆,但是,這兩個人都沒有接受此任。宗炳還是隱居在江陵,畫他的畫兒,寫他的書。次年,宗炳得知慧遠大師圓寂了,急忙從江陵趕到了廬山東林寺,悼念恩師。潯陽太守造墓,謝靈運撰寫了碑文。宗炳便為慧遠大師立碑,豎在東林寺大門口。這是宗炳第三次來到廬山。由於陶淵明對於慧遠的成見,住在東林寺附近的湖畔山村裡也沒有來參加慧遠的治喪活動,他和宗炳這麼兩個氣節相近、在思想文化史上各有傑出建樹者,失之交臂成了永遠。
公元420年,劉裕稱帝,建國號“宋”。這年宗炳45歲了。宋武帝劉裕確實老是記得他,多次召征,給他的官職為“太尉”(這是劉裕當皇帝前的職務,國家最高武官,正一品,朝廷最顯赫的宰相大臣“八公”之首)併兼“行參軍”、“驃騎將軍”。劉裕給予一個從未做過官的文人這麼高的職務,這是頭一回。這年,他大概是為了顯示禮賢下士,廣納賢才,也徵召了16年前他任鎮軍將軍時任他的參軍的陶淵明,卻僅僅是給了個掌管國史的“著作郎”(六品)的閑職。
陶淵明是有過幾次大起大伏的仕途生涯,才認識清楚了他沒有政治才能,沒有軍事才能,他無法實現儒家的“兼濟天下”的政治理想,無法解決社會問題,才永遠退隱歸田的。宗炳沒有這樣的經歷。他或是冷眼旁觀而看清了,一旦捲入了政治鬥爭,就會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毀滅於政治鬥爭之中;或是像王羲之那樣認為自己“非廟廊器”,不是做官的料?……他謝絕了劉裕的器重。然而,做官畢竟是古代獲取優越的生存的捷徑。在殘酷的生存現實面前,他又不得不考慮物質的獲取。於是,仍然是隱士的宗炳,樂於接受民間的捐贈。後來,地方公府考慮到他漸老多病,耕作不易,十分貧困,又請他出任“記室參軍”,可他還是不去。宋武帝命令南郡的長官多次將糧食錢財贈送到了他的家門口,他還是不接受,他像陶淵明。宋武帝還記得宗炳頗有音樂才華。荊楚自古就流傳著名曲《金石弄》。此曲也為桓氏世族所器重喜愛。桓玄篡位后被殺了,這首名曲幾乎消亡了。但是,宋武帝劉裕聽說《金石弄》僅僅是宗炳一人得傳,惟有他能彈奏。於是,宋武帝便派樂師楊觀來拜宗炳為師,學習此曲。宋武帝此舉,表示他仍然敞開著大門,歡迎宗炳任何時候來朝廷做官。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宗炳52歲了,朝廷還頻頻召征他。他仍然不去。他做官的機會太多了,然而,他就是不肯進入權力圈。他甚至像逃難那樣,“好山水愛遠遊”。這就是他頑固的本性。京都及各地也常有官員、學者主動與他頻頻交流學術思想。
元嘉十二年(435)建康彭城寺僧人慧琳寫了《白黑論》,認為儒學、道教、佛教各有其長,應該并行,而不必彼此對立,還就佛教若干理論提出異義,被佛教界視為異端。但是,此著得到了宋文帝劉義隆的賞識,並請他入宮討論國家大事,慧琳被稱為“黑衣宰相”。天文學家、衡陽太守何承天將慧琳的《白黑論》寄給了宗炳。此時,宗炳著的長篇佛學論文《明佛論》(又稱《神不滅論》)完成,正交人抄繕書寫,能騰出精力思考回復,他宣稱“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宿緣綿邈,億劫乃報。”並稱:“夫精神四達,併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形雖滅而神不滅。令人深思的是,宗炳對於山水美學有著全新的俯瞰目光,卻對於成佛的虛構有著特別的痴迷。這既是他接受外來文化,建立了多元的思維方式,跨越了儒學就是終極真理與絕對真理的傳統誤區,又是他以佛教哲學的思維方式來構建生命哲學的體現。他的“神不滅論”與山水美學這兩者固然是不同範疇的哲學理念,但是這兩者在思想空間有著怎樣的互動關係或者某種聯繫?我想,或許是佛教的理論幫助了他構建另外一個形而上的思維空間,擺脫了單一的以儒學理論為導向的大一統的思維方式,提升了他的美學理論。而那時,何承天給宗炳寫了一封信,直接駁斥宗炳的“神不滅論”中的種種觀點。何承天說:“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他還著有《性達論》,駁斥佛教的輪迴之說。宗炳並不因為何承天的背後有個慧琳,而慧琳又是皇帝身邊的“黑衣宰相”,就有什麼心理障礙,就輕易地改變自己的觀點。他寫了《答何衡陽書》、《又答何衡陽書》兩篇佛學文章,與慧琳、何承天開展辯論。他篤信佛教的基本理論,矢志不改。此後,他的《明佛論》及他對慧琳的論爭文章,都得到宋文帝的稱讚。宋文帝說:“宗少文之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尢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
他下旨恭請已60多歲的宗炳進京,出任“太子中舍人”,既教皇太子,又掌朝廷文翰,純化民心。可宗炳就是不去。此期間,與宗炳同樣受到朝廷的召征的是:與他曾同在廬山參加慧遠的蓮社且為“十八高賢”之一的雷次宗。雷次宗隱居豫章,被朝廷召徵到京都,為皇太子教書。他給太子講了慧遠給他講過的《喪服經》,編寫了註解闡述《喪服經》的論著,並且署了自己的名字。宗炳得知此事,出於對恩師慧遠的權威的維護,很動感情地作《寄雷次宗書》,與雷次宗爭辨,還嘲笑他:“昔與足下共於遠和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稱雷氏乎?”那年代,對於註解闡述原創作品的編著者是否也有著作權沒有共識。這倆人,一個在長江上游,一個在長江下游,相隔千里。宗炳有沒有看到雷次宗“別著義疏”的原貌,或是雷次宗在編著上有沒有寫明原著姓名?此時,論述《喪服經》的著作原創者離世20多年了,宗炳便主動當了恩師慧遠的代理原告。這該是中國最早的一樁著作權糾紛案了。
《南史》說:“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他能夠視仕途如糞土,與他有個情懷高尚、與他志趣和諧的妻子有關。他喪妻之後,衡陽王劉義季為荊州剌史,親自來到鄉間,設宴請他出山,任命他為“咨議參軍”。他謝絕了。真是一輩子都有人請他做官,他也一輩子拒絕做官。他要的只是一件:讓自由的精神在山山水水之中暢遊。
他老了,自嘆:“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睹,唯當澄懷觀道,卧以游之。”他把所游過的名山畫出來,掛在牆上,或者就直接畫在白牆上,半躺在床上,邊喝著酒邊彈著琴觀看(此即他所說的“澄懷觀道”,強化心理暗示的外在方式吧),邊細細品賞著畫里大山險峰瀑布叢林。他喜滋滋地稱之為“臥遊”,並且以一種在幻覺世界里遨遊的舒暢,說:撫琴動操,令眾山皆響。在他的感覺世界里,那畫上的千山萬壑,直到真實的萬壑千山,都回蕩著他靈魂暢遊時彈奏的動人的旋律。
元嘉二十年(4430,宗炳逝世了,時年六十九。衡陽王劉義季與司徒、江夏王劉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始終可嘉,為之惻愴,不能已已。”
他明白自己將要走向生命的終點了,病重了也不肯醫治。於是,他十分冷清,很少走動,本色的衣服顯得更加寬大,但是精神始終很愉快。連在荊州的衡陽王劉季義在他臨終前,來到他的身邊,看著他那從容豁達的樣子,都非常感動。我想,他如此從容平靜地看待生命的結束,也與他對美學的深刻理解有關。一個把中國的山水美學觀提升了的大師,此生還有什麼不滿足呢?遙想那義熙八年(412)底,宗炳離開廬山,若不是回到江陵故宅,而是因了法顯歸國去了山東嶗山,登門拜訪85歲高齡的法顯大師,詳細地採訪了他西行求法15年,遊歷30餘國,最終從海路歸國,不斷地向生命極限挑戰的事迹,詳細地研究了由法顯等旅行僧、商人開拓的通向外部世界的陸路與海路交通,以及各國地理、政治、文化風情等極珍貴極重要的材料;那麼,宗炳給予世界地理、科學與宗教、文化諸方面的新的著作,將又是怎樣的第一啊!在我看來,如若宗炳真的這樣做了,縱使他因此而興趣轉移了,不再開創“暢神”說了,那也是更為值得的。那將是催生著一個新的文化基因!可是,他沒有這樣做,他連那樣的敏感也沒有。他的“暢神”說,還是藉助於外來文化帶來的時代新風,在舊的文化基因基礎上的新發現。或者說,他的“暢神”說是一種“轉基因”。那時代,沒有一個儒者會像法顯老僧那樣,越過帕米爾高原走向外部世界,也沒有一個儒者會在中國通向古印度的海路上出現,就是法顯歸國了,千萬儒者都一片寂靜,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
宗炳的人生設計是非儒家傳統的,他始終沒有像那時代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那樣做一個正宗的儒者。然而,他把自己封閉於一個較小的認知天地里,他浪費了原本可能做一個更具有思想涵蓋力、更能影響後世的文化基因多元發展的文化大師的信仰條件。當然,宗炳沒有那樣做是很正常的。這正常在於一個巨大無比、寬闊無邊的陳舊文化基因,像高原,像大海,阻隔在正宗的儒者、儒佛兼容的學者藝術家、還有本土的宗教道教徒們的心中,儘管宗炳處在的時代尚是一個思想比較解放的時代。
萬趣融其神思……暢神而已。
也就是說,觀賞山水,引起無限的情思,目的只不過是讓精神愉悅罷了。“暢神”說,是他從對山水畫審美的升華,對真實的山水審美與關於山水的藝術創作的審美的總的精神狀態的概括。“暢神”說,是審美進入自覺狀態,對原始社會遺留的“致用”觀與先秦的“比德”觀的大跨越。宗炳的“暢神”說,鮮明地突出了人的審美的愉悅功能,強調把握審美的主體意識的絕對意義,強調個體審美的自由和及其個體審美認識的價值,強調徹底擺脫“致用”與“比德”的束縛。因而,他是中國美學發展史進入審美自覺期的傑出代表。
魏晉南北朝的文化大師,發現了自然美與人格美。自然美與人格美,成了中國山水美學的雙胞胎。如果說陶淵明是以田園詩來表達自己對於自然美與人格美在與生存相聯繫的詩歌領域裡的獨特發現的話;那麼,宗炳就是以山水畫來表達自己對於自然美與人格美在超脫於生存的視覺領域中的獨特發現。
宗炳和陶淵明一樣,把自然美與人格美的發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和諧在彙集於一體。更為重要的是,宗炳《畫山水序》中鮮明地提出了“山水以形媚道”,“神本亡端,棲形感類、理入影跡”的美學觀點。他第一個提出了自然美是一種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的客體。“萬趣融其神思”,“暢神而已”。他第一個探索自然美的本質具有哲理的意義。在他看來,由於自然美具有不一定是孔子所規範的與社會功利相聯繫的獨立的審美價值;那麼,一個人對自然美的追求,就是他個人的才能、風貌、素質、性格以及他的人生意義、人生價值的重要體現。自然美與人生緊密相聯的哲理關係,在其千古名著《畫山水序》中,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注意和重視。“萬趣融其神思”,“暢神而已”。在山水之中的精神狀態,最緊要的是一個“暢”字。沒有禮教的拘束,沒有權威的壓抑,沒有快餐式的眩耀,沒有作秀式的虛榮,一切都是自己靈魂的真實的自由。

宗炳
東晉末至南朝宋屢征其為官,都堅辭不就。長於棋琴,尤喜書畫,精於言論。曾遊歷名山大川,著《明佛論》和《畫山水序》。其論述的遠近法中形體透視的基本原理和驗證方法,早於義大利畫家呂奈萊斯克創立的遠近法1000年。文末的“暢神”說,強調山水的創作是畫家藉助自然形象描摹意境的過程,進一步推進了中國畫“以形寫神”的論點。代表作有《永嘉屋邑圖》、《潁川先賢圖》、《問禮圖》等。
“暢神”是宗炳山水畫的最高追求。他認為“萬趣”與神志融合之後,才會物我一體,使自己精神舒暢,並顯現出“道”來。他這種“暢神”與陶潛《飲酒》詩中的得意“忘言”、謝靈運《游名山志》中的“意得”有相通之處。面對“神”,宗炳並沒有簡單把它視為山水之靈,而是以法身來解釋的。神即法身,精神即我身,山水之神是連自己也包含在內的。山水畫家,面對山水自然,“妙會感神”,捕捉它的精神美,以無我之心契合對象的精神美,達到物我一體的精神境界,從而創作出一幅凝聚作家心靈世界的作品。而鑒賞者在披圖幽對時,在虛靜的狀態下,達到“萬趣融其神思”的境界,從而捕捉到山水作品中的神韻,達到“暢神”的目的。
劉宋朝的王微在《敘畫》中也曾論及山水畫“暢神”的功用:“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彷佛之哉?披圖按牒,效異山海,綠林揚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此畫之情也。”王微認為繪畫作品就是要以內在神明去捕捉和表現山水之美,這種創作和玩賞過程中的審美享受,是玩賞金石之樂無法比擬的。
二者相較,宗炳從藝術本體論的高度去把握審美過程中的精神活動,認為“暢神”的享受是美感體驗中的最高享受,比王微的認識又深入了一步,更符合中國山水畫的藝術特徵。
《畫山水序》又曰:且夫崑崙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睹。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今張素綃以遠應,玄、牝之靈,皆可得之以一圖矣。這種對自然界以宇宙的規模從宏觀上把握,涉及到事物的細微之處時,則從微觀上觀察,視點既對置於無限大,又面向無限小的方法,是師承於陸機的。陸機《文賦》中曾說:“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觀古今於須臾,扶四海於一瞬”,“含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雖然陸機論的是詩文,宗炳論的是繪畫,但思理相通,都具有開啟後來者的作用。
本來,藝術反映生活就是以小見大,以近見遠的,是一種不全之全。對於主要作用於人的視覺的繪畫,更是如此。宗炳在這段話中揭示了繪畫中的遠映透視原理。其“制小”,但“不累其似”,就是從小中見大,其強調的重點在於小而似。這是山水畫藝術表現方式最基本的要求。“去之稍闊其見彌小”,這就是遠小近大的透視原理最簡練最精闢的描述。
根據這一原理,由於“崑崙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睹”,作畫時,就需“張絹素以遠暎”,那麼“昆、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具體方法是“豎划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這樣處理好了空間關係,畫面才有層次,有縱深感,才會讓尺幅天地產生出牢籠萬物的氣勢。宗炳提出的技法和原則,為後世畫家和繪畫理論家廣泛接受。如姚最的《續古畫品錄》云:“蕭賁含毫命素,動必依真,嘗畫團扇,上為山川,咫尺之內,而見萬里之遙;方寸之中,乃辨千尋之勢。”宋代畫家郭熙《林泉高致》亦云:“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氣勢磅礴的山水,只有通過透視的原理,才可被籠於方寸之內。宗炳揭示的這一原理和方法,不僅啟示了中國的山水畫家和理論家,同時,比西方繪畫透視法的發明,也早了一千多年。
大畫家,宗少文,飲溪谷,棲山林;
不為官,願為民,三十年,避世塵。
畫奇山,興雲霞,灑春雨,染杏花;
王微畫,神氣揚,千岩秀,山河壯。
大名家,技純熟,遺精品,世所睹;
顧愷之,圖六幅,五峰圖,廬山圖。
夏侯瞻,吳山圖,謝約畫,大山圖;
陶宏景,山居圖,張僧繇,紅樹圖。
題材廣,技藝好,方寸間,千仞高;
一尺素,百里遙,描山水,皆精妙。
《山水畫序》

畫山水序
余眷戀廬、衡,契闊荊、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砧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構茲雲嶺。
夫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繚。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
且夫昆崙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睹。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今張絹素以遠暎,則昆、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豎划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
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岩。城能妙寫,亦城盡矣。
於是閑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藂,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嶢嶷,雲林森眇。
陳傳席著《中國山水畫史》(江蘇美術出版社,1988年第1版)說:“宗炳這一篇《畫山水序》方是中國最早、當然也是世界最早的山水畫論。”
《畫山水序》有著鮮明感性體驗色彩,它不是以嚴格的科學定義、嚴密的思辨方式來論證,而更像是一篇關於山水的散文。它提出了三個論點:
一、山水是有一定的精神的。
山水輝映著古代賢人的思想。宗炳說:“聖人含道映物,賢者澄懷味象。至於山水,質而趣靈。”這是對先秦“比德”觀的繼承與發展。先秦的“比德”審美觀,是拿社會或群體的道德偶像比擬大自然,以人比山水。他則進一步說,山水本身的性質而決定它有一定的精神方面的要素。他強調審美客體處於主宰地位,這又初步擺脫了“比德”的社會功利性。
二、好的山水畫,高於真山真水。
藝術美高於自然美。他說,外界的物象作用於畫家的眼睛,使心有所感悟,從而認識到大自然運行變化的法則,再把它畫下來,使畫家和觀賞者引起共鳴。這種共鳴帶來精神上的振奮,既加深了對大自然運行變化的法則的認識,又使思想超脫於塵世之外。所以,觀賞好的山水畫,強於遊覽真實的山水。他把繪畫美看作是高於自然美,強調了審美中的人的主觀創造。在那個時代,這是一種創新的見解。但是,自然美與藝術美也有許多不可比擬的因素。對於自然美,隨著社會的進步,人的素質的提高,也有不斷深化的空間,也就是自然美的內涵是能夠不斷挖掘的。對此,宗炳卻有認識上的局限性。
三、欣賞自然美和藝術美,就是為了精神愉悅。
他說,我摒除一切雜念,獨自欣賞山水畫,使我彷彿置身於沒有塵埃的寂靜的山林。峰巒聳峙,雲林繁密而深遠,聖賢的思想輝映著古老的歲月。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主簿,舉秀才,不就。高祖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咨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高祖納之,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為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賚,其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
宋書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兔置》潛處,《考盤》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雁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征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征通直郎;東宮建,征為太子中舍人,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不分,未易可達,三複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宴,命為咨議參軍,不起。
宋書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睹,唯當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惟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
宋書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臨川王義慶闢為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病卒。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王義季與司徒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為之惻愴,不能已已。”子朔,南譙王義宣車騎參軍。次綺,江夏王義恭司空主簿。次昭,郢州治中。次說,正員郎。
——《宋書 卷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隱逸》
兒子:宗說、宗昭、宗朔、宗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