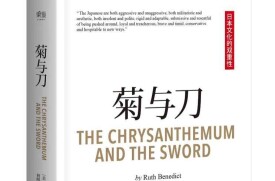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菊與刀的結果 展開
- 商務印書館圖書
- 增訂版
菊與刀
商務印書館圖書
《菊與刀》是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創作的文化人類學著作,首次出版於1946年。
本尼迪克特在二戰結束后寫成《菊與刀》。《菊與刀》共13章:從對戰爭的看法講起,講到明治維新,再分述日本人風俗習慣、道德觀念、一直到怎樣“自我訓練”(修養)和孩子怎樣受教育。全書夾敘夾議,拋開了對櫻花、茶道、武士道等煽情描述,更多是對家庭關係、精神信仰進行白描式的對比,諸如美國人和日本人看待健康、物質、戰爭宣傳、家族關係等的不同觀念。
《菊與刀》直接影響了美國對日政策,美國戰後對日政策的成功也證明了《菊與刀》對日本人所做研究的成功。從此,西方對日本文化的研究熱潮也揭開了序幕。
全文分為十三個部分展開論述,第一章提出問題之後,第二章研究了日本人性格的現象:戰爭中的日本人。本尼迪克特抓住了日本民族的兩大典型性格表現,一是天皇的神最不可侵犯,二是被俘虜的日本人與美軍的高度合作。她毫不避諱地談到了這樣的性格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處置有參考價值。接下來的章節里,本尼迪克特還討論日本的等級制度和明治維新對傳統等級的衝出和改變,並尖銳地指出日本對等級文化的迷信導致其在侵略外國時也試圖輸入這種等級觀念,而這種日本獨特的倫理體系當然難以為他國所接受和消化。然後她分析了日本文化的“負恩”邏輯,並進一步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和美國的罪感文化差異極大。為了洗刷恥辱,日本人最極端的行為就是自殺。“按照他們的信條是,用適當的方法自殺,可以洗刷污名並贏得身後好評。美國人譴責自殺,認為它只不過是屈服於絕望而自我毀滅。”在此基礎上,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極端的道德準則使他們的生活經常處於高度緊張狀態,作為補償,日本文化對感官享樂寬容得令人驚訝。本尼迪克特還探討了日本人的自我修養和育兒方式,不管具體的方法與形式,其本質上與嚴格的道德準則是一脈相承的。最後,她分析和評價了投降后的日本人與對日政策。
| 章節 | 章節名 |
|---|---|
| 前言 | - |
| 第一章 | 任務——研究日本 |
| 第二章 | 戰爭中的日本人 |
| 第三章 |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
| 第四章 | 明治維新 |
| 第五章 | 歷史和社會的負恩者 |
| 第六章 | 報恩於萬一 |
| 第七章 | “情義最難接受” |
| 第八章 | 洗刷污名 |
| 第九章 | 人情的世界 |
| 第十章 | 道德的困境 |
| 第十一章 | 自我修養 |
| 第十二章 | 兒童學習 |
| 第十三章 | 投降后的日本人 |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尾聲,軸心國的失敗已成定局。此時,美軍進佔日本本土只是時間問題。也許同是歐洲文化背景,美國對德國戰後問題的決策較為清晰。但是如何處置具有東方文化背景的日本戰後問題,美國政府需要迫切作出決策。為此,美國政府動員了各方面的專家來研究日本,提供資料和意見,以期制定出最後的決策。魯思·本尼迪克特是接受這一課題的眾多專家學者之一。她是一位美國人類學家,在大學期間學習的是英國文學,后從事人類學研究,師從於二戰前最偉大的人類學家之一——弗蘭茨·博厄斯,並取得博士學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主要從事對羅馬尼亞、荷蘭、德國、泰國等國民族性的研究。
當時日美還在交戰狀態,本尼迪克特不能到日本本土進行調查。於是,長於田野調查的本尼迪克特,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調查了居住在美國的日本人和戰時拘禁在美國的日本戰犯,同時收集了大量有關日本的文藝學術作品,從日常生活細節中去解讀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和習慣,特用“菊”與“刀”的形象,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民族性。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6年她把這份報告寫成書出版,即《菊與刀》。
| 書名 | 譯者 | 出版社 | 出版時間 |
|---|---|---|---|
| 菊與刀 | 浙江文藝出版社 | 2016年7月 | |
| 菊與刀 | 田偉華 | 中國畫報出版社 | 2011年8月 |
| 菊與刀 | 一兵 | 武漢出版社 | 2009年6月 |
| 菊與刀 | 劉鋒 | 當代世界出版社 | 2008年1月 |
| 菊與刀 | 北塔 | 上海三聯出版社 | 2007年11月 |
(以上資料來源)
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年生於紐約。原姓富爾頓(Fulton),其祖先曾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她本人大學時期主修英國文學。1919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人類學,是Franz Boas的學生,1923年獲博士學位。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寫成《文化的類型》(Patterns of Culture,1934年出版)一書。1940年著《種族:科學與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種族歧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事對羅馬尼亞、荷蘭、德國、泰國等國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對日本的研究,即《菊與刀》一書成就最大。戰後,她繼續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當代文化研究”,於1948年9月,病逝。
“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徵,“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體現。本尼迪克特用這兩個詞表示了日本人的兩種矛盾的性格: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對於日本人的這種國民性格,本尼迪克特從等級制度、報恩意識、義理、日本兒童的養育方面展開分析。
作者認為,“在日本民族有關人際關係以及個人國家關係的整個觀點中,他們對等級制度的信賴乃是核心地位。”“各守本位”是描述他們等級思想的關鍵詞。在人際關係中,每個人都有其在社會階層中的地位,每人都應安守其地位,享受其地位應得的權利,履行該地位所要求的義務。一個人必須向地位高於他的人表示敬意,而地位高的人不得侵犯地位低的人的權利,否則地位低的人的報復是正當的。
日本人在觀念上認為自己是歷史的“負債者”,這種債既有父母的“恩”,還是兒子欠父母的一切;又有“皇恩”,是一個人對天皇的負債;還有別人施加給他的“恩”。這些恩都是必須償還的欠債。一個人要成為有德行的人,就必須報恩。由於報恩意識的存在,日本的人與人之間產生了服從的關係,比如子女要服從父母,下級要服從上級,人人都要服從天皇。
本尼迪克特還從日本兒童的養育習俗上來說明日本人的性格形成的原因。她認為,日本人的人生曲線和美國的不同。日本的幼兒和老人享受了最大的自由和從容。幼兒期過後,限制逐漸加強。到了結婚前後,個人的自由達到最低的限度。到60歲以後,日本人又可以像幼兒一樣不受恥辱的煩擾。日本兒童特別是男性兒童的教育存在著兩重性,即幼時雖然要對父親表示恭順,但可以為所欲為,可以對母親和祖母大發脾氣,隨意發泄自己的挑釁心,而六七歲以後,慎重與“恥辱感”逐漸加至他們身上,並隨著年齡的增大,訓練越來越嚴厲。這種教養方式在日本人的人生觀中產生了矛盾的性格,即一方面日本人可以愛好賞櫻花、菊花之類的優雅行為,另一方面又可以手執刀槍進行殘酷的殺戮或者自殺。
《菊與刀》1949年被翻譯成日文,受到日本國民極大關注。1951年,這本書被列入日本“現代教養文庫”。
1990年中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這本著作,在學界引起關注。2005年後,中國多家出版社先後出版了此書,商務印書館也重印了七萬冊,並意外地登上了暢銷書排行榜。《菊與刀》的熱銷,引起日本媒體注意,《讀賣新聞》等對此做過專題報道,並分析認為這本書暢銷,是因為時值中國抗戰勝利60周年,中國的年輕人對那段歷史產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