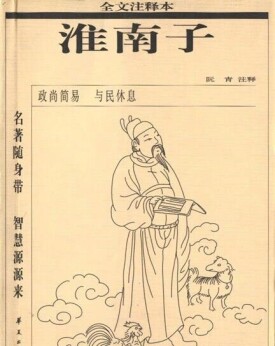淮南子·說林訓
西漢劉安所做兵書
《淮南子·說林訓》出自《淮南子》。西漢劉安所做,劉安(公元前179--前122),漢高祖劉邦之孫,淮南厲王劉長之子。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速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跡,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為帝者也。曹氏之裂布,蛷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足以蹍者淺矣,然待所不蹍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游者以足蹶,以手柿,不得其數,愈蹶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椎固有柄,不能自椓,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眥。狗彘不擇甂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鳳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能有修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干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斵,大豆不具,大勇不鬥,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鐘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以瓦鉒者全,以金鉒者跋,以玉鉒者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逐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欲在外,則明所蔽矣。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 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於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
水火相憎,鏏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讒賊問之,而父子相危。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以適履,殺頭而便冠。昌羊去蚤虱而來嶺窮,除小害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壁瑗成器,礛諸之功;鏌邪斷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虻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飢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唇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鉤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冠則戴致之,緯則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卻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況疏遠乎!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撩,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
躄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駙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芻狗能工向個能行,蛇床似麋蕪而不能芳。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人莫不奮於其所不足。以免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蝸所以七十化也。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牛蹄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的,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舌之與齒,孰先礱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鱔之與蛇,蠶之與蠍,狀相類而愛憎異。晉以垂棘之壁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聾者不歌,無以自樂;高盲者不觀,無以接物。觀射者遺其,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
使但吹竿,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無其君形者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情 泄者,中易測。華不時者,不可食也。
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蔐苗類絮而不可為絮,磨不類布,而可以為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羊肉不慕蟻,蟻慕於羊肉,羊肉膻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波可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射者儀小而遺大。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而發痤疽,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托埵防,便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鱉,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弒其君而被大謗,所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項托使嬰兒矜,以類相慕。
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蝯狖之捷來乍。行一棋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壁有考,不得為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盜賊之輩丑吠狗。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鱉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幹明也。替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飢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汗不可再。環可以喻員,不必以輪;條可以為繶,不必以紃。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斵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蠹眾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隧;枝格之屬,有時而弛。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當暑而不喝者,不亡其適;未嘗適,亡其適。
湯沐具而蟣虱相吊,大廈成而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餡,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脫;蚌游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署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魚食巴寂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揚垛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翼,豈若適衣而已哉!槁竹有火,弗鑽不;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蛖象之病,人之寶也;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為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漱,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鄰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
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一膊炭熯,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逾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釣者靜之 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小國不鬥於大國之間,兩鹿不鬥於伏兕之。佐祭者得嘗,救斗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簽。頭虱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修而秋風敗之。
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墮武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
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堁之也。屠者羹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必用,用者弗肯為。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水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袖有鄉,雚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蘇秦步,曰何故,趍,曰何趍馳;有為則議,多事固苛。皮將弗睹,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欲觀九州之上,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旳旳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未嘗稼稿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胔,太山不上小人,光不升俎,聊駁不入牲。
中夏用箑,快之,至冬而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於環帶一也。獻公之賢,欺於驪姬;叔孫之智,欺於豎牛。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丑。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當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渡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
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跟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善用人者,若蚈之足,眾而不相害;若唇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
清醠之美,始於耒耜;黼黼之美,在於杼軸。布之新不如紵紵之獘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在頰則好,在顙則丑。綉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馬齒非牛蹄,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污准而粉其顙;腐鼠在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再生者不獲,華大旱者不胥時落。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有何為驚!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為蟌孓孓為,兔嚙為螚。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磨燭確,膏燭澤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病熱而強之餐,救喝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雖欲謹亡馬,不發戶磷;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責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
山雲蒸,柱礎潤;伏苓掘,兔絲死。一家失熛,百家皆燒;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顫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狂馬不觸木,猘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心所說,毀舟為杕;心所欲,毀鐘為鐸。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利溺人矣。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之瑟不可聽。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床;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荊。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眾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蛖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慾馳;飲酒而樂,使人慾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
聖人處於陰,眾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舍茂林而集乾枯,不弋鵲而弋烏,難與有圖。寅丘無壑,泉原不溥;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暗晦,必留其謀。以天下之大,托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 鉤之重於木之一技。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兩人傷。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歌,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蝮蛇螫人,傅以和堇財愈,物故有重而害反為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逾易忍也。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 能思於心。兕虎在於后,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兔,決於金之貨者不爭銑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兄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編。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豪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巧冶不能鑄木,工巧不能斵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鱉千里;累積不輟,可成丘阜。城成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
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數之則弗中,正在疏數之間。從朝視夕者移,從在准直者虧;聖入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趍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幹防者,雖近旨射;其當道,雖遠旨釋。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讀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涔 則具擺對,早則修土龍。臨淄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為之悖戾。室有美貌,繒為之纂繹。徽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抮和切適,舉坐而善。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伔。木大者根攫,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署老,莫之疾也,賊心。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而又況一不信者乎!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
用某個朝代的制度來治理多變的社會,這就好像外鄉人乘船,船至江中,這位外鄉人的劍掉入水中,他就趕快在劍掉落下的船舷部位刻上記號,等傍晚船靠岸后他就在所刻的記號處下水去找劍,這實際上反映了此人不懂事物已變化很多了。只知道在掉劍的船舷旁打轉,而不知道因順自然遨遊,沒有比這更糊塗的了,雖然有時偶然間有所合,但這種“合”不值得珍貴。就好像大旱之年求雨用的土龍,求神保佑疾病痊癒用的芻狗,只是暫時地在祭祀中起主宰作用。也就好像小孩用過的尿布,只有患蝫蛷瘡的人視為寶貝,但是它終究不是夏后氏的玉璜。沒有古今,也沒有始終,天地未分時的混沌狀態能夠產生天地,這就是最深奧又微妙且廣大的道。人走路時跨出的每一步都是有限的,但就是不停地跨步踩踏未曾踩踏過的地方才能走向遠方;同樣,人的智慧每次能掌握的事理也是有限的,但就是不斷地認識未曾認識過的事理才能越變越聰明。初學游泳的人用腳亂撲騰、用手亂抓挖,沒有掌握游泳的技藝,越撲騰、亂抓挖,越往下沉;而當人一旦掌握了游泳的技藝,就用不了手腳如此慌亂了。鳥兒飛翔再遠再高,也總得返回鳥巢;兔子跑得再快再遠,也總得返回洞穴;狐狸死時,頭總朝著巢穴;寒將水鳥總貼著水面飛翔,它們各自依戀著自己生存的環境。不要給盲人送鏡子,不要送鞋給跛子,不要送帽子給越國人,這是因為這些物件對他們來說是無用的。木椎本來安著木柄,但它不能自我敲擊;眼睛能看到百步開外,但看不到自己的眼眶。豬狗不管這裝食物的器具是什麼,它們只顧進食,苟且貪生吃肥了自己,但這樣反而是接近了死亡;鳳凰高飛在千仞的高空,不隨便棲息進食,所以也沒什麼人能誘它上鉤自投羅網。月亮能夠照亮天下,卻被蟾蜍所侵蝕;騰蛇能夠騰雲駕霧,卻被蝍蛆所制服;烏鴉經得起太陽的灼熱,卻對付不了禮鳥:這說明它們各自的能耐有長有短。如果認為沒有比夭折歸天更長壽的了,那麼彭祖活八百歲也算是短命的。短繩的汲水器不能汲取深井的水,容量小的器皿裝不下大的東西,這是因為它們勝任不了。憤怒出自不怒之時,有為出於沒有作為之前。能看清無形,那麼就能看清所有物體;能聽見無聲之聲,那麼天下就沒有什麼不能聽到的了。最鮮美的味道嘗著沒有快感,最高深的語辭不講究文飾,最大的快樂是無笑意,最高的聲音不呼叫;最高明的工匠無須砍削,最高明的廚師無須陳列食具,最勇敢的人不以打鬥取勝。這些均是掌握了“道”,“德”也就隨著而來了,就像黃鐘配宮音、大蔟配商音,不可更改這聲音的調配。用瓦器作賭注的人心定不慌,以黃金作賭注的人則心神不安,將美玉作賭注的人就內心焦慮。這是因為過於看重這些黃金和美玉這樣的外物,導致內心世界的心智變得笨拙起來。這就好像追逐野獸獵物時,眼睛和心志一直盯著這獵物,導致連泰山都看不見了,眼睛被外物所蒙蔽了。聽有聲之聲會耳聾,聽無聲之聲會耳靈;而“道”要求是不聾不聰,這樣才能和“神明”相通。占卜者拿著龜殼,占筮者拿著蓍草,而要詢問占卜的方術,這哪裡是他們該問的呢!跳舞者合著節拍起舞,在座觀賞的人不約而同地鼓起了掌,這是因為兩者欣賞的觀念相同、節拍一致的緣故。太陽從暘谷升起,到虞淵落下,沒有人知道它是怎麼運行的,片刻之間就偏西了,人只須反轉頭頸就能看到。人都不想學駕龍技術,而想學御馬技術;都不想學習治理鬼的本領,而想學治理社會的本事,因為御馬駕車、治人管理社會是急需的事。將門板卸下劈了當柴燒,將水井堵塞作碓臼,人們有時做的蠢事就像這樣。
水火不相容,但是裝有水和食物的小鼎鍋放在火上卻能煮成五味俱全的美食;骨肉親情,但被讒賊小人從中挑撥,父子都有可能互相危害。為貪養生之物而傷害生命,這就好像削足適履,又好像削尖腦袋去帶小帽子。菖蒲能除掉跳蚤和虱子,但卻又招來蚰蜒害人,這真是除去小的害蟲卻招來大的害人蟲,貪圖小的快活而傷害大的利益。牆壁毀壞倒不如沒有牆壁來得好,但總比房屋倒塌好得多。璧瑗能成為玉器,是諸的功勞;莫邪寶劍削鐵如泥,是砥礪的力量。狡兔捕捉到手,獵犬就被烹煮;飛鳥射殺了,這強弓就被收藏起來了。虻蠅叮咬在馬身上,隨馬賓士而不用飛動,沒有乾糧供應也不挨餓。失火正好碰上下雨,失火是件不幸的事,但遇上了下雨卻又是件幸事,所以說禍中有福。賣棺材的老闆希望大家都得不治之症,囤積糧食的奸商希望鬧飢荒。水靜止就平正,平靜就清澈,清澈就能映出物形,使它不能藏匿,所以靜水可以作為鏡子來幫助整飭衣冠。川澗枯竭則溪谷空虛無水,山丘夷平則深淵填塞,嘴唇翻裂則牙齒受寒;河床之所以深,是水沖刷山崖泥土形成的。將一塊白絹分成兩半,一半做成帽子,一半縫成襪子,帽子戴在頭上,襪子卻被踩在腳下。有自知之明的人是不能拿物質來誘惑他的,明白生死由命這個啟發的人是不能用危難來脅迫他的,所以會游泳的人是不可以用涉水渡河來嚇唬他的。親密關係莫過於骨肉相連,全身的關節筋絡將它們緊緊相連;但如果心臟失去對人體的控制,人體的各個器官就會互相殘害,更何況關係本身就疏遠的事物呢?聖人對於“道”,就好像葵花向太陽,雖然不能和太陽同始共終,但朝向仰慕太陽的心情是真誠的。辟挖出來的水池,久雨積水就會漫溢,天旱就會幹涸,而有源頭的長江之水,卻像深泉那樣不會枯竭。傘蓋離開蓋架的支撐便不能張開遮陽;車輪沒有輻條便不能飛快賓士。但是光靠蓋架和輻條又是不行的。說金能克木,並不是說一刀就能砍倒樹木;說土能克水,並不是說一塊土就能堵塞長江。
跛子看到老虎不逃跑,不是他勇敢,而是他的腿腳不方便。傾斜的東西容易傾覆,斜靠的東西容易推倒,飢餓者容易得到幫助,空氣潮濕容易成雨。捕捉老鼠靠機關發動,釣魚則要看浮子的飄動,車輪轉動則車子發出聲響。芻狗能像狗一樣站立但不能行走,蛇床草外表像蘼蕪但沒有芳香。如果誰說許由缺德,說烏獲不是大力士,那麼他們必定臉色難看不高興,人沒有不竭力來彌補自己不足的。按兔子奔跑的速度,如果讓它長得像馬那樣大,這奔跑的速度一定能追上太陽、趕上風;但兔子真的變成馬,就說不定奔跑的速度還不及兔子。冬天有時會打雷閃電,夏天有時會降霜下雪,但這種偶然現象無法改變冬寒夏暑的基本規律,這說明小的變化不足以妨害大的常規法則。黃帝化生陰陽兩氣,上駢造出耳目,桑林造出手臂,女媧所以能化生七十變而造出人類,靠的是眾神的幫助。從早說到晚,一定能說出通達聖明的話;上百次的射中目標,這其中必定有像羿和逢蒙那樣的射箭技巧。儘管如此,世人並不認為他們就是聖者和神射手,因為他們並沒有掌握真正的法度、技巧。牛的蹄子和豬的頭顱也是骨頭,但世人就是不用它們來灼燒占卜,而一定要用龜甲來占卜凶吉,這是因為龜的年歲經歷久遠的緣故。住在敖倉附近的人並不因為靠近糧倉而飯量特大,生活在江河邊的人也不因為靠近河邊而多飲水,他們只求吃飽喝足就行了。蘭草、白芷因為芳香,所以不到下霜的季節就被人摘掉了;世人有五月望作梟羹以避凶,所以梟鳥也就活不過五月五日。舌頭和牙齒,哪個先磨損?刀痴和刀鋒,哪個先破損?繳繩和箭枝,哪個先折斷?鱔和蛇,蠶和蛾,形狀相似,但人們對它們的一愛一憎,態度各異。晉國用垂棘之璧作誘餌而奪得了虞、虢兩國,驪戎用美女嫁給晉獻公而使晉國滅亡。聾子不能唱歌,因此沒法享受這其中的樂趣;盲人因為眼瞎,所以無法看到外物。觀看別人射箭的人忘記了自己所做的事,看書入迷者遺忘了自己的愛好。思想集中在某個地方,就會忘記自己所應持守的東西。假如古代所做的一切不可更改,那麼原始的椎輪車就可能一直使用到現在,也不可能有大輅車的出現。
讓倡優吹竽,卻叫樂工給他按發音孔,雖然能合節奏音調,但奏出的音調不好聽,這是因為兩人共奏一隻樂器使之失去了主宰。和死者患同一種毛病的醫生是難以成為良醫的,與滅亡的國家採用相同的治國之道是難以再產生新的治國方針的。給客人準備飯菜而自己卻吃野菜,這種人是將名聲看得比實際更重要。哺乳時期的母狗敢咬老虎,孵化小雞的母雞敢與狸貓斗,這是因為它們將一切都傾注在幼畜身上,而不考慮自己的力量能否斗得過老虎和狸貓。使影子彎曲的是彎曲的物體,讓迴音濁重的是濁重的聲音。真情外露的人,他的內心世界容易測度;開花結果不合時宜的果實不可食用。
到越國去的人,有的乘船、有的坐車,雖然交通工具和路線都不同,但是所要達到的目的地是一樣的。佳人體態各異,美女臉蛋各不相同,但都招人喜歡。梨、橘、棗、栗味道各異,但是人們都喜歡吃。有人是靠偷盜發財的,但發財的人並不一定是盜賊;有因為廉潔而清貧的,但清貧的人並不一定是廉潔的。蘆荻花像棉花絮,但是不可以將它當棉花絮來使用;粗麻不是布,但是可以用它來織成布。要穿出林子的人不可能走直道,在險要地方行走的人不可能走直線。羿之所以射中遠距離的細微目標,不只是憑著弓箭;造父之所以駕車跑得又快又遠,不只是靠韁繩和馬嚼子。大海能容納百川,所以是浩瀚無邊;車輪能周而復始地不停轉動,所以能走得遠。羊肉並沒有引誘螞蟻,是螞蟻找上了羊肉,因為羊肉有膻味;酸醋並沒有招惹蚊蚋,是蚊蚋叮上了酸醋,因為醋有酸味。嘗一小塊肉,便能知道一鼎鍋的肉味;懸掛羽毛和木炭能知道空氣的濕度,這是從小可以見大,由近可以知遠。十頃大的池塘可以澆灌四十頃的農田,但一頃的池塘就不夠灌溉四頃農田,這是因為有大小的差別。明亮的月光,可以用它看到遠處的物體,但不可以靠月光來寫蠅頭小字;大霧迷漫的早晨,可以看清蠅頭小字,但卻看不清幾米以外的物體。繪畫者如果只注意到畫好毛髮這樣的細節,就不可能畫好人物的全貌;射箭者瞄準有微小的偏差,就會帶來很大的差錯。為了捉老鼠挖開鼠穴而破壞了宅院,為了挑破叮皰而引發毒瘡,這就好像珍珠上有疵點、玉石上有斑點,這疵瑕斑點不去雕掉,珠玉也就完整無損,如一去掉這些疵瑕斑點,這珠玉也就會弄殘缺了。在樹木叢生的森林裡築巢的鳥兒,將巢築在樹林茂密的深處,因為那裡安全。挖洞的小獸將洞穴建在堤防的高處,因為那裡方便。王子慶忌雙腳能追上麋鹿,雙手能搏殺犀牛和老虎,但如果將他關在黑暗的空房間里,恐怕就連龜鱉都捉不住,這是因為環境地勢不方便他捉拿龜鱉。商湯放逐夏桀而獲得美名,而崔杼卻因殺死齊莊公而受到他人的譴責,他們所做的事均為臣犯君主,但冒犯君主的原因卻不一樣。呂望到晚年才大有作為,這樣使得老年人也為之振奮;項托小時就難倒孔子而為孔子之師,這樣使得少年們也為之驕傲:這都是因為同類互相仰慕的緣故。
使樹葉飄落的是風在吹動,使水渾濁的是魚在攪撓。虎豹因長著美麗的皮毛而招致捕殺,猿猴因動作敏捷而遭到刺傷。走一步棋不足以顯示智慧,彈撥一下琴弦不足以表達悲哀。三寸長的竹管如果沒有底,那麼天下再多的糧食也無法填滿它;十石大的容器如果有底,那麼一百斗糧食就可以盛滿它。用竹篙來測量江水的深度,如果竹篙沒了頂就以為篙長等於水深,那就糊塗了。漁夫在河邊奔走,樵夫在山裡兜轉,因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在那裡。早上趕集的人走得飛快,傍晚到集市的人則踱著方步,這是因為此時他要購買的貨物集市上已沒有了。毛色駁雜的豹皮大衣不若毛色純一的狐裘大衣;白璧有了污點裂縫,就不能變寶貝了:這是說絕對純粹是困難的。死於戰爭的人的鬼魂是討厭神巫的,偷盜之徒是討厭吠叫的狗的。沒有主的社神,隨便弄些黍肉就可祭祀它;亡了國的穀神,容易向它祈求降福。鱉沒有耳朵,但眼睛卻蒙蔽不了,因為它沒有了聽覺,這視覺就變得特別靈敏;盲人沒有了眼睛,但耳朵卻無法閉塞,因為他失去了視覺,這聽覺就變得特別靈敏。遺腹子不思念他的父親,因為他心裡原本就沒有父親的印象;他連做夢都不會夢見到父親的形容,因為他從來就沒見過父親是什麼樣的。蝮蛇不可以給它們添上腳,虎豹不可以讓它們爬上樹。馬不吃油脂類的食物而只吃草料;桑扈鳥不啄食粟粒而愛吃油脂類的東西,它們不吃什麼東西,並不表示它們廉潔。秦國修通崤山要塞,魏國便築起城牆加以防範。餓馬呆在馬廄里安靜無聲,而一旦有草料出現在它們身旁,互相間的爭奪就發生了。拉弓射箭,沒有什麼弦箭射不出去;但弦箭的長度與射程相比,不到百分之一。道和德是可以永恆不變的,但是權變就不能永遠不變。所以從關卡處偷渡出去的,就再也難以重新來一次;越獄逃跑不可能會有第二次成功。圓環可以用來比喻圓形,就用不著用車輪來比喻圓形了;絛帶可以用來作飾鞋的絲帶,就用不著用眐帶了。太陽月亮不可能同時出現,一雌狐不能配兩隻雄狐,神龍沒有配偶,猛獸不會群聚,猛禽不會成雙。照著墨繩彈出的墨線砍削就不會出差錯,用秤來稱量計算就沒有誤差,立圭表來觀測就不會迷惑。少報年齡就和弟弟相混淆,多報年歲就和哥哥難分清,不如老老實實遵循事理,順隨真情行事。人看不見龍之飛舉而能將龍高高托起的,是風雨的幫助。蠹蟲多了木頭就會折斷,縫隙大了牆就會倒塌。懸掛下垂的物體,時間長了就會墜落,長得長長的枝條一類的東西,時間長了也會脫落。在冰天雪地里凍不死的人,有著他的適應能力;在酷暑高溫下不中暑的人,有著他的適應能力。從來沒有不適應的,也就不知道什麼叫適應性。
洗頭的熱水準備停當,頭上的蟣子虱子就會互相弔唁;大廈落成,燕雀就會互相慶賀可以築巢了,這憂樂各不相同。柳下惠見到飴糖說:“可以用它來贍養老人。”而盜跖見了則會說:“用它可以來粘鎖簧。”看到的物件相同,但所得出的觀念卻不一樣。蠶只吃桑葉而不喝水,經二十一天後化為蛾子;蟬喝露水而不吃食物,經三十天後蛻化;蜉蝣既不吃也不喝,只三天就會去。人吃礜石會被毒死,而蠶吃了卻不會飢餓;魚食巴豆會死,而老鼠吃了巴豆卻會長胖。事物的啟發和緣由不一定弄得清,所以也無法以類相推。瓦是經過火燒后形成的,但直接用火干燒這瓦就會破裂;竹子是靠水生長的,但將竹浸泡在水中這竹子就會死掉。以揚起塵埃來消除塵埃,穿著皮衣卻又用扇子來散熱,哪裡比得上根據不同季節穿合適的衣裳?枯竹能起火,但不鑽就不會出火燃燒;地下有水,但不挖掘就不會出泉水。給蚌蛤、大象帶來災難的是珍珠象牙,而這正是人類的寶物;而人的病痛、災難又有誰當寶貝呢?為了不讓賣酒者獲得更多的利就不去買酒,那就只好乾渴著;為了不讓駕車者獲得更多的利就不去租車,那就不能到達遠處目的地;手握火把去擲擊人家,自己反倒燒傷。鄰居家的母親死了倒前去哭吊,而自己的妻子死了卻不掉淚,那是在一種怕被人說成溺於情色的脅迫下的表現。
西方的裸國,鳥獸也不迴避人群,那是因為人和它們混和為一,習性相似。一根燃燒著的炭,用手去拿,就會燙傷手指;一萬石的炭放在一起燃燒,離它十步之外就燒不傷人,這是因為同是熱氣而聚散方式不同。大的勇氣和小的勇氣的情況與這種情況相似。現在有六尺寬的席子,平鋪在地上,一般性的人越過它並不困難;但如果將席子豎立起來,就是彈跳力出眾的人要跨越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這是因為席子擺放的態勢不一樣。百顆梅子足以調配一百人食用的酸汁,而一顆梅子就不足以調配一個人所需的食用酸汁。如果因有人吃飯給噎著而禁止天下所有人吃飯,如果因有人坐車出車禍而禁止天下所有人乘車子,那就顯得十分荒唐了。釣魚的靜靜地等待魚兒咬鉤,水中積柴捕魚的扣舟驚魚,用魚罩的下罩捉魚,用罾具的舉罾得魚:方法各異,但能捕獲魚則是一致的。看到象牙便能知道象比牛要大,看到老虎的尾巴就能知道老虎比狸貓大,掌握了部分,整體也就能推斷出來。兩小國不在大國面前爭鬥,兩隻鹿不在卧伏的犀牛旁爭鬥。幫助祭祀的人得以嘗新,制止打鬥的人卻受了傷。在不吉祥的樹蔭下躲雨,會被雷電所擊。有叫“冢”的,有稱“隴”的,有叫“笠”的,有稱“簦”的,名稱不同但實物一樣。頭上“虱子”的“虱”和空心木做的“琴瑟”的“瑟”,二字讀音相同,但所指的物體卻不同。總想太陽月亮永遠光明,但浮雲就是遮蓋它們的光;總希望蘭芝四季生長,但秋風就是使它們枯萎。
老虎產下的虎子,如果不會搏擊獵物,老虎就會將它們吃掉,因為這樣傳代下去會將虎的威武喪失殆盡。裝飾著龜鈕的印章,賢者將它當作飾物來佩戴;土壤分散在田裡,能幹的人靠它致富。丟給溺水者黃金美玉,不如拋給他一段救命的繩索。看書時,看到前有一個“酒”字,就知下面必有一個“肉”字;看到前有一個“年”字,就知下面必有一個“月”字:這是根據它們的類別而推知的。
蒙上灰塵就會眯起眼睛,這是理所當然的;但說他不出門就被塵土蒙眯了眼睛,這就不合情理了。屠戶殺豬宰羊卻吃的豆葉羹,製造車輛的人卻用腳步行,燒制陶器的人卻用的缺口盆子,蓋房造屋的人卻住在狹窄簡陋的小屋裡:這些製造某物的人不一定自己使用,而使用這些物件的人又不從事這類工作。車轂設置三十根輻條,各盡自己的力量,互不妨害;如果讓一根輻條聯接車轂,其餘二十九根輻條都不用,這車哪能行走達到千里之外?黑夜走路的人,眼睛就像被東西蒙住,只好伸手摸索著走;渡江涉水的人只得將原來騎的馬裝載到船上去:事物總有它適用的範圍,也有它不適用的範圍。橘子和柚子都有自己的產地,荻草和蘆葦各有自己的叢生處,獸類腳爪相同的在一起從游,鳥類翅翼相同的在一起翱翔。田地里的積水最終流入大海;貼在耳邊講的悄悄話最終會傳到千里之外。像蘇秦這樣有爭議的人物,他走得慢些,人家就會問:“為什麼走得這麼慢?”他走得快了,人家也會問:“為什麼跑得這麼快?”這說明有所為人家就要說三道四,好多事就會被別人吹毛求疵。皮都要磨得差不多了,到哪裡還能看到毛!畏首畏尾,那麼身上還有多少是不怕的呢?要想視察九州大地,但雙腳又不作千里跋涉;內心沒有治政教化的想法,卻想身居萬民之上,那就難了。明眼看得見的東西容易抓獲,暴露明顯的目標容易射中,所以最潔白的東西容易污染,德行最高的人總像空虛不足。未經過辛勤耕種就糧食滿倉,未經過採桑養蠶就蠶絲滿袋;東西來得不是正道,用起來也必定揮霍無度。大海不接納漂浮的腐肉,泰山不容許小人攀登,膀胱不能上俎案,雜色斑駁的馬不能作犧牲。
盛夏季節使用扇子很涼快,但到了寒冬還不曉得放下扇子;提著衣裳趟水過河,但上了岸還不知道放下:這樣的人就顯得相當呆板而不能適應變化著的形勢。有的山沒有樹林,有的山谷沒有風,有的礦石不含金屬。滿堂坐客,看看他們的衣帶鉤各不相同,但都用來環扣衣帶卻是一致的。晉獻公本來是很賢明的,可是後來被驪姬所蒙欺;叔孫如此聰明,卻被豎牛耍弄,竟連自己的性命也不保,所以鄭國的鄭詹來到了魯國,《春秋》就記載了“佞人來了,佞人來了”。君子飲酒表示歡樂,鄙陋的人敲擊瓦缶表示歡樂,這雖然不見得好,但也不見得丑。人生性以穿絲帛來得舒適方便;但當有人用箭射他時,就以穿上鎧甲為好了,這穿上鎧甲儘管不輕便舒適,但卻能換得防身保命的安全和方便。車輻條插入車轂,各自正對著相應的孔鑿口,互相不干擾,這就像臣子各守本職,不得互相干犯一樣。曾經因穿著鎧甲而免遭箭傷,現在還以為穿著鎧甲能到水中去游泳;曾經因有大瓠而得以渡過江,現在還以為抱著大瓠能擋著火:這些人真是叫不懂事物的類別的不同啊!
君臣處在民眾之上,這就像用腐爛的草繩駕御賓士的馬;也就好像踩在薄冰之上,下面有蛟龍等著;也好像進入森林遇到哺乳的母虎。善於用人者,就像盚蟲之百腳,多而不會互相傷害;又好像嘴唇和牙齒,儘管柔軟和堅硬經常摩擦,但並不互相傷害。清醇的美酒,是來自於耕種后獲得的穀物;艷麗華美的衣裳,是來自於紡織織布。新的布帛不如盝麻織的夏布;而盝麻織的夏布破敗之後又不如新的布帛。這正是有的東西新的好,有的東西舊的好。酒窩兒長在面頰上很好看,但如果長到額頭上那就醜陋不堪了;刺繡的絲織品用來做衣裳很合適,但用它來做帽子就要遭人譏笑了。馬的牙齒不是牛蹄,檀樹根不是椅枝條。所以看到事物的本源,這各種事物也就能分別看清。石頭生來就堅硬,蘭草生來就芳香,從幼小時就具備了美好的素質,長成后就越發鮮亮。扶持和擲擊,道歉和責備,得到和失去,許諾和拒請,相差十萬八千里。弄髒了鼻子而粉飾了額頭;死老鼠在庭院的台階上,卻在室內薰香以驅惡臭;要入水中,卻又怕沾濕衣服;揣著臭物,卻去尋找芳草:這些即使是有能耐的人也無法做到的。重新發芽生長的禾苗是不會有收穫的;花開得太早就不會按季節凋謝。不要說不走運,甑終究不會掉到水井裡。抽下簪子時會摩出火花來,這沒有什麼可驚奇的。讓人不要渡江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但已經航行到江中卻要人家不渡江,這是不可以的,也是不可能的。只見虎皮上的一點斑紋是不會知道老虎的威武的;只看到騏驥身上的一根毛,是不會知道它善跑的。水蠆變成蜻蜓,孑孓變成蚊子,兔嚙變成虻蟲。事物的變化出人意料,不理解的人驚奇,了解的人就不會感到奇怪了。銅的光澤呈青色,金的光澤呈黃色,玉的光澤呈奶白色;麻桿火光昏暗,油脂燈光明亮。由微暗襯托明亮,由外表了解內質。象肉的味道,誰也沒有嘗過;鬼神的模樣,誰也沒有親眼見過;對鬼神的捕風捉影的講法,是不可能在內心留下深刻印象的。冬天的堅冰會消融,夏天的樹木會衰敗,時機難以掌握而容易失去。樹木正茂盛時,即使整天採伐也不顯衰敗凋敝;而秋風一刮,寒霜一打,一夜間樹葉都落光。患傷寒症的人被強迫進食,搶救中暑者卻讓他飲冷水,搭救自縊者時卻又遞給他繩索,拯救溺水者時卻遞給他石頭,這本身想救助他人,但卻反而害了他。即使要謹慎,丟失馬後也不必非得拆掉門檻來尋找;即使要預防,喝酒時也不必一定要抱著席子,以防醉倒時可以躺下。勇士孟賁用手掏鼠洞,老鼠雖然會隨時被抓獲,但也必定會咬傷勇士的手指,因為伸入鼠穴捉老鼠,使勇士本身的優勢無法發揮出來。
山中雲霧蒸騰,柱子石墩濕潤;伏苓被挖掘,兔絲草則枯死。一家失火,百家被燒;進讒者玩弄陰謀,百姓就暴屍荒野。粟被水浸泡就會發熱,甑在灶鍋上受火燒煮就會冒汽滴水,水能生熱,火能生水氣。迅雷能劈開石頭,這是陰陽二氣相交的自然現象。洗澡水倒入河中,會增加河水,但相當有限;雨水和積水注入大海,雖然無法使海水水位升高,但還是改變了原來的狀態。一個網眼的羅網是不可能捕到鳥兒的;沒有魚餌的垂釣是難以釣到魚的;對待士人無禮是不能得到賢才的。兔絲草無根而能生長,蛇無腳卻能爬行,魚沒有耳朵卻能聽到聲音,蟬不長嘴而能鳴叫,這些都有著它們的一定合理性和原由。仙鶴壽長千年,因此能游遍天下;蜉蝣雖朝生暮死,卻也能享盡生命樂趣。紂王把梅伯剁成肉醬,周文王就和諸侯計劃要推翻紂王統治;桀肢裂勸諫的忠臣,商湯就派人去弔唁。狂奔的馬不會撞到樹上去,瘋狗不會自己跑入河裡去,即使是最沒有理性的獸類都不會自取滅亡的,更何況人呢?喜歡大熊卻喂它吃鹽,熱愛水獺卻讓它喝酒,這真是想要飼養它們,但卻違背事理。心裡喜歡就會毀掉船來做船舵;內心想要就會不惜毀熔大鐘鑄鈴鐸。管子是忍受了無數次小的恥辱才得以成就大榮耀的;蘇秦是說了無數次的謊話才實現“合縱”想法的。箭靶一張開就招來箭矢射聚,樹木一茂盛就招人砍伐,這並不是它們想召引人們,而是客觀形勢所致。等到得到好處以後才去救溺水者,那麼時間一長,也必定有人以借溺水者而謀利。一艘破損易沉的船隻,就是連愚蠢者都不會去乘坐;一隻趕它不前進、勒它不停止的千里馬,那麼君王是不會用它來趕路的。諷刺我的品行的人,是想和我交往的;貶低我的貨物的人,是想和我做生意的。用白開水摻和白開水,是清淡無味沒什麼好吃的;單根弦的琴瑟是彈不出好聽的曲子來的。駿馬因為受遏抑而死去,鯁直之士因為正直而受困窘;賢能的人被排擠在朝廷之外,美女則在宮內被冷落。遠行的人在旅途思念家人,家人則在睡夢中和遠行者相會;慈母在北國燕地嘆息,親生兒子則在南方楚地懷念母親。新鮮的肉懸掛起來,烏鴉喜鵲就會紛紛飛來啄食;而老鷹鷂子搏擊食物,眾鳥就會四處逃散。物類的聚散,是互相感應造成的。吃他的食物不會搗毀盛放食物的器皿,吃樹上結的果實不會折斷樹枝;堵塞源頭水流就會枯竭,損壞樹枝樹木就會枯死。錯綜交叉的線條不流暢,連環相套的環子不易解,解開它的方法是不解。臨河羨魚,不如回家織網以便打魚。明月之珠是蚌蛤的病害,卻是我們的寶貝利益;虎爪象牙是禽獸的利器,卻是我們的禍害。平坦的道路,優良的駿馬,使得人想騎馬快鞭賓士;喝酒喝得痛快時,使人禁不住引吭高歌。認為是正確的就去做,所以這叫“決斷”;認為不對的,卻還去做,這就叫做“亂來”。箭矢飛快,但頂多也不過射到兩里地遠;步行雖慢,但走上上百天,也可達到千里之遠。
聖人處在陰隱處,眾人處在陽露處;聖人行於水而無跡,眾人履霜雪而有跡。音律不同者是不能欣賞同一種旋律的;形制不同的東西是不能歸為同一類體的。農夫辛勤勞動而官僚貴族從中得到供養;愚者七嘴八舌而智者從中選擇有用的語言。捨棄茂盛的大樹不歇涼而停歇在枯樹之下,不弋射天鵝而戈射烏鴉,這樣的人是難以和他謀划大事的。大丘深山沒有溝壑,是因為泉水的源頭不廣浡;而普通的溝壑水源不斷,可以灌滿千頃湖澤。看得明白,處事就能像玉石那樣堅定明確;見識昏昧,則必定心存疑慮,行動猶豫。將天下大事託付給一個人的才能上,就好像將千鈞重物懸掛在一根樹枝上。背著孩子爬牆頭,叫做不吉祥,因為一個人從牆頭上跌下來卻是兩個人受傷。而善於處理事務的人是像乘船悲歌,一人唱歌而千人應和。不能辛勤耕種卻想收穫黍粱,不善紡織卻想穿著亮麗,不費功夫卻想事業有成,這些都是困難的。有繁榮的時候,也必有憔悴的日子;有穿羅衣絹服的時間,也必有披麻卧草的時候。大雕展翅翱翔水面,扇起水波,河伯因此不敢弄潮,這是敬畏大雕的真誠。所以一個勇士敢於拚死決戰,那麼就是有千輛戰車的大軍也不可輕視他的勇氣。蝮蛇咬傷了人,敷上和堇就可治癒,事物本來就有大害反而變成大利的情況。聖人處於亂世之中,就像盛夏處在正午烈日暴晒之下等待傍晚清涼降臨;如果太陽已經西沉,那就容易熬過去。水雖然平靜,但也一定會起波紋;衡器雖然平正,但也一定會有誤差;尺才雖然整齊劃一,但也一定會有出入。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沒有準繩不能定曲直;使用規矩準繩的人,也必定有使用規矩準繩的法則。船翻沉了才顯示出遊泳的水平,馬驚奔時才顯示出駕御的優秀。嚼著沒有滋味的食物,不能咽進喉嚨;看不見形象的東西,不會在心中留下回憶的印象。犀牛和老虎在後邊追著,即使前面有隋侯寶珠,也來不及彎腰拾取,因為首先是要避開可能被傷害的危險,然後才談得上是不是有可能拾取隋侯寶珠。追捕鹿的獵人是看不上在身邊跑的兔子;做價值千金貨物生意的人是不會去計較銖兩的價錢的。弓先調好,然後才講究它的強勁有力;馬先馴服,然後才講究它的品質優良;人首先要誠實,然後才看他是否能幹。陶人扔掉的繩索,車夫感到可用而拾回家;屠夫丟掉的生鐵,而鐵匠卻把它拾起重新使用:這各人所急需的物件各不相同。百顆星星的光明不如一牙月兒明亮;十扇敞開的窗戶不如敞開一扇門亮堂。箭在十步之內,其力量可以穿透皮鎧甲,但等到箭飛到極限,其力量連薄薄的細絹都穿透不了。泰山那麼高,但背朝著它是什麼都看不見的;秋毫的細端,如盯住它看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山出產金礦,也因為出產金礦,這山也就因此被不斷挖掘,所以說山是自招挖掘;木頭生出蛀蟲,這木頭反而被蛀蟲蛀空。人愛沒事找事,就會自己禍害自己。不管怎樣靈巧的冶鍊工,他是不能熔鑄樹木的;不管怎樣靈巧的木匠,他是不能砍削金屬物的;這是由他們所從事的職業特點決定的。潔白的玉不需雕琢,美麗的珍珠無須文飾,因為它們的內在本質夠美好的了。所以只要一步一步堅持下去,就是跛腳的鱉也能爬行千里;不斷地積土築土,就可以堆成山丘。高大的城牆是由一筐筐土築成,高聳入雲的大樹靠它植入土中的根基,這些都不可能人為造成,而是由事物的必然規律所決定。
大凡用人之道,就好像用燧鑽木來取火,鑽得太慢、不連續不能出火,鑽得太快過密又不容易鑽准,最好是快慢疏密恰到好處。從早上看晚上,太陽是移動了;用曲的東西來校正直的東西,這物體就殘缺不全;聖人對待事物,像用鏡子照物一樣,能夠周密精緻地反映出事物的本來面貌。楊朱看到四通八達的道路就哭泣起來,因為這道路既可通南也可通北;墨子看見潔白的生絹就掉淚,因為這絹既可以染成黃色也可以染成黑色。人的取捨志向投合,就像金鐘石磬一旦定形,音調也就固定,就是相隔千年還是發出當初一樣的聲音。對於沒有危害的鳥,即使棲息在家門口也不會去射殺它;但如果是危害人類的鳥,即使是遠離人類,人也不會放過它們。買鄰近酒家的酒是酸的,買附近肉店的肉是臭的,但人們買酒買肉仍上這些店家,因為人們求得物件習慣是就近購取的。用欺詐來對付欺詐,用詭譎來應對詭譎,這就好像披著蓑衣去救火,挖開河渠來堵水一樣,只會亂上添亂。西施和毛嬙模樣不可能相同,但世上人都稱道她們長得好,因為她們容貌美麗是相同的;堯、舜、禹、湯的治國法典是各不相同的,但他們的德政深得人心則是一致的。聖人是順應時勢來做事的,根據自己的才能資質來建功立業的;多雨時準備好貯水器具,天旱時製作土龍以求雨。臨淄的女子,織絹時思念遠行的親人,因此將絹織得粗劣毛糙;家室中添了美貌的女子,織布的絲線也因此打結蓬亂。徵和羽這樣的高雅樂曲,卻不為那些粗俗人欣賞;將中和的曲調轉變為激切的音調,卻獲得滿堂喝彩。路過存放錢財的倉庫時故意將手背在後面的人,很少沒有偷盜之心的;所以致人生病的鬼魅,經過寺廟時總要搖動樹枝作掩護。晉國陽處父討伐楚國來解救被圍困的江國;所以平息打得不可開交的爭鬥,不在於摻在其中拉架勸阻,而在於打擊其要害,使爭鬥者自動撒手停止爭鬥。高大樹木的根一定根系發達,高聳的山峰一定以寬厚牢固的土地作基礎;腳掌寬大的人善走遠路,個兒大的人血脈流暢。瘋子傷人,沒人會埋怨;幼兒罵老漢,沒人會嫉恨:這是因為他們並無害人之心。像尾生那樣守信,不如跟牛者弦高的欺詐有意義,更何況只是偶爾一次不講信用呢?憂慮父親疾病的是子女,而能治病的是醫生;求神時供奉祭品的是巫祝,而備辦祭品的是廚師。
《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是西漢宗室劉安招致賓客,在他主持下編著的。據《漢書。藝文志》云:“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顏師古注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現今所存的有二十一篇,大概都是原說的內篇所遺。據高誘序言,“鴻”是廣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全書內容龐雜,它將道、陰陽、墨、法和一部份儒家思想糅合起來,但主要的宗旨傾向於道家。《漢書。藝文志》則將它列入雜家。
《淮南子》具有重要的文史價值。其博奧深宏的內容中蘊涵著豐富的哲學、史學、文學等各個領域的思想文化資源。
劉安(公元前179--前122),漢高祖劉邦之孫,淮南厲王劉長之子。文帝8年(公元前172年),劉長被廢王位,在旅途中絕食而死。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把原來的淮南國一分為三封給劉安兄弟三人,劉安以長子身份襲封為淮南王,時年十六歲。他才思敏捷,好讀書,善文辭,樂於鼓琴。他是西漢知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奉漢武帝之命所著《離騷體》是中國最早對屈原及其《離騷》作高度評價的著作。曾“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集體編寫了《鴻烈》(后稱該書為《淮南鴻烈》或《淮南子》)一書,劉安是世界上最早嘗試熱氣球升空的實踐者,他將雞蛋去汁,以艾燃燒取熱氣,使蛋殼浮升。劉安是我國豆腐的創始人。

問津書院名宦祠劉安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