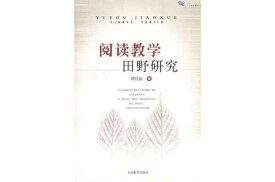田野研究
田野研究
田野工作(fieldwork,亦譯作田野研究)被認為是人類學與其他學科的最主要區別之一,田野研究方法的成熟被認為是現代社會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成熟的標誌。
在人類學史上,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wski)之所以被看作是劃時代的人物,就是因為他在西太平洋的長年“田野”工作經歷,並由此把人類學從安樂椅上解放出來,成為一門當時最具魅力的學科。
自那時起,所有欲在人類學領域上有所建樹的人都計劃著到“田野”中去,在那裡長期駐紮下來,挖掘地方知識,以求反觀自我的文化,並對整個人類的文化能夠更清楚地理解。人類學專業的從業者都必須受到田野研究的嚴格訓練,將田野研究作為人類學的不二法門已成為人類學長期以來引以為榮的學術傳統。
20世紀,對深入田野工作(intensivefieldwork)的強調,成為人類學最為突出的特徵。說一個人“沒有田野”,或者說“田野不過關”,均是在批評這個人是不合格的人類學者,同時也包含著其作品不太具備專業信賴的意思。
自馬林諾夫斯基以來所發展起來的田野工作主要是對異文化(otherculture,也譯作“他文化”)的研究,因為人類學家一直被認為是不能從事自己所屬文化研究的。換句話說,人類學是通過研究異文化來反觀“本文化”(myculture)的。因此,人類學又被打上了研究異文化的胎記。
馬林諾夫斯基在特布里安(Trobriand)群島的田野研究有一定的偶然性,他花費約3年時間(確切為2年多)實在有點迫不得已的味道。但無論如何,是馬林諾夫斯基而非他人,把人類學從維多利亞時代的“安樂椅”上帶入了科學研究的廣闊時空之中。告別了傳教士異域採風式的人類學,從此人類學被賦予了嶄新的意義。就馬林諾夫斯基而言,民族志意味著確立了構建其“關於文化的科學”的基石,無論支持他或是反對他觀點的人也無不首先回到他的田野研究工作上。所以,田野研究是現代社會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發生、發展的開端。
(一)當地觀點與學術研究
儘管我們工作的初衷是要盡量貼近被研究者的語言和思想,可是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醒自己,我們的研究結果可能不同於我們研究對象的看法。但我們所做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在肯定或偏袒當地人的解釋和觀點,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可能最終也不會成為我們著述的讀者。
當然,人類學者更多的是對當地觀點持有一種尊重的態度。這種態度事實上是自馬林諾夫斯基以來一直被人類學者遵循的基本原則,而我們之所以要遵循這種原則,則是為了保證研究結果的真實性,也是為了保證順利地進入當地開展工作。不過,客觀地講,不管我們認為自己所做的工作有多麼重要,也不論我們自認為所做的研究有多嚴謹,我們的研究結果對於當地人來講,可能並沒有什麼權威性。它只是我們自己對某些文化現象的詮釋,當地人可能並不能看懂我們寫的研究報告,儘管我們是在他們所提供的資料的基礎上進行寫作的,儘管我們描寫的是當地人的文化現象。
(二)戶訪:有前提與無前提
戶訪的有前提和無前提是相對的,重要的是看什麼樣的方法更適合我們在當時、當地的需要,更有助於我們的研究工作。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時,有前提的工作有時會驚擾被訪者(被調查者),此時,僵硬的表格式問答常常會導致掛一漏萬的結果。有時,由於我們缺乏對當地人的了解,我們設計的調查表未使用當地人的語言,因此問卷調查不能使我們獲得最佳的調查效果,這就使我們不得不用無前提的方式開展工作。當然,完全的無前提會使我們的工作變得無序和盲目。兩者結合起來靈活運用最為理想。
(三)進入調查地:有身份與無身份
我們進入“田野”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是誰?幹什麼來了?當然,接下去還會有人問我們:調查這些有什麼用?接下去的問題你可以先不考慮,因為,如果你提供給對方一個合適的身份,這些問題有時就可以迴避不答。但第一個問題是每一個進行田野工作的人都無法迴避的,因為我們進入了這樣一種環境,它時時提醒人們: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之間存在著差異。而且,我們的工作又不斷提示被調查者意識到自己的文化特性,意識到與我們或與其他人的文化差別。這就使我們在一開始就面臨有身份進入與無身份進入的選擇。
有身份進入是指帶著介紹信(或其他形式的身份介紹)進入“田野”。無身份進入是指在無任何官方介紹或證明的狀況下,以個人身份進入“田野”。這兩種方式各不相同,其效果也大不一樣,但卻各有其優劣之處。有身份進入的優點是明顯的:它能獲得比較充分的官方資料;戶訪的人家由於是特意挑選出來的,比較有特點,可以節約較多的調查時間,因此效率較高,收穫也比較大。但有身份進入也有其缺點:信息大多是與地方經濟建設相關的,地方文化(特別是民間文化)的資料盲點多,需要補充的空間相對較大;在田野調查的各個時段中,自己都是處於被動接受的地位,無法進行一般的交流。無身份進入的優點是:所調查的文化內容比較貼近生活,貼近民間;問答輕鬆,隨機性強,易於捕捉信息;被調查者精神放鬆,易於進行交流,並且能夠與我們保持長期的聯繫。無身份進入的缺點是:案例的典型意義可能不大,或者說,想獲得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的難度較大;調查時間的長短也難以把握。因此,田野研究是一個個性化的研究工作,也是一個必須付出時間、付諸實踐的工作。
“田野研究”,對於當前的課程改革來說,是一種新的科研方式,是教育科研的走向和方式的變革。國外人類學與社會學非常重視和流行的田野作業,比如“田野考察”、“田野調查”、“田野描述”等。這裡的“田野”已經不僅僅是“野外”的意思,實際上已經成了“現場”的代名詞。稱其為“田野”,其真正的含義是指真實的、本來的、甚至是原始的;是開放的、豐富的,甚至是完全敞開的,因而,這種“研究”是實打實的。只有在“田野”里,才能呼吸到新鮮的“空氣”,產生研究的激情,獲取原始而真實的信息。一種新的理論的生成點,不是在書本、書房裡,而是在“田野”即教育教學的實踐中。所以,變革教育研究的方式,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其實,當前的教育科研應該是走向“田野”的。新課程改革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將理想的課程、正式的課程轉化為運作的課程、教師領悟的課程,最終轉化為學生體驗的課程、生活的課程。學生學習的場所就是課程改革的“田野”,就是教育科研工作者所要付出努力的地方,在這裡有著無數鮮活的思想與經驗在涌動,等待我們去發現與挖掘;也有無數困惑與困難,等待我們去研究和解決。課程改革不能只停留在“理念”和“通識”上,更多的是如何具體設計,如何實際操作,如何變革教與學的行為方式。走進“田野”,就是真正走進課程,走進課堂,走進生活。只有這樣,我們的新課程改革與教育科研才能走進教師與學生的心中,才具有親合力、凝聚力,才能真正的成為研究。
“田野研究”的內涵要旨是注重“現在時”和“在場感”。作為教育科研工作者和管理者的校長、教導主任、教師要有更多的“在場時”和“在場感”;“田野研究”要注重真實感,不粉飾,也不躲避,從“田野”中獲取第一手的資料信息,據實記錄、據實研究;“田野研究”還要注重個案研究與行動研究,加大“浸入”的時間和程度,從個別到一般,從行動到認識的飛躍;“田野研究”更為注重的是教師的作用,因為教師是我們課程改革的關鍵,他是教育的實施、執行者,也是教育的研究者,讓教師去敘事、去分析,甚至讓教師進行“內心的獨白”。當然,“田野研究”不能停留在現場的“白描”,要離開田野去進行反思與“深描”。即我們所說的,從實踐中來,也要回到實踐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