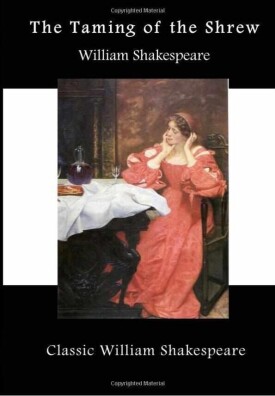共找到11條詞條名為馴悍記的結果 展開
馴悍記
莎士比亞著戲劇劇本
《馴悍記》是英國戲劇家威廉·莎士比亞創作的劇本,創作於1590年至1600年。
《馴悍記》講述了富家女凱瑟琳娜接受彼特魯喬的改造,凱瑟琳娜的服從是為了躲避彼特魯喬的折磨,彼特魯喬成功地讓凱瑟琳娜成為一位“失去自我”的溫柔妻子的故事。
在該劇本中,以凱瑟琳娜為代表的女性們,籠罩在以男性統治和權威的絕對控制下,對自我個性的追求和社會現實的理想化,使得女性在夾縫中難以生存,不得不上演一出震撼人心的悲劇。《馴悍記》探討了女主人公凱瑟琳娜從“悍女”到“賢妻”,從“語”到“失語”這一轉型過程中的心理變化及其“失語”成因。
《馴悍記》講述的是精明的彼特魯喬迎娶“彪悍”的富家女凱瑟琳娜的故事。凱瑟琳娜脾氣不好遠近聞名,她是“潑婦”、“活閻王”,所以她的父親著急把她嫁出去,寧可拿出昂貴嫁妝,也無人問津。“紳士”彼特魯喬得知這個消息后,便向凱瑟琳娜求婚。可是從求婚到結婚開始兩人就不斷爭吵,因為凱瑟琳娜脾氣火爆所以從不把彼特魯喬放在眼裡。聰明的彼特魯喬為了改造妻子,想出了一個對付妻子的奇怪方法,就是比凱瑟琳娜脾氣更火爆,以寵慣妻子為借口,製造出脾氣暴躁的假象,讓妻子受到外人誤解和怠慢。凱瑟琳娜受到各種折磨之後終於明白作為妻子應該遵守婦道,不該野蠻粗暴,完全服從“婦道宣言”,從此以後凱瑟琳娜成功被彼特魯喬改造成溫柔賢惠的妻子。
| 序 幕 | |
| 第一場 | 荒村酒店門前 |
| 第二場 | 貴族家中的卧室 |
| 第一幕 | |
| 第一場 | 帕度亞;廣場 |
| 第二場 | 同前;霍登旭家門前 |
| 第二幕 | |
| 第一場 | 帕度亞;巴普底士他家中一室 |
| 第三幕 | |
| 第一場 | 帕度亞;巴普底士他家中一室 |
| 第二場 | 同前;巴普底士他家門前 |
| 第四幕 | |
| 第一場 | 彼特魯喬鄉間住宅中的廳堂 |
| 第二場 | 帕度亞;巴普底士他家門前 |
| 第三場 | 彼特魯喬家中一室 |
| 第四場 | 帕度亞;巴普底士他家門前 |
| 第五場 | 公路 |
| 第五幕 | |
| 第一場 | 帕度亞;盧生梯奧家門前 |
| 第二場 | 盧生梯奧家中一室 |
《馴悍記》的故事背景約為16世紀的英國。伊麗莎白時代,法律沒有針對婦女地位的專門條款,但從婚姻、繼承權等條款中可以揣測出婦女的社會地位。女性在婚前是父親的棋子,若女性沒有足夠體面的嫁妝,就會被鼓勵進修道院,成婚後女性便成為丈夫的財產。妻子被視為男人的私有財產,自然與丈夫不能形成對等關係。女性的重要使命就是嫁個好丈夫,因此,父母們不惜花費高昂的學費送女兒去學習舞蹈、交際禮節、精美的針線活,以及廚藝和家務等技能。女人為了突出細長的腰身,將木片、鯨骨或者金屬製成的撐架緊緊地綁縛在自己的身上。由於撐架的束縛,許多女人在交際場合呼吸急促,臉部發紅,這些“嬌嗔嫩喘”的狀態,正是刺激男人的因素。丈夫是妻子要絕對服從的主人,女性作為“第二性”或“他者”,被排斥在男性中心社會之外。男人們在外喝酒狂歡,追逐名利和女人,往往被認為是一種社交時尚。女人卻只能“嫁雞隨雞,夫唱婦隨”,不允許有一點“出格”、“出軌”。
《馴悍記》取材於古代蘇格蘭民謠《一張馬皮裹悍妻》,繼承了宣揚大男子主義的歷史背景及馴悍文學傳統,“男尊女卑”的歷史現實,使作者不自覺地從男性視角維護自己的話語權。莎士比亞對殘暴虐待女性的故事進行了大改動,嬉笑怒罵取代了極端場面。
凱瑟琳娜
凱瑟琳娜是個超標“悍女”、“活閻羅”、“野貓”、“惡鬼一樣的脾氣暴躁的賤人” 、“喜歡吵吵鬧鬧的長舌婦”。她大大咧咧的出場,無理取鬧式地狂罵妹妹的追求者,粗魯地頂撞父親,毫無淑女風範。她因為性格暴躁、脾氣倔強,找不到任何一個敢娶她的男人,她的“悍”甚至讓父親和妹妹都難以忍受,她把妹妹貝恩卡綁在椅子上質問最喜歡哪一個求婚人,由於沒得到答案,她就打她的妹妹。所有的男人都“懼怕”這樣的悍婦,都對凱瑟琳娜避之不及,連妹妹的幾位求婚者都想盡辦法想把這個“眼中釘”除掉,把她嫁出去,結果費盡周折,吃盡苦頭,最後彼特魯喬先生的出現讓這個根本不懂社會規則,不屈從當時社會要求的女人凱瑟琳娜脫胎換骨,成為了溫柔體貼,順服又頗具當時社會女性共有品質的模範。
貝恩卡
貝恩卡在眾的眼中是符合父權制社會要求的、滿足男性期待的溫柔賢淑女性。在擁有同樣的嫁妝、家世的條件下,眾多的追求者看重的就是她身上那名叫“服從”的屬性。
主題思想
對性別壓迫下的父權、夫權的顛覆和嘲弄
《馴悍記》表現了彼特魯喬改造凱瑟琳娜的“勝利”,實際上體現了男權思想的專制蠻橫和對女性地位的剝削。按照作品中男性地位的規範,女性從出生開始就決定了悲慘結局,在父親和丈夫的男權壓迫下,讓凱瑟琳娜失去地位和意識,表現了女性在男權思想夾縫中難以生存的現狀。
《馴悍記》戲劇一開始,莎士比亞就點明貴族老爺打算通過戲弄斯賴逗逗樂,給斯賴安排的妻子是男性假扮的,而伊麗莎白時期的戲劇女性演員都是男性伶人扮演的,這似乎是在暗示凱瑟琳娜和貝恩卡所表達的並不是女性真實的想法,因為“她(他)們”並不是真正的女性。藉助“戲中戲”的藝術手法,作者暗示接下來的內容不過是一場虛幻。看似荒誕的鬧劇中,在凱瑟琳娜的掩護下,貝恩卡對父權和夫權的反抗容易被人們所忽視,莎士比亞正是通過這一明一暗的女鬥士的性格,突轉實現了對封建倫理保護傘下的父權與夫權的嘲弄和諷刺。
凱瑟琳娜的去“悍”化:該戲劇中彼特魯喬對凱瑟琳娜的馴服過程,體現了作者所採用的陌生化手法,他沒有塑造一個手持皮鞭或大棒的悍夫形象,儘管在那個時代丈夫對妻子使用暴力是法律許可的,而是刻畫了一個兼具丈夫與醫生雙重身份的男性形象。他嚴格按照體液說醫療理論,對妻子暴躁的體液進行調理、降溫,最後成功將妻子轉變為滿足社會期待的、傳統溫順的女性角色。在文藝復興時期重新流行的眾多古羅馬文化中,體液說不僅是醫學上的一個熱門話題,也是當時反覆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影響人物性格塑造的一個重要元素。根據體液說理論,主暴躁體液為黃膽液,由冷熱乾濕四種素質中的熱干素質構成,所蘊含的熱量也就最大。而熱量被認為是熱血動物與生俱來的特有的性能,它是源自心臟的一種能動的力量,讓人具備生長的功能,和消化,行動,情感以及思想。
莎士比亞筆下的悍婦凱瑟琳娜,正是溫順女性中的一個例外,體內燃燒的熱量讓她變成了一個脾氣暴躁的渾人,一言不合必定暴跳如雷,成為了眾人談之色變的恐懼對象。這樣一位彪悍的女士自然得不到男性的愛慕,而當時的風俗要求次女不能在長女之前出嫁,無人問津的凱德成為了必須搬走的路障,堵塞了多位男士求娶溫柔賢淑的妹妹貝恩卡之路。不過幸好天上掉下了一個掘金者彼特魯喬,宣言“‘我’的求婚主要是為錢,無論她怎樣淫賤老丑,潑辣兇悍,‘我’都一樣歡迎,只要她的嫁妝豐盛, ‘我’就心滿意足了。”
雖然是為了嫁妝才求婚,但彼特魯喬不甘忍受暴躁的妻子,一步步按照“醫學理論”對妻子進行的改造。在婚禮進行的時候,彼特魯喬當即展開了對凱瑟琳娜的治療。女性的溫順緣於身體的溫度或者說熱量要比男性低,而凱瑟琳娜暴躁的原因無疑是體內過高的熱量,顯然彼特魯喬得設法讓她的溫度降低。根據體液說的理論,影響人體熱量的因素包括氣候、飲食、休息、睡眠和情感。彼特魯喬的第一步治療方案就是用蠻橫無理的態度迫使凱瑟琳娜在寒冷的天氣里和他一起騎馬回家。他的僕人一語道破其中玄機:“在冬天沒有到來之前,她(指凱瑟琳娜)是個火性很大的潑婦,可是像這樣冷的天氣,無論男人、女人、畜生、火性再大些也是抵抗不住的。連‘我’的舊主人,‘我’的新主婦,帶‘我’自己全讓這股冷氣制伏了。”凱瑟琳娜在途中落入泥濘,身上又濕又冷、又累又餓;到家之後彼特魯喬展開了他的第二步治療方案,即“讓她睜著眼,不要休息”,他將卧室弄得亂七八糟,在她昏昏欲睡時大聲吵鬧。接著,彼特魯喬讓僕人在飢餓的凱瑟琳娜的面前奉上一道道菜肴,卻又不讓她吃這些會“上火”的食物。在連續幾天的“治療”以後,無法補充熱量的凱瑟琳娜變得溫順無比。看似步步合情合理的降溫治療下掩蓋的是對凱瑟琳娜無情施行的生理和心理的雙重冷暴力,孤立無援的她只能選擇屈服。精密的醫學理論的嚴肅性與喜劇中的嬉戲和滑稽矛盾卻又異常地契合,對整個男權社會的夫權專制進行了嘲諷。
貝恩卡的性格突變:貝恩卡在沒有獲得父親同意的情況下與路森修秘密結婚,這是對父親在她身上享有的權利的觸犯,因為貝恩卡是屬於她父親的,更是對父權制意識形態和國家法律的違反。在與路森修結婚之後,路森修與彼特魯喬打賭測試誰的妻子更為順服,貝恩卡和凱瑟琳娜的逆轉讓眾人大為吃驚,兩人似乎互相交換了性格和秉性。
凱瑟琳娜的馴服來自外界對她的身體熱量的調控,這暗示她的性格變化處於一種現實與虛幻隨時轉變的中間地帶,缺乏恆定性。但貝恩卡的變化來自自身的意志和思想,並沒有受到外界的影響。她對父親和丈夫的反抗是其自由意志的體現,她的婚姻不是遵循傳統觀念中“婚姻始終是兩個家庭之間的毫無感情的事務,是一種為了久遠的相互利益和為了生養繼承人以擴大世系的安排”,而是出自與路森修的自由戀愛;而貌似悍婦的凱瑟琳娜最終卻是遵循父親的安排嫁給了彼特魯喬。按照當地的法律,貝恩卡將被剝奪所有的嫁妝,但莎士比亞巧妙地通過安排一場賭博讓她的父親將屬於她的嫁妝給了彼特魯喬,以這種滑稽的方式達成法律的要求,實質是以此嘲笑那表面莊嚴、實則不合理的法律,表達了對父權專制家長利用嫁妝實現對女性的權力掌控的諷刺與不屑。她因為愛情私自與路森修舉行了婚禮,但妻子角色的轉變並沒有讓她放棄自己的驕傲與尊嚴,變成一個“唯夫命是從”的附屬物品。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凱瑟琳娜對彼特魯喬的完全屈服。劇中凱瑟琳娜最後的那番宣言,揭示了男權社會下女性艱難掙扎的本質,“‘我’的心從前也跟你們一樣高傲,‘我們’的力量是軟弱的”,在面對強大的父權制思想意識形態和社會機制的壓迫下,強悍如凱瑟琳娜也只能變成匍匐在男性的腳下。
《馴悍記》道盡了對束縛女性尊嚴與自由的封建專制下的父權與夫權的嘲弄與諷刺,以及對維護這種專制的法律制度的批判和譏諷。
藝術特色
《馴悍記》是莎士比亞早期創作的一部喜劇作品,其用滑稽、詼諧、荒誕的文學語言對文藝復興時期兩對男女的婚戀關係進行生動、形象的表現,並以此為基礎對當時英國社會現狀和存在問題進行揭示和諷刺,使該部戲劇作品具有極為典型的寫實主義藝術特徵。同時,在《馴悍記》進行創作活動過程中,莎士比亞還靈活地運用了詩歌的創作手法、藝術表達方式,使該劇作在對現實英國進行反映的同時還具有顯著的浪漫主義藝術特徵。
藝術手法
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並存:在《馴悍記》中,現實主義是指戲劇創作的一種藝術表現手法,即莎士比亞在《馴悍記》中將內容、人物形象等直指當時現實英國社會現狀與問題,以及當時社會中的各類人群。例如,在《馴悍記》作品中,序幕中的“貴族”和接下來其他幕次中陸續登場的“巴普底士他”、“路修森”、“葛萊米奧”等人都代表著現實英國社會中的上層社會人群,他們擁有金錢和地位,同時也擁有“特權”,在《馴悍記》文本中,“貴族”可以閑來無事和僕人、戲班伶人等一起捉弄醉酒的乞丐,以博自己一笑;而巴普底士他可以控制、掌控他人的婚姻;路修森、葛萊米奧也同樣可以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與別人打賭上等等。
在《馴悍記》中,莎士比亞將現實英國社會中的下層貧民等弱勢群體在該作品中進行了精準的刻畫,比如說,序幕中的乞丐、戲班裡的伶人,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他們卻沒有享有獨立的人權,反而要受到特權階級的支配,欺辱,以獲取更好的物質生活。巴普底士他的兩個性格迥異的女兒,雖然擁有富商千金的身份,但實際上是代表當時英國社會中處於劣勢地位的女性,在該劇作中,無論她們自身的性格是兇悍還是溫順,她們都沒有辦法真正去擺脫父權和男權的統治和欺壓,換句話說,作為《馴悍記》劇中主要女性角色,凱瑟琳娜沒有獲得真正的尊重以及與男性平等的地位,這是莎士比亞利用戲劇中人物形象及其關係對於當時英國社會兩性關係的反映。由此可見,在《馴悍記》中,莎士比亞通過對劇中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進行塑造、刻畫、表現,成功的在劇作中對當時英國社會中的階級關係、兩性關係等主題進行了尖銳的揭示和反映,使該劇作從現實意義角度來說更具深刻性。
寫作手法
浪漫主義的寫作手法在《馴悍記》中主要表現為,該戲劇作品秉承了莎士比亞詩體劇的藝術特徵,台詞、唱段等以詩歌為載體,通過長短句和修辭等表達方式在對戲劇內容進行表述的同時對人物角色的內心感受、情緒、情感等進行準確的表達。譬如,路森修第一次見到貝恩卡時對身邊的人感慨,“‘我’看見她的櫻唇,她嘴裡吐出的氣息,把空氣都熏得充滿了麝蘭的香味。‘我’看見她的一切都是聖潔而美妙的。”在該段話中,莎士比亞先後使用了比喻和誇張的修辭手法,將貝恩卡的紅唇比作櫻桃,又用“空氣都熏得充滿了麝蘭的香氣”誇張的表現出貝恩卡身上迷人的氣質,同時將路森修對於貝恩卡的好感表現得淋漓盡致。又如,彼特魯喬在為了錢而決定向凱瑟琳娜求婚時表示,“既然‘我’的求婚主要是為了錢,無論她怎樣淫賤老丑,潑辣兇悍,‘我’都一樣歡迎;儘管她的性子暴躁得像起著風浪的怒海,也不能影響‘我’對她的好感”,莎士比亞用“起著風浪的怒海”來形容凱瑟琳娜暴躁、兇悍的性格,同時,該段文字也充分地將彼特魯喬貪婪的形象表現出來。莎士比亞在賦予戲劇以詩歌韻味的同時,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深刻、形象,並更有利於劇情的繼續發展。
喜劇與悲劇並存
《馴悍記》是一部具有鬧劇特徵的典型喜劇。莎士比亞首先選擇以“戲中戲”的形式,講述了貴族戲耍乞丐的內容,即貴族遇見大醉伶仃的乞丐,利用自己的僕人和路過的戲班伶人為乞丐製造了一個虛假的生活場景和社會身份,以至於乞丐否定了自己之前的身份,欣然的接受了自己新的身份、地位,欣然的和“太太”一起觀賞戲劇表演。隨後,莎士比亞對巴普底士他的兩個女兒的婚戀生活進行了生動、形象的敘述,其間,莎士比亞運用了具有荒誕、詼諧特徵的文學語言,例如,為了追求自己的心上人,路森修和自己的僕人調換身份,又假裝是家庭教師與比恩卡親近,隨後為了身份不被揭穿又找人假冒自己的父親,卻沒有料到自己親身父親又正好出現。如彼特魯喬在自己的婚禮上遲到並且打扮得極為怪異,“他戴著一頂新帽子,穿著一件舊馬甲,他那條破舊的褲子腿管高高捲起,一雙靴子千瘡百孔,可以用來插蠟燭,一隻用扣子扣住,一直用帶子縛牢;他還佩著一柄武器庫里拿出來的銹劍,柄也斷了,鞘子也壞了,劍鋒也鈍了。”可是,彼特魯喬還是和富商的女兒凱瑟琳娜結婚了。莎士比亞運用滑稽的語言推動戲劇作品中情節的發展,使戲劇本身呈現出荒誕的藝術特徵,同時對於相關人物角色進行形象的刻畫,進而對當時英國社會現狀進行反映和諷刺,比如,貴族戲耍乞丐,滑稽的表現出了當時統治階級對於底層人民群眾的欺壓,而凱瑟琳娜嫁給形象上並不與自己匹配的彼特魯喬則是因為在當時社會父權、男權具有統治地位。
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馴悍記》的最後一幕)為“對女性和男性的徹頭徹尾的惡劣冒犯”。
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陸谷孫說:“該戲劇劇不是一個鬧劇,而是一部浪漫主義戲劇,因為劇中有很多浪漫主義的人物。”

威廉·莎士比亞(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