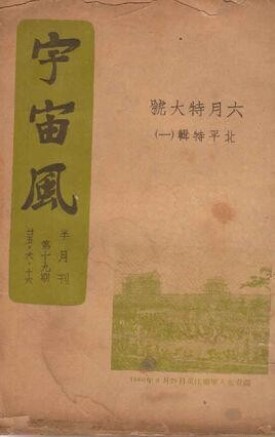宇宙風
宇宙風
《宇宙風》是文藝期刊,1935年9月在上海創刊,林語堂等主編。初為半月刊,后改為旬刊。抗戰時期曾在廣州、重慶等地出版,是繼《論語》、《人世間》之後出現的資產階級的文藝刊物,1947年停刊。

宇宙風
1935年9月《宇宙風》在上海創刊,出至第66期,
1938年5月遷廣州1出67—77期,
1939年5月社址遷香港,同時在桂林設分社,出78—105期(在香港排版紙型運至桂林印刷出版),
1944年編輯部遷桂林,出106—138期,
1945年6月遷重慶,出139—140期,
1946年2月遷廣州出141—152期(終刊號)。
這一條路線也是當年上海許多文人撤退的路線。曹聚仁在“《宇宙風》一三九期”文內說:“……昨晚,手邊便是一本重慶版的《宇宙風》一三九期,我相信這本刊物到了某人手裡,該是最可寶貴的古董了。這本刊物用那麼可憐的草紙印行,看起來實在模糊得很。
1945年6月15日,二十五年前的事。這一期,乃是他們去桂林失陷后,避居重慶,喘息初定,總算復了刊的第一期。可是,這一期的刊行,離日軍投降只有一個半月,他們續刊了不及三個月,便‘漫卷詩書喜欲狂,’要順流東歸了。我手邊這一本,便成為海外孤本了,也許在海內也是孤本了。”在海外算不算孤本不好說,在海內算不得孤本,塞齋雖不存全部152期《宇宙風》,但此139期是存的,亦因曹聚仁的話而珍惜有加。
《宇宙風》除了這152期之外,還於1939年3月—1941年12月在上海出了《宇宙風之刊》56期。據當年此刊編者周黎庵回憶,由於編輯部內部人事矛盾,協議分的家,《宇宙風》的牌子給了林憾盧(林語堂三哥),算是正牌,陶亢德另創乙刊,算是副牌。周黎庵說林憾盧與巴金最要好,林遷桂林后,巴金也去了,巴金和蕭珊便住在《宇宙風》社,並是在那裡結婚的,
2010年來,許多舊期刊出過“精選本”,《宇宙風》的精選本由周黎庵(周劭)作前言,這是惟一的一種由當事人作前言的精選本,當然是最真實最具史料價值的前言。
今天的人們評論《宇宙風》,偏見多有,那是他們只看到了(甚至沒看到只是人云亦云)前期《宇宙風》的“不合時宜”地宣揚“小品文與幽默”而沒有看到後期《宇宙風》在堅持抗戰方面的宣傳力度。即便是在前期,《宇宙風》的期銷售量45000份(僅次於《生活》的12萬份,《東方雜誌》的8萬份),排在雜誌年”的第三位,也並非魯迅那句“本是麻醉晶,其流行亦意中事,與中國人之好吸鴉片相同也。”所能一言全否的。至今未能看見哪怕是一篇對《宇宙風》及此類期刊的詳盡的始末性論文式的文章。一個豐子愷自始至終都為它作畫作文的期刊,絕不會是一個太差的期刊。你讀過了嗎?就說不好?
《宇宙風》無“發刊詞”,但林語堂在最前面的“無姑妄言之”欄中的兩篇短文可視為辦刊主旨,—曰《孤崖—‘枝花》,’—曰《無花薔薇》。前者曰:“想宇宙萬類,應時生滅,然必盡其性。花樹開花,乃花之性,率性之謂道,有人看見與否,皆與花無涉。故置花熱鬧場中花亦開,使生萬山叢里花亦開,甚至使生於孤崖頂上,無人過問花亦開。香為蘭之性,有蝴蝶過香亦傳,無蝴蝶過香亦傳,皆率其本性,有欲罷不能之勢。”後者曰:“雜誌,也可有花,也可有刺,但單叫人看刺是不行的。雖然肆口謾罵,也可助其一時銷路,而且人類何以有此壞根性,喜歡看旁人刺傷,使我不可解,但是普通人刺看完之後,也要看看所開之花怎樣?到底世上看花人多,看刺人少,所以有刺無花之刊物終必滅亡。
《宇宙風》的離滬南遷,主要是“八·一三”上海抗戰全面爆發的原因,刊物的出版和發行沒有了保證。另一個原因在於主編之間的矛盾,林語堂學習西方刊物實事辦法,把幾本小品文刊物辦得有聲有色。但《宇宙風》開始鼎盛之時,林語堂卻於1936年夏季,因沒當上南京政府立法委而赴美定居,編刊之事託付其三兄林撼廬。由於各自見解和習性的不同,陶亢德對於林語堂之舉頗為不滿,導致矛盾升級無法共事而各行其是,《宇宙風》正牌歸林撼廬,陶亢德在上海另辦《宇宙風乙刊》。其實《宇宙風》在離開上海之後漸顯頹勢,儘管有不少的抗戰內容和名家作品,影響力已不能和在上海的鼎盛時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