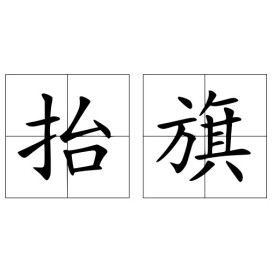抬旗
抬旗
抬旗,指清朝旗人為了提高出身而抬升旗籍的制度。
八旗制度初建時設四旗:黃旗、白旗、紅旗、藍旗。1614年因“歸服益廣”將四旗改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增設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合稱八旗。清朝建立后,正黃旗、正白旗、鑲黃旗為上三旗,直屬皇帝,其餘五旗為下五旗。康熙朝後,皇后(包括被追封皇后)和貴妃及其母家在下五旗者,皆編入上三旗以提高身份,即抬旗。
康熙帝之第四子胤禛即位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至雍正元年二月冊封貴妃之前,將原隸下五旗之鑲白旗的側福晉年氏一支,以及分佈於正白旗、鑲白旗及正黃旗包衣下的其他年氏家族成員全體抬入上三旗鑲黃旗。雍正三年年羹堯獲罪,除其於雍正二年青海戰場立功其子年興獲封的世管佐領被撤銷,年氏全族仍隸鑲黃旗。(署理廣東巡撫·布政使年希堯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奏摺)
雍正五年(1727年),正藍旗軍人河南巡撫加兵部尚書田文鏡,以政績突出,“命抬入正黃旗”(《清史稿》卷294,《田文鏡傳》)。所謂“抬”,即由低向高提升之意。抬旗乃是褒獎酬勞之舉,是旗員改變身份地位的一種重要途經,是一種顯赫的榮耀,獲此殊榮多由皇帝特旨或部議。
願意做普通百姓之旗人,可以脫離八旗組織,不再承擔八旗的義務,但也不再享受八旗的福利,即出旗為民。乾隆七年(1742年)發布《籌漢軍歸籍移居諭》,諭曰:
“八旗軍自從龍定鼎以來,國家休養生息,戶口日繁。其出仕當差者,原有俸祿錢糧,足資養贍。第閑散人多,生計未免艱窘。又因限於成例,外任人員既不能置產另居,而閑散之人,外省即有親友可依,及手藝工作可以別去營生者,皆為定例所拘,不得前往。以致袖手坐食,困守一隅,深堪軫念。朕思漢軍其初非滿洲,有從龍入關者,有定鼎后投誠入旗者,亦有緣罪入旗與夫三藩戶下歸入者,內務府王公包衣撥出者,以及召募之炮手,過繼之異姓,並隨母因親等類,先後歸旗,情節不一。其中惟從龍人員子孫,皆系舊有功勛,歷世既久,自毋庸另議更張。其餘各項人等,或有廬墓產業在本籍者,或有族黨姻屬在他省者,朕意欲稍為變通,以廣其謀生之路。如有願改歸原籍者,准其與該處民人一例編入保甲。有不願改入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里遠近,准其前往入籍居住。
此內如有世職,仍許其帶往,一體承襲。其有原籍並無倚賴,外省亦難寄居,不願出旗仍舊當差者聽之。所有願改歸民籍與願移居外省者,無論京外官兵閑散,俱限一年內具呈本管官查奏。如此屏當,原為漢軍人等生齒日多,籌久遠安全計,出自特恩,后不為例,此朕格外施仁原情體恤之意,並非逐伊等使之出旗為民,亦非為國家糧餉有所不給。可令八旗漢軍都統等詳細曉諭,仍詢問伊等有無情願之處,具摺奏聞。”(《清高宗實錄》卷164,乾隆七年四月壬寅)
此向漢軍發出的上諭雖然說得很委婉,但下令允許漢軍人退出八旗,回歸漢籍則是千真萬確的。其理由是因為漢軍生齒日繁,生計未免艱窘,又因限於成例不能置產另居,而別去營生。為解決因此造成的只能“袖手坐食,困守一隅”的問題,而採取的措施。即“稍為變通,以廣其謀生之路”,鑒於“漢軍其初非滿洲”,因而准其“改歸民籍”,“與民人一例編入保甲”,而脫離八旗回歸漢籍,實為卸磨殺驢,“亦非為國家糧餉有所不給”,而是隨意找的借口。但滿洲八旗除外。同時限定此項工作要在一年內結束,並指出此乃“出自特恩,后不為例”。似乎這又是臨時舉措。儘管這時主要針對的是八旗漢軍。然而事態的發展足以說明這並非權宜之計。
因為令漢軍改歸民籍的決策一經實施便再未停止,而皇帝暨朝廷一再以“諭”、“旨”,或“議准”、“奏准”等形式繼續明確提出一系列出旗為民的政策、原則以及具體要求。繼續推動這項漢軍改歸民籍決策的實現,且步步加緊,範圍亦逐漸擴大。一年到期后,八旗漢軍都統等上奏稱:京師八旗漢軍中情願出旗為民者共1939647人,其中有官員身份者達14178名,包括現職官員2213名。其餘為“現食錢糧”的馬步兵、拜唐阿,並告休、參革官員,以及閑散(《清高宗實錄》卷189,乾隆八年四月戊申)。這個狀況乾隆帝很是滿意,於是他頒布上諭稱,准許八旗漢軍改歸民籍,乃“原指未經出仕及微末之員而言。至於服官既久世受國恩之人,其本身及子弟,自不應呈請改籍,朕亦不忍令其出旗。”於是明確規定:“嗣後文職自同知等官以上,武職自守備等官以上,不必改歸民籍”()。對出旗一事作出了限制性的規定,對出旗者要從嚴掌握。似乎收縮了政策。然而這是明緊實松,因為此諭一出,就等於宣布出旗之事限一年內完成,且下不為例之決定作廢。因為在這裡未言及的其它人員,根據自願原則當然可以繼續出旗。這也等於宣布出旗為民之事照舊進行。乾隆十二年(1747年),上諭說:“朕觀漢軍人等,或祖父曾經外任置立房產,或有親族在外依倚資生,及以手藝潛往直隸及各省居住者,頗自不少。而按之功令,究屬違例。伊等潛居於外,於心亦不自安。朕思與其違例潛居,孰若聽從其便。亦可各自謀生。”於是又決定,“嗣後八旗漢軍人等願在外省居住者”,“不拘遠近任其隨便散處”(《清高宗實錄》卷294,乾隆十二年七月乙未)。顯然這是根據實際情況又一次放寬出旗為民的限制。
十九年(1754年)三月,乾隆帝頒諭稱:“八旗奴僕受國家之恩,百有餘年,邇來生齒甚繁,不得不為酌量辦理。是以經朕降旨,將京城八旗漢軍人等,聽其散處,願為民者准其為民。現今遵照辦理,至各省駐防漢軍人等,並未辦及。亦應照此辦理,令其各得生計。”至此,又將八旗漢軍出旗為民的範圍由京師擴展到各地駐防,八旗漢軍出旗為民的決策已全面鋪開。此上諭緊接著又稱:“所遺之缺,將京城滿洲派往。而京城滿洲亦得稍為疏通矣”(《清高宗實錄》卷459,乾隆十九年三月丁丑)。同年七月,遂議准福州駐防漢軍兵一律出旗。其願為民者,聽其散處為民,“令指定所往省份州縣,呈明出旗人籍,子弟與民籍一體應試”。其“仍願食糧者,分派綠營改補”。而漢軍原住房屋,無論官房、自蓋,均留給滿兵駐紮。乾隆帝又針對軍機大臣等“所有京口、杭州、廣州各駐防漢軍似應照此辦理”,並“請令各該總督將軍按各處情形,詳悉妥議”之奏請,乃頒旨稱:“不用將來再看,若要辦,從京口起”(《清高宗實錄》卷469,乾隆十九年七月甲午)。這是令駐防漢軍立即出旗,不得遲延。不久,乾隆帝又說,令漢軍出旗“正為伊等生計起見”。其出旗后所空之缺額,“即以滿洲充補,亦於滿洲生計有益,所謂一舉而兩得也”(《清高宗實錄》卷500,乾隆二十年十一月癸酉)。顯見這更透露出令八旗漢軍出旗為民的舉措,大有丟卒保車,即捨棄漢軍保存滿洲之真實用意。一聲令下,從十九年起,各地駐防漢軍出旗為民之舉便陸續展開。至四十四年,各地駐防之八旗漢軍已幾乎全部被命令出旗為民(見《清朝文獻通考》卷184至卷188;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128。又見《杭州八旗駐防營志》卷15,《經制志政》、《京口八旗志》卷上,《營制志》)。而乾隆二十三年,議准:“八旗漢軍年老疾殘不能當差,以及差使平常不堪教養者,俱令為民;其閑散人等無以養贍依靠親屬者,亦令出旗為民;至於領種官地之人,久在各州縣種地,業屬各州縣管束,應即令其就近為民”(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統》)。這是對八旗漢軍出旗為民的硬性規定,凡符合此條件者,一律出旗,在這裡已完全取消了自願原則,沒有商量餘地。一切年老疾殘、庸劣無能及謀生乏術者,皆勒令出旗,由此看來令漢軍出旗為民一事大有“甩包袱”的味道。與數十年前上諭中所謂為漢軍人等著想,籌長久安全之計的“特恩”,已大相徑庭。實際上,清廷同時還有規定,對所謂“旗人漸染惡習,竟有不顧顏面,甘為敗類者”,認為乃是一些“寡廉鮮恥,估終之徒,留之有損無益”,且“有玷旗籍”,因此凡屬此類“不但漢軍當斥令為民,依律遣發,即滿洲亦當削其名籍,投畀遠方”(《清高宗實錄》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丑)。可見出旗為民,又是對八旗中“敗類”的一種懲罰手段。所以在政治上,從總體來說出旗為民並無光彩可言。
乾隆二十七年,議准:“八旗漢軍從龍人員,如直省有可依靠之處,任其隨便散處,願為民者聽”(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統》)。從而突破了漢軍出旗為民政策實行二十年來,從龍人員子孫除外的防線。從龍人員子孫備受青睞,永在八旗的優越地位動搖了。從龍人員即清入關前編入八旗的人員,本是八旗構成的基礎,現在允許他們的子孫出旗為民,無異於動搖基礎,這不論對漢軍乃至八旗總體來說都是一種重大的變化。此年,又議准:“漢軍內六品以下現任官員,並一應候補、候選、告退、革退文武官員,及兵丁閑散人等,有情願改入民籍者”,呈明報部后可收入民籍(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統》)。這裡雖然有是否“情願”的一項條件,只不過是官樣文章。“一刀切”或“一風吹”的現象勢所必然。這對八旗存在之基礎不能不構成嚴重的威脅。所以,此政令推行了二十八年後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在奏准中又收回成命:“漢軍六品以下職官准其為民之例,即行停止。”但同時再次申明,“如有兵丁及閑散人等,情願改入民籍者,仍照舊例准其為民”(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統》)。亦即八旗漢軍出旗為民的進程繼續運行。
就在清廷允許八旗漢軍出旗為民之令頒布不久,允許包衣的出旗為民令,便隨之出現了。這就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頒布的“定八旗另記檔案人為民例”,及允許宗室王公等包衣出旗為民諭(《清高宗實錄》卷506,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庚子)。所謂八旗另記檔案之人,又稱“開戶家奴”,簡稱“開戶”,這些人本為八旗異姓貴族、官員以及富顯者之奴僕,后以效力年久,允許其脫離本主另立戶口,而取得正身旗人之地位者。但他們仍歸原主名下,即仍然留在原主佐領下,是被控制在八旗中具有特殊身份地位的奴僕,這是又一種包衣。而宗室王公等包衣其大部分皆為漢姓人。清廷之所以令這些開戶家奴及宗室王公等包衣出旗為民,皆因“八旗戶口日繁”,“致生計日益艱窘”,“旗人眾多,伊等不能遽得錢糧,生計未免艱窘”;而由“王公等養贍,亦恐拮据”。故令其出旗為民,以“聽從其便,俾各得為謀”,使之“均得一體謀生”(《清高宗實錄》卷506,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庚子)。如此表白分明是向世人昭示:此舉乃為諸包衣著想。但不久卻出現了有些已出旗為民的包衣,因不適應而又返回故主,重入旗籍的現象,對此乾隆帝認定這是“侵佔旗缺”之犯罪行為,而頒諭禁止並加驅逐。下令凡於限期內自首者,“不必治罪,仍令為民”。如隱瞞不報被查出者,“即從重治罪”(《清高宗實錄》卷668,乾隆二十七年閏五月乙酉)。隨即又嚴申此令,規定凡於限內“匿而不首之人”,查出者“悉發往伊犁”。並嚴令各旗都統“宜不時悉心嚴查”,以杜絕此事之發生。此後若有復行入旗者,“一經查出,除將本人從重治罪外,定將該旗都統等一併從重治罪,決不姑貸”(《清高宗實錄》卷664,乾隆二十七年六月丁酉)。對這些人簡直是棄之如敝屣,留之同贅疣,惟恐清除不凈,充分暴露了允許包衣出旗為民的真實用意:為八旗“甩包袱”。當然這還未涉及內府包衣,即上三旗包衣。然而這隻不過是時間問題。
上三旗包衣漢姓人即內府世仆,旗籍為八旗滿洲,而乾隆帝弘曆曾頒諭明確地說:“至包衣漢軍則皆系內務府世仆,向無出旗為民之例,與八旗漢軍又自有別”(《清高宗實錄》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丑)。在這裡所稱的“包衣漢軍”,並非八旗漢軍,指的乃是包衣佐領,即旗鼓佐領,隸屬於八旗滿洲的內務府包衣漢姓人,即上三旗包衣漢姓人,他們是直接為皇帝服役者,當然不能脫旗而去。但內府漢姓包衣佐領不是內府漢姓世仆之全部,內府世仆除包衣佐領外,還有如前所述的內務府管領下人、內務府會計司管轄下的庄頭旗人,即散處於各庄頭服役的屯居旗戶丁口,或稱屯居旗人。實際上它們在這股出旗為民潮中也受到了猛烈的衝擊,而被捲入了這個進程,雖然其時間有所滯后,但最終還是未能倖免,儘管程度有所不同。當然這仍然是清朝最高統治者決策所致
道光四年(1824年),道光帝針對直隸總督蔣攸銛奏請革除屯居旗人總催、領催名目一折,諭內閣曰:“向來屯居漢軍旗人事件,俱歸所隸州縣管理,應與民人一律編查,自不得任其區分抗阻。著照所請將總催、領催名目概行革除。並著內務府及八旗滿洲、漢軍都統,將包衣、外旗王包衣各項莊頭屯居旗產丁口,分晰各州縣城鄉住址,造冊移交該督,轉發各該管官存貯,以備查核,毋得視為具文”(《清宣宗實錄》卷66,道光四年三月乙亥。又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015,《八旗都統》)。這裡的“包衣、外旗王包衣各項屯居旗戶丁口”,既包括上三旗即內務府屬也包括下五旗各王公所屬下的庄頭旗人,均為包衣漢姓人。現在將其與屯居漢軍旗人,即與屯居八旗漢軍人等同對待,一律劃歸所在州縣管理,與民人一律編查,亦即出旗為民。至此,內府包衣向無出旗為民之例終被打破。這樣八旗出旗為民,就不只包括漢軍改歸民籍,也包括包衣漢姓人中之大部分改歸民籍的內容。不論出於何種原因,構成八旗的基本成份紛紛離去,對八旗總體來說不能不是一種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