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上書
清末歷史事件
公車上書,全稱公車孝廉連署上書,指康有為於清朝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率同梁啟超等公車孝廉聯名向北京的光緒皇帝上書,反對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此舉被認為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標誌,也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
公車上書
拼音:gōng che shàng shū
解釋:公車:漢代負責接待臣民上書和徵召的官署名,后也代指舉人進京應試。原指入京請願或上書言事,也特指入京會試的人上書言事。
出處:《史記·東方朔傳》:“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
《漢書·張敞傳》:“天子思敞攻效,使使者即家所在召敞。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
示例:制台原是不得已之舉,台民不甘臣日,公車上書反抗,列名的千數百人。
用法:作賓語、定語;用於政事
典出
《史記·滑稽列傳》載:漢武帝時,齊地人東方朔喜歡古代流傳下來的書籍。他廣泛地閱讀了諸子百家的書,因此學富五車,滿腹經綸。他到長安后,到公車府那裡給皇帝上書,共用了三千個木簡。公車府派兩個人一起來抬他的奏章,才勉強抬得起來。武帝花了兩個月才讀完東方朔的奏章,讀完後龍心大悅,下令任命東方朔為郎官。
典義
漢制規定,吏民上書言事均由公車令接待。上書人多有因此而被大用者。指普通人向當權者上書言事。

公車上書史物

百日維新 德宗載湉
一、下詔鼓天下之氣:即下“罪己之詔”,以鼓舞人民,同雪國恥;下“明罰之詔”,懲辦主和辱國、貪婪畏縮、作戰不力的官將,獎賞有功績的將帥疆吏;下“求才之詔”,對有才幹的人,不論其資歷與出身,都應當量才錄用。
二、遷都定天下之本:要求遷都長安,將二萬萬兩賠款改充軍費,誓不對日求和。
三、練兵強天下之勢:主張選將不以資格,購械宜用西洋,並准許南洋僑商組織軍團,以增強抗日軍事力量。
四、變法成天下之治:變法的內容包括富國、養民和教民三方面。
富國之法的內容是:國家發行鈔票,建立郵政系統,設局鑄銀幣,准許私人投資修築鐵路、創辦機器廠、設立輪船公司及開礦。
養民之法的內容是:設立農學會,採用新式農業生產方法,傳播西方農業科學知識;設立絲茶學會,整頓絲茶業;設立考工院,翻譯外國有關工業問題的著作;惠商:設立商會,傳播西方商學知識;提倡國貨和撤銷厘金及減低出口稅;移民墾荒,組織無業遊民從事生產勞動,孤寡孤獨廢疾者設院以養。
教民之法的內容是:設學堂,改革科舉,獎勵著書立說,設報館,倡孔教。
此外還建議裁汰冗官、緊縮機構、澄清吏治和改革官制。
康有為指出前三項還只是權宜應敵之策,第四項才是立國自強的根本大計。
雖然,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都先後失敗,但是維新思想從此喚醒和激勵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救亡圖存,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並拉開維新變法的序幕。“公車上書”標誌著醞釀多年的資產階級維新變法思潮已發展為愛國救亡的政治活動,對社會的影響和震動很大,康有為從此取得了維新運動的領袖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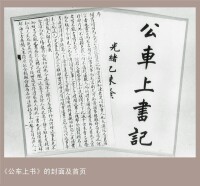
《公車上書》封面及首頁
如茅海建等不少學者則根據許多文獻認為康有為所謂的組織舉人聯名上書,事實上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公車上書實則是由當時的翁同龢、李鴻藻、汪鳴鑾等京城高官發動組織,目的是阻撓《馬關條約》的簽訂。另有研究者認為,當時清政府內部已經趨於求變,即使是保守派的徐桐和榮祿,也曾對變法做過努力。公車上書的時候,十八行省“公車”絕大多數都沒有參加康有為組織的簽名運動,他只徵集到80名廣東人的聯署。而僅僅是另一人陳景華就鼓動了一場280多人簽名的“廣東公車上書”。
關於“戊戌變法”的所有“定論”中,“公車上書”都是一個重要情節。隨手翻出《中國近代史辭典》(上海辭書82年版)說:“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后,派李鴻章赴日本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定《馬關條約》,激起全國人民強烈反對。
梁啟超徠聯合在北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多人於松筠庵會議,聯名上書光緒皇帝。上書雖被都察院拒絕,但在全國廣泛流傳,是資產階級改良思潮發展為政治運動的起點,史稱公車上書。”對於這樣一件教科書中言之鑿鑿的事情,史學家姜鳴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語對枯棋》中斷然質疑:“這說法大可懷疑。”
姜先生用自證、它證、反證的方法,論證這件事其實相當可疑。史稱“公車上書”的這件事,作者又考出翁同龢當日日記。再據宮廷檔案證明“被拒”之不存在。簽名者342人。
首先,康有為說,他起草的萬言書曾於5月2日投遞,“都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而他的弟子梁啟超則曰,該上書“言甚激切,大臣惡之,不為代奏”,意思是說都察院收下了康有為的萬言書,而不願轉呈皇上。二者明顯矛盾。事實上,都察院自4月22日起,即陸續收到了各省公車的聯名上書,“初難之,故遲遲不上”,后因文廷式彈劾該衙門“壅上聽、抑公議,上命廷寄問之”,都察院才轉變了態度,於4月28日後逐日將收到的上書及時上呈,5月2日一天就轉呈了15件條陳,其中包括各省舉人的聯名上書8件,直至5月9日還代遞了分別由江西舉人羅濟美、雲南舉人張成鐮領銜的兩分上書。如果康、梁等真的曾於5月2日至都察院上書,都察院是絕對不可能“卻不收”或“不為代奏”的。
其次,康有為說,4月15日李鴻章“電到北京”,他就先知道割地賠款的消息了;而刊印《公車上書記》的滬上未還氏卻明明說是4月17日《馬關簽約》簽訂后,電至京師,才“舉國嘩然”的。二者亦不相符。據查證,馬關議和期間,日方於4月1日提出媾和條款,於4月10日提出條約修正案,李鴻章都於當天電告了總理衙門,此後雖仍逐日向清廷彙報談判情況,卻再未逐條開列條約內容,康有為根本不可能從4月15日到京的電報中獲悉條約都有哪些具體條款。另外,中外議和事關機密,朝臣多未知曉,康有為當時不過是一名應試的舉人,何以能夠在《馬關條約》簽訂前兩天“先知消息”?假如他果真於4月15日最先了解到議和的內幕,併當即令梁啟超發動各省公車上書,為什麼直到4月22日才有廣東和湖南的舉人上書?他本人為什麼要遲至十餘日後才開始起草上朝廷的萬言書?康有為把自己獲得消息的時間提前,無非是要搶佔發動公車上書的頭功。
再次,康有為說,5月2日各省公車“有請除名者”,欲給人造成一種他們已在其所擬萬言書上簽名的錯覺;而未還氏和徐勤都說他們僅僅是要求“取回知單”,這足以證明各省公車尚未在萬言書上簽名。事實上,康有為等在簽名及人數問題上,有一個明顯的造假過程。起初,未還氏說康有為“草疏萬八千餘字,集眾千三百餘人……文既脫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諫草堂傳觀、會議”;徐勤說“先生於是集十八省公車千三百人於松筠庵,擬上一公呈”。甚至連康有為自編年譜所說,“合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開會,與名者千二百餘人”,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所載,“既而合十八省之舉人聚議於北京之松筠庵,為大連署以上書,與斯會者凡千三百餘人”,都清楚地說明是開會的人數,而非聯名上書的人數。後來,梁啟超在《康南海傳》中提及:“甲午敗后,又聯合公車千餘人上書”;在《三十自述》中曰:“南海先生聯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稱:“有為當中日戰後,糾合青年學生數千人上書言時事,所謂公車上書者是也”。不但人數直線上升,而且語意也含混不清了,很容易讓人想當然地以為這就是聯名上書的人數。康有為《汗漫舫詩集》內有“抗章伏網公車多,連名三千轂相摩”句,且附有文字說明:“東事戰敗,聯十八省舉人三千人上書”,始明確地把這三千人都說成了在萬言書上簽名者。
歷史在細節中!有時候,“證實”不厭其煩,“偽證”一條足矣!歷史就是歷史。當那些事情發生、演進的時候,有的是某種利益或價值的遵從,原是沒有什麼革命、反革命,進步、倒退,愛國、賣國,好人、壞人的界定。那些標籤是後人按彼時的遵從製作的,即使採信,也該先讀一遍那些標籤的分類手冊,看看是不是那麼回事。歷史學家姜明在書中告訴我們,簽了《馬關條約》的李鴻章是明知道要擔千古污名而自去肩承苦澀的;甚至名滿天下的變法第一烈士譚嗣同,當年也曾開出過一份向英、俄出賣蒙古、新疆、青海國土,以籌款變法的策論吶!
常識上,動機與效果,目的與手段,標籤與內里時常是兩回事。比如康有為編造的關於“公車上書”的假新聞,作者就有觀照歷史的通達之判:“在他身上,既有關心國家命運,希望變法圖強的強烈願望和奮不顧身地投入現實運動的實踐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虛榮自負、狹隘偏激的性格缺陷,這就是歷史給予中國的不成熟的改良維新運動的領袖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