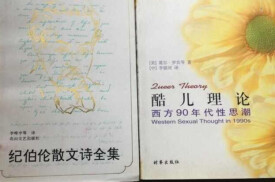酷兒理論
1990年代初在美國形成的文化理論
“酷兒”(Queer)由英文音譯而來,原是西方主流文化對同性戀的貶稱,有“怪異”之意,后被性的激進派借用來概括他們的理論,含反諷之意。酷兒理論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西方火起來的一種關於性與性別的理論。是建立在女性主義的基礎上,與父權理論中二元性別理論不同的理論。它起源於同性戀運動,但是,很快便超越了僅僅對同性戀的關注,成為為所有性少數人群“正名”的理論,進而,成為一種質疑和顛覆性與性別的兩分模式,是後現代主義在性學研究上的典型表現。
酷徠兒理論認為性別認同和性傾向不是“天然”的,而是通過社會和文化過程形成的。酷兒理論使用解構主義、后結構主義、話語分析和性別研究等手段來分析和解構性別認同、權力形式和常規。米歇爾·福柯、朱迪斯·巴特勒、伊芙·科索夫斯基·賽菊寇和邁克爾·華納等是酷兒理論的重要理論家和先驅。把酷兒理論應用到各種學科的研究被稱為酷兒研究。
新一代的酷兒理論不僅解構性,而且還分析文化的各個方面,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總是聯繫到性別和性別角色,尤其是批評其中的壓迫成分。
酷兒理論是一種1990年代初在美國形成的文化理論。它批判性地研究生理的性別決定系統、社會的性別角色和性取向。酷兒理論認為性別認同和性取向不是“天然”的,而是通過社會和文化過程形成的。酷兒理論使用解構主義、后結構主義、話語分析和性別研究等手段來分析和解構性別認同、權力形式和常規。米歇爾·福柯、朱迪斯·巴特勒、伊芙·科索夫斯基·賽菊寇和邁克爾·華納等是酷兒理論的重要理論家和先驅。把酷兒理論應用到各種學科的研究被稱為酷兒研究。
新一代的酷兒理論不僅解構性,而且還分析文化的各個方面,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總是聯繫到性別和性別角色,尤其是批評其中的壓迫成分。在這個過程中酷兒這個概念不斷被重新定義,來擴展它的含義,擴大它包含的人群。但是正是由於這個概念定義的不清晰性和任意性,它也受到各種不同團體的批評。
酷兒理論的一個中心內容是語言哲學和言語行為理論。酷兒理論這個名詞本身就是把本來貶義的酷兒這個詞使用到另外一個背景中。

LGBT
酷兒理論反對二元劃分的方法,反對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
酷兒理論不是指某種特定的理論,而是多種跨學科理論的綜合,它來自歷史、社會學、文學等多種學科。酷兒理論是一種自外於主流文化的立場:這些人和他們的理論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願意在主流文化中為自己找位置。
“酷兒”這一概念作為對一個社會群體的指稱,包括了所有在性傾向方面與主流文化和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性別規範或性規範不符的人。酷兒理論就是這些人的理論。“酷兒”這一概念指的是在文化中所有非常態(nonstraight)的表達方式。這一範疇既包括男同性戀、女同性戀和雙性戀的立場,也包括所有其他潛在的、不可歸類的非常態立場。
酷兒理論的第一個重要內容是向異性戀和同性戀的兩分結構挑戰,向社會的”常態”挑戰。所謂常態主要指的是異性戀制度和異性戀霸權,也包括那種僅僅把婚內的性關係和以生殖為目的的性行為當作正常的、符合規範的性關係和性行為的觀點。對於學術界和解放運動活躍分子來說,把自己定義為”酷兒”,就是為了向所有的常態挑戰,其批判鋒芒直指異性戀霸權。
酷兒理論的第二個重要內容是向男性和女性的兩分結構挑戰,向一切嚴格的分類挑戰,它的主要批判目標是西方占統治地位的思維方法,即兩分思維方法。有些思想家把這種兩分的思維方式稱作”兩分監獄”,認為它是壓抑人的自由選擇的囹圄。
徠第三,酷兒理論還是對傳統的同性戀文化的挑戰。酷兒理論和酷兒政治預示著一種全新的性文化,它是性的、性感的,又是頗具顛覆性的,它不僅要顛覆異性戀的霸權,而且要顛覆以往的同性戀正統觀念。酷兒理論提供了一種表達慾望的方式,它將徹底粉碎性別身份和性身份,既包括異性戀身份,也包括同性戀身份。酷兒理論向男女同性戀身份本身質疑,批評靜態的身份觀念,提出一種流動和變化的觀念。酷兒理論不把男女同性戀身份視為具有固定不變的內容的東西,而將身份視為彌散的、局部的和變化的。對於一些人來說,身份是表演性的,是由互動關係和角色變換創造出來的。
第四,酷兒理論具有重大的策略意義,它的出現造成了使所有的邊緣群體能夠聯合起來採取共同行動的態勢。酷兒理論相信民主原則在個人和個性的發展中也同樣適用。酷兒政治建立了一種政治的聯盟,它包括雙性戀者、異性者、女同性戀者和男同性戀者,以及一切拒絕占統治地位的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體制的人。酷兒政治接受所有認同這一新政治的人,不論他們過去有著何種性身份、性傾向或性活動。嚴格地說,一個人既不能成為一個同性戀者,也不能是或不是一個同性戀者。但是一個人可以使自己邊緣化,可以改變自己,可以成為一個酷兒。
最後,酷兒理論與後現代理論的關係。酷兒理論出現於後現代思想盛行之時,與後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酷兒理論的哲學背景是后結構主義和後現代理論。後現代理論是遇到最多誤解的理論,例如,它常常被人們誤解為要取消一切實際行動和現實鬥爭。因為它解構了所有的”宏大話語”,解構了所有的分類和身份,因而取消了所有現實鬥爭的可能性。其實,酷兒理論具有強大的革命性,它的最終目標是創造新的人際關係格局,創造人類新的生活方式,它的做法是向所有的傳統價值挑戰。
酷兒理論是一種具有很強顛覆性的理論。它將會徹底改造人們思考問題的方式,使所有排他的少數群體顯得狹隘,使人們獲得徹底擺脫一切傳統觀念的武器和力量。酷兒理論因此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為我們昭示了新世紀的曙光。

米歇爾·福柯
酷兒理論學家研究分析那些基於社會主流文化而創造出的各種文字記錄–從《呼嘯山莊》(WutheringHeights)到電視肥皂劇–試圖從中找到文字背後所反應出的真實的文化意義、文化差別以及不同文化群體間的關係。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基於主流文化的性行為社會規範一直在迫害,或者說壓制,那些對性有不同理解的人群,而這些人對性的不同理解要麼違反世俗化的性禁忌,要麼其行為模式與被社會普遍認同的性及性別角色不同。
酷兒理論的主張比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同志解放運動(gayLiberation)”的主張更進了一步,它除了驚世駭俗的的運動策略,亦指挑釁與桀驁不馴的實踐,以高亢的聲調肯定自我的存在價值,拒絕被主流社會所同化。同志解放運動在歐洲和美國,為性少數群體應有的生存空間而戰,而酷兒理論則主張更多權利。它的目標是從根本上動搖“正常”,“性別(sexuality)”,以及“異性戀”“同性戀”這些傳統概念,因為這些概念人為的區分了所謂的不同群體,並作為工具迫害與一夫一妻異性婚姻制度不符行為模式。簡單說,就是學者們不認為傳統的性與非“正統”的性之間有什麼不同,他們試圖摧毀舊的概念,重新界定什麼是“正常”,什麼是“性別”,什麼是“性”,什麼是“家庭”,並在此基礎上,讓人們以自由,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或性別,影響所及不僅止於同性戀者,而強調各種邊緣弱勢者的正當性。
儘管酷兒理論是在純學術研究的基礎上被提出的,但它迅速與性的少數族群運動結合到一起。作為一種對酷兒理論的回應,舊金山將“同志光榮遊行”(gayprideparade)重新命名為“gay/lesbian/bisexual/transgender(GLBT)parade”。酷兒這個詞包含的範圍最廣,但它並沒有被最大限度接受。由於在歷史上,這個詞是反同人的,是對同人的一種歧視稱呼,許多年長的男女同志拒絕接受這個詞。
反對酷兒理論的人,如RictorNorton,認為同性戀,是社會群體中的少數派,而且“同志解放運動”的早期領袖們也強調同性戀是“性”的少數族群。但越來越多的男女同人群體開始接受酷兒這個詞,這種趨勢說明在酷兒運動中,年輕的一代開始重新界定酷兒運動的範圍和發展方向,而酷兒在新一代中,不再帶有貶抑的色彩。
"酷兒理論"這一概念的發明權屬於著名女權主義者羅麗蒂斯(TeresadeLauretis),她是美國加州大學桑塔克魯斯(SantaCruz)分校的教授。酷兒理論最初見於1991年《差異》雜誌的一期"女同性戀與男同性戀的性"專號。這個理論的發明還有一個小小的故事:首先使用這一用語的羅麗蒂斯是在批評的意義上使用這一用語的。這位女同性戀女權主義者的觀點是:用酷兒理論取代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的提法有一個問題,即掩蓋了二者之間的區別,她擔心這一用語會"解構"我們自己的話語和男同性戀者的建構性沉默,這就違背了她提出的強調男女同性戀各自的特殊性的初衷。她還擔心,在酷兒理論以其自身實踐與女權主義理論相區別時,婦女問題,特別是女同性戀問題,會遭到被強制性邊緣化的命運。(Heller,36-37)
關於"酷兒理論"的發明,羅麗蒂斯說過這樣一段話:"有趣的是,魏格曼(Wiegman)談到了酷兒理論,她正確地將這一用語的發明權追溯到我,那是我為1990年(在SantaCruz組織召開的一個會議在《差異》雜誌上所編的一個專集上首先使用的。她注意到,從那時起,酷兒理論的建立'實際上將差異中性化了',這一點的確違背我創造酷兒理論這一用語的初衷,我創造這個詞的本意是希望用它來取代無差別的單一形容詞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以便將性的多重性放在它們各自的歷史、物質和語境中去理解。顯然,我是贊同魏格曼的意見的。我也贊同瓦特尼(SimonWatney)在一篇文章中的意見。他寫道:目前使用'酷兒'一詞的最方便之處在於,它是性別中立和種族中立的。他又說:酷兒表達了這樣一種立場:它歡迎和讚賞一幅更寬廣的性與社會多樣性的圖景中的差異。"(轉引自Heller,46)
酷兒理論的前身是各種與同性戀有關的理論。羅麗蒂斯認為,同性戀如今已不再被視為一種遊離於主流的固定的性形式定外的邊緣現象,不再被視為舊式病理模式所謂的正常性慾的變異,也不再被視為北美多元主義所謂的對生活方式的另一種選擇,男女同性戀已被重新定義為他們自身權利的性與文化的形式,即使它還沒有定形,還不得不依賴現存的話語形式。
著名性別和性問題專家威克斯是這樣認識酷兒、酷兒理論和酷兒政治的:從60年代以來登上歷史舞台的女權運動和同性戀運動可以被解釋為對當代世界中一種主體形成形式的反叛,是對權力的挑戰,是對個人定義方式、把個人定義為某種特殊身份、固定在某種社會地位上這種做法的挑戰。"酷兒政治"(queerpolitics)是90年代在北美及世界其他地方同性戀中產生的一種新的政治力量。新一代人自稱酷兒,而不稱女同性戀、男同性戀或雙性戀。酷兒意味著對抗--既反對同性戀的同化,也反對異性戀的壓迫。酷兒包容了所有被權力邊緣化的人們。
正像"gay"這一用語在60年代打破了舊式同性戀運動中那種自我辯護的姿態一樣,新出現的酷兒政治打破了70年代和80年代同性戀政治的少數派化和整合策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的出現正當同性戀運動成功進入主流文化之時。酷兒政治通過將許多互不相通的成分結合在一起,建造出一種新文化。他們也許是接受後現代主義的當代模式的第一批活躍分子。他們運用舊有和新式的成分建造出他們自己的身份--他們從大眾文化、有色人種社區、嬉皮士、反艾滋病活躍分子、反核運動、音樂電視、女權主義和早期同性戀解放運動中借用風格和策略。他們的新文化是奇妙的,敏銳的,無政府的,反叛的,反諷的。他們絕對認真,但是他們又想從中取樂。酷兒政治之所以是一個重要的現象,不僅因為它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而且因為它提醒人們,性政治這一整體在不斷地發明創新,從而走向存在的不同方式。(Weeks,inParkeretal,45-49)
酷兒理論有哪些主要的觀點和主張呢
長期以來,人們以異性戀為常態,以同性戀為變態。在20年前,大多數社會還認為同性戀是某種疾病(在中國,許多人至今認為同性戀是疾病),人們想給他們治病,想理解他們,或詛咒他們。這不是同性戀者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結構問題。在這種社會規範的統治之下,異性戀者憎恨同性戀者,同性戀者也因為自己的不"正常"而長期自我憎恨。同性戀恐懼症不再是個人的問題,而成為社會的問題。70年代活躍的同性戀群體打破了異性戀自然秩序的觀念。如今,異性戀的"自然性"受到了酷兒理論的挑戰,它提出了使性慾擺脫性別身份認同的可能性。
在傳統的性和性別觀念中,異性戀機制的最強有力的基礎在於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慾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一個人的生理性別就決定了他的社會性別特徵和異性戀的慾望。儘管有大量研究證實了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區別,儘管有大量違反這三者之間關係的實踐,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一直沒有受到質疑。儘管根據金賽性學報告,有50%以上的男性和30%以上的女性在一生中曾經有過同性性行為經驗,異性戀霸權仍舊認為,性慾的表達是由社會性別身份決定的,而社會性別身份又是由生理性別決定的。
在對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傾向的嚴格分類的挑戰中,巴特勒的"表演"理論有著特殊的重要性。她認為,人們的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的行為都不是來自某種固定時身份,而是像演員一樣,是一種不斷變換的表演。在巴特勒看來,沒有一種社會性別是"真正的"社會性別,是其他的表演性的重複的行為的真實基礎。社會性別也不是一種天生的性身份的表現。異性戀本身是彼人為地"天生化"、"自然化"的,用以當作人類性行為的基礎。性身份的兩分模式(彼或此,異性戀或同性戀)從遺傳上就是不穩定的,這種截然的兩分是循環定義的結果,每一方都必須以另一方為參照系。同性戀就是"非"異性戀;異性戀就是"非"同性戀。因為對"表演"理論的強調,巴特勒的思想被人稱作激進的福柯主義,它被認為是一種新的哲學行為論,其中沒有實存(being),只有行為(doing)。
對於巴特勒來說,根本不存在"恰當的"或"正確的"社會性別,即適合於某一生理性別或另一生理性別的社會性別,也根本不存在什麼生理性別的文化屬性。她認為,與其說有一種恰當的社會性別形式,不如說存在著一種"連續性的幻覺"(illusionsofcontinuity),而它正是異性戀將其自身在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慾望之間天生化和自然化的結果。在異性戀中,這一幻覺靠的是這樣一種假設,即"先有一個生理性別,它通過社會性別表現出來,然後通過性表現出來。"巴特勒反其道而行之,她認為,異性戀的性統治是生理性別的強迫性的表現。
社會性別表演在下列意義上是強迫性的,即一旦偏離社會性別規範,就會導致社會的排斥、懲罰和暴力。更不必說由這些禁忌所產生的越軌的快感(thetransgressivepleasures),它會帶來更嚴重的懲誡。這一表演帶有緊迫性和強迫性,這一點由相應的社會懲戒反映出來。為了建構異性戀的身份,異性戀要求一種社會性別的連續性表演。(Butler,19-24)
在巴特勒看來,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慾望這三者之間的聯繫建構了異性戀,而它必定是強迫性的和脆弱的。弗洛伊德所發明的"俄底浦斯情結"是對同性之愛的原初否定。俄底浦斯情結是借用古希臘神話中一位王子殺父奸母的故事來說明,所有的人都有異性戀的亂倫衝動。巴特勒認為,原初的禁忌並不是異性戀的亂倫,而是同性戀。異性間的亂倫禁忌不是原因,而是禁止同性性慾望的結果。異性亂倫禁忌所禁止的是慾望的對象,而同性戀禁忌禁止的是慾望本身。"換言之,不僅喪失了對象,而且慾望也被徹底否定,於是'我從未失去過那個人,我從未愛過那個人,我真的從未感到過那種愛'。"(Butler,69)
通過剷除異性戀以外的一切慾望,扼殺掉一切其他選擇的可能性,異性戀霸權的社會建構了一種性慾與性感的主體。社會性別的表演將身體的一部分器官性感化了,僅僅承認它們是快樂的來源。在異性戀傾向的建構過程中,人們認為只有身體的這些部位是用來製造性快感的,社會性別的表演和性活動連在一起:一個"具有女性氣質"的女人要通過陰道被插入而獲得快感,而一個"具有男性氣質"的男人則通過陰莖的插入體驗快感。易性者陷入兩難境地,他以為如果自己沒有相應的性感器官,就不可能擁有某種社會性別身份。易性者通過植入或切除某些器官以表達他或她的身份,這不是一種顛覆性的行為,而恰恰反映出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慾望已經被"天生化"和"自然化"到了何等程度。在這一過程中,人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適當的性別表演上,而不是性感的性活動上。
這一表演就是"社會性別"關於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表演。這種表演使人理解了什麼是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兩分體系。因此,一個男扮女裝的表演並不是對原初形態的模仿,用巴特勒的一句名言來說,它是"一個對模仿的模仿,是一個沒有原件的複製品"。當一個男孩想穿女孩衣服或像女孩那樣生活時,是什麼力量逼著他非要去對自己的身體下那樣的毒手呢?為什麼他不能夠穿裙子,為什麼他不能夠簡簡單單地過他想過的女孩的生活呢?這就是因為他生活在異性戀霸權的淫威之下,一種無形的暴力在規範著他該穿什麼衣服,有什麼樣的作派舉止。這是一種多麼強大又是多麼可怕的力量。它能逼著人殘害自己的肢體。我們簡直不再能把它當成一種無形的力量,它簡直是有形到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程密了。性身份和性慾的對象來劃分個人的類型就會變得毫無意義。酷兒理論傾向於接受虐戀和其他角色表演實踐,將其違反性規範的越軌行為定義為反禁制的性。把酷兒的性建立在一個不斷改變的表演的系列之上,就是對異性戀霸權的挑戰。一言以蔽之,酷兒理論造成了以性傾向或性慾為基礎的性身份概念的巨大變化,它是對於社會性別身份與性慾之間關係的嚴重挑戰。
酷兒理論的第二個重要內容是向男性和女性的兩分結構挑戰,向一切嚴格的分類挑戰;它的主要批判目標是西方占統治地位的思維方法,即兩分思維方法。有些思想家把這種兩分的思維方式稱作"兩分監獄",認為它是壓抑人的自由選擇的囹圄。
酷兒理論自覺地跨越了性別類型的尊卑順序,它的中心邏輯是解構兩分結構,即對性別身份非此即彼的劃分。這個具有反諷意味的概念"酷兒"並不指稱某一種性別類型,並不指稱某一種性別,而是指這樣一種過程:性別身份的表達能夠擺脫這樣的結構框架。酷兒並不是一個新的固定"性別主體"的標籤,而是提供了一個本體論的類型,它與現代主義話語中的兩分核心相對立。它拋開了單一的、永久的和連續性的"自我",以這樣一種自我的概念取而代之:它是表演性的,可變的,不連續的和過程性的,是由不斷的重複和不斷為它賦予新形式的行為建構而成的。
在反對性別的兩分結構(男性與女性)的問題上,巴特勒也是最有權威的理論家。跟隨福柯的理論脈絡,她向固定的女性身份的必要性提出質疑,探索一種批判各種身份分類的激進政治的可能性。她向性別的內在能力、本質或身份的概念提出質疑,認為它們不過是一種重複的實踐,通過這種反覆的實踐,"某種表象被沉澱、被凝固下來,它們就被當成某種內在本質或自然存在的表象"。"慾望的異性戀化需要'女性氣質'與'男性氣質'的對立,並且把這種對立加以制度化,把它們理解為'男性'和'女性'的本質。"(轉引自Segal,190)
在酷兒理論對各種身份分類的挑戰中,跨性別(transgender)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所謂跨性別包括異裝和易性,還包括既不異裝也不易性但是喜歡像另一個性別的人那樣生活的人。巴特勒認為,男女兩性的界限是不清楚的,生理學統計表明,世界上有6%至10%的人天生就處在兩性之間,他們的生理性別是不確定的。
兩性界線不清和有越來越模糊趨勢的表現在當今世界隨處可見,正在形成一種新的社會時尚。
在悉尼,打破兩性界線的人們舉行了一日的遊行,有成千上萬的"正常"人看到了他們,成為這一新時尚的見證人。
美國的麥可.傑克遜是貓王以後最著名的歌星,是彼得.潘以來最著名的男女同體的民間英雄。他的存在是對男女兩分觀念的威脅。
英國的辛普森(MarkSimpson)在大眾傳媒中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最新的同性戀色情明星、被動肛交者和性受虐者的詼諧的公眾形象,他的形象出現在從足球和健美到關於去毛和男褲的廣告當中,他的形象說明,男性身體--裸露的、被動的、作為性感對象而被人渴望、被人觀賞的--開始以前所未有的姿態被展露出來,他說:"傳統異性戀的觀念在這種顛倒面前已難以為繼。"(Segal,198-199)顯然,傳統的男性形象和行為規範也被他的形象顛覆了。
除易性行為外,異裝行為也是超性別潮流中一個重要的形態。異裝行為的一個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是對兩分的簡單概念的挑戰,是對男性和女性這種分類法的質疑。
超越性別角色這一社會潮流中的另一個重要形式是男角的女同性戀者和女角的男同性戀者,他們的存在使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傾向的全部定義都成了問題。這兩種人的自我社會性別認同與生理性別不符,他們的生理性別是男性或女性,而他們的社會性別認同是另一種性別。他們的性傾向也與生理性別不符:在心理上是異性戀的,而在生理上卻是同性戀的。
進入90年代,超越性別和性別角色的模糊化有愈演愈烈之勢。在某個心理診所,一個女孩向醫生描述自己所遇到的問題:她想做一個男性,而且是一個同性戀男性。也就是說,她的生理性別是女性,她的社會性別是男性,她的性傾向是同性戀。她是女人,她愛男人,但是她不想作為一個女人來愛男人,而是作為一個男人來愛男人。這就是90年代人們所面臨的新局面。
伯恩斯坦(KateBornstein)在1994年說:對於"誰是易性者"這一問題的回答完全可以是這樣的:"任何承認這一點的人。"一種更政治化的回答是:"任何人--他的社會性別表現從社會性別結構本身看來是有問題的。"(Beemynetal,35)對此,巴特勒有一句名言:每個人都是易性者。她是指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成為一個標準的典型的"男性"或"女性"(也沒有人能夠成為標準的"同性戀者"或"異性戀者")。
對於超性別現象的重視,使得雙性戀傾向在酷兒理論中擁有了特殊的重要性。酷兒理論認為,自由解放的新版本就是取消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區別;如果實現了這一變化,所有的人將不得不承認他們自己的雙性戀潛力。雙性戀之所以有著特別的重要性正是因為,雙性戀者的存在本是就對"正常人"、女同性戀者和男同性戀者的區分質疑,雙性戀的形象就是一個重要的越軌的(transgres-sive)形象。雙性戀能夠解構社會性別與性的兩分結構的原因在於:首先,因為雙性戀佔據了一個在各種身份之間曖昧不清的位置,所以它能夠昭示出所有身份之間存在的缺陷和矛盾,表明了某種身份內部的差異。其次;因為身份不定,雙性戀揭示出所有政治化的性身份的特殊性質:一方面是個人性行為和情感選擇隨時間不同的巨大不連續性;另一方面是個人政治身份的不連續性。
有些酷兒已經幽默地自稱為"彎曲的直線"(straightwithatwist)。"直線"本是英文中"正常人"或"異性戀者"的通俗說法。"彎曲的直線"這種說法充分揭示了各種分類界線之間正在變得模糊起來的新趨勢。將來,我們會有彎曲的直線,會有搞同性戀的異性戀,會有具有女性氣質的男人和具有男性氣質的女人。一位學者打趣地說:"誰知道呢,也許在明年的學術研討會上,我們會看到這樣的論文標題:女同性戀的異性戀--最後的未知領域。"(Heller,47)
英國背景的瓦特尼(Watney)和美國背景的沃納(MichaelWarner)將酷兒政治定義為偽裝神聖的道德主義的男女同性戀身份政治的對立面。瓦特尼指出,傳統的同性戀身份政治為了向人們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和熟視無睹挑戰,有一種以"同性戀社群價值"的名義壓抑在酷兒性行為中大量存在的差異的偏向,因此創造出一套關於同性戀生活方式的高度正規化的圖景。相反,酷兒文化是對這種高度正規化的同性戀價值的否定,其性多樣化的圖景囊括了從奧斯卡·王爾德到芬蘭的湯姆(TomofFinland),甚至包括麥當娜這樣的人。瓦特尼宣稱,酷兒文化是對"占統治地位的性認識論權威"的挑戰。
酷兒理論抨擊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分別,揭露和批判了這種兩分論的隱蔽的運作方式。酷兒理論家司德維克(Sedgwick)是這樣解釋的:某種文化中兩極對立的分類,比如異性戀和同性戀的劃分,實際上是處於一種不穩定和動態的關係之中。因此,僅僅爭取對同性戀的正面評價是不夠的,還要保護人們選擇做酷兒的權利。
酷兒理論向男女同性戀身份本身質疑,批評靜態的身份觀念,提出一種流動和變化的觀念酷兒理論嘗試將個人身份政治轉向意義政治(thepoliticsofsignification)。酷兒理論認為,身份是表演性的,是由互動關係和角色變換創造出來的。酷兒理論批判了傳統同性戀理論在身份問題上的排他性,揭示出在建構男女同性戀身份的同時,異性戀是如何被正規化的。
第四,酷兒理論具有重大的策略意義。酷兒理論相信民主原則在個人和個性的發展中也同樣適用;酷兒政治建立了一種政治的聯盟,它包括雙性戀者、異性者、女同性戀者和男同性戀者,以及一切拒絕占統治地位的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體制的人。酷兒政治接受所有認同這一新政治的人,不論他們過去有著何種性身份、性傾向或性活動。嚴格地說,一個人既不能成為一個同性戀者,也不能是或不是一個同性戀者。但是一個人可以使自己邊緣化,可以改變自己,可以成為一個酷兒。
"酷兒"一詞因此具有策略性的意義,而不是指稱某種具有永久性意義的身份。酷兒性(queemess)並不是一種新的身份,這一概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這些人們擁有共同的經驗,他們共同作為性越軌者(sexualoutlaws)的生活方式,而並不是一種這些人共同擁有的本質主義的身份。它出現在那些孤立的個人當中,與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價值相對立,與異性戀霸權相對立。
許多酷兒活躍分子不再將自己定義為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甚至不說自己是異性戀者,而簡簡單單單地自稱為酷兒。酷兒的性活動很難在傳統的性結構領域中加以定位,它是一些更具流動性、協商性、爭議性、創造性的選擇。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也許需要"走出來",但是酷兒身份卻是"走進去"的。酷兒還創造了他們自己的分類方式:酷兒,較酷兒,最酷兒(queer,queerer,queerest)。這種分類方式與以往的任何分類方式都不一樣。
酷兒理論的多重主體論(multiplesubjectivities)造成了在不同社會和種族的歷史背景下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不連續性(discontinuities),為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超性別者、易性者和雙性戀者的社群之間更強有力的聯合,為他們改造制度化的異性戀霸權的共同努力創造了條件。
值得提出的一點是,酷兒理論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在中國這樣的社會具有特殊的意義。由於中國文化中一向就有一種把各種事物之間的界限搞模糊而不是把它們區分清楚的傾向,由於同性戀身份政治在中國一向不發達,也由於國家和社會對於同性戀的壓制一向不像西方那麼激烈,因此,借鑒酷兒理論,中國的同性戀政治有可能跨越身份政治的階段,直接進入與所有非常態性傾向者聯合起來共同抵制異性戀霸權的階段,共同創造抵抗權力壓抑的新局面。
酷兒理論的一個根源在於1980年代的艾滋病運動。當時的同性戀組織(如同性戀解放陣線)代表的身份政治在實踐中被證明不合用。受艾滋病威脅的不僅僅是同性戀者,而且還有其他少數人群,比如自認為是異性戀的男男性接觸者以及性工作者及他們的客戶,共用針頭者及血液垂直感染等等。針對身份的艾滋病啟蒙運動無法包括這些非常不同的人群(而且往往他們自己並不把自己歸入一個人群)。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的本質主義與解構主義之間的爭論中形成了一個新的意識,即身份政治過時了,自然科學也支持解構主義的觀點,因此身份政治被擴充:假如一個人沒有本質的話,那麼典型的同性戀者也不存在。這個在原來被看作是統一的同性戀人群中出現的新發展認為,民族、社會階層或者宗教等因素同樣是一個人的身份的一部分,並且擴充一個人的身份。在一個友好的環境中(社會寬容,法律平等)這些不同的人群不必形成一個統一的群體,而可以每個人發揮自己的意志和愛好。在這種情況下同性戀人群內部不同的意識形態和間接就明顯暴露出來了,因此過去的身份定義不再滿足新的需要,新的定義必須取而代之。
米歇爾·福柯和大衛·哈珀林通過把性別、性別角色和性行為歷史化為對傳統身份政治的批評提供了另一個理由。在歷史上同性戀不總是像今天人們想象中的現象,隨不同社會條件和思想的不同對這個概念的想法也不同。在卡爾·亨利希·烏爾利克斯提出對性趨向的壓迫的理論之前同性戀者可能覺得自己不正常、在犯罪、不自然或者不舒適,但是他們沒有覺得自己被壓迫。從歷史的角度上來看現代歐洲的性別兩分和愛的概念只不過是眾多同等的和同樣原始的概念,而不是天經地義的和自然的,也就是說現代歐洲的這些理論不是完美無缺的。朱迪斯·巴特勒是最早認識到這一點並開始探討這一點的作家。她把傳統的性別角色說成是主觀的意識。她認為雖然身份是社會形成的,但是它也不是任意的,一個人不能像換衣服一樣每天戴上另一個身份。
對非酷兒同性戀組織的身份政治的批評不僅來自於理論。多重被歧視的邊緣人群(比如黑人女同性戀由於她們的膚色、性別和性趨向被三重歧視)在這些組織內也批評這個政治,這些組織的領導人往往是沒有缺陷的男性白人,現在這些多重被歧視的人群開始進入組織的中心。在女權運動中也有類似的趨向,富有的女性白人的領導地位受到挑戰,女權運動和酷兒運動內部的角色分配開始擴展。從酷兒、非身份政治的角度出發清潔工和妓女在女權運動內同樣佔有一席之地,儘管她們的形象不符合被解放的、現代婦女的形象。
一個對酷兒理論經常提出的批評是酷兒理論忽視兩個性別這個事實,或者說性別兩分的物質性。酷兒理論迴避這個問題。但是酷兒理論為什麼要基於科學的基礎上?巴特勒認為這個理論的優點正在於把“科學認識”(包括自然科學的認識)看作是一種社會認識。物質性的身體只有在社會上下文里才有意義。把人體按照性別來分類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實踐。酷兒理論正是要突出這一點,而不是陷入生物學的理論中去。
儘管如此生物學的發展和成果也可以用來支持酷兒理論:因為許多因素影響性別特徵。比如不同染色體上共19個不同的基因控制一個人的性器官形成。也就是說不只是X和Y染色體控制性器官的形成,而是第1、9、11……染色體也有作用。人類的其它許多特徵也是這樣的,有些是由於激素如雄性激素或者雌性激素來控制的。而雄性和雌性都有這些基因和激素。
在生物學和醫學中許多不同的特徵可以用來區分性別:染色體、基因、性腺、激素、內生殖器、外生殖器、教育。估計把所有這些特徵綜合到一起沒有一個人可以說是典型男性或者典型女性的。
酷兒理論批評傳統科學忽視現實中的過渡,而是把現實分解為明確的單一體,由此形成了統一的、包羅萬象的、可以解釋的世界的印象。此外酷兒理論批評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和萬能性。
莫尼克·維蒂格在她的文章中批評傳統和女權主義思想結構中的性別角色,因為它們都是從異性戀的角度出發的,它們都認為世界上有兩個明顯不同的性別。而實際上性別的界限是模糊的,因為它們是人為的。
朱迪斯·巴特勒繼續發展了這個思路,她認為突出女性身體也是這樣的一個單調的思路。但是巴特勒的理論也受到批評,因為突出的不只是女性身體,而且這也是一種歧視。
大衛·哈珀林則主要研究同性戀。伊芙·科索夫斯基·賽菊寇、特麗莎·德·勞麗蒂斯和蓋爾·魯賓則重點研究同性戀恐懼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