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國玲
霍國玲
霍國玲,“紅樓解夢”派的領軍人。

曹雪芹 / 霍國玲(校勘) / 紫軍(校勘)
轉眼到了80年代,由於當時工作不太緊張,霍國玲買了一套新出版的《紅樓夢》,在空閑時間閱讀。也許是從事多年技術工作養成的專業素質和習慣,她看《紅樓夢》特別仔細,一些看似與故事情節沒有多大關係的詩詞、謎語,她也不放過,直到搞清它的真實含義為止。結果,她很快發現了書中許多“矛盾”和“疑點”,比如《紅樓夢》第二回述說林黛玉離開江南進京,當時作者交待是6歲,可是到了京都進入榮府後,鳳姐問她幾歲,黛玉回答是13歲了。難道她在路上走了7年不成?
霍國玲把這些疑惑告訴丈夫,張暉也無法解答。看到妻子如此痴迷《紅樓夢》,熟悉中國文學史的張暉覺得自己應該幫幫她。他從外文局的圖書館借了一部《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回來,對霍國玲說:“《紅樓夢》原來叫做《石頭記》,上面都有脂硯齋的批語。帶脂批的《紅樓夢》才是真正的原著。看書就得看原著。”
聽了丈夫的話,霍國玲開始如饑似渴地研讀《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她將《紅樓夢》的正文、詩詞以及脂硯齋批語結合起來閱讀、研究,霍國玲覺得眼前豁然開朗,許多原來難以理解的矛盾和疑點紛紛水落石出。她窺到了隱藏在《紅樓夢》故事背後的歷史。 “剛開始研究《紅樓夢》,純粹是出於愛好。我五六歲時很喜歡理雜亂的線團,而且總能把它理清纏好。看到《紅樓夢》里的一些疑點,我也產生了類似理清散亂線團的衝動。曹雪芹在小說開篇說‘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我覺得自己理解了書中的一些意味。”霍國玲用平淡的語氣說。
張暉便鼓勵妻子把自己的發現寫出來。1982年2月,霍國玲寫出了第一篇紅學論文《曹雪芹生辰考》,同年提交在上海召開的第三屆全國《紅樓夢》研討會並發表,引起了紅學界的重視。這個成果後來被載入《紅樓夢鑒賞辭典》中。這篇論文的成功鼓舞了霍國玲,之後她又寫出了《反照“風月寶鑒”》和《“紅樓夢”中隱入了何人何事》等文章,奠定了“解夢”學說的立論基礎——《紅樓夢》有正(小說)、反(歷史)兩面,而且首次披露了一個重大發現:雍正皇帝系曹雪芹夥同雍正皇帝的情人竺香玉(林黛玉原型)所毒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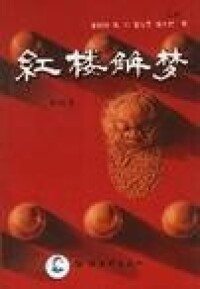
霍國玲著作
隨著研究的深入,霍國玲覺得時間越來越不夠用,於是產生了提前退休做一個專職紅學研究者的念頭。1985年她還不到50歲,提前退休便意味著要放棄工資增長、職稱晉陞等許多優厚的待遇。一些親友不理解,對此感到十分驚異。霍國玲沒有辯駁,但很認真地徵求了丈夫的意見。張暉考慮了一下,投了贊成票。為了潛心研究曹雪芹和《紅樓夢》,兩口子帶著他們的孩子移居到香山腳下的傑王府村,這裡遠離鬧市,而且據霍國玲論證,曹雪芹第二次被抄家后便在這一帶隱居、寫作。
“最開始我支持霍國玲研究紅樓夢,並不是以為這種研究可以給她和家人帶來多少名利,完全是看她做這件事情感到快樂。她快樂我也就高興了。夫妻之間就應該這樣。”張暉回憶說。

霍國玲
1989年,霍國玲和弟弟合著了《紅樓解夢》(初版),開印就是兩萬八千冊,打破了建國以來學術論著一次印數的最高記錄。
不久,他們的大姐霍力君也加入了紅學研究的行列。霍力君古典文學修養很深,對《紅樓夢》有自己的獨到見解。有一次,姐妹倆談起脂硯齋是誰的問題,霍力君認為從一些批文看,只能是曹雪芹所寫,而霍國玲舉例說許多批語出自女性之手。經過多次探討、爭論,姐妹倆終於取得一致意見:脂硯齋系曹雪芹及其妻子合用的批書筆名。據此,霍力君寫出了《解開脂硯齋之謎》一文,解決了一個紅學界多年爭論不休的問題。
1995年,霍氏三姐弟合著的《紅樓解夢》(增訂本)第一集出版。霍國玲多次受邀到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二十多所高等院校演講,受到學生們的歡迎和追捧。“紅樓解夢”學說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紅學熱潮。
正當霍氏三姐弟沉浸在成功的喜悅中時,暴風雨卻悄悄降臨了。1996年上半年,京城一些媒體和《紅樓夢學刊》開始連篇累牘批判“紅樓解夢”派,說他們的觀點“太過離奇”,是“異端邪說”,說他們研究紅學,是“沽名釣譽”,而且已經“走火入魔”。有的報刊、雜誌甚至登出了帶有人身攻擊的雜文和漫畫……面對洶湧而來的批評和攻擊,霍國玲一下子懵了。
“我原以為研究《紅樓夢》、宣傳《紅樓夢》,對弘揚民族文化是一件大好事,沒想到他們會這樣圍攻我們。你不贊成我們的觀點,可以寫文章爭論嘛。一下子把我們的觀點全盤否定,我當時確實接受不了……”事情過去了近10年,霍國玲的心情也早已平靜,但對當時的情形仍然記憶猶新。
看到妻子承受委屈和痛苦,張暉無法袖手旁觀了。他寬慰、鼓勵霍國玲:“不怕,我們和他們好好說理。現在是90年代了,文革時期那種以勢壓人、以權整人的事情再也不會發生了。”為了更好地支持妻子的事業,他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暫時放棄自己手頭的工作,全力以赴投入紅學研究。憑著長期從事對外文化交流和領袖著作的翻譯出版工作所積累的深厚的理論基礎和哲學素養,張暉於是主動承擔了對“紅樓解夢”學說的理論闡述工作和回應那些正統紅學派的“圍剿”:“《紅樓夢》既有‘假語存’,也有‘真事隱’。只承認《紅樓夢》是小說,而不承認同時也是一部史書,是不尊重事實的表現!”“誰說《紅樓夢》不是一部謎書?《紅樓解夢》作者列出了《紅樓夢》310個謎(脂硯齋稱之為“誤謬”),實際比這還要多得多……”“誰說曹雪芹‘毒殺’雍正不可能驗證?只要論證的是真實的歷史,當然就可以驗證,而且可以從各個角度去驗證……”
從那以後,張暉以紫軍的名字正式成為“紅樓解夢”派中的一員。經過他的論證,“紅樓解夢”派的學說更加系統化和理論化了,霍國玲姐弟的底氣和自信心也更足了。此後兩年,夫婦倆和姐弟手攜手,頂著各種壓力又連續出版了《紅樓解夢》第二集、第三集和單行本《紅樓圓明隱秘》,總算守住了“紅樓解夢”派的陣地。
隨著正統紅學界對“紅樓解夢”學說批判的擴大和升級,原來已經訂了《紅樓解夢》的書商和書店紛紛中斷協議,已經印好的書大多壓在了庫房裡。
“辦法總比困難多,一定能挺過去的!”張暉沉著地一次次給霍國玲打氣,分擔妻子的壓力。平時,夫妻倆省吃儉用,把稿費和微薄的退休工資積攢下來,用於償還債務和維持紅學研究所需的基本開銷。為了補貼紅學研究,弟弟霍紀平也毅然下海經商。
困難的日子一天天過去,夫婦倆患難與共,相互扶持,心貼得更近了,合作研究也越來越默契。在性格和能力上,兩個人各有所長,張暉思路敏捷,邏輯性強,打字速度也快;霍國玲心細,思維活躍,對《紅樓夢》內容、詩詞、脂批都很熟悉,善於聯想,常常有奇妙發現,所以往往是霍國玲想出一個點子,由張暉寫成文章,再由霍國玲修改,定稿。為了確立和修正某一個觀點,夫婦倆有時也因為意見不一致而發生爭論,但每次只要對方較真,另一方就趕快退讓,等到心平氣和時再討論,最後總能相互諒解,達成一致。“爭論歸爭論,我們不會因為學術爭論而傷了夫妻感情。”霍國玲說。
進入21世紀后,霍國玲夫婦和霍氏姐弟的紅學研究迎來了又一個春天,他們先後出版了《紅樓解夢》第四集和第五集。到現在已論證了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問題:《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所隱寫的就是圓明園;寧國府隱寫清皇宮;原“恭王府”前身為曹雪芹在京城內的故居;原“燕京大學”前身系曹雪芹在西郊的故居;香山正白旗村39號院是曹雪芹家第二次被抄后的居住地;黛玉原型竺香玉葬於陶然亭公園……
“現在,紅學研究已經成了我們兩口子生活的一部分。”霍國玲告訴筆者,他們的生活平淡而又充實,每天6點多鐘起床,天氣好就去爬香山,或者在院子里鍛煉鍛煉,白天其他活動很少,一般就在家裡看看書,寫寫文章,晚上10點多準時睡覺。家務分工是霍國玲負責做飯,張暉負責打掃衛生。2005年9月張暉因腰椎柱狹窄動了手術,之後所有家務事都由霍國玲包了下來。他們的孩子在城裡上班,只能在節假日回家看看父母。
到目前為止,霍國玲夫婦和姐弟寫作並出版了6部9冊著作,包括67篇論文,共計200多萬字的紅學著作。他們最新的紅學研究成果——《紅樓解夢》第六集、《脂硯齋全評石頭》和《反讀紅樓夢》也將在2006年初出版。霍國玲淡然地說:“紅學研究不但沒有給我們帶來什麼名利,還給我們一家人帶來了一些煩惱甚至困難,但我們還是從中得到了許多快樂,所以我們決不會放棄,而且只要有讀者願意看,我們還會繼續把研究成果公之於眾。我覺得我們有這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