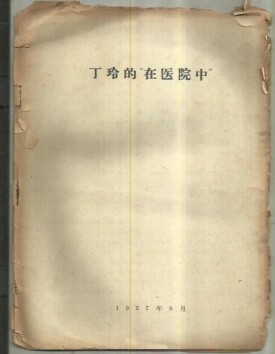在醫院中
在醫院中
《在醫院中》是以抗日戰爭時期“醫院”為題材的小說。《在醫院中》初次發表於《穀雨》,題目為《在醫院中時》。作品中有一個女大夫的形象,她正直、善良、有責任心。作家主體的思想、經歷、體驗必然會影響到其作品中的人物,構成人物形象的獨特性。正是人物獨特的“這一個”才具有更為感人的藝術力量,也體現出了作家獨特的思想感情和藝術表現手法。
丁玲的《在醫院中》是以抗日戰爭時期“醫院”為題材的小說,作品都塑造了一個女大夫的形象——陸萍。她正直、善良、有責任心。文學是時代社會的反映,同時代作品中同類人物形象帶有一定的普遍性也是合理的,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人物的獨特性。作者主體的經歷、思想、情感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作品中人物的獨特性。
《在醫院中》初次發表於《穀雨》 ,題目為《在醫院中時》。1942年發表於重慶《文藝陣地》時更名為《在醫院中》。小說因揭示了初到延安的知識青年與環境的矛盾和衝突而受到人們的關注,小說也因此頗受爭議。在1958年《文藝報》的“再批判”中它被當作“奇文”和“毒草”重新刊登出來,張光年的批評文章《莎菲女士在延安——評丁玲的〈在醫院中〉》被置於該篇小說前面隆重推出。1980年代,人們為丁玲翻案,又提起了這篇小說(註:嚴家炎:《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樁舊案——重評丁玲小說〈在醫院中〉》,《鐘山》1981年第1期。)。

在醫院中丁玲
小說中的主人公陸萍是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兒,但我們若細細品味卻能覺察到,就對人和事的感知和洞察力而言,陸萍不太像是一個20歲的不諳世事的少女。從上海的產科學校畢業后,她在傷病醫院服務了一段時間,後來到延安進入抗大學習。抗大畢業后,她本想從事政治工作,但卻被分進了醫院作“產婆”。她對初次見面的人在短時間內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判斷和把握:指導員黃守榮,“一副八路軍里青年隊隊長的神氣,很謹慎,很愛說話,衣服穿得整齊,表現一股很樸直很幼稚的熱情,有點羞澀,卻又企圖裝得大方”;產科主任王梭華給了她很好的印象,可是她卻看穿了他的虛偽:“這是一個有紳士風度的中年男子,……時時保持住一種事務上的心滿意足。雖說她看得出他只不過是一種資產階級所慣有的虛偽的應付,然而卻有精神,對工作熱情”。陸萍知道如何對待他,如何與他相處:“她並不喜歡這種人,也不需要這種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上卻樂意和這種人合作”。由此可以看出陸萍具有一種不被人的表象所迷惑而直取其本質的洞察力,並且能把個人的喜好和工作上的合作分開來對待。尤其是她對幾個女性的犀利觀察,更讓讀者難以相信陸萍只有“二十歲”,她喜歡用刻薄的語言來描畫周圍的女性。對抗大同學張芳子她批評得更加不留情面,甚至可以稱得上是惡毒了:“這是一個最會糊糊塗塗地懶惰地打發去每一個日子的人。她有著很溫柔的性格,不管伸來什麼樣的臂膀,她都不忍心拒絕,可是她卻很少朋友。這並不由於她有什麼孤僻的性格,只不過因為她是一個沒有骨頭的人,爛棉花似的沒有彈性,不能把別人的興趣絆住”。陸萍固然洞見了張芳子內心的軟弱,但用語卻過於狠毒了,張芳子只不過是一個溫柔的沒有主見的女孩子罷了。陸萍是一個很自信的人,她對周圍的女性似乎都很難瞧得上:她覺得產科主任王梭華的太太“總用著白種人看有色人種的眼光來看一切,像一個受懲的仙子下臨凡世,又顯得慈悲,又顯得委屈”;醫院裡自我感覺良好的兩名女看護在陸萍眼裡卻醜陋無比,“這兩位夫人,尤其是那位已經二十六七歲的總務處長的夫人擺著十足的架子,穿著自製的中山裝,在稀疏的黃髮上束上一根處女帶,自以為漂亮驕傲地凸出肚皮在院子中擺來擺去”。作者說“她(陸萍)有足夠的熱情和很少的世故”,然而陸萍對周圍人洞悉得如此透闢,哪能稱得上是“少世故”呢!在小說的另一處,她評價陸萍“不會浪費她的時間,和沒有報酬的感情”。這句話也分明體現了陸萍的理性和世故。所以一開始,丁玲便向讀者展現了一個頗為矛盾的陸萍。
陸萍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丁玲的生活歷程有很大關係。《夢珂》發表時,丁玲還是初為人妻、不諳世事的25歲少婦,但後來的一段時間裡,她相繼經歷了丈夫被國民黨槍殺、自己被國民黨囚禁等諸多磨難。到延安之後艱苦的戰爭環境又把她磨礪成了一個成熟的中年女性。《在醫院中》假借一個初來乍到的少女的眼光來敘述整個故事,實際上則可說是丁玲本人對延安認識深化之後,提煉升華自己生活感受的作品。寫作《在醫院中》時,丁玲36歲,她的生活體驗更為豐富了,她對人和事的洞察力也變得更加敏銳了,三年多的延安生活,又使她對延安的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細緻的了解。儘管丁玲作為一個成熟較早的女作家,在早期也塑造過諸如莎菲女士這樣複雜的人物形象,但莎菲女士的複雜性基本上體現在年輕女子對男性所玩弄的種種技巧上,而陸萍這一形象因滲透了中年丁玲的生活體驗而較莎菲顯得更有深度。作為延安文化界的核心人物,她一度任陝甘寧邊區文藝協會副主任,這也有助於她深入到延安生活的肌理中去深層地了解延安。知識分子敏感多思的天性也決定了她比平常人更易於發現生活中的矛盾與問題。《在醫院中》丁玲藉助陸萍這一青年知識分子的視角揭示了邊區醫院管理的不科學、技術的落後、醫護人員的懶惰散漫。1941年後丁玲對延安的了解就更加深入了,她發現了很多問題,相繼寫下了《什麼樣的問題在文藝小組中》和《三八節有感》。
同時,《在醫院中》也反映出了丁玲到延安后感情的變化過程。初到延安,她的心情是異常愉快的。1937年7月1日她寫下了《七月的延安》來歌頌對延安的喜愛崇敬之情:“七月的延安太好了。/青春的心燃燒著/要把全中國化成像一個延安。”,丁玲作為一個30年代就已成名的女作家,到延安后她一直受到重視和重用,這是她心情愉快的原因之一。她剛到保安,黨中央就派她隨總政治部到前方。她還當選為“中國文藝協會”的主任。次年2月,她出任中央警備團政治部副主任。8月15日她組織“西北戰地服務團”出發到前線,1938年7月才返回延安。丁玲帶著興奮喜悅的心情投入到迥異於“莎菲女士”的新生活之中。1937年8月1日在日記中她這樣寫道:“我以最大的熱情去迎接這新的生活。”但丁玲初到延安的喜悅之情並沒有完全湮沒一個女作家應有的敏感。儘管1939年她在《我怎樣來陝北的》說過“感情因為工作的關係,變得很粗……”,但我們注意到丁玲把她對生活的細膩而獨到的觀察放在小說中來表現了,小說成為她表達自己微妙感情的一個最好方式。短篇小說《東村事件》寫於1937年5、6月間,描寫發生在宗法制控制下的農村裡的一場糾紛。農民陳得祿的媳婦被地主趙老爺搶去,他因男人的尊嚴被侮辱而壯著膽子衝到趙老爺家,但一見趙老爺,他立刻就蔫了。丁玲充分發掘了陳得祿性格的複雜性,並將之刻畫得絲絲入扣。短篇小說《秋收的一天》寫於1939年丁玲在延安馬列學院的短暫小憩中,它沒有什麼情節,像一篇散文,講述了一個知識女性在集體生產勞動中的種種細膩感受。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敏感而細膩的丁玲。這篇小說的風格很類似於她早期的一些小說,全篇幾乎都是同性之間的瑣屑故事與她們感情上的互通與理解。最巧合的是裡面的女主人公叫“薇底”,與她早期的一篇小說《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1928)的女主人公的名字相同,這似乎暗含著丁玲對過去心情的留戀和對新生活的游移。在《秋收的一天》中“薇底”的心情是異常矛盾的,她一面肯定地評價自己的生活狀態:“自從來到這裡,精神上得到解放,學習工作都能由我發展,我不必怕什麼人,敢說敢為,集體的生活於我很相宜。我雖說渺小,卻感到我的生存。”一面卻又對集體生活的熱鬧和別人的歡愉保持著懷疑和距離,“‘為什麼大家那麼興奮而愉快呢?’她一面懷疑地問著,那些動人的場景和演說詞,便像銀幕一般地連續映了出來”。“薇底”不像別的同伴在勞動后就能甜甜地睡去,她常在熄燈之後思考一些問題,因而“一到四五點鐘就睡不著了”。由此我們隱約感覺到了“薇底”的困惑——如何處理個人與集體之間的矛盾。丁玲延續著通過小說來表達其異於“集體”的敏銳感受和獨到觀察這樣一個思路,在1940年寫出了《在醫院中》。《在醫院中》中丁玲從一個青年知識分子的視角看到了自己與周圍環境的格格不入。
陸萍對環境的不適集中體現在小說的環境描寫上。《在醫院中》的環境描寫一直受到批評家的特別關注,燎熒在文中說:“作者在小說裡面的環境的安排,便是不正確的。作者為了表現她的人物,她是過分使這個醫院黑暗起來。”(註:《丁玲全集·在醫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頁。張光年為了駁斥丁玲對醫院環境的描寫,講述了自己在邊區醫院的親身體驗:牆壁是多麼的潔白、醫護人員是多麼的熱情等等。)這些描寫可用一個“冷”字來概括。一個是自然環境之冷,另一個是人事之冷。“人們都回到他們的家,那惟一的藏身的窯洞里去。”(註:《丁玲全集·在醫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頁。)用“惟一”、“藏身”來形容人們最熟悉的居住地——窯洞,包含了對艱苦環境的幾多無奈!還有她初次踏進窯洞,那種不舒服的感覺:“當她一置身在空闊的窯中時,便感覺到在身體的四周,有一種怕人的冷氣襲來,薄弱的,黃昏的陽光照在那黑的土牆上,浮著一層慘凄的寂寞的光,人就像處在一個幽暗的,卻是半透明的那末一個世界,與現世脫離了似的”(同上,第235頁)。同為女性的陳學昭對窯洞則有迥異於陸萍的感覺:“這是一個小小的土窯洞,裡面用石灰粉了的,也還潔凈,面南。那些住慣了西式房子的人,他們一定不能想象住窯洞的樂趣。那天我住窯洞實在是太快樂了……”,在陳學昭看來,窯洞冬暖夏涼,而且“光線也還充足,在窗口,只覺得光線太強烈”(註: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頁。)。窯洞在延安是人們最普遍的居住場所,但它對陸萍來說卻如此冷漠,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陸萍的落寞沮喪心情是有關的。正是由於陸萍的這種落寞沮喪心情,在陸萍的眼中,窯洞里的舊的白木桌和凳子“也似乎是從四面搜羅來的殘廢者”(同上,第236頁);“院子里的一個糞堆和一個草堆連接起來了,沒有插足的地方”(同上)。老鼠也出來搗亂了,“被子老裹不嚴,燈因為沒有油只剩一點點凄慘的光。老鼠出來了,先是在對面床底下,後來竟跳到她的被子上來了”(同上,第238頁)。可以想見,這裡物質條件的落後是出乎從上海來的知識青年的想象的。此外,作者還把故事的背景選擇在冬季,自然更增加了一層蕭瑟冷清的氣氛。除過自然環境之冷,還有人事之冷,這是比自然環境之冷更讓人難以忍受的。這種冷從一開始就布下了陣腳,陸萍以為李科長“匆匆地走了”大約是找斧子幫她修理床鋪去了,但實際上,他並沒有回來,她只好在地上熬過了過一夜。她碰到兩個在鍘草的女人,和氣地問:“老鄉!吃了沒有?”但卻受到了她們的嘲弄:“呵!又是來養娃娃的呵!”對她這樣一個未婚的二十歲的女性簡直就是侮辱。因此陸萍感覺“如同吃了一個蒼蠅似的心裡湧起了欲吐的嫌厭”。化驗室的林莎見到陸萍,眼睛只顯出一種不屑的神氣:“哼!什麼地方來的這產婆,看那寒酸樣子!”並沒有“同志”般的親切。醫院裡的病人,漸漸地對陸萍的付出也並不在乎了,她拿著掃帚把院子打掃乾淨,但“不一會兒,她們又把院子弄成原來的樣子了。誰也不會感覺到有什麼抱歉”(同上,第242頁)。她成了醫院中“小小的怪人”(註:《丁玲全集·在醫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頁。),不被人理解。1942年燎熒的批評文章已經隱隱約約地指出了陸萍與周圍環境衝突的合理性,“一個熱情但不知世故的青年,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矛盾和糾紛是不可免的吧?”(註:燎熒:《“人……在艱苦中成長”——評丁玲同志的〈在醫院中時〉》,《解放日報》1942年6月10日。)小說的最後,陸萍與環境得到了和解,“她所要求再去學習的事也被准許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頁。)。與小說前面的環境描寫相比,這個結局和小說最後的那句話就顯得有些蒼白無力了,但它們似乎反映了身處革命環境的丁玲為融入到集體生活、為滿足黨對自己的要求而作的內心的掙扎,以及她在孤獨失望中願與黨和集體保持一致的複雜心理。
1938年後丁玲的生活發生了一些變故,她的心情也隨之黯淡下來了。丁玲從西北戰地服務團回到延安馬列學院之後,遭遇到了被孤立的尷尬。1938年上半年,康生擔任中央黨校校長,公開在黨校大會上宣布,丁玲“不是我們的同志”,黨校不接受丁玲前來學習。康生為什麼這樣說一度春風得意的丁玲?我們可以推測,負責審查幹部的康生對丁玲被國民黨逮捕以及和馮達同居這一段歷史抱有懷疑和蔑視的態度,因此才把丁玲孤立於“同志”之外。1940年丁玲的舊傷疤又被揭開了。在這一年,新一輪“審干”已在公開狀態下全面推開。中共還把“審干”與“除奸”聯繫起來,劃定了大量的“嫌疑分子”。丁玲因為自己的那一段歷史又受到了衝擊。雖然這次審干不像1943年整風時那樣猛烈,但可以想象,丁玲,作為一個女性,由於自己在被捕期間與馮達同居這樣的私生活而受到審查時的尷尬與痛楚。這些使丁玲感受到了延安生活的另一面,它不再是喜悅的歡歌,而是革命的嚴酷。寫於1940年的《我在霞村的時候》流露出了丁玲精神上的痛苦。《我在霞村的時候》中村子里的人們對失去貞操的貞貞的冷漠和嘲笑,是“我”所鄙夷不屑的:他們的麻木、自私、冷漠使“我”失望之極。可以猜想,丁玲通過貞貞這一形象在努力傳達出自己的清白和對黨的忠誠,而對村子里敘述者“我”的孤立(因“我”對貞貞的熱情與讚賞)也暗示出了丁玲自己此時的落寞情緒。這篇小說透露出了丁玲由對環境和人事的不滿而產生的失落和孤獨的情緒,這種情緒成為她寫作《在醫院中》的背景。
為何把陸萍寫成二十歲?還有一個原因值得分析。回到當時具體的歷史語境里,“青年”在延安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抗戰期間,更多的青年知識分子奔赴延安——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抗大里都是青年知識分子,青年問題,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問題,更是延安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問題。陝甘寧邊區於1939年把5月4日定為中國青年節(註:當時國民黨迫於壓力,同意了這一規定。後來國民黨又改定以三月二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廣州黃花崗革命烈士紀念日)為青年的節日。但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則繼續以五月四日為青年的節日。),此後每年都要舉行大型的紀念活動。中共中央委員會還出版了一份關於青年工作的雜誌《中國青年》。在延安特殊的語境里,丁玲把陸萍寫成“二十歲”,會使她更具代表性,會使得陸萍這一人物得到更多讀者的共鳴。丁玲之所以塑造陸萍這一人物與青年特有的精神氣質——“青年是可貴,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著生命底新銳的力。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到的骯髒,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地說”(註:朱鴻召編選:《王實味文存》,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28-129頁。)有很大關係。丁玲把自己中年的人生體驗灌注在青年陸萍身上,使得陸萍這一人物對延安的青年更具魅力和感召力。陸萍的遭遇和經歷是來到延安的許許多多知識青年的遭遇和經歷,陸萍也就成為來到延安的許許多多知識青年的縮影:他們往往自視很高,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張聞天曾分析過青年知識分子的優缺點,優點是他們有對崇高理想的追求,不滿意黑暗的現實社會;反對迷信、黑暗、無知、愚昧,愛好光明真理。缺點是鬥爭的堅定性、堅持性不夠,了解問題的具體性與透徹性不夠;對群眾的接近了解不夠(註:《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中國文化》第1期第2卷。)。因此對黨來說青年知識分子如何改變自己以適應延安的環境和革命的需要是當時延安一個核心問題(註:謝挺宇:《第二代》,《延安文藝叢書·散文卷》,湖南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文章標註的時間是1941年6月26日。發表比《在醫院中》還要早幾個月。裡面的女主人公史瑋,也有著與陸萍一樣的藝術愛好,割捨掉音樂在她內心是非常痛苦的,“自己會去做看護什麼的,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的,沮喪地回到窯洞,翻了翻扭著蝌蚪般的音符的五線譜,看看一些這幾年苦心畫下來的速寫,像有東西在心裡面扎進去似的,她痛楚地感覺到今後是要跟這些心愛的東西分離了,眼淚就懊惱地流出來了……”。),1939年毛澤東曾提出了“知識分子工農群眾化”的口號(註:《毛澤東選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2),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頁。)。但丁玲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從自己的體驗出發看到了知識分子與延安的環境的衝突的某種合理性。所以陸萍在延安的青年中產生了很大反響,小說的最後一句話:“人是要經過千磨百鍊而不消溶才能真正有用。人是在艱苦中成長。”據說在延安被很多青年當作語錄和座右銘廣泛傳抄。
《在醫院中》的發表與當時興起的“暴露文學”的潮流有關,1941年在延安形成了“暴露文學”的熱潮。延安的許多文人作家發表了大量揭露、諷刺延安黑暗面的作品。丁玲塑造了陸萍這一人物形象,通過她——一個初來乍到的女孩來傳達出了丁玲自己在延安的生活感受。在延安特殊敏感的政治環境里,《在醫院中》的小說的虛構性既可以使丁玲傳遞出自己內心的微妙感受,又可以避免讀者和敏感的批評家把陸萍與丁玲本人等同起來。另一方面,丁玲從自己的體驗出發觸及了延安的青年所遇到的普遍問題,揭示出了陸萍與環境的衝突的某種合理性(註:我們注意到延安整風時,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受到了批判。對陸萍和環境的矛盾,當時還沒有把它上綱上線。看來,當時人們對此持寬容態度。)。隨著整風的開展,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嚴峻了,丁玲本人和陸萍這一形象所代表的青年知識分子都必須改變自己以適應革命的需要。《講話》以後,延安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開始了“改造自己”和“改造藝術”的漫長過程。
丁玲的《在醫院中》,陸萍的遭遇表徵著民族國家解放后,作為新政權雛形與象徵的解放區,法律、條文上的性別平等並未深入社會機制和婦女的思想意識與日常生活;女性整體上處於精神匱乏、價值缺失和無法獲得類的存在的生存狀態。陸萍的悲劇揭示了將女性的解放等同或捆綁於民族國家解放的狹隘和困境,同時也將民族國家解放後婦女解放之路將走向何處的問題揭示了出來。啟示社會應深入社會機制和思想文化的肌理,在社會生活和個體精神層面確立女性的主體存在,尊重女性個體生命的價值,發展女性獨立個性和豐富人性,實現女性自由、自覺的類本質。而這正可以為新的歷史條件下,女性的進一步解放提供借鑒。
《在醫院中》寫於一九四零年,主人公陸萍是個性格複雜的人物形象。她仍是丁玲筆下經常出現的小資產階級青年女性,但她和夢珂、莎菲顯然不同,她曾在“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後到傷兵醫院熱情服務,後來經過長途流浪,“受了很多的苦,輾轉的跑到了延安”。《在醫院中》表現了來到延安的小資產階級青年女性的生活和思想。
來到延安的陸萍,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仍然存在。她想按照自己的喜好選擇工作,對黨組織的安排“聲辯過”、“甚至她流淚了”,最終的服從不是源自思想認識真正的轉變,而是在黨的需要的“鐵箍”套在頭上不能違抗的想法的支配下,“她只有去”,甚至還討價還價,“說好只去做一年”。很多評論者都對陸萍“打掃了心情,用愉快的調子去迎接該到來的生活”給以褒揚,但細讀文本,我們就會發現她這種愉快的心情不是因為認識到即將開始的新生活的意義,而是因為想到了伊里基的“不愉快只是生活的恥辱”這句話。在去醫院的途中,她還懷著“安靜的,清潔的,有條理的獨居的生活的夢想” 。
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使得來到延安的陸萍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她內心的痛苦、猶疑、動搖遠非她“打掃了心情,用愉快的調子去迎接該到來的生活”的努力所能克服的。陸萍與周圍的人關係並不融洽,甚至充滿敵視。她和化驗室的林莎之間互相充滿敵意,覺得同學張芳子“庸俗”“平板”,覺得產科室的看護——張醫生的老婆和一個總務處長的老婆,無論衣著打扮,還是工作方面,都是令人生厭的,甚至對待病人也是“剛開始”時感到一些“興奮和安慰”,“可是日子長了,天天是這樣”,她也感到厭倦。如何看待這種矛盾?僅僅是因為陸萍自身的原因嗎?當然不是。
我們先看一下陸萍周圍的環境是怎樣的。院長是“種田的出身”,“對醫務完全是外行。他以一種對女同志並不須要尊敬和客氣的態度接見陸萍。像看一張買草料的收據那樣懶洋洋的神氣讀了她的介紹信。”醫院的指導員把“醫生太少,而且幾個負責些的都是外邊剛來的,不好對付”作為醫院的困難之一。許多護士“一共學了三個月看護知識,可以認幾十個字,記得幾個中國藥名。她們對看護工作既沒有興趣,也沒有認識”,“她們毫無服務的精神,又懶又臟,只有時對於鞋襪的縫補,衣服的漿洗才表示無限的興趣” , “做勤務工作的看護沒有受過教育,什麼東西都塞在屋角里,洗衣員幾天不來,院子里四處都看得見有用過的棉花和紗布,養育著幾個不死的蒼蠅”,產婦們也“不愛乾淨”……這就是陸萍周圍的人,他們不是壞人,而是自己的同志,他們也沒有什麼毛病和惡行。然而由這些人物構成的環境,卻是陰沉的、令人窒息的。“世界上什麼是最可怕的呢,決不是艱難險阻,決不是洪水猛獸,也絕不是荒涼寂寞。而難於忍耐的卻是陰沉和絮聒”。在這種環境中,陸萍是怎麼辦的呢?她沒有熱情衰退、隨波逐流,也沒有獨善其身、不聞不問,而是積極熱情地推動醫院的改革。“她陳述著,辯論著,傾吐著她成天所看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去參加一些會議,提出她在頭天夜晚草擬的一些意見書”;“她照顧著那些產婦,那些嬰兒,為著她們一點點的需要,去同管理員、總務處、秘書處甚至院長去爭執。在寒風裡,束緊了一件短棉衣,從這個山頭跑到那個山頭,臉都凍腫了。腳後跟常常裂口。她從沒有埋怨過”。可以說,陸萍是這個醫院中的改革家,而這也是作者極力推崇的,“人的偉大也不只是能乘風而起,青雲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橫逆之來,而是能在陰霾的氣壓下,打開局面,指示光明”。
從實質上來說,陸萍與周圍的人和環境的對立是一種高度的革命責任感和現代科學文化要求與矇昧無知、褊狹保守、自私苟安、自由散漫的小生產者的思想習氣的尖銳對立。黃子平認為:“陸萍等人的努力,實在是在要求‘完善’這個環境的‘現代性’,她們的意見其實經常被承認是‘好的’、‘合理的’,卻又顯然無法經由這個環境本身的‘組織途徑’來實行。她們是這個有機地組織起來的單位中的‘異質’,從所謂‘社會衛生學’的角度看,她們正是外來的‘不潔之物’。”作品不僅在於揭示了這種對立的存在和實質,還進一步寫出了這種思想習氣的頑固性及與之作鬥爭的困難性。無論是醫院的領導,還是看護、病人,或者是周圍的老百姓,都瀰漫著這種思想習氣。“她該同誰鬥爭呢?同所有人嗎?要是她不同他們鬥爭,便應該讓開,便不應該在這裡使人感到麻煩,那麼,她該到什麼地方去?”這種小生產者的思想習氣和當時物力、財力的匱乏結合在一起,使知識青年陸萍憤怒而又束手無策,她顯然不是對手,她太稚嫩了,感情太脆弱,再加上自身小資產階級的東西還比較多,不懂得聯繫群眾。作者借一個老戰士之口指出了陸萍自身的問題及必然失敗的結果,“你的知識比他們(院長和指導員)強,你比他們更能負責,可是油鹽柴米,全是事務,你能做么?……你是一個好人……可是你沒有策略……”“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幾個人身上,否則你會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種劇烈的自我的鬥爭環境里,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這也就難怪陸萍的躊躇和動搖了,“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於革命有什麼用?”
《在醫院中》暴露了“離延安四十里地的一個剛開辦的醫院”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而這所醫院有可能取當時的拐峁醫院為背景①。丁玲於一九三六年滿懷豪情地奔赴革命聖地,主動要求上前線、當紅軍,擔任過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職務。為什麼她在其中生活了四年之後,對一心嚮往的革命聖地展開了批判呢?是她對在延安的生活不滿意嗎?顯然不是。在寫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風雨中憶蕭紅》中,丁玲寫道:“延安雖不夠作為一個寫作的百年長計指出,然在抗戰中,的確可以使一個人少顧慮於日常瑣碎,而策劃於較遠大的。並且這裡有一種朝氣,或者會使她能更健康些。”那麼怎樣理解她對現實生活的批判呢?說到底,是源自她對革命的忠誠,因為她清醒地認識到:“即使在進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這裡更需要督促、監視,中國的幾千年來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惡習,是不容易剷除的,而所謂進步的地方,又非從天而降,它於中國的舊社會是互連接著的。”可見,她不是對革命提出質疑,而是期待革命陣營更加純潔。為什麼要選取一個入黨不久、仍有不少小資產階級感情的革命知識青年陸萍作主人公呢?通過她的所見所想來批判現實是否有不妥之處?我想,陸萍的思想歷程是丁玲及其他一些進入解放區的左翼文藝家的真實寫照。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後期,許多左翼文藝家帶著“回家”的嚮往湧向解放區,丁玲在出席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歡迎晚會上激動地說,這是她“一生中最幸福最光榮的時刻”,她“就像從遠方回到家裡的一個孩子,在向父親、母親那麼親昵的喋喋不休的饒舌”。他們對革命的嚮往和熱情是帶有浪漫蒂克情調的,這種浪漫蒂克的熱情在嚴酷的革命現實面前被擊得粉碎,就像魯迅早在一九三零年就指出過,“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確是麻煩的事。所以,對於革命抱著浪漫蒂克的幻想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在醫院中》表現出的批判意識體現了作家的主體自覺,而通過陸萍這一形象,不僅實現了對社會現實的批判,也實現了作者深刻的自省和自我批判。正是因為在這個人物身上凝結了作者本人的感受、體驗和真誠,她才是感人的、真實的,也是一個成功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