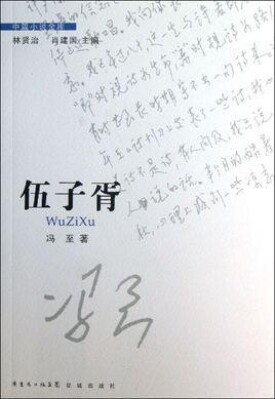共找到4條詞條名為伍子胥的結果 展開
- 春秋末期吳國大夫
- 馮至所著小說
- 褚兢所著歷史書籍
- 《白馬曾騎踏海潮》中的角色
伍子胥
馮至所著小說
《伍子胥》是1985年四川文藝出版社,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馮至。
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聯大任教的馮至,住在昆明城郊的鄉間農舍里,課餘過著寧靜的書齋生活。抗戰爆發以來在從沿海到內地的顛沛流離之後,終於安定下來了,但一路上自己祖國大地上的痛苦、呻吟,深深刺激了他,早已走學者之路的馮至,情不自禁地又一次燃起了創作的激情。1941年,他寫就了著名的詩集《十四行集》;1942年又開始寫作《伍子胥》,實現多年前的夙願。
馮至告訴我們他的審美觀:正如物體的拋落,這中間有剎那的停留與隕落,人生正是“這停留與隕落結成的連鎖”,“因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為了愛或是為了恨,不管為了生或是為了死,都無異於這樣的一個拋擲:在停留中有堅持,在隕落中有克服。”馮至將這樣的思想用來指導創作,出現在他筆下和讀者眼前的古代歷史人物伍子胥的形象便產生了。於是,我們看到一個年輕人,父兄被殺,自己也被迫流浪,胸懷復仇大願,一路漂泊,遇到許多人事,對他的復仇有不同的影響,引起他不同的感覺和體驗。這是一個復仇的抉擇在一些列的情境中經受考驗,不斷進行矯正性選擇的主題。古人伍子胥被馮至描繪成闡釋“選擇”哲學命題的“存在主義”式的英雄。
“我這裡寫的這個故事裡的主人公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離開熟識的家鄉,投入一個遼遠的、生疏的國土,從城父到吳市,中間有許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堅持,有的使他克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段。”苦難本身固然令一般人同情,但這顯然不是作者馮至的興趣所在。所謂“最有意義的一段”“美的生活”,在我們看來,絕不是可憐的流浪者的感受,倒是作家自己的創作興趣。
這部小說共分九章,開始的第一章“城父”,作者便為主人公設置了一個大的存在主義的“抉擇”的境遇:父親被囚,楚王設下圈套,兄弟倆是去還是不去?哥哥主動選擇去死,為了可見到父親,更為了一個存在主義式的目的:作為一個大的力量,一個沉重的負擔落在弟弟伍子胥的肩上,加強伍子胥“生存下來並且復仇”的抉擇的分量。“存在先於本質”,經過這樣的存在抉擇,一個本質為“復仇者”的形象便誕生了。這正象一個註定被拋落的物體,作者首先得完成拋出手心的工作。接下來才是更重要的,存在主義式的美學關注是接下來的“這停留與隕落結成的連鎖”。主人公伍子胥的身影被按時間順序置放在八個場景之中,這正好構成了文章的後面八章。而存在主義式的英雄形象正是必須在這一次又一次選擇的情境中逐步完成。
“首先是人存在、露面、出場,後來才說明自身。……世間並無人類本性,因為世間並無設定人類本性的上帝。人,不僅就是他自己所設想的人,而且還只是他投入存在以後,自己所志願變成的人。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東西,這就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原理。”出逃途中的伍子胥經過的八個情境是這八章的標題。一次情境是一次對自己當初抉擇的重新審視,是一次面臨著選擇,以及品味這其中的感覺和體驗。這樣他便投入存在主義的審美視野,成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東西。”在“林澤”,他遇到過著隱居生活的楚狂夫婦,這裡使他空虛,因為與他仇恨的本質相排斥;在這裡他又巧遇舊友申包胥,與楚狂正相反的人,在另一意義上也正與伍子胥自己相反,兩人都求用於世,但而今一個要找楚王報仇,另一個志在為楚國服務。
存在主義在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上,更強調它們的不和諧,正如薩特所說“他人的存在就是我的原罪”,或“他人就是地獄”。在楚國追捕他的陰影之外,伍子胥身處的大多數的情境也都是異己的。在“洧濱”,父親的同案、出逃鄭國的公子建打破了他投奔來的夢想,這人不思報仇,反而參與了晉國危害收留他的鄭國的陰謀。伍子胥便又在“宛丘”出現了,這仍然是一個“地獄”,卑鄙的陳國人要把他出賣給駐紮在此地的楚軍。伍子胥來到了“昭關”,關外便沒有了追捕,他可以獲得自由,但這不是存在主義理解的經過選擇的自由。
伍子胥在磨難中發白了的頭髮幫了他的忙,他僥倖地出了關,並且被一個好心的漁夫送過了江。但伍子胥仍沒有獲得與外在世界的和諧,他的已有抉擇成就了他的一種本質,就必然排斥了其它本質。於是,在“江上”,品行高潔的漁夫與伍子胥發生了矛盾,這是他流亡以來所遇到的唯一的恩人,他要送自己的佩劍報答他,但漁夫平淡中拒絕了。小說中,作者發出了這樣的的感慨:“這兩個人的世界不同,心境更不同。”
伍子胥與昭關外的新世界仍是一種不自由的關係。在“溧水”邊,美麗又多情的少女不能擋住他既定的步伐。在“延陵”,對他過去一直敬慕的大賢人季札有了拜訪的機會,但伍子胥感到運命把他們分開了,如果沒有楚王的殘暴,沒有逃難和復仇之心,他完全可以成為另一個季札,但現實的境遇和抉擇使一切全變了,他只能過其門而不入。“吳市”上遭遇俠士專諸,感到專諸象是都市裡的楚狂;而舊友陳音到越國去了,無緣相見;他在小說中最後的出場是扮作一個吹簫的畸人以引起吳王的注意,為他的復仇大業繼續努力。伍子胥的“一段美的生活”,在作者馮至看來,正是無異於這樣的一個拋擲:由停留與隕落結成的連鎖,在停留中有堅持,在隕落中有克服。而這可以看成是存在主義觀的另一種表達。
中國古人伍子胥成了薩特筆下的存在主義者的兄弟,這自然與西方的文藝、哲學思想對現代中國的影響有關,也與四十年代的特定歷史背景密切聯繫;兩者最終結合於作者馮至身上,他才是存在主義式的英雄伍子胥的實際創造者。而馮至自己在這一創作中又何嘗不顯示出由“停留與隕落結成的連鎖”?
寫作《伍子胥》是馮至十幾年前就有的夙願,但那時不會寫成現在這個樣子。“伍子胥逃亡的故事,我青年時就在腦里縈迴著,什麼江上的漁夫呀,水邊的浣衣少女呀,充滿了詩情畫意,使人神往。我早有把他們的故事寫成敘事詩或小說的願望”。照這樣寫來的話,只會是浪漫主義作品,伍子胥便會是浪漫王國的騎士。但沒有寫成。那時的馮至還浸在沉鍾社浪漫主義的余續里。
馮至的人生軌跡的“拋擲”在1930年有了變化,曾被魯迅讚譽為“二十年代傑出的抒情詩人”,如今決定了要走學者道路,到德國留學去了。那麼,他四十年代的重新創作也象他自己所說的“在停留中有堅持,在隕落中有克服”?不管怎樣,這次選擇與後來《伍子胥》的創作有內在的聯繫。馮至正是在德國留學、走學者之路時由浪漫主義者逐漸轉變為現代主義者。
馮至說他留學期間,“在這幾年內,我書是讀了,也很少沾染一般留學生的習氣,但是頭腦里裝的是存在主義哲學,里爾克的詩歌和梵高的繪畫,嚴重地脫離了中國社會的實際。”這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早在國內他就讀了卞之琳譯的里爾克的散文詩《旗手裡爾克的愛與死之歌》,並且想仿照來寫伍子胥逃難故事。但浪漫主義余續里的馮至誤讀了里爾克這位帶有存在主義味的象徵主義詩人。後來作者自己承認:“但那時的想象力多少含有一些浪漫的元素,所神往的無非是江上的漁夫與溧水邊的浣衣女,這樣的遇合的確很美,尤其是對於一個像伍子胥那樣的憂患中人。昭關的夜色、江上的黃昏、溧水的陽光,都曾經音樂似地在我的腦中閃過許多遍,可是我並沒有把他們把住。”留學以後,馮至才獲得了轉變,而這要到他四十年代初在重新創作中體現出來。
在四十年代,“停留與隕落結成的連鎖”、馮至重新的創作終於開出了花朵。這個時期受西方現代主義,特別是存在主義影響的他,從沿海流亡到內地,一路上與民族同遭陣痛,不會感到“嚴重地脫離了中國社會的實際”。四十年代初的中國與法國有著驚人的相似,都正被法西斯強國欺凌,知識分子在民族血與火的罹難中面臨著存在主義的境遇的選擇。理論一旦與現實發生了共鳴,發出的靈光是巨大的,這就是馮至四十年代又重新創作並取得重大成績的主要原因!屢次願望都沒有成功的《伍子胥》的寫就正是這次爆發的重要收穫之一。
往日的浪漫已經難再,時代賜給了新的因素,而今的《伍子胥》“其中摻入許多瑣事,反映出一些現代人的、尤其是近年來中國人的痛苦。這樣,二千年前的一段逃往故事變成一個含有現代色彩的‘奧地賽’了”,作者自己也與伍子胥一道發生變化,“伍子胥在我的意向中漸漸脫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為一個在現實中真實地被磨練著的人,這有如我青年時的夢想有一部分被經驗給填實了、有一部分被經驗給驅散了一般。”
於是,出現在我們眼前的伍子胥變成了一個存在主義式的人物,在存在主義式的境遇里演繹著存在主義的人生哲學主題。伍子胥是由“種種利害關係、興趣和未來計劃組成的,這就是存在主義現象學者想要研究的東西,因為他們主張那些東西是真正基本的人類生活結構”。死亡是人生的最大生存困境,是存在主義最感興趣的問題,馮至也不例外。當別人問他吳市以後的伍子胥是否還繼續寫下去?他顯然對復仇結局失去了興趣,他回答說:“如果寫,我就寫他第二次的‘出亡’——死”。
正如里爾克的散文詩被一種神秘的情調支配著,馮至也在《伍子胥》中重視現代主義的心理氣氛的渲染,用一個個散文詩的片斷來表現一個流亡者存在主義式的選擇境遇中的感覺和體驗。小說中的《延陵》一章用優美、流暢的散文詩的語言盡情描繪了大賢人季札領地的富庶、人民的安居樂業和和平寧靜生活;接著便轉到了伍子胥的選擇境遇:是否去拜訪季札?帶著心理分析手法、又有著濃郁的抒情的筆觸強化了作者心中的伍子胥的的形象。從小說中,我們也看到了過去的浪漫主義者馮至的印痕,他十幾年前關於伍子胥流亡途中故事的浪漫遐想固執地顯露了自己。昭關的夜色、江上的黃昏、溧水的陽光,何其美麗;而樸實的兵士、做好事不求報答的漁夫、施捨米飯的浣衣少女,何其美妙!我們甚至誤認為伍子胥的逃難是一種浪漫的享受了。這說明馮至不可能成為薩特那樣的存在主義者,他無疑帶有濃厚的中國特色,甚至保有浪漫主義因素,這就是馮至創作道路上的“停留與隕落結成的連鎖”吧。
《十四行集》和《伍子胥》是馮至四十年代創作的重大收穫,反映了他的創作已由早期的浪漫主義發展到現代主義階段。對馮至來說,這是一個遞進式發展,四十年代才代表他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而《伍子胥》的出現也標誌小說家馮至誕生了。二十年代他也寫過小說,但幾乎沒有影響,《伍子胥》之後的小說家馮至還為我們奉獻了又一部敘事性力作《杜甫傳》。馮至小說的詩化、散文化傾向是對二十年代浪漫主義小說的繼承和發展,“符合了現代世界嚴肅小說的詩化以及散文化(不重情節)這樣的創作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