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女兒書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圖書
《致女兒書》是200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王朔。是王朔對女兒關於自己家庭、血緣、歷史和個人情感的真實敘述。它原本是一個相當私密的文本,是當遺書寫的,準備要有個萬一可以給女兒一個交代。他要告訴女兒咱們家是什麼來歷,你的爸爸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內心深沉的歉疚和痛苦……在書中他細緻地告訴女兒什麼是正確的世界觀,拳拳的為父之情漫洇紙上。
在書里,王朔和女兒交流的尺度相當寬泛,包括他在家庭倫理關係中的困擾、他在自己創作中的種種思考和苦苦探索,以及實際上以己為例,坦率地告示女兒真實的男人什麼樣。這種非常平等的視孩子為獨立個體的父女關係在現代社會也還是僅見的。
而文字極其優美和細密。王朔在這個私人情感領域裡傾身投入,袒露摯愛親情,這在他以前的創作中從未有過。其中《致女兒書初稿》就是一篇上乘的抒情散文,濃情熾愛,此時心情;愛而不得,去而復返,一吟三嘆,低回曲折。是顯露王朔真實心性的性靈文字。
尤為難得的是,這裡有他最深刻的自我批判和反省。因為在所有的事情上也許都有為自己辯護的理由,惟獨面對女兒,只要你離開就意味著自己從根兒上的不負責任。因此,這本書可以稱為王朔的懺悔錄和思痛書。
真摯、深情、不留餘地的自我省思是《致女兒書》品高一格的鮮明標誌。
| 自序 | 對這個世界的一些看法 |
| 致女兒書 | 關於人和與人相處應該知道的 |
| 關於咱家我這一方的來歷 | 對未來的看法 |
| 關於爺爺奶奶 | 對你的看法和幾個小叮囑 |
| 對我影響最大的幾件事 | 大大 |
| 我的前後道德觀 | 你媽媽 |
| 不同時期我喜歡進行的活動 | 最後幾句話 |
| 我的違法記錄 | 致女兒書初稿 |
| 朋友 | 幾張照片的說明 |
| 與其他女人的關係 | 答編輯問(代跋) |
他在《致女兒書》的自序中透露,該書的寫作開始於三年之前,本來是想當遺書寫的。“事兒不大,只是中年危機,焦慮什麼的,沒到生死關頭,自己把自己個兒想緊張了,自己給自己個兒製造了一恐怖氣氛。”想當遺書寫的意思,就是要等死後才能發表。所以,王朔自認提前出版了這本書是一種“破罐子破摔”,“人老了就沒皮沒臉了,隨時都有破罐子破摔的念頭倏起忽落。”他還頗為自嘲地把這本書定義為“陰暗心理小說”,因為“光明源自黑暗。”
“很多心思對你說才說得清比自言自語更流暢,幾次停下來想把這本書變成給你的長言。坦白也需要一個對象,只有你可以使我掏心扒肝,如果我還希望一個讀者讀到我的心聲,那也只是你。”
“最後一次離開你們,你媽媽一邊哭一邊喊你的名字,你不應聲,悄悄坐在自己屋裡哭,我進你屋你抬頭看我一眼,你的個子已是大姑娘了,可那一眼裡充滿孩子的驚謊。我沒臉說我的感受,我還是走了。從那天起我就沒勇氣再說愛你,連對不起也張不開口,作為人,我被自己徹底否定了。從你望著我的那眼起,我決定既剝奪自己笑的權利,也剝奪自己哭的權利。 ”
《致女兒書》是王朔為自己女兒寫的一部書,也是王朔的自傳。書中以身在美國成長的女兒為傾訴對象,敘述了王氏家族的血脈淵源、歷史遺傳以及自我成長經歷。書中無時不體現出一個父親對女兒的摯愛深情。在書里,他細緻體貼地告訴女兒這個世界原本的樣子和人的本質,以益於她確立一種正確的價值觀以及應對生活的態度和能力。和他以往的全部作品相區別,這是王朔的第一次“真人秀”,面對女兒他坦誠地打開了真實的內心和情感世界。作品情感真摯,尤以毫不留情的自我剖析獨樹一幟。既有一個作家的創作野心,還有一個父親因對女兒的成長不在場而產生的深深自責與懺悔,更有一個人時時面臨的孤獨與脆弱,他對生命敏銳而獨特的體驗。讀者正可以從中找出形成王朔複雜而特殊的個性的原因。
離你越遠,越覺得有話要跟你說,在你很小的時候就想,等她大一點,再大一點。2000年開始我給自己寫一本小說,本來是當給自己的遺書,用那樣的態度寫作,把重要的人想說的話那些重要的時刻盡量記錄在裡面,當然寫到了你,寫我們在一起時的生活。寫到你時閘門開了,發現對你有說不完的話,很多心思對你說才說得清比自言自語更流暢,幾次停下來想把這本書變成給你的長信。坦白也需要一個對象,只有你可以使我掏心扒肝,如果我還希望一個讀者讀到我的心聲,那也只是你。

王朔
王朔的關鍵詞(責任編輯的話)
有關王朔的一個關鍵詞一直被我忽略,那就是:講真話。其實它從頭到尾或隱或顯地貫穿在王朔的文學創作實踐中和他本人的處世態度上。
上世紀九十年代,王朔成為了一個文化符號,作為“反諷”、“調侃”的王朔的語言風格,表明了他嘲弄虛假崇高的精神姿態。這些其實都與他求“真”的心理相關。
當他反對的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以後,王朔的求“真”便開始轉向了對自我精神世界、個人內心生活的探究。這便是“現在就開始回憶”的結果:長篇小說《看上去很美》的寫作。它是要弄清楚:我是誰?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本質命題。因此有讀者稱王朔老了,已經開始回憶了,不是知人論世的懇切評語,至少它不貼切。
我們說十九世紀馬克思他們探究人類社會發展的理想道路是偉大的求真精神,那麼在二十一世紀人類尋求和諧共同發展的今天,從自身出發、從個人出發,探究個體生命的真諦也是一種誠實和誠懇的求真精神。改造社會和改造自我從來是人類社會進化并行不悖的兩個支點。
從王朔個人的創作看,《看上去很美》以後直到今年以前的這一段沉寂,正是他不斷“求真”的一個身體力行的實踐過程。他打破了很多藩籬:許多固有的小說觀念、文體模式、體裁限制…力圖做到不違背生活的規律和內心的感受。當他遵循內心的真實感受和寫作的真實情狀時,他的求“真”讓他達到了自由的狀態。《我的千歲寒》《致女兒書》《和我們的女兒談話》等作品俱讓人感受到他寫作的自由無羈狀態。當靈魂袒露無遺時,你便可看到它本質的皎潔和美好。
因此,王朔的寫作成為今天的樣子是自然而然的。求“真”的理念使他的創作向內轉,尋求一種最自我最個人的表達。因為人不能對自己講假話這是最低限度。《致女兒書》的出版與“隱私”無關與炒作無關。王朔克服了他內心極大的矛盾和猶豫,這是因為他深知“講真話”在今天依然很難。他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做一個人類的標本,一樣樣揀出那些自私、唯我、暴虐、陰暗、慾念以後,剩下的讓我們對自己還有信心。
求真的結果,是王朔不惜把自己拿出來論斷是非。因為大家都是人,要錯都有錯。他起初是想在女兒面前為己辯白,說說爸爸的理由,但結果所有的理由對別人都說得通,惟獨對女兒說不通。在女兒這裡,他成了一樁原罪的肇因。
而王朔就敢把這樁原罪放大在眾人面前。我敬佩他的寫作。
人民文學出版社 禾佳
王朔答編輯問
問:《致女兒書》很特別,跟你以前的創作都不一樣,直接拿自己說事,怎麼突然有衝動要對女兒說自己呢?
答:心情倒也沒什麼特別的衝動,我其實很早就想把過去的生活找個合適的口氣一股腦講在一個故事裡,因為它們本來就在一個故事裡——我是寫自己的那種作者,不虛構,全玩真的,假裝是一堆故事挺不誠實的,有點自己騙自己的意思,而且我也煩透了要把一個正在進行的故事找一個結尾變成過去完成時的所謂創作要求。我從前的小說好多是故事剛開始——譬如一九八七年發在你社刊物《當代》的《浮出海面》——卻要在小說里預置結局,因為小說必須有結尾,跟自個兒方自個兒差不多我這麼虛榮當然不能犯臭寫成大團圓,所以經常廉價地使用“死”這種方式結尾。譬如《空中小姐》——也是你社首刊處女作——其實也不是處女了,中篇處女;但是招來一些埋怨,因為人都活著,還挺好。有點兜售隱私的意思——我;或多或少感到一點壓力聽到點議論,也是個苦惱。能不能不編故事了,就跟著生活跑,其實死、散,都是簡單的辦法,過分戲劇化,好像凡事都有個了結其實人活著,都不死,就要面臨一個,以後呢?我也不想寫太多小說,重複自己是一件可恥的事,最後寫一個小說就完了,把自己來龍去脈交代了——對自己交代。等於實際上我從一九九一年以來這十幾年一直在找一個說話的口氣,但是一直就找不到,幾種口氣都不太合適,比如我用第三人稱特別客觀全知的角度,述說下來一盤散沙,因為好多事情全知角度會非常難受——你並非全知,一寫就知道,只能假定讀者更暈,看不出幌張兒,這個不是我所欲。用自言自語的口氣,就是第一人稱吧,寫起來也覺得漫無目的,沒有對象也就沒了傾訴熱情,說給誰聽呢?有一年有一天,突然好像想起對她——女兒說,她必須聽,就有一個對象了;寫自己,誰會感興趣,不是太自信;女兒必須感興趣,有一個讀者就應該是她,也希望是她,曾經彷彿如獲至寶找到通道。但是你看,講來講去,感情太濃了好像也講不下去了,講到那麼幾萬字就講不下去了。另外,當然其實對我來說更關鍵的是一個結構問題,你要講一個很長的故事的時候,結構特別麻煩,根本沒可能一個視角講到底,中間不換角度就有視野狹窄症的感覺。《致女兒書》是對女兒講的,假裝真摯的,很親昵的一對一的私語口氣,講久了局限性就出來了。原來我想的是對女兒講呢就有所講有所不講,有些話就她的理解力不能講,或者說有些社會禁忌自然地就出來了。因為寫作的時候老覺得不太自由,過去那麼多年我們對寫作有太多要求以後,自己就有很多束縛,你掙脫束縛的過程特別難受,結果後來《致女兒書》是對我自己女兒講,這樣講下去就覺得太隱私了,而且講的時候情緒波動太大,對敘事也不好,好像就跳過很多敘事直接抒情了,太濃了就敘事而言,情緒波動太大對敘事也並不好,好多地方跳過敘事直接抒情,就出現這種情況了。所以在後來——忘了哪一年,一怒之下就換成《和我們的女兒談話》,就換成了別人——方言的女兒,好像情感就能夠不那麼激動了,所以那個就講得長點,講了十六萬字,也仍然講不下去了。因為有些事情也牽扯到其實還是心中有顧忌,好多生活經歷過的事情想把它全講出來,但是你說我再肆無忌憚,我也在考慮社會的接受能力。有些事情社會接受以後反正我也覺得不好,就一直在矛盾,這矛盾一直到今天也沒有解決,所以就造成所有的東西都寫不完,寫到一半,那段寫的東西全都是寫到一定程度找到一個敘事調子以後,敘事到一定程度后就敘事不下去了。最後就形成了瘢痕,索性有寫作痕迹就有寫作痕迹吧,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作為小說來說,再自由的心態和方式恐怕也沒法窮盡生活,我那時候也有個不太對的想法,也是想畢其功於一役,就想把生活全部窮盡在一個結構里恐怕也做不到。比如說寫性,我想我現在寫我終於可以無拘無束可以都寫了,但是寫到一定程度,會出現自己心情不是那麼穩定,不是那麼肯定,我發現我還是挺道德化的一個人,自己開始審查自己,以一個老古板的眼光,就開始猶豫了,自我否定了,會出現這種問題。所以這個書,我私底下當然認為寫得是失敗的,在敘事上是失敗的,基本上技術考慮偏多。
問:當時寫的時候你想過出版嗎?真是當遺書寫的?
答:當時沒有想過。實際上當時我得克服自己那種觀念上的束縛,其實我自己在寫的時候,寫到一個句子的時候,所有敏感的句子就是你們可能提到的,我都會在那兒停下來想這能不能通過,因為這麼多年來被限制成這樣以後,自己就有這個問題,有自我的約束在裡頭。當然這特別妨礙我講事情,或者對我要寫的東西進行一個透徹的描述。我特別想掙脫這個東西,在寫的過程中,當然那時候我自己把自己放下,我想我不發表,這樣就好多了顧忌就沒有了。但其實仍然有。譬如說,這裡頭全沒有性描寫,但我在另外一個小說裡頭寫過。
問:是《和我們的女兒談話》嗎?
答:不是,那個我就沒敢拿出來,我就認為不能拿出來,就我現在也認為不能拿出來,因為那個東西我老覺得是個社會禁忌。其實社會禁忌對人的影響特別大,所以當時寫,當遺書寫,也是一個姿態而已,就是不發表,或死後才發表。這麼想你能放開一點,實際上也沒有全部放開,也仍然受限制,所謂的道德觀念或是什麼的。
問:這是私人化敘事範疇里的?
答:當然是,就是不想做宏大敘事或者是觀念性的東西做是非判斷,做道德化的判斷我都不願意。依據我自己的生活經驗,真實是第一的,道德判斷根本就不是應該作者來下的,當然我認為讀者也沒有權力來下道德判斷。但我們特別習慣於道德判斷,這特別影響敘事,當然我自己不認為小說中誰虛構過什麼,都是存在過的東西,不管是在你腦子裡還是在生活里存在過。那因此真實描述是第一位的,因為有道德判斷在前面之後肯定會做一些隱瞞在裡頭,或曲筆在裡頭,我覺得那個都會妨礙別人的觀感的,或者自己的,寫寫就不誠實了。真正把性寫真實了又特別難,實際上就是你不習慣講真話的時候甚至講真話的方式都找不到了,老實說我碰到的就是這個,因為講假話的一堆,我們所有的文學技巧其實都是在講假話,方便講假話。烘托也好,比興也好,其實都是為了遮蔽真實,或者把真實美化了,把醜陋的東西寫得不那麼醜陋了。講真話想坦白地講的時候特別困難,它就變成了只有直抒胸臆那麼一個直接表達,但是這種簡單的表達又不太適合表達複雜的東西,譬如說出現平行的這種心理感受的時候,它在一個敘事中要中斷敘事來鋪陳心情,講一層層心情,把敘事節奏就打掉了,所以有的時候就接不上敘事,出現技術上的好多問題。
問:私人化寫作跟你以前的社會化寫作有什麼區別?
答: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回事,其實我一直認為我是寫自己的。私人化寫作可能是觀感問題吧,譬如說,(問:是內容問題吧?)我覺得不是內容的問題,我寫的都是自己的生活啊,我沒有寫過別人的生活啊,我也沒體驗過別人的生活啊。因為寫親情,這種赤裸裸的親情被認為比較私人化,而實際上我也不認為它有多私人化,就說我們那一代人吧,親情是被嚴重扭曲了的,甚至空白的。所以我倒認為這本書引起的共鳴可能會超過我原來所有的小說。所以你得從效果上來看它是社會化寫作還是從題材上看,當然從題材看我從來認為我是有故事的。當然我認為我的故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當然不只我有代表性,每個人都有代表性,其實越個性越共性,我認為有好多作品不能引起共鳴是因為它個性化不夠,它概念化了,概念化是不可能引起共鳴的。要避免概念化沒有別的,只能真實和極端真實,因為每一個細節都是別人不可能替代的,同樣的故事不管親情還是愛情,每個人經歷的細節是不一樣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必須把最真實的那部分寫出來才可能避免概念化,否則真的會掉入概念化,當然道德化也會掉入概念化。
問:你說自己是個自私的人,你有自己做人的原則。但在女兒面前你感到行不通了。這本書也可叫“懺悔錄”、“思痛書”。
答:你說的是自私的原則,是吧?凡事當前先替自己考慮。其實,我也是這麼做的,我對我女兒也並沒有比對別人更好,但是不一樣的是跟她自私時我產生了罪惡感,這是跟別人自私時沒有產生過的,差別在這兒了。這個我覺得當然中國人不講究什麼罪惡感,咱們認為自己從來都很無辜,包括我過去也這麼認為:錯,永遠是別人的。我只是在主張權利或更惡劣的:顯示公平。反正我個人認為這個特別重要——有沒有罪惡感,對你看清事情的真相特別重要,假如你永遠認為自己是清白的,你就永遠看不到真相,天經地義也有可能不對。我們講自私是人的本性,好像是天經地義的,道德評價就放到一邊去了,講利他主義也是在確保自私——生存的前提下講的,要先活著才能利益他人嘛,一般人都這麼說。有一段提倡大公無私,犧牲自己——放棄生存,這個底線算拉高了還是拉低了,分從哪頭說。我倒認為共產主義的價值觀裡頭可能比傳統儒家價值觀先進就先進在這兒了,但顯然不合人情沒有實施下去,也確實不合人情造成了很大傷害,所以你看現在價值觀復辟呼聲特別高。但是我就覺得中國一場革命死了這麼多人,大家一點進步也不接受,都回到老路上去了,真是血都白流了,回到老路上並不太平我認為。當然不講緣由無條件犧牲自己,一般人也做不到;硬要別人做,強制別人做,用高壓手段壓別人這麼做,結果只能是集體互相翻臉。價值觀本身是先進的,操作過程太猛了,當然這是其他的話題了。但之前誰覺得過自己有罪過啊,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都是生活的受害者,這個當然使我自己覺得,因為沒有罪惡感,你會把好多廉價的行為稱之為愛,給別人點錢就叫做愛,叫博愛,才不叫呢!就造成滿街險象,抓起來一問都是弱者——好人?這種怪事。說實在的,我認為價值觀顛倒是造成人無力向善的根源——以本人為例。
問:作為父親,給女兒寫這樣一本書,在很多地方驚世駭俗。魯迅在上世紀初有一篇文章叫《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你是怎樣的父親?
答:我覺得,我當然覺得我做得很不好,其實我真沒想過怎麼做父親,假如讓我選擇,我寧肯選擇不當父親。我曾經以為好像知道自己是誰,給我女兒講我們家故事寫到筆下,才發現壓根不知道自己是誰,來自何方,甚至連我是什麼種族也搞不清楚,連我爺爺奶奶叫什麼名字我都不知道,好多事情不知道,而且往回捋的時候你才會發現我們原來想當然地認為我們是地老天荒就住在這兒的,但實際上不是,是遷徙來的,而且遷徙之遠簡直是,在這書里我才上溯到炎黃那兒,其實我得上溯到非洲去,炎黃不是周口店下來的北京猿人,我在書里追根兒追到北京猿人實際上是個錯誤,炎黃不是北京猿人是非洲直立人來的。我們老是強調我們的特殊性,其實我們一點都不特殊,不過“性相近,習相遠”而已,只是環境造成了一些差異,把差異當了文化。我們強調文化上的特殊性實際上是沒有生物上的根據的,環境變了你可以隨著環境變異,與時俱進么。你不必堅持你所謂的獨特性,您不特殊,您很一般,
您堅持的所有的跟別人反著的價值觀都是無源之水,當初也是權宜之計,笨笨地承認殘酷現實,給現象命名。老實說普世價值在我們身上是適用的,儒家和普世對立的這套等級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挺原始的,一點不高明。堅持這一套一有空就拿出來招魂的骨子裡這是一種種族主義我以為,暗示我們的種族是獨有的,具有不可調和性,且不說是不是優越,中國人太多都是種族主義者我們這裡自己人人知道。這妄想恐怕都進入基因了,可惜它不建立在一個歷史真實上面,是建立在一個假象上。最近復旦大學搞的DNA調查我們百分之百的都是非洲來人,跟北京猿人混血的一個都沒採到,我們強調自己是龍的傳人——爬行動物傳人?要不要考證一下個別恐龍和猴子雜交的可能?說給誰聽呢彰顯自己的無知么?跟這世上所有人一樣很沒面子么?黃是中間色,肯定是黑白混的別不好意思承認了。祖宗之法不可變?祖宗是非洲,祖宗之法、祖宗的規矩是:真相與和解。你還法哪兒啊?道法自然——豈是君君臣臣所能扮演的?失去了生物狹隘性,我覺得我作為父親——複製生命接力賽的上一位傳手也沒有了優越的必要。我可不想當一個野蠻的儒家父親,愚昧地認為位置靠前判斷力就一定準確。孝,實在是弱者之間可憐的互相拴對兒的口頭承諾。我的全部經驗告訴我,正確的生活態度實在和年齡沒關,非和年齡掛鉤也一定呈反比關係。父親所能做的、大發慈悲的就是小心不要把自己的惡習傳染給孩子,必須在孩子第一次發問時就學會對他說:不知道,我不懂。從我們這一代開始堵住這隻自上而下索取的臟手,並且隨時準備揭發上一代乃至上上無數代的偽善我是這麼想的。一個人失去本質了覺得特別痛苦,但實際上我們原來就沒有什麼本質,就是一系列的文過飾非這古老史,所有這些畫地為牢以為純粹的描述都是不合時宜的。我希望我女兒將來是個天性解放的不背歷史包袱的,也不因為她的膚色她的來歷使她到世界其他地方生活有什麼障礙。還是說到那句,就是說我們在精神上實際上是無產者,無產者失去的只是鎖鏈,沒有一個精神特質失去了你就不能稱之為人,或者不能稱之為中國人這回事。我想跟她說的其實也是這個,因為她後來到國外去念書,她也面臨很多文化困境。我們經常講的東西方文化困境。我很心疼她,我還是那種古老的觀念,在一個正常的國家和家庭,小孩子不應該背井離鄉去外國讀書,那不是一種發達、可炫耀的事兒。另一方面我覺得那困境——反正已是既成事實了——不是不可逾越的,如果你認為它不可逾越它就不讓你逾越。不讓出身成為孩子成長的累贅我覺得這是我做父親的義務,不是教育她的意思,只是想告訴她好多格言都是錯覺。
問:噢,原來這個根是這麼寫出來的。
答:當然寫起來,就是往前,是從果往因那兒,你就必須到猿人那兒去。當然我這本書也有很多東西搞錯了,因為當時有好多最新DNA測試結果不知道,加上是三年前寫的東西後來沒看,前面說的那個最近剛做的對中國人一萬兩千份的調查,復旦大學做的,上星期才公布。原來的歷史只聊到我們是炎黃子孫,再往前就不聊了,周口店發現猿人化石就想當然地把它們和我們聯繫到一塊,也是一筆糊塗賬我就不說是認石作父了。
問:你是一個懂得推己及人的現代父親。書里有一句話,“用我的一生為你的人生打前站”……
答:那都是很感性的話。一代人和一代人就是那麼一種前仆後繼關係,我有了女兒后首先痛感儒家倫理有悖生活切實感受,孩子給你帶來多大的快樂,早就抵消早就超過了你喂她養她付出的那點奶錢,這快樂不是你能拿錢買的,沒聽說過獲得快樂還讓快樂源泉養老的這不是訛人么?她大可不必養我,我不好意思。儒家倫常是保護老人的,是保護落後的,是反自然法則的。你看野生動物有養老的么?老動物們都自覺著呢。實際上養老是個國家福利問題,不是個人的生物義務,生物義務是養孩子,把DNA 往下複製, 你讓他倒行逆施不是人人都有這個反自然行為能力的,你把它規定為法律責任,你因此讓他在這個無法完成的任務上產生罪惡感是不道德的。我們的父母這一代喪盡安全感,下意識不自覺——個別人故意——把自己的恐懼傳遞到孩子身上,家庭其實都破裂了但還拿鐵絲箍在一起假裝完好。老實說,我這一代孩子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這些破裂家庭關係的影響,多少人家演正常的父母其實已經瘋了很多年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往昔歷次政治運動的風暴並沒有在中年以上人群中的心理上真正平息。中國的事情很鏡相,總給人錯位倒置感,最後老是要子女原諒父母,雖然大家都很可憐,其間只見強弱關係的轉換,親人之間的懺悔和赦免搞得像做賊,怕丟臉,結果老人鬼鬼祟祟或者假裝文靜致遠,中年發福的孩子都成了偽君子,一家子演戲勤勤懇懇,說起來都默然嘿然家家一本糊塗賬。譬如說家庭暴力大量的是父母打孩子,這何止是不道德,純粹是犯罪,弱者的殘忍。但是在我們的電視上隨便一對父母談到打孩子都不怕承認——坦承,口口聲聲為孩子好,我謝你了真不知道寒磣特別是父親;心理學家的規勸都極盡溫婉生怕驚擾、磕、碰、貶損了他這權力。善良民俗就認為這是可以的,他擁有這個權力,他終身擁有,不管他走到哪兒,醜惡到什麼樣,你都要對他盡義務。而且你要強調這個,你就讓世代中國小孩這一生得不到他擁有的權利,實際上從一出生就剝奪了他免受屈辱、疼痛的權利。人是條件反射動物,哺乳動物都是。你打次貓試試,狗是奴才,狗能不反抗,貓反抗不了也跟你玩陰的——你怎麼能指望這樣的小孩組成的國家將來一直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我們黨建軍之初就在古田會議上提出不打罵士兵,連隊實行民主管理實際是官兵平等這樣一個制度,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羅榮桓同志提出來的,這是優良傳統喲。不打仗了,打孩子——什麼情況?一家子老是打來打去也是會傷感情的喲。在我們這兒,孩子對長輩不敬的事與長輩對下一代的虐待相比是不成比例的,父母普遍虐待孩子或虐待過孩子,而子女反過來虐待父母的屈指可數最多是不愛搭理,因為父母的權力大得多,父母打孩子社會不認為是不正常的,國家也不干涉,但是孩子不體諒父母,社會就一片嘩然,我認為這是不公平。這體會我自己有了孩子更深感到所謂父母之恩之虛幻,是旌表包裹自私舉到雲端的欺世。贍養老人當然是一個義務,我的意思也不是就不要贍養老人,但那種東西是國家的義務,不能轉嫁到公民身上去,國家不許逃避責任!獨生子女他們也沒有能力這麼管呀,一家四個老人、八個老人就是所謂親情慰藉——走面兒,他都走不過來凈剩落埋怨了,包括老人最後的癱瘓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垂危火葬入土。一個孝子正經一點我以為每個月至少要去醫院一趟陪護掃墓什麼的——將來。你看現在這社會仍然在或明或暗地給孩子們施加壓力,常回家看看呀如何如何呀,多陪陪老人呀,這東西會變本加厲的,解決這個問題你不能又建立在一個錯誤的認識上:你不這麼做就是犯罪。那我覺得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做父母的都是成年人了,至少從我們這一代開始父母應該懂事、自尊,應該知道人的生老病死是人必須經歷的,我作為成年人得自己去扛這個事,國家當然應該統籌一下,在我能掙錢的時候就把後事安排好,這實際上是一個服務的問題,反過來要求孩子不太好。我覺得中國人的家庭關係不太正常,孩子承擔這麼多的義務,父母拚命來要求孩子,說什麼贏在起跑線上我特別討厭這種說法,把孩子訓練成一個賺錢機器,這就叫成功,表面是為孩子好,其實是想自己將來有個靠山,無情剝奪孩子童年的快樂。這是一種顛倒,顛倒的人性,這不是愛孩子,所以就會出現那樣奇怪的邏輯,就是我為你好我可以打你,我愛你我打你。我靠,不帶這麼聊天的。(笑)你說你愛我,其實我很清楚你骨子裡是髒心眼,是叫我將來在你老了失去勞動能力后保障你——你不肯學習意味著你將來不打算為我的衰老負責任。你看這麼多父母都快——已經——把孩子打死了。我靠,您這不是愛,愛是不能交換的,無條件付出,不要回報,想都不想,起這念已是罪惡了,付出中已經達成次級回報——快樂獎賞了;跟犧牲肉體放棄清白遺臭萬年享受痛苦那種境界又怎麼聊呢——聽都沒聽說過吧?我國人群的基本價值觀是混亂的,混沌不明的,越老越不懂事。
問:這本書你女兒看過嗎?
答:沒有。
問:從目錄看你只寫了計劃的前兩章,沒有完成它。
答:因為後來老實說,我的那點勇氣也已經耗盡了,這裡頭其實涉及到點隱私。這些人都還在,再往下寫,我覺得涉及的人再多的話,說實在的我有點擔心,我認為我女兒不會說什麼她不滿最重的口頭語就是:太過分了。但涉及到的成年人未必會如孩子般諒解我,年齡越大的人面兒越薄你沒發現么?自我往上年代的人都特小心眼,越沒什麼越盼什麼,對什麼越敏感。
其實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衝突是最激烈的,因為大家之間沒有什麼顧忌。中國人好像聊這個是把它視為家醜,我認為根本不是什麼丑,這證明中國人是有情感的,在家庭裡頭才能顯示情感,當然大家可能認為情感就是互相容忍,但我認為那不是情感是客氣,真正的情感只有在衝突中才表現出互相的情感深度。其實大家都很沒面子老實講,誰有什麼面子啊我都不知道,但大家都維持一個默契好像不說就都有面子。當然我自己也不是天天有勇氣,所以我不再往下寫了。我現在什麼心理啊,挺矛盾的,比發表別的小說不安,反正我就想看看大家有多正經就想看看,等著看別人說我如何地不顧別人感受呀,等有人認為我涉及到其他家庭成員不懂尊重人呀什麼的。但是我不在乎,我就想看看大家什麼反應呢,沒什麼了不起的,最多就是得罪得罪,反正早已經得罪了,互相得罪而已,別假裝好像挺好的。(笑)誰要覺得被得罪了,活該,就照死了得罪。罵人身體健康。寫了嘛我文責自負,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社會禁忌。(笑)誰都不好意思公開談論,覺得好像談論我犯了什麼大忌似的。
問:所以《致女兒書》三年寫了以後放了這麼久才拿出來也跟你今天的心理狀態有關。
答:對呀,後來包括《和我們的女兒談話》《躍出本質謂之駭》呀都是後來寫的,基本上每年都要把腦子裡的事重寫一遍,想找一個新的敘事方式,哩哩啦啦的發現也寫得差不多了,就這樣吧。(笑)不必再合在一個大敘事框架裡頭,這是過去那種文學觀念造成的,好像一個文體有它文體的純潔性和完整性,其實在今天這個密克斯的時代根本無所謂了,都跨文體了,反正把事說清楚了感受說清楚了就可以了。包括那種很可笑的自我束縛的觀念,什麼長篇小說怎麼也得十二萬字以上,今天顯然不能成其為理由是吧,就是特別形式化,下意識里就有這麼個概念,這麼簡單要破掉它,說實在的我花了多少年啊,花了二十多年才破掉。什麼長篇短篇,差不多就行了,有感而發寫哪兒算哪兒,今天破了你覺得這事特可笑,可當時你就不這麼想了,覺得不到十二萬字就算沒完成就擱下了。我都不知道是不是還有很多真實可怕的東西就是因為不合發表體裁都沒有拿出來壓在各家箱底兒了。原來出版社門檻太高,勢利眼,網路時代就可以了。
問:你現在的創作應該說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就是自主意識更強了,找到了更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更自信了。
答:當然有變化了。其實是更自信了,就是我原來老實說是要照顧讀者,就是有包袱必把包袱給抖了,追求效果甚至不惜破壞節奏,就是話都說得特別滿。因為你把話說得滿了,很多其實不屬於這個故事的話,花哨的東西,就加了色兒了,很多讀者會給你廉價的好評。覺得逗讀者樂特別有意思。可那麼寫的時候,老實說你寫作的動機就不真誠,寫寫就不真誠就變得油滑了。後來,當然也跟那個時候寫作的目的不一樣,那個時候還是沽名釣譽,不是說現在不沽名釣譽,就是說那個時候主要目的是沽名釣譽,效果是重要的自己不重要。寫這個的時候是當不發表寫,寫得就不一樣了,再加上有了罪惡感寫和沒有罪惡感寫,跟以前不一樣。同樣的事情他怎麼感覺是不一樣的。
問:現在你的創作可以稱為向內轉嗎?就是完全追求一種個人內心生活的獨立性。
答:對,因為後來我發現有一個“宇宙同構”的道理,就是說同一個世界,就是社會上的東西全都可以集中到內心中來,不必藉助外部的東西,過分地訴諸客觀的因素吧就會把它情節化了,情節化的東西我覺得會影響認識,而一般的社會生活相似性太強了,大家也無非都在吃飯聊天,泡吧什麼的,所以我看現在那些年輕作家他感受很真實,可是有相似感,因為生活太相似了。過去我們中國人的生活在毛時代是有它的獨特性的,所謂地域性特彆強,你(的寫作)就可以建立在地域上,包括農村生活,普遍地跟城市生活是不一樣的,好像農村生活你從情節上看它就不一樣,現在這個地域性被沖淡了,你不管內心的話你藉助外部你天天在飯館里聊天,酒吧里聊天、泡妞什麼亂七八糟的,最後說的話會趨於一致,你碰到的感受、受到的困擾都一樣,就沒有你自己存在的必要了。甚至就是說每個人好像只能寫一本小說,寫到第二本就開始重複了。我當然也碰到過這種東西,我也有過自我重複的東西,所以你必 須只有內心的豐富才能擺脫這些生活表面的相似。當然,在描寫內心的時候,你也有拿感性 的東西寫還是拿理性的東西寫的問題,看上去拿感性的寫舒服,但是他太缺乏理性就會敘事 不長,敘事不長就沒有節奏,在裡頭就沒有支點,情緒發泄完了之後就不行了。而且情緒在 一天中是不停起伏的,情緒高的時候寫什麼都有意思,情緒低的時候怎麼看都沒意思,用情 緒是支撐不了太長的寫作的,好像這是永遠解決不了的。只能是不停地亂寫吧,情緒高的時候就寫,情緒低的時候就不寫,只能這樣。看似雜亂無章,其實寫到一定規模的時候,它方方面面就顯示出一種呼應來了。
問:感覺你現在怎麼寫寫什麼都能成。
答:我現在在寫的時候也有自由感了,就是,這其實跟追根有關係,就是追到根上再往回寫,特別好寫。之前假如停留在生活的印象中寫,寫寫就收不起來,就會出現好多廉價的感慨,廉價的感慨可能每一個作家甚至那些寫歌詞的人都能發出來,那我其實覺得你要自己寫作有存在的必要的話你怎麼也得有點跟別人不大一樣吧,對吧?就不說高低了,你得跟別人不一樣。你要跟別人一樣、相似的話,就會打擊自己的自信,這個甚至我都不認為是多麼深入的問題,就是功利性的要求,你就是為了功利目的也得這樣。你要跟別人完全一樣就沒必要存在了。說實在的,到上個禮拜我的認識才告一段落,在寫這書的時候都算在認識的過程中,但比過去的認識深了,處理的題材還都是這類題材,個人生活有什麼區別呀,都在家呆著呢。
問: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答:我沒有了。說真的,我特別猶豫,原來我想再寫一點,但也不想寫了。這裡頭,我也需要一個勇氣,我的勇氣也有限。簡短點吧,說多了反而言不由衷。最後想對我媽說聲:對不起。要是冒犯了誰使誰不痛快了請你這麼想:反正咱們也不會永遠活著,早晚有一天,很快,就會永不相見。
2007.8.28.下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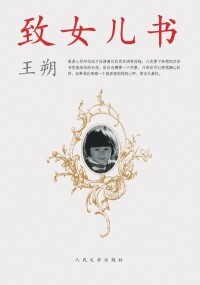
致女兒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