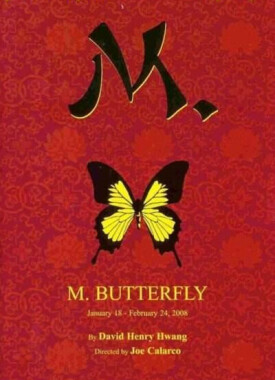蝴蝶君
1986年黃哲倫創作的話劇
《蝴蝶君》是美籍華裔劇作家黃哲倫所寫的話劇劇本。該作講述冷戰時期,一名男性法國外交官迷戀上一個中國京劇演員,他們熱烈相戀,在一起生活了20年,還生下了一個孩子,可是結果,他卻發現她是一個男人。
該作以歌劇《蝴蝶夫人》作為顛覆的原型創作而成,著力探索的是民族與種族、東方與西方、性別與政治、身份與認同,乃至殖民與后殖民等等重大文化命題。
黃哲倫塑造了一個用西方傳統思維和觀念看待東方的主人公,法國外交官瑞內·伽里瑪,正像《蝴蝶夫人》中的來到日本的美國海軍軍官平克頓一樣,當他來到中國后遇見並喜歡上在舞台上扮演蝴蝶夫人的京劇演員宋麗玲時,他以為宋麗玲就是他的蝴蝶夫人,並且會像那位痴情於平克頓的日本藝妓秋秋桑那樣傾倒於自己,並且會因為失去自己的愛而自殺。這當然是個錯覺,實際上,真正的事實是他反過來被宋麗玲控制了。而他一直身陷自己――同時也是西方人所建構的對東方的單向的想象中,直到局終,真相大白,他才明白自己所付出的代價,但卻為時已晚。
《蝴蝶君》有著真實的故事“本事”。劇中京劇演員宋麗玲的原型就是時佩璞,一位集演員、間諜於一身的傳奇人物,2009年6月30日在巴黎逝世,終年70歲;而劇中的瑞內·伽里瑪,也實有其人,他就是伯納德·布爾西科,曾經的法國駐中國大使館官員。當然,把劇中人與現實人對上號,已經是後來的事,黃哲倫當初創作《蝴蝶君》,僅僅憑的是1986年5月11日《紐約時報》對這一離奇間諜案件語焉不詳的報道。所以,《蝴蝶君》不是忠於歷史史實的紀實性劇本,而是黃哲倫基於一個基本事實的文學性再創造。
伽里瑪
伽里瑪是法國駐中國大使,他相信,只要他能對一個關麗而又順從的東方女子施加權利,就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當法國大使就越南局勢徵詢他的意見時,伽里瑪便以宋對自己的順從、依附為依據,傲慢而又可悲地認為只要關國人表現出取勝的意志,越南人肯定樂意與他結盟,並且說東方人總是屈服於比他們強大的敵人。從伽里瑪的判斷中可以看出他自恃作為西方人的優越感和狂妄,他沉浸在愛情和事業的自信和興奮之中。而他沒想到的是正是他的這種傲慢和狂妄被宋利用,一步步陷入了“她”設訓一的陷阱之中。他為了愛而拋棄了自己的妻子,泄露了國家機密,失去了關好的前程,最後身敗名裂。而更為殘酷的現實卻是,他心口中“完關女人”竟是男兒身,二十多年來他所迷醉的只是一個關麗的幻境。在劇的最後,伽里瑪而前的宋不再是他想象中的那個順從、羞怯的東方蝴蝶,而變成一個與他對質的東方男人。他對東方女人的想象化成泡影,最後不願面對這個殘酷的現實自殺身亡。伽里瑪的結局是他受西方社會對東方的偏見的影響造成的,西方文化對東方的偏見使他成為犧牲品。
宋麗玲
宋麗玲是中國京劇演員,與伽里瑪的傲慢相對照,宋在與他的交往中處處故意表現為順從、卑下,讓他認為宋是個真正的東方女人。宋裝扮成符合伽里瑪想象中的東方女人的刻板形象:害羞、迷人。宋麗玲正是抓住了西方社會中的東方主義思想誘使伽里瑪一步步進入他的圈套達到他的目的。宋麗玲最後達到自己的目的以勝利者的形象出現。
由《蝴蝶君》這一書名,不難看出,黃哲倫是要寫出一部“偉大的《蝴蝶夫人》似的悲劇來”,或者說,他是要解構蝴蝶夫人這一對東方女於的刻板印象,顛倒《蝴蝶夫人》一劇中所隱含的東西方的權力關係和性別關係。
眾所周知,普契尼的《蝴蝶夫人》講述的是一個失敗的異族婚姻關係的故事。黃哲倫寫出了一部男女關係、東西方關係以及殉情方式都顛倒過來的《蝴蝶君》,不僅解構了西方人心目中東方女子作為蝴蝶夫人的刻板印象,而且也顛倒了原有的東西方權力關係,成為與西方中心主義相對立的他者的聲音,對原有的東西方關係中潛在運作的文化與權力關係進行了一次驚人的倒置,倒置原有的角色關係:無怨無悔的東方女子和殘忍薄情的西方男子,黃哲倫試圖打破西方白人男子腦海中關於東方女子等同於蝴蝶夫人的刻板印象。
《蝴蝶君》一劇曾被視為是一部反美戲劇,但是黃哲倫在該劇中並不是要宣揚東風壓倒西風的政治觀點,而是希望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今天,東西雙方都能反省自我,豐富自我,彼此坦誠相待。“切穿層層的文化和性別的錯誤感受”,拋棄舊有的刻板印象,由對立、對抗轉為對話和交流,這就是黃哲倫在《蝴蝶君》一劇中所要表達的觀點。
如果撇開意識形態的問題去看,伽里瑪的悲劇是一則最為典型的因認識滯后而導致的悲劇案例。他站在所謂西方人的立場上,臆造出一種逆向思維的產物,而所有和東方有關的形象均是和西方對比后得出的,是與所謂西方形象完全對立的存在。形象學研究中,形象具有三重意義:異國的、出自一個民族(社會、文化)的、由某一個文人創作完成。當主觀性的認識偏離航向時,形象就會滑向“幻象”的一邊。最有名的例子是斯達爾夫人給我們帶來的伽里瑪在追逐“幻象”的歷程中,始終沒有真正關照過東方文明的主體、東方人個體的差異、現實和幻象的區別,因此,他的悲劇是集體無意識的悲劇,也是個人無知的悲劇。
《蝴蝶君》一劇中在對《蝴蝶夫人》的模擬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戲劇語言,雖然這齣劇中的人物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又都從事著高尚的職業,但觀眾看到的法國外交宮不講法語,中國演員不講中文,日本女僕鈴木也不講日語,他們都講著英語,而且是充斥著不登大雅之堂的俚語、俗語的英語。這樣貌似荒誕的做法在觀眾的期待與舞台表演、演員與角色、觀眾與人物之間拉開了距離,而也正是這種“間離的效果”打破了故事的現實性與特定的歷史性.也就是布萊希特所強調的“歷史時間錯位和文化發生斷裂”,使劇作獲得了發生在不同時間的歷史事件在不同的文化空間相互碰撞、談判的可能性,從而使現實的和特定歷史情景中的事件獲得了普迫意義。正是這種戲擬放的語言運用有效地改變了對蝴蝶夫人僵化、固定的注視方式,使它原有的文化象徵符號意義得到了徹底的消解。劇作者時刻沒有忘記模擬的本意,沒有忘記讓我們時刻置身於被模擬者那宏大的殖民敘事框架之內:那一直貫穿全劇、重複出現的《蝴蝶夫人》台詞(如“屈辱的生不如榮譽的死”)和歌劇一遍遍響起的主題音樂旋律,使讀者時刻不忘這是對《蝴蝶夫人》所代表的殖民話語刻意的模擬、含混與消解。
黃哲倫很好地運用了戲劇誤會的方法,使得觀眾在最終有一種謎底昭然若揭的快感。宋麗玲的男身女扮在戲的前部分已有表露,但男主角伽里瑪卻陷在這種身份的隱瞞中,他尊重東方女性,但並不了解,只能通由《蝴蝶夫人》這樣的藝術方式來誤讀東方女性的脆弱和她們看似矜持的外表,在戀愛的過程中使自己化身為劇中男主角,他的行為看似在憐憫對方,代替劇中人來撫慰對方的傷痛,實際上卻迷失自我,深陷這種誤讀的情緒里無法自拔。
關於此劇本涉及的性的層面,實際上放大了西方社會的愚昧無知,它的尖銳在於表現這種對待兩性問題的東西方的態度,的確,它也包含了時代性、政治性,然而“性”是它無可避免的一個手段。直至最後宋麗玲在伽里瑪面前赤裸相向,使得此前一直深埋觀眾心底的那層誤會(人物不知,觀眾知)赫然撥開,抵達最高潮的部分。
《蝴蝶君》是黃哲倫的代表作,獲得托尼獎最佳戲劇獎。
《蝴蝶君》的劇本自從20世紀80年代誕生以來,被搬上百老匯的舞台,又經傑瑞米·艾恩斯和尊龍的電影演繹,影響遍及全球。
這本書的影響如此深遠,被作為眾多國家英美文學系的教材,情節的離奇是最直接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