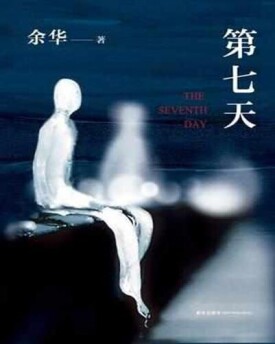第七天
余華創作的長篇小說
《第七天》是中國當代知名作家余華繼《兄弟》之後,時隔七年後最新長篇小說。用荒誕的筆觸和意象講述了一個普通人死後的七日見聞:講述了現實的真實與荒誕;講述了生命的幸福和苦難;講述了眼淚的豐富和寬廣;講述了比恨更絕望比死更冷酷的存在。
《第七天》選擇一個剛剛去世的死者“我”(即楊飛)作為第一人稱敘事者,由“我”講述死後七天里的所遇、所見、所聞之事與往事,“我”力所不及的一些故事或故事片段則蟬蛻給與“我”相關的他者,由他者以第一人稱講述自己所遇、所見、所聞之事與往事。
主人公楊飛是主環,這一主環分別連套一些不同的次環,次環又連套次次環,從而形成多重連環式結構模式。分別是楊飛——李青——李青的後夫,楊飛——楊金彪——生父生母一家,楊飛——楊金彪——養父兄弟姊妹,楊飛——鼠妹與伍超——肖慶,楊飛——李月珍夫婦——楊金彪,楊飛——李月珍夫婦——二十七個嬰兒等均構成一個個三連環結構。三連環結構涉及第一人稱蟬蛻敘事。所謂第一人稱蟬蛻敘事是指由第一人稱敘事者“我”蟬蛻到下一個以第一人稱敘事的敘事者的敘事方式。楊飛到“死無葬生之地”后不久,遇到“我”出租屋的鄰居“鼠妹”,她認出新到的防空洞地下室的鼠族鄰居肖慶,肖慶為大家帶來了“鼠妹”的男朋友伍超在陽界的消息。於是,故事的講述者就由楊飛蟬蛻到“肖慶”,然後“肖慶”以第一人稱為大家講述“鼠妹”到“死無葬生之地”后大家所不知道的關於伍超的故事。
| 章節 | 標題 |
| 第一章 | 第一天 |
| 第二章 | 第二天 |
| 第三章 | 第三天 |
| 第四章 | 第四天 |
| 第五章 | 第五天 |
| 第六章 | 第六天 |
| 第七章 | 第七天 |
2014年5月,余華在答《京華時報》記者問時說,他一直有這樣一種慾望,“將我們生活中看似荒誕其實真實的故事集中寫出來”,“讓一位剛剛死去的人進入到另一個世界,讓現實世界像倒影一樣出現。”余華試圖同時塑造死者世界與現實世界,並通過死者來描寫現實世界。在《第七天》里,用一個死者世界的角度來描寫現實世界,這是我的敘述距離。《第七天》是我距離現實最近的一次寫作,以後可能不會有這麼近了,因為我覺得不會再找到這樣既近又遠的方式。”余華塑造的近景世界是現實世界,遠景世界是死者世界,其現實世界是一個荒誕的、冷酷的世界;死者世界是一個至善的、溫暖的世界。正如他所言,“在寫的時候感到現實世界的冷酷,寫得也很狠,所以我需要溫暖的部分,需要至善的部分,給予自己希望,也想給予讀者希望。現實世界令人絕望之後,他寫下了一個美好的死者世界。這個世界不是烏托邦,不是世外桃源,但是十分美好。”通過這兩個世界的描繪,作品呈現出複雜豐富的社會生活畫面,以揭露各種社會矛盾衝突,給予作者的愛憎褒貶之情,體現作者強烈的現實批判精神和鮮明的理想主義情懷。於是,余華藉助於《舊約·創世紀》開篇的方式,儘管中國有頭七的說法。余華寫作的時候“不讓自己去想頭七,腦子裡全是《創世紀》的七天。”在《第七天》的正文前,作者引用了《舊約·創世紀》中的一段話,“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這段引文告訴表明,小說《第七天》的外在形式藉助於《舊約·創世紀》的“七天”,其七個部分分別以“第一天”、“第二天”乃至“第七天”命名,但其內容不是機械地與《創世紀》的七天一一對應。
《第七天》廣泛涉及官僚腐化、官民對立、貧富分化、道德淪喪、價值觀混亂、暴力執法、食品安全、農村留守老人和兒童、城市鼠族等各階層各方面的問題,其通過雜聞的“信息價值”和隱喻功能來對當下政治發言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此外,余華對眾多雜聞進行了改寫,這種改寫不是隨意的,而是慎重的,這也並不單純是一項技術問題,改動多大程度,朝哪個方向改,怎麼結合雜聞和文學想象,都包含著余華對這些社會新聞的認識和理解,折射著余華對這個社會的思索和期望,也暗示了作為作家的余華在對這個社會發言時為自己選擇的立場以及他對發言尺度的考量。《第七天》幾乎零距離地逼近社會現實,使小說文本與社會文本對彼此完全敞開的原因吧。平心而論,余華的鋌而走險不能說是失敗的。在余華自己,他又完成了一次自我突破和藝術蛻變,他為“政治”寫作的初衷基本實現了;對中國當代小說而言,《第七天》提供了處理當下題材的另一種新的方式和可能性。當然,在收穫政治性的同時,《第七天》也付出了藝術性不足的代價,這從人物形象的蒼白、細節的粗糙、情緒的泛濫以及語言的乏味等方面,都可見一斑,這裡不細論。
《第七天》描寫的都是日常見怪不怪的新聞事件。譬如,暴力拆遷、災禍後有關方面瞞報死亡人數、醫院將死嬰做醫療垃圾處理、冤假錯案、刑訊逼供、男子假扮女人賣淫,等等。每個人,他身邊發生的事情都不是新聞了,因為我們在一個巨大的新聞裡面,而在新聞裡面發生的暴力拆遷等,只不過是這個巨大新聞裡面的日常生活,所以處在這樣的一個現實當中的人有一個怎麼來理解今天這個時代的問題。
《第七天》藉助一個死人赴死的魔幻故事外殼,將一段衍生於中國當代的殘酷寫真展現了出來。用文藝作品觸及讀者的心頭之痛似乎並非多有難度之事,而是在觸及之後還要留有餘響和餘震則變得鳳毛麟角。《第七天》中的“我”在餐館吃飯意外死亡,揭示了一種唐突的、貿然的命運降臨,它不寄託於非凡或者離奇的生活,而是對苦命的一種無可奈何。而這如何造成的,以及現實對悲劇性命運的反饋又是如何影響的,我們的作家連追問和冒犯的心思都沒有,在殘酷而凜冽的現實面前,自己的意志力和能力已率先被敲打得七零八碎。
《第七天》的不同之處在於它藉助新聞熱點,但非為了製造噱頭。相反,這種處理會讓讀者的悲喜更身臨其境,感慨更深。漆黑之中,余華小心翼翼地擦出一束束溫暖的火苗,給死去的人最體貼細微的安慰,不至於讓讀者在喘息間完全絕望——李青死後懺悔,承認丈夫只有楊飛一人;鼠妹的男友伍超雖然最後死於賣腎,但他並未為了物慾而是希望圓滿真愛;鄭家夫婦無辜,不過他們有個最堅強懂事的女兒;飯店老闆譚家鑫生前善良體貼,至死也沒有奪走他快樂的希望,“一家人能在一起,到哪裡都是好”;說到最曲折離奇的李姓男子被掃黃警察張剛踢爆睾丸而尋仇殺人的恩怨,兩人死後也一笑泯恩仇,成了最好的棋友。
講述一個人死後七天的經歷。這個人沒有墓地,無法安息,在生與死的邊境線上遊盪,然後來到一個名叫死無葬身之地的地方,那裡聚集了很多沒有墓地的死者……那裡人人死而平等。
《第七天》體現了余華對現實的焦慮和絕望,他對現實中的慾望、混亂、不公平和弱肉強食的極度憤怒。洪治綱認為,余華採用了“用死者來觀看生者”迴避了正面敘述的尖銳性。《第七天》里建立了兩個完全相反的世界生的世界和死的世界。每一個篇章,余華都花了大量篇幅,來描寫沒有等級、絕對平等的人道世界,充滿了歡樂的、創世紀般的祥和世界。
《第七天》採用的社會新聞正是當下社會或剛剛謝幕或正在上演的景觀,其荒誕之程度遠遠超乎作家的想象,作家又何必再費心思編造情節。把雜聞原樣照搬進小說文本,迅速編織出小說文本的當下背景,使小說文本具備了與當下社會共在的現場感,使其與社會文本的對話在同一個舞台展開。小說文本與社會文本就成了彼此敞開的空間,雜聞的大量存在標誌著小說進入了一種探索活動,它力求在現實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中思考並闡釋現實。《第七天》採用雜聞這一點上放棄了經典現實主義的做法,而轉向了探索。他的目的不再是要讀者相信經他以雜聞為底本改造而成的故事是真實的,而是以這些故事作為話語標記,在文學想象與社會現實之間搭建一些可被讀者辨識的聯繫,提醒讀者小說與社會是相互指涉的,啟發讀者由一個空間走入另一個空間,真正關注現實社會的荒誕,真正思考自己以及整個中國的命運。
《第七天》引用雜聞的做法所提供的更多的是一種真實的幻覺,不論是似乎無所用心的雜聞拼貼,還是對可以大做文章的事件的輕描淡寫,都反映了作者或諧謔而近於遊戲的或冷靜而近於冷漠的筆調,這種筆調的意蘊耐人尋味:荒誕才是最大的真實,荒誕已是司空見慣。這層意蘊的底色是十分灰暗冰涼的,它透露著作者對現實深深的絕望和無奈。《第七天》與社會的互文是如此強烈,難怪會有人認為余華是借這部小說來探政治的底線。這種揣測並非無稽之談。“真實的雜聞故事往往顯現為一些揭示性的社會縮影,具有一定的信息價值。某些從社會現實中剪切的片段,表面上無足輕重、虛假且平庸,但卻顯露出某種預兆。在政治當局掌控下的時間及空間的結構中,人們可能會在日常現實的縫隙中,發覺一種正在孕育的未來,06隱約感受一些難以進行理性分析的新現象的成型。”“雜文故事更進一步地構成了展現現實問題的前提,引導讀者從原本事實的戲劇化畫面背後發掘涉及社會和意識形態的複雜現實。
《第七天》雖然荒誕有餘,並未帶來像《活著》的那種厚鉛壓心頭的沉重。以楊飛的視角為基點,關聯起網狀的人物關係,打通了這個城市各類小人物的生老病死,結局哪怕仍有悲壯和諷刺的意味,但並不妨礙他勾勒出心中烏托邦的輪廓。人人死而平等”,置於死地而後生是一種恩慈、一線憐憫,我相信這是《第七天》的創作初衷。就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說的,“與其咒罵黑暗,不如燃起一支明燭。在《第七天》中,余華就是這個舉燭人,而我們借著燭光,看清了來時路,抓住了延續的意義和溫暖,《第七天》的文學細節處理得相當好,既沒有刻意迴避,也沒掉進去。”“很多人批評《第七天》像新聞的部分,其實正是這部作品里特別重要的真實的文學細節,這些活生生的生活用文學的方式表達出來,它才能跨越時間、國界,沒有這樣的真實,《第七天》就失去色彩了。
陰陽兩隔,逝者如何得知生者的境遇,以此為主題的小說並不多見。而余華的新作《第七天》,卻以此為切入點,通過主人公楊飛穿梭於陰陽兩界,敘述7天中那些不堪的死亡事件,用回憶將故事串聯,追憶和思考愛恨情仇,將生者與逝者的種種不堪與悔恨傳遞給每個無家可歸的遊魂。一種宗教式的懺悔情愫充滿著全書中每個逝者的靈魂,也讓讀者更深地懂得生命的價值。
《第七天》中的荒誕與黑色幽默,空間與空間迅速變換,時間與時間顛倒更替,情節內容的怪誕離奇,一直是余華小說的敘事風格。把看似不合情理、不符敘事邏輯的情節支撐故事的鋪陳,摒棄傳統小說里注重時間的時序性與完整性的敘事脈絡,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如果把每個看似不合情理、不合邏輯的情節放之於夢境中,瞬間荒誕的情節,都變得如此的合乎情理、符合敘事邏輯,而落在現實世界,故事便顯得荒誕不經。
小說《第七天》並沒有擺脫余華一直以來的荒誕、黑色幽默的敘事風格。《第七天》以馬爾克斯式的敘事開頭,通過回憶講述故事的原委,藉助於類似但丁《神曲·地獄篇》式的表現手法,對當下中國社會的現實進行些許勾勒。不同的是,小說中布滿了大量的描寫死亡的情節,在這些不同的死亡故事中,既有作者刻意擷取的,又有作者隨意而為的。比如,鼠妹為男友的假手機欺騙事件而死,伍超為愛情賣腎而死……凡此種種,無不勾勒了人性中殘忍、黑暗、醜惡的一面。
余華的《第七天》把中國人的悲哀和善良都寫絕了。
——北大教授黃燎宇
網友之所以會認為余華只是在做新聞剪報,是因為余華寫的是我們已經視而不見的日常生活,太真實,觸及了我們這個時代一些我們遠遠沒有講清楚、不願意講的東西。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
《第七天》是一個值得精細閱讀的文本,絕不是網傳那樣簡單的新聞堆砌和記錄。
——北師大學教授張檸
《第七天》將視覺延伸到了整個社會,裡面反映了一群人物的悲慘命運,在小說中讀者能夠真實地看到渺小而平凡的自己。——青年作家賈飛
| 2014年4月12號 | 余華憑《第七天》獲第12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作家” |

余華
1978年,高考落榜後由父母安排進入衛生院當牙科醫生。1983年,發表個人首部短篇小說《第一宿舍》。1987年,發表《十八歲出門遠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等短篇小說,確立了自己先鋒作家的地位;同年,赴北京魯迅文學院進修。1990年,通過作家出版社出版首部小說集《十八歲出門遠行》;同年,出版首部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1992年,出版長篇小說《活著》。1995年,創作的長篇小說《許三觀賣血記》在《收穫》雜誌發表。1998年,憑藉小說《活著》獲得義大利文學最高獎——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
2003年,英文版《許三觀賣血記》獲美國巴恩斯·諾貝爾新發現圖書獎。2004年,被授予法蘭西文學和藝術騎士勳章。2005年至2006年,先後出版長篇小說《兄弟》的上下部,該書因極端現實主義的寫作,曾在中國引起爭議。2008年5月,出版隨筆集《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10月,憑藉小說《兄弟》獲得法國國際信使外國小說獎。2013年,發表長篇小說《第七天》,並憑藉該小說獲得第十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作家獎。2015年,出版首部雜文集《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2018年1月,憑藉小說《活著》獲得作家出版社超級暢銷獎;7月,出版雜文集《我只知道人是什麼》。2021年,出版八年來的首部長篇小說《文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