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3條詞條名為玉鼎真人的結果 展開
- 《封神演義》角色
- 藤崎龍改編日本動漫封神演義角色
- 電視劇《封神榜》中角色
玉鼎真人
藤崎龍改編日本動漫封神演義角色
玉鼎真人,藤崎龍改編日本漫畫《封神演義》 及日本STUDIO DEEN製作動畫《仙界傳封神演義》中登場的男性角色。楊戩的師父,對於楊戩來說像是父親般的存在,在王天君的紅水陣中為了保護楊戩而遭封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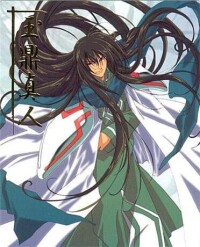
玉鼎真人
相對於太乙,普賢,道德,和雲中子等等各有各的怪癖和執著的表現,玉鼎正常得根本就是十二仙中的異類。但也是因為太過於“正”,在陰謀面前就格外脆弱。從某種意義上講,玉鼎比普賢更天真。與孫天君的戰鬥中,憤怒地吼著“居然不現身,簡直是卑鄙小人”的同時,他就自己意識倒如果單獨面對“奸詐的敵人”,很容易就會犧牲掉。有了這樣的自知之明,當他為了營救楊戩而獨自踏上王天君得空間移動寶貝時,大概也已經有了死的覺悟了吧。王天君,畢竟是與太公望匹敵的陰謀家,他很快就抓到了玉鼎真人表面上的無懈可擊背後那個致命的弱點——對楊戩的溺愛。太公望如此評論玉鼎的行為:“和太乙一樣過分保護自己的弟子”如果說太乙對哪吒屢次威脅師長的縱容是過分保護,玉鼎對楊戩逃避自己身份的縱容就是溺愛了。不同於太乙創造了哪吒,楊戩是作為妖怪的人質交給玉鼎的。如果說毫不顧忌身份的區別盡心地教養楊戩,將他培養成出色的道士僅僅是出於正直,幫助楊戩自欺欺人地喬裝人類的所為,就已經超出一個師父所該做的了。雖然出發點是為了讓年幼的楊戩免於遭人排斥帶來的心靈創傷,卻也造就了楊戩最大的弱點。即使有天才道士的稱號,有敏銳的洞察和分析能力,卻不敢面對自己是妖怪的事實,無法對任何人敞開心扉,以爭強好勝掩飾著孤寂和恐懼。這個弱點抑制了楊戩發揮自己真正的實力。但即使意識到這一點,玉鼎也沒有推動楊戩,告訴他不應該繼續逃避;卸去自身的偽裝必然會經歷一個痛苦的過程,可是他更本不忍楊戩受到任何的傷害,於是只是耐心的等著,等著楊戩自己的覺悟,等著他為了要保護的人們而自己拋下這個桎梏。所以,那已經是溺愛了。因為這份溺愛,此後玉鼎的一舉一動都正中了王天君下懷。為了不讓楊戩的真實身份暴露,他拒絕了太公望的幫助,獨自赴約;為了保護虛弱的楊戩,他放棄了與王天君戰鬥;為了把楊戩帶出血雨陣,他如王天君所期望的那樣,一步步在高度腐蝕的血雨中前行,直至在楊戩面前灰飛煙滅,只餘一屢魂魄往封神台而去。說是煽情也罷,那一幕滴落的鮮血,溶化的長發,和佝僂著腰把楊戩如嬰孩般護在懷中步步前行的身影,以及不經意般的一句“楊戩,你長大了”,無法不讓人心頭壓上一塊巨石,緊得發慌,慌得不覺淚水已經悄悄上來。不得不說,玉鼎的犧牲他自己有一大部分責任。是他的溺愛,造成了楊戩的軟弱,造成了讓王天君有機可乘,間接造成了他自己的死。可是誰又忍心去指責他什麼呢?只能說“可憐天下父母心”吧,玉鼎之於楊戩,已是遠勝於父親的存在。
玉鼎應該料想不到正是他自己的死推動了楊戩,不僅去正視自己身為妖怪的身份,當著眾人的面解放了更強大的半妖形態;更是不再逃避自己是通天教主兒子的事實。王天君也有失算的時候,楊戩的妖怪身份沒有引起抵觸,楊戩亦沒有與親生父親自相殘殺。從幼年的耐心開導,直至臨死的囑託,那個一身正氣的師傅,慈愛溫和的師傅,從未教給楊戩憎恨。相比起那個意氣用事地說“告訴我父親,我是人類,就是這樣。”的天才道士,當半妖的楊戩說出“從今以後我也一直會是昆崙山仙人的同伴,但也會是妖怪。”時,玉鼎真人也當可以含笑再說一句:“楊戩,你長大了。”作為師長的玉鼎真人,從出場到犧牲都是作為楊戩渡過難關,超越自我的踏腳石,這是從他自元始天尊手中接過幼年楊戩時就已經註定的宿命;而玉鼎本人,只要看到楊戩能夠在他自己的舞台上好好表現,就已心滿意足了吧。並不需要歷史的認可,那個佝僂著腰緊抱著懷中稚嫩靈魂的身影,只要永遠存於一個人的心中,便已足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