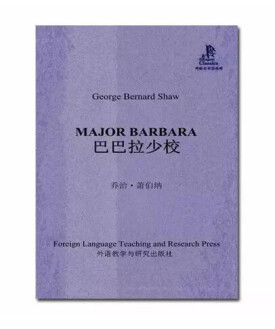巴巴拉少校
巴巴拉少校
肖伯納在劇本結束時並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是劇本明確反對貧富不均,揭露資產階級的慈善事業和議會制度的本質,仍具有積極的意義。主人公巴巴拉是個有理想的青年,虔誠的基督教徒,救世軍中的少校。她認為宗教是整個社會的基礎,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女兒,而她的理想就是在救世軍中拯救窮人的靈魂。救世軍的慈善事業需要金錢,由於經費短缺,巴巴拉所在的救世軍收容所面臨困難。巴巴拉的父親安德謝夫是軍火商,他出於個人的目的,在參觀收容所時當場捐出5000英鎊。
《巴巴拉少校》以救世軍為題材,反映了貧富不均和勞資衝突等尖銳的社會問題。《巴巴拉少校》不僅抨擊了社會上貧富懸殊等醜惡現象,還揭露了資本家培養工人貴族的陰險用心。資本家在工廠里建立一套等級制度,藉此分化瓦解工人隊伍。安德謝夫收買“救世軍”,就是為了利用各種慈善措施來緩和工人們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比得·舍爾利是劇本中的正面形象,他雖然被解僱並因此而流落街頭,但依然保持著人格的完整。
肖伯納在劇本結束時並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是劇本明確反對貧富不均,揭露資產階級的慈善事業和議會制度的本質,仍具有積極的意義。
戲劇的主人公巴巴拉是個有理想的青年,虔誠的基督教徒,救世軍中的少校。她認為宗教是整個社會的基礎,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女兒,而她的理想就是在救世軍中拯救窮人的靈魂。救世軍的慈善事業需要金錢,由於經費短缺,巴巴拉所在的救世軍收容所面臨困難。巴巴拉的父親安德謝夫是軍火商,他出於個人的目的,在參觀收容所時當場捐出5000英鎊。巴巴拉起初說服救世軍,希望他們不接受父親的金錢。她和父親的衝突,是經濟和信仰的衝突,理想和現實的衝突。巴巴拉後來在別人的勸說下,還是要了這筆錢。人們在安德謝夫走後,感謝他的善行。巴巴拉的幻想破滅,痛苦地摘下救世軍領章,別在父親的衣領上。而當安德謝夫要收買救世軍時,她終於屈服,相信是“威士忌大王”鮑吉爾和軍火商救活了窮人。如果她離開父親,就是“離開生活”。巴巴拉的轉變雖然顯得唐突,但也並非完全不可能。巴巴拉的精神苦悶,也表達了一些和上層社會有千絲萬縷聯繫的青年知識分子的苦悶。
軍火商安德謝夫在劇中佔有中心的位置。他厚顏無恥、貪得無厭,認為金錢萬能,聲稱買進賣出是他的哲學,利潤是他的宗教信仰,而金錢與火藥是他的宗教基礎,他自己就是國家和政府,是真正的統治者。國家只不過是為資本家服務的機器而已。他認為貧窮是最大的罪惡,要消滅貧窮就需要儘可能地賺錢。但是,他的“死亡工廠”無疑揭示了資本家財富的本質。
巴巴拉的戀人、詩人科森斯是個實用主義者。他曾經批評軍火大王。為了追求巴巴拉,而混進救世軍。他的出身在澳大利亞符合法律,在英國則是一個私生子,因為怕人們歧視,隱瞞了自己的身份。時機一到,他便拋棄自己的理想,公開自己的身份,同意做安德謝夫的助手,並且成為“死亡工廠”的繼承人。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金錢的腐蝕力量。
肖伯納的喜劇形式和以前人的的確不一樣,而且和之後的布萊希特、迪倫馬特,荒誕派的劇作也有明顯的不同。在這裡,主要不是和同時代或者後人比;而是著重於其本身的一些特點,還有和傳統的喜劇的不同。之所以稱為“淺見”,是因為學力使然,也因為所涉及的劇本面十分窄,主要只是拿《巴巴拉少校》來進行簡單的評論,旁及其他。而且別人的評論也沒有很看,只是算“管窺”“謬評”一下而已。
我們不妨先看看古典喜劇的一些特點,或者說,一些套路。諾斯羅普·弗萊所寫的《春天的神話:喜劇》中,讓我們看到了古典喜劇的一些模式的總結。他說“在喜劇中,我們常常見到一位小夥子,想得到一位姑娘,他的願望往往受到某些對立面(通常是父母)的阻撓,但是在戲快要結尾時,情節中的某一轉機,卻使主人公如願以償。”他還告訴我們“構成喜劇情節的是主人公願望受到阻礙,而克服這些阻礙即構成了喜劇的情結”,緊接著,他還補充了一句“阻礙通常來自父母,因之,喜劇往往圍繞父子之間不同的衝突而展開。”這樣的經典範例就是普勞圖斯的《一壇金子》。而且,從人物的角度,《一壇金子》也是範例,老一代人是頑固而愚蠢的。他們是年輕人的阻礙,可是由於他們的過度愚蠢,所以自己老是處在受愚弄的尷尬境地。但是由於喜劇的本質使然,弗萊寫道“喜劇傾向於盡可能多將各種人物包容在它最後形成的那個社會裡:起阻撓作用的人物,大多可以回心轉意,重歸於好,而不是把某個人簡單排斥在外。”年輕的人呢,往往是性格單一而中性的。他們並沒有太多可以被記住的東西,弗萊談及時就說道“興趣只集中在起阻撓作用人物身上”。其實可以對比的還有很多,但是先就結構和人物來說。
我們如果看了《芭芭拉少校》,就會發現這部劇的確“很古典”。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它的結構是和古典的一樣,圍繞著新老兩代人展開的。雖然老的一代人不是典型的阻撓愛情的勢力,但是可以感覺到某種威脅。也就是新老兩代人完全不同的思想思維所帶來的衝突。年輕一代人的願望照例是受到老一代人的阻礙。而且最後還是以大完滿,沒有排斥任何人而告終。
可是如果談到了人物,就發現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了。首先,我們發現一個特點,就是肖伯納的劇作里沒有真正的“蠢人”。老一代的安德謝夫和薄利托瑪夫人都不是傳統意義上“容易被欺騙的頑固、愚蠢的老年人”,相反,他們非常有人生智慧。年輕一代人也不是紙片一樣單一性格的,無論作為主角的巴巴拉和柯森斯,還是配角的莎拉和勞邁克斯,都是很精於世情的。傳統的喜劇是並不平等的,人物一開始出場就不在一個高度,有的人物一出場就是被人欺騙的愚蠢之物,而劇作家的作用是讓人們一起看他如何的出乖現丑,以次達到諷刺的效果。人們心理早就有預期了,只是在這裡看看過程,解解恨,笑一笑。可是在肖伯納的《巴巴拉少校》里我們看到的人物卻在一個平台,一個水平線上,他們在互相控制與反控制。觀眾不可能馬上看出來誰是最後的贏家。所以人們的興趣依然“只集中在起阻撓作用的人物身上”,但是每一個人都是阻撓者,好像是打牌一樣,每一個人都有一副牌,但是贏家只有一個,這讓人感到未知,可是他們都“拭目以待”呢。這樣就直接導致結構和情節上與傳統喜劇的不同了。首先,這不是以愛情為中心主題的了,第二,由於沒有了明確的阻礙者和被阻礙者,所以情節就不是圍繞著“克服阻礙”展開,人們的興趣點也不是這裡了,而轉為了“誰會贏牌”。這樣,真正的階層意義也就取消了。在這裡,我們不會認為安德謝夫和柯森斯的距離會比柯森斯和巴巴拉大,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在互相做這場遊戲。所以我們最後發現,這不是有勢力的老一輩和有聰明的年輕一輩的鬥爭,而是誰能更好地說服誰的問題。
我們首先看安德謝夫。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人,因為他不是懷疑論者,而是無比堅定的信著自己的一套東西。他相信只有金錢和權利才能使人們幸福,他相信這些實實在在的東西比什麼宗教、藝術、精神強多了。他給巴巴拉出牌的方式很簡單,就是他去巴巴拉的地方一趟,讓巴巴拉來自己的地方一趟,比較就行了。他是這場精神鬥爭遊戲的贏家。因為在現實上,巴巴拉所帶他去的自己的理想之地——救世軍收容所,弊端百出,而且工作艱難,尤其在需要錢的時候,是安德謝夫慷慨解囊,而救世軍好像對待聖人一樣對待這樣一位居心叵測的施主。這使巴巴拉精神危機並最終放棄了救世軍的方式。但是他帶一家人去看自己的製造殺人武器的工廠時,人們看到的卻是非常完美的一個小鎮。一切問題都由於基本物質問題解決而解決了……他的牌總是非常好,自己也堅信這一點。作為解決了問題的人,他也無愧於這一點。這讓我想起了肖伯納本人,他是一個費邊主義者,但是費邊主義者本身也應該是社會主義者。雖然我們說肖伯納在這部劇中是揭露和抨擊萬惡的帝國主義者的,但是我覺得說這句話並不硬氣。因為我們可以發現首先肖伯納在劇中對安德謝夫的態度並不是什麼批判,作為一個敘述牌局的人,他盡量做到不加自己的好惡。但是在實際上最終的勝者是安德謝夫(雖然他沒有真正征服巴巴拉的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沒有改變,而其他人的思想卻因他而改變了),作為喜劇的結尾,人們總是站在勝者一邊的。所以這部劇本身會牽引觀眾去認同安德謝夫,至少是不很反感他。而且,由於他一直站在一個思想上可以戰勝別人的強者和智者的地位,人們更沒有理由去認為肖伯納是要揭露與批判這個人物的萬惡本質。總結一下,我們第一,看到肖伯納並沒有反對者個人物;第二,我們看到這個人物在這部喜劇中勝利了。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肖伯納對於這個人物是有很大程度上認同的。想想看,肖伯納是個社會主義者,而且是不反感,甚至支持暴力和強權的社會主義者。雖然他本身支持費邊主義,但是,正如弗蘭克·赫里斯所說的“當列寧在一九二一年象托洛茨基槍殺白沙皇黨人那樣,忙於槍殺無政府主義者時,蕭把一本題上贊語的書贈送給了列寧。這本書已經用平版印刷出版,流傳於蘇聯了……蕭和墨索里尼一樣,相信自由是一個腐爛的屍體,他指望通過建立奴隸制的科學組織,他說這是政府唯一的工作,也是大自然的一條不變的規律。”看了這段話,我們就不奇怪安德謝夫這個人物了。安德謝夫在劇中反對的主要是宗教,就是巴巴拉的那個救世軍。他揭露了宗教的許許多多的虛假倒是真的。而自己的想法卻和赫胥黎的《天演論》,以及許多唯物主義的概念不相悖。他的肯定現實存在的態度,使我們不但會想到“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還會想到許多別的我們課本上認同的東西,而他的一切東西都不如他的軍火大炮的觀念,也讓我不得不想到我們的“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所以他和蘇聯還有我們紅色中國關係非常好,也是很不足為奇的了。而他對於安德謝夫,是不是在這個代表著帝國主義的商人身上載入了更多自己的思考呢?如果不用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來套,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肖伯納獨立思考的一些自己嚮往的東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