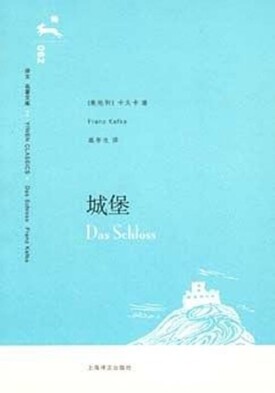共找到20條詞條名為城堡的結果 展開
城堡
弗蘭茲·卡夫卡創作的長篇小說
《城堡》是奧地利作家卡夫卡晚年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未完成)。作品講述主人公K應聘來城堡當土地測量員,他經過長途跋涉,穿過許多雪路后,終於在半夜抵達城堡管轄下的一個窮村落。在村落的招待所,筋疲力盡的K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它們都是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平民。其中有招待所的老闆、老闆娘、女招待,還有一些閑雜人員。城堡雖近在咫尺,但他費盡周折,為此不惜勾引城堡官員克拉姆的情婦,卻怎麼也進不去。K奔波得筋疲力竭,至死也未能進入城堡。
在《城堡》中,卡夫卡以冷峻的筆調敘述了一次絕望的掙扎,由此揭示世界的荒誕、異己和冷漠。
![城堡[弗蘭茲·卡夫卡著長篇小說]](https://i1.twwiki.net/cover/w200/mc/d/mcd910af1d4ddae6842348c72f5e77333.jpg)
城堡[弗蘭茲·卡夫卡著長篇小說]
卡夫卡於1922年1月開始寫作《城堡》,同年9月卻不得不中止,於是《城堡》和他的其他長篇小說一樣,也成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說。它是卡夫卡最後一部長篇小說,也是最長的一部小說。好友布羅德於1926年整理出版了《城堡》。為了讓小說顯得比較完整,布羅德將小說後面幾章刪除掉。1981年出版校勘本,許多未完成的章節收入書中,被改動的詞語也恢復手稿原樣。
K
K在《城堡》中就像一隻迷途的羔羊,他沒有身份,沒有親人,沒有真正的朋友.似乎他所處的整個村莊都對他充滿了敵意,也得不到城堡當局的信任。這種絕望事實上在K的追尋中表現到了極致,追尋成了他失望情緒的流露和發泄的一種方式。是他在追尋意義的過程中一種絕望的吶喊,又是一種對終極意義追求的絕望哀號。當人與上帝交流的渴望被自我的獨白所取代的時候,卡夫卡說,“我們人間的不幸是由成群的魔鬼構成的……但只要不存在統一性,即使所有的魔電都關懷著我們,那又有什麼用呢”。
孤獨
單純從《城堡》這部小說沒有結尾的結局來看,它就可能昭示著現代人類對一個從不存在的上帝的訴求的失敗,小說完全強調的是現代和後現代意義,這部小說就是關於意義本身的小說。對於事件,時間及其空間的多重闡釋構成了無限混雜和變化多端的意義網路。卡夫卡所設計的迷宮其實也是一座語言的迷宮,因為語言從本質上來說是寓言性的。他的話語也是他的世界觀和宗教觀的折射。“《城堡》和《天路歷程》一樣,是一部關於宗教的寓言”。因而作品的意義也是開放的,上帝的缺失可以讓很多人為的因素得以介入。
積極的絕對權威意義似乎並不存在,這在《城堡》中可以得到例證,臂如當K到達村子,拿起電話——他聽見無數的聲音。村長解釋說.當一部電話被接通后,城堡以及村子所有的電話同時被接通,誰也無法保證聽到的聲音來自城堡。這就是說村長和K一樣其實對城堡的概念摸糊不清,很多權威都是虛無飄渺的,而且是在一連串不確定的聲音中建立起來的,並不斷地在一種錯誤的方式中得到鞏固的。總之一切的一切都是不確定的,所有的東西都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悖論。
《城堡》事實上可以認為講述的是整個人類的故事。他揭示了20世紀人類所面臨的一個共同的問題:即面對上帝的缺失,我們怎麼才能拯救自己?現代主義徹底地否定了人類社會的傳統信仰,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可是由於其形而上的慾望仍然存在,他們仍然執著地追求某種所謂的“意義”。然而,這種追求註定必然會導致失落。《城堡》正是以其平靜穩重而徹底的絕望成為這一表現的具體實現。這不能說不是一個絕望而又絕妙的悖論。陷入城堡這樣一個未知的荒誕世界,一切都是虛妄的,都是徒勞的,永遠也達不到任何的目的,這不僅反映了個人與上帝的疏遠,也擱置了意義,並把對意義的追問變得遙無蹤跡。
K的身份是孤獨的,他在追求進入城堡的過程中,一直是單槍匹馬,孤立無援。但是當這種努力化為泡影后,孤獨本身卻變成了他的追求。我們知道卡夫卡是位自傳性色彩很強的作家,孤獨是卡夫卡創作的動因。《城堡》中這種孤獨感表現到了極致。K或許可以代表生活中真正的卡夫卡,K開始需要孤獨,於是他就迫尋孤獨。但是K找到孤獨了嗎?沒有。既然K連自己的工作、身份都沒有著落,卻被城堡派來的兩位助手時刻跟在身後,他們不僅不幫K,相反還需要K及其情人弗麗達的照顧,使得他們沒有片刻獨處的時間。這時,K的悲哀已經不是孤獨的厄運,而是孤獨被侵犯的苦境。在這裡,卡夫卡顯然以人物K的遭遇來訴說著人類對孤獨的渴望與追求。同樣的遭遇也發生在《變形記》中的格利高爾身上,他在變形后感到弧獨,但孤獨使他逃避了苦役般的推銷員生涯和作為長子的責任感,因此,雖然遭到家人的冷遇,卻也安於蟲類的生活樂趣,與《城堡》中K的遭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K展示了絕望中的一次次的反抗,其根本原因就是拯救自己身處的窘境。當這種拯救的努力歸於失敗時,測量員的形象只能留在了我們關於宗教的想象中。
K的失敗留給讀者的是痛苦的沉思和無言的悖論。卡夫卡似乎在向人們揭示,當上帝的權威一旦坍塌,孤獨個體的命運便朝不保夕,夢幻與現實在個體對世界的存在體驗中達到了統一。在《城堡》里,“上帝之死”的結局使我們變得沒有淚水,也沒有笑容,有的卻是對K追求和慾望的誤解和嘲弄,還有對作為宗教本身的一種深深思索。作為20世紀重要的現代主義小說之一,《城堡》似乎在暗示警醒個人類的命運。
權力專制
![城堡[弗蘭茲·卡夫卡著長篇小說]](https://i1.twwiki.net/cover/w200/mb/8/mb80d3d70786f55da95c43357ff9811eb.jpg)
城堡[弗蘭茲·卡夫卡著長篇小說]
另一方面,城堡又是某種抽象理想的象徵。不僅城堡顯得虛無縹緲,朦朦朧朧,人物形象和故事本身也是飄忽不定,既談不上典型性格,也談不上典型環境,但細節描寫的真實性依然受到尊重。進入城堡的努力象徵了人對美好事物的追尋,K的失敗是作者悲觀厭世的產物,是作者對人生的否定和對人的存在價值的否定,這就使得小說通篇貫穿著痛苦惶恐和壓抑絕望的情緒。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這種情緒使卡夫卡生前不為世人所理解。在《城堡》中,卡夫卡以冷峻的筆調敘述了一次絕望的掙扎,由此揭示世界的荒誕、異己和冷漠。
在《城堡》中,卡夫卡並沒有對“政治”進行直了當的描寫,而是經由人物悖論性的語言或交織、或組合,把它置放於一個龐大的悖論性語言環境內。這部小說的最大意義,莫過於蘊含其中的悖論思維如何戲劇化為作者把握世界與人生的方式。無論是客棧老闆、老闆娘,還是巴納巴斯、弗麗達、教師等,他們對於城堡世界的盲目遵從,以及樹子里中的一切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政治問題”。所以,小說中人物的悲劇沒有那麼多、那麼深的關於人性的探討,有的只是K與城堡世界的關係處理過程中遇到的許多荒涎的事情。而促成這些荒誕事情發生的正是卡夫卡創作中的相悖事,即他如何運用跳式思維,宣指人物命運,進而顯示特定製度與個人命運之間,政治與個體因素的相悖。
《城堡》通過對話的形式,實現了對於傳統小說敘事方式的挑戰。傳統小說的線性結構模式,又稱之為時間方式,是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或主人公經歷事件的因果關係來組織故事情節的。這種方式也被稱之為“轉喻”。其小說結構就像“糖葫蘆”:以主人公的經歷串起一個個事件的“糠葫蘆”。而且,只要竹籤足夠長,事件可以被無窮地串下去。因此.傳統的線性結構模式的根基和底部是無數的事件。《城堡》與傳統的敘事方式截然不同表現在以下兩點:第一,主人公K作為小說軸心式人物,他所連接的不是一個個相對獨立的事件,而是小說中不斷出現的人物。通過對話,這些人物不斷地打開了K的視野,並且通過對同一事件的不向敘述使得故事的進展變緩。第二,小說中的敘事方式與傳統小說連貫、統一、清晰的敘事方式大相徑庭。通過K與不斷相遇的人物的對話,衝擊著原先對話所形成的叔事線條,造成了文本內部的相互矛盾和衝突。由此“對話”在文中已成為一種解構中心話語的途徑和方式。
主人公K與小說中人物的多重對話——尤其是較長篇的對話,如同給主人公K打開了一扇扇的窗子,讓我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認識我們“所見”的和所“經歷”的一切。不僅如此,“對話”還擴展了《城堡》的時間和空間。
因此,《城堡》以其佔到小說一半以上篇幅的“長篇對話”,形成了對於傳統小說的線性敘事結構的挑戰。這種獨特的對話結構方式給我們打開了無限“隱喻”的空間,使得我們對於小說的線性結構形式的假想受到衝擊。與此同時,對話也不再是傳統小說所假設的消晰、連貫、統一的形式,而是在悖謬和相互矛盾中跟隨K完成對“城堡”的立體的建構。
《城堡》中大篇幅的長篇對話,使得小說的敘事時間和故事時間形成落差。美國學者庫楚斯就《城堡》的情節結構特點指出:《城堡》從第一章到第三章.僅僅58頁的篇幅,就幾乎佔去了敘述內容所包涵時間的一半;而其餘的十七章,篇幅多達303頁,敘述內容包涵的時間並不比前三章多多少”。這即表明,《城堡》中的“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之間的差距是很大的。
按照美國學者庫楚斯關於《城堡》的文章情節結構特點和時間(包括敘事時間和故事時間)的關係展開的討論,得到的結論是:從情節的衰減到對話的繁複的演變,說明K在現實中的行動越來越少,K進入城堡的可能性也因此越來越小。因為《城堡》中的長篇對話,已經涉及小說故事時間之外的事。其中,有涉及故事開始之前的“往事”的。例如,K和村長的談話使我們得知土地測量職業的來歷。有涉及的故事結束以後的“未來”的。如K同孩子漢斯的談話表明K目前雖然還地位低下,令人退避,但將來——當然這個將來要遠得很,還在虛無飄渺中——將來他終將出人頭地”(第十三章)。
因此,“對話”以另一種方式展現了不同人物的內心世界和他們眼中的“現實”,不但沒有指向K現有的處境和道遇,許多還指向了過去和未來,從而使得小說的情節發展在後十七章中變得迂迴繁複。
從小說的情節結構上來講,《城堡》中的對話使得小說的基本構架顯得臃腫、繁瑣。與傳統小說中的對話形成鮮明的對比和反差。傳統的小說中的對話是小說創作中塑造人物、推動情節的重要手段。往往講求“口語化和個性化”,穿插於情節之中或本身構成情節,力求簡練,講究節省。《城堡》中的對話長篇累牘、毫無精鍊可言。這些對話的存在,使得本來就沒有取得什麼進展的故事顯得更加迂迴曲折,饒舌反覆。也可以說,由情節到對話的演變,說明K在現實中的行動越來越少,敘事者對於當前時間的意識在不斷地縮小。而且,那些主要涉及遙遠的過去或未來長篇對話,使得K最終耽於行動;小說越往下發展,K離他所追求的日標也越遙遠。因此,《城堡》中的對話指向了情節之外,並且打破了小說的基本情節的發展軌跡。
如果說關於卡夫卡的研究在過去更多提及“荒誕”和“異化”的話,那麼“悖謬”無疑是值得人們進一步關注的焦點。自葉廷芳先生提出這一問題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對此予以認同。對於《城堡》而言,“悖謬”是貫穿於全篇的,例如從敘事的層面來看,敘事線條的交錯、蔓生形成了小說文本的開放性,這是敘事的情形;從內容的層面來看,小說情節之間的相互矛盾衝突形成了真相與表現的雜燴,這是內容的悖謬;從小說的整體寓意來看,撲朔迷離、紛繁複雜是主題的悖謬,最後從小說的思想內涵來看,“對話”最終指向了非對話性,這正是文本內涵的悖謬。
《城堡》是一部開放性的小說,因為文本通過“對話”早已實現了小說的無中心和無邊界的特徵。假如把K與之交談的人物比作一個敘事的亮點的話,讀者便是跟隨主人公K從一個亮點遊歷到另一個亮點,新的亮點與前亮點之間相互對立且相互消解。隨著前亮點的淡出,其敘述的情節也就如同融入黑暗一般變得依稀含混。從而新亮點從另一個視角確立敘述,並構成對前亮點的消噬。而後一個亮點在繼續確立新的敘述的同時進行著消解。依此往置,構成了小說文本。從形式來看,小說的“未完成”的結構依舊不影響小說的完整性。《城堡》發表於1926年,而後人無人熱衷續寫其未完成的部分,這大概也正是《城堡》的“對話模式”特點所決定的。
從時間意義上看,與K的有關及其產生的圖像都是以城堡為核心展開,敘述所夠及的故事屬於不同的時間層次,因而不同人物的“回億”成了揭示城堡世界最好的圖像。這瞬間產生的圖像對不同人物生活的補充及其相互之間的重疊,消解了線性時間的敘述,也喪失了敘事內容方面的連貫性。但這些圖像的排列和組合卻不斷加深著讀者對城堡世界的印象,加強了故事空間敘述的可能性。如果故事中的“城堡”是主要的圖像,而其他人物的不同圖像以循環形式反覆出現,零散點綴在周圍,就構成了一幅城堡世界因,這是因為讀者感受到的已不僅僅是K的故事,而是看到了K以及村民們為城堡畫的“圖像”。它們在消解時間的同時,表現了人的心理和情緒,深刻細緻地刻畫了城堡世界。
對於卡夫卡來說,《城堡》的各種敘事因子都是在“政治化”社會的標尺下進行的,在強化角色的政治特徵的同時,削弱了與此存在的其他特徵,促成了小說中人物的類型化和日常生活的單向度。這樣,卡夫卡就把K放置於一個明顯的政治化社會裡,卻又讓每一個村民在交談時顯得竭力為他們的處境做出辯解。因而,文本內的人物話語就不只是為了說明他們的生活狀況,更是為了揭示他們生活的“政治化”和簡單化,而採取的一種反相位突冗。通過人物間的交談揭示了城堡政治的強大統治。或者說,通過類型人物的塑造,取消了人物間的其他會因素差別,取消了各種生活觀等方面的衝突,轉而圍繞與城堡之間的矛盾的產生來組織故事,顯得十分有意義。
《城堡》以相當大的篇幅描寫婦女的遭遇和命運,橋頭客棧老闆娘的自述,奧爾加敘述自己和阿瑪利亞的故事,弗麗達的故事,各佔了一整章甚至幾章的篇幅,婦女的故事在一篇小說中占如此大的比例,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是絕無僅有的。
《城堡》寫於1922年,是卡夫卡最後一部小說。它不僅是卡夫卡生命體驗與哲學思想的總結,也是卡夫卡創作風格成熟與定型的標誌。這部小說最能體現卡夫卡的創作風格和特徵,故一向被認為是卡夫卡創作的壓軸之作和代表作。卡夫卡作為“現代藝術的探險者”,一反傳統小說的創作模式,採用全新的審美視角和獨特的藝術風格構築了這部現代藝術的迷宮,使《城堡》具有高超的藝術性和美學上的震撼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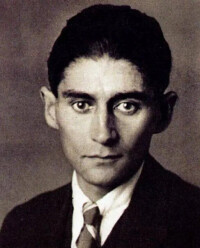
卡夫卡
卡夫卡1883年出生猶太商人家庭,18歲入布拉格大學學習文學和法律,1904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為四部短篇小說集和三部長篇小說。可惜生前大多未發表,三部長篇也均未寫完。他生活在奧匈帝國即將崩潰的時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學影響,對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觀態度,故其作品大都用變形荒誕的形象和象徵直覺的手法,表現被充滿敵意的社會環境所包圍的孤立、絕望的個人。
卡夫卡與法國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並稱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和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