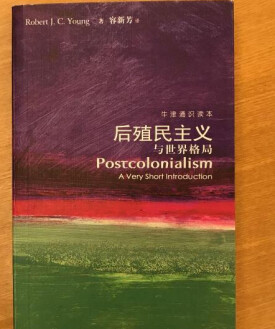后殖民主義
后殖民主義
后殖民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興起於西方學術界的一種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學術思潮,它主要是一種著眼於宗主國和前殖民地之間關係的話語。后殖民主義的特點就在於,它不是一種鐵板一塊的僵化的理論;自誕生之初它就常常變化,以適應不同的歷史時刻、地理區域、文化身份、政治境況、從屬關係以及閱讀實踐。
出現的理論背景

愛德華·賽義德
伯明翰學派
伯明翰學派認為,文化是“一種整體生活方式“,而文化研究就是對這種整體生活方式的完整過程的描述。這一學派所堅持的平民主義傾向使得他們把研究對象從高雅文化及傳統的文學經典中解放出來,注重對通俗文化、大眾傳媒的研究,大眾文化現象從此登上了學術的“大雅之堂”。這就拋棄了舊的學院體制對"文化"的狹隘的、固步自封的立場,更加深入到人們的新的文化經驗之中。它引入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更注重一種新的“內容”的解析策略,對文本進行一種“價值閱讀”。霍加特指出:“‘價值閱讀’這個術語並不表示閱讀者此刻正試圖作出有關自在的作品的‘價值判斷’,而是說此刻他試圖儘可能敏銳和準確地描述他在作品中所發現的價值。”這種‘價值閱讀’提供了理解文化的新的途徑。這兩個方向使“文化研究”始終與社會、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歷史緊密結合,在注重理論進展的同時保持世俗的關懷。而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也在報紙、廣告、電視節目以及工人階級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並培養了許多此領域的學者。
當代文化研究
1970年代之後,西方的“文化研究”從早期對工人階級及其亞文化的關注擴展開來,把注意力集中到性別、種族、階級等文化領域中複雜的文化身份、文化認同等問題上,關注大眾文化和消費文化,以及媒體在個人、國家、民族、種族、階級、性別意識中的文化生產和建構作用,運用社會學、文學理論、美學、影像理論和文化人類學的視野與方法論來研究工業社會中的文化現象。
概述
后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又叫后殖民批判主義(postcolonial criticism)。事實上,與其說后殖民主義是一系列理論和教義的策源地,不如說它是一個巨大的話語場,或“理論批評策略的集合體”。在其中,所有的話語實踐都基於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即“基於歐洲殖民主義的歷史事實以及這一現象所造成的種種後果”。
特質
關於后殖民主義的特質可以歸納為:
1. 后殖民主義話語主要是關於文化差異的理論研究。這裡的差異主要是指原宗主國與殖民地和第三世界之間不同於殖民主義的複雜關係。
2. 后殖民主義特別倚重福柯關於“話語”和“權力”關係的學說。按照這樣一種學說,世界上的任何“知識”,歸根結底都是一種“話語/權力”的較量。
3. 后殖民主義否認一切主導敘述(Master-narratives),認為一切主導敘事都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因此批判歐洲中心主義是后殖民主義的基本任務。與此相關聯,對以“現代性”為基礎的發展觀念的質疑和批判是其重要特點之一。
4. 后殖民主義對全部的“基礎的”歷史寫作予以否定,認為一種基礎的視角總是通過一種“同一性”而壓制了“異質性”。這樣,后殖民主義拒絕了資本主義這一“基礎的範疇”,也否定了作為一個範疇的“第三世界”以及當代資本主義的世界結構。
5. 后殖民主義把批評的注意力由“民族起源”(national origin)轉向“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它的著眼角度在於主體形成過程中“自我”與“他者”之間相互依存、相互扭結的錯綜複雜的關係,這樣,對它來說,混雜性的重要程度遠高於差異性。
6. 總體而言,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把現代性、民族國家、知識生產和歐美的文化霸權都同時納入自己的批評視野,從而開拓了文化研究的新階段。
西方特權視角下的世界
西方中心主義是從一種特定的特權視角來審視這個世界的。通過把世界從空間上劃分為作為世界中心和唯一意義源泉的歐美與“籠罩在黑暗愚昧的陰影之中”的、“成為恐怖、毀滅、邪惡、烏合的野蠻的象徵”的剩下其他地區。通過運用一套複雜的語言與修辭策略設置了一系列二元對立,如文明與野蠻、理性與非理性、先進與落後、科學與迷信等,對世界加以描述。正如薩義德所說,“東方是非理性的、墮落的、幼稚的、‘不同的’;因為西方是理性的、道德的、成熟的、‘正常的’,而且西方以這種宰制的架構來圍堵、再現東方”,正是通過這種方式,世界一體化的進程似乎就成為一種“文明”與“野蠻”的衝突構成的歷史,而敘述者絕對是站在所謂“文明”一方的。
貫穿時間的目的論敘事
西方中心主義還從時間上設定了一種目的論的歷史敘事,即世界的歷史就是西方的歷史,作為“世界中心”的西方享有對歷史的唯一敘述權利。從古希臘的民主政體,羅馬帝國,黑暗的中世紀經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到資本主義發展史,這個敘事開始並終結於西方的經典文化,西方成為“上帝的選民”,整個世界被歸入沒有自己的歷史的奴隸性狀態。這個敘事方式不僅模糊了西方文明內部的混雜性,而且還最大限度地淡化了殖民主義與霸權主義之間的一種必然聯繫。從這種敘事中所能得到的必然推論是:西方的進步完全源於其內在的特質:科學理性、新教倫理,工業革命,議會民主,市場經濟等,對於殖民主義在西方發展史上並不光彩的作用隻字不提。
西方文化下的種族優越論
西方中心主義還抱有西方文化的普遍化情結,它時而利用種族優越性把自身作為規範強加於內部及外部的“他者”,時而又掩蓋其種族優越性使自身成為一種隱形規範。在西方的強勢文化面前,“東方”失去了古老神奇迷人的光環而淪落為現代“灰姑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殖民主義在世界範圍內退卻、宗主國已經無力左右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政治事物的時候,這種優越意識卻併入文化的領域,通過藉助規訓的力量而日益強大起來,這也就是后殖民理論興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化的力量由於久已有之的原因,常常容易被與政治的或經濟的因素被區分開來進行論述,而事實卻早已證明,並不存在任何超越了時代政治或經濟因素的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文化本身,就只可能產生於一個與之對應的特定的社會之中。
后殖民理論的興起,有其深刻的理論基礎。一般來說,前意共領導人葛蘭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文化霸權”(又稱“文化領導權”、“領導權”)理論與法儂(Franz Fanon,1925-1961)的“民族文化”理論對於后殖民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而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話語”與“權力”理論則是后殖民主義理論的核心話題。
文化霸權理論
“文化霸權”,或稱“文化領導權”、“領導權”,這個詞的希臘文和拉丁文表達分別是“egemon”和“egemonia”,這個詞最初來自希臘文,指來自於別的國家的統治,到了19世紀以後才被廣泛用於指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政治支配或控制,到了葛蘭西手中,這個詞開始被用來描述社會各個階級之間的支配關係。而這種支配關係並不局限於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試圖成為更為普遍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觀看世界、人類特性及關係的方式。由此,領導權不僅表達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且還滲透到大眾的意識之中,被從屬階級或大眾接受為“正常現實”或“常識”。
在《獄中札記》中,葛蘭西明確把“統治”(壓制)和“領導”區分開來,強調了文化霸權的這樣一面:通過大眾認可進行統治的方式。葛蘭西指出,一個社會集團能夠也必須在贏得政權之間開始行使“領導權”,這是贏得政權的首要條件之一;當它行使政權的時候就最終成了統治者,但它即使牢牢地控制了政權,也必須繼續以往的“領導”,因此,文化霸權首要的不是一個爭奪“領導”的問題,而是一個爭奪領導“權”的問題,是使自身領導合法化的問題。因此,就必須藉助於政治與文化的力量,超越自身經濟的局限性,體現為一種精神和道德的統治。因此,文化霸權是一項全面的統治工程,既是一個文化或政治的問題,也是一個經濟的問題。
這說明了一個后殖民主義的主要問題,即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統治方式。儘管直接的政治控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二十年之內基本結束,但是其對於殖民地人民的經濟與文化掌控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這也是后殖民主義考察的一個重要方面,即西方因其政治權力而對東方的重構過程中東方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知識──權力
“權力──知識”是法國哲學家福柯哲學的核心之一。福柯的“權力──知識”的思想創造了一種解剖整個現代社會將身體政治化的“生命政治學”,這種生命政治學是對極權制度以及現代社會中的法西斯主義因素的微觀運行機制的分析,它深刻地改變了我們對政治的觀察和理解的基本模式,在社會理論、法學、哲學和政治學等領域中都引起了研究範式的革命。
在福柯看來,權力是一個龐大的網路,是各種力量關係的幾何。福柯的權力不是某個集團、某個主體的所有物,權力永遠是關係中的權力,只有在和另外的力發生關係時才存在。在《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中,福柯表明了人僅是一種由話語生產出來的形式,而在《規訓與懲戒》中,福柯進而指出,主體不僅是一種知識形式,它更是一種權力的建構,它通過一整套技術、方法、知識、描述、方案和數據,對軀體和靈魂進行塑造。這種積極的權力還表現在知識的生產,權力同知識結成同盟,互相促進,權力操控著知識的生產,知識反過來又幫助權力擴張社會控制。因此,沒有中立的、完全客觀的知識,知識無不受到權力的浸染。所謂的“真理”實際上是權力的產物。
福柯突破了從宏觀上分析權力的傳統,轉而從微觀的角度對權力的性質、功用和運作方式進行了剖析,而這種微觀的、彌散的權力並非無所不能,不能加以反抗,恰恰相反,福柯認為:“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反抗。”這種權力觀正是后殖民主義汲取營養的重要土壤,一種構建在西方殖民霸權之上的、對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話語暴力,不僅使殖民地文化殖民化,更重要的是,構建在西方敘事上的文化觀念使被殖民的民族產生一種被強制的文化認同感,后殖民主義就是試圖解構這一建構在不平等話語上的權力──知識體系。
“后結構主義”這個名稱本身表明了它與結構主義又直接的時間關係和因果關係。“后”作為一個歷史時間標記,也是一個理論邏輯標記。它產生於結構主義之後,是對結構主義的調整、改造和反撥,或對結構主義某一方面的發展、擴充與超越。
解構:對於結構主義的反思
延異:對於“在場的神話”的消解;對於中心的消解
身份/認同(Identity)
在當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中,identity具有兩種基本含義:一是指某個個人或群體據以確認自己在一個社會裡的地位的某些明確的、具有顯著特徵的依據或尺度(性別、階級、種族),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用“身份”這個詞語來表示;另一方面,當某個人或群體試圖追尋、確證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時,它也就可以被理解為認同。簡單的說,就是一個人在理論上追問自己在社會和文化上是誰(身份),以及如何及為什麼要追問是誰。
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提出,“想象的地理和歷史”(例如殖民探險者和小說家們講述的故事)有助於“精神通過把附近和遙遠地區之間的差異加以戲劇化而強化對自身的感覺”,“它也成為殖民地人民用來確認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存在方式”。
自我/他者(Subject/Object)
對身份和認同進行討論,必然會引出一個關於“我”(我們,主體)與“他”(他者,他們,客體)的關係問題。文化身份的建構,始終都與建構者(敘述者“我”)和被建構者(被敘述者“他”)密切相關。
在一個後現代的語境中,關注自我/他者的問題,通常都是在一種二元對立的關係中進行討論。例如殖民與后殖民、男人與女人、白種人與黃種人等。對於自我/他者關係的研究,實際上是通過文化研究進行社會批判、政治批判和意識形態批判,並由此解構和消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某些既定的概念與偏見。
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
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是對於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文化輸出對不發達和欠發達地區實現文化霸權和文化控制的討論。它關注國際文化生產與流通過程中的不平等結構以及由此形成、擴大和加強了的跨國支配,文化帝國主義理論也被認為是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東方學》中,賽義德指出,東方主義是與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西方關於東方的話語形式,在東方話語背後體現出來的是一種權力關係,一種支配關係,一種不斷變化的複雜的霸權關係。而他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更進一步,將文化和帝國時間直接聯繫起來。薩義德明確指出,在帝國擴張的過程中,文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實際上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湯林森(J. Tomlinson)於1991年出版了《文化帝國主義》一書,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全面的論述。在這裡,他將有關文化帝國主義的論述分為四個層次或是途徑來加以解剖和分析,而其中,現代性批判是其關注的焦點。
第一,不平等的信息流,即作為一種媒介帝國主義論述的文化帝國主義。
第二,對民族國家文化認同的威脅,即作為一種民族性論述的文化帝國主義。
第三,消費文化對傳統社會的衝擊,即作為一種全球資本主義論述的文化帝國主義。
第四,現代性的發展及其對傳統文化的挑戰,即作為一種現代性批判的文化帝國主義。
混雜性(Hybridity)
從詞源上來講,混雜性一方面指生物或物種意義上的混雜,特別是人種方面的混雜;另一方面指的是語言,尤其是不同語系、語種或方言之間的混雜。后殖民主義理論家霍米·巴巴最早將混雜性的概念借用到了后殖民理論對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關係的研究中。
在後殖民研究中,巴巴認為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統治與壓迫並不僅僅是權力的單向運作,實際上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彼此交織、難以嚴格劃界和區分的。被殖民者通過帶有差異的重複模擬殖民話語,使之變得不純,從而進一步解構、顛覆殖民話語。巴巴還特彆強調被殖民者的能動性(agency),認為唯有混雜的狀態才能使能動性成為可能。
巴巴之外,比爾·阿什克勞夫特等人對混雜性的解釋更加具體。他認為混雜性是“由殖民行為所帶來的兩種文化接觸地帶所產生的跨文化形式”。在後殖民話語中,混雜現象既不完全屬於殖民者一方,應該注意的是,它也不完全屬於被殖民者一方,它一方面重複現有文化的起源,另一方面也在殖民壓迫下又不斷創造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實踐,以新的文化來抵抗舊的文化。
模擬(Mimicry)
模仿(mimesis):同源系統內的運作表現,是模仿者對被模仿者忠實的複製;
模擬(mimicry):目的在於產生出某種與原體相似與不相似之間的“他者”。這個他者介於模擬者與被模擬者之間。
模擬,正是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關係的生動描述。
從后殖民的角度看,被征服者在被殖民之後被迫不斷地對殖民話語進行模擬,在模擬的過程中也不斷從內部對其進行改造,在殖民意識中發現、撕開裂縫,打破二者之間的二元對立,在其中製造含混與雜糅,生成第三個空間,以抵抗本質主義、整體性的西方文化霸權話語。
模擬對於后殖民寫作富有極為深遠的意義。因為模擬的重要性並不在於有意的對抗,而在於它自身內部所天然帶有的分裂和消解功能。這種殖民地對其宗主國的模擬,正是一種德里達解構主義意義上的“溢出”(excess)。這種溢出打亂了殖民話語或文化霸權穩定的常態和秩序,使其固定、完整的含義遭到了破壞,而且這並不是模擬的蓄意所謂,而是它與生俱來的潛在威脅性。
用後現代的敘述手法無情地戲擬了殖民話語的“宏大敘事”,使人們看到代表西方高雅文化的經典文學與藝術作品中原本存在的矛盾和裂隙,使原本籠罩在這些作派之上的本真性和權威性的光環失去,其挑戰和顛覆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有人指出,后殖民主義可以說是一個“困難重重”的概念。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 )曾指出,“現在我們所談論的后殖民涉及的領域如此之廣,而且又顯得那樣地內在不一致,因而連那些賦予它們理論地位的學者們,對這個術語闡述完畢隨即對它敬而遠之。”的確,后殖民批評在時間與空間上巨大的包容力使得對這一理論的建構工作顯得極其龐雜。而這一理論與生俱來的一些局限與缺點也限制了它的運用。因此,對后殖民文論的局限性進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后殖民主義批評自身存在矛盾。首先,后殖民研究的中心是獨立后的前殖民地國家如何擺脫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束縛,但是,和它批判的對象“東方主義”一樣,后殖民研究卻又不得不藉助於西方的話語。
其次,有人批評斯皮瓦克和巴巴等人僅僅注重紙上的文本再現……離現實越來越遠。(研究僅停留在學術研究的層面,缺乏社會研究和歷史研究的科學性。)
再次,后殖民研究越來越體制化之後,關注的範圍越來越集中,論述方式越來越程式化,忽視了文化的特殊性、不可譯性,輕易走地走向了普遍化。
文化保守與東方主義傾向對藝術普遍性的傷害
當我們在中國的語境中談論后殖民主義的時候,很多時候會被誤讀為一種文化保守主義傾向。出現這樣的誤讀原因很多,例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內的后殖民批評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民族主義傾向,這樣難免產生一種偏激的批評觀。
此外,后殖民文論的東方主義傾向也很明顯,這樣就很難秉承一種絕對客觀公允的態度審視批評的對象本身。這或多或少與理論的建立者有關。無論是賽義德還是斯皮瓦克或是霍米巴巴,都來自前殖民地國家,又有在西方接受教育的背景,在審視西方文化時始終以一種“他者”的角色介入。賽義德在其《東方學》一書中全面詳盡地闡述了西方對東方的奴役與侵略,但是卻有明顯的淡化東方與西方內部各民族文化間時常帶來殘酷後果的紛爭的嚴重漏洞,在這個意義層面上,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拒斥總體敘事而強調“異質性”
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有這樣一種傾向,即拒斥總體敘事,強調異質性、差異性,在重估一切價值的批判精神中迴避採取一種堅定的價值立場。這樣的一種傾向或許與后殖民主義採取后結構主義立場有關。
主體的消解,是后結構主義消解中心的努力的必然結果,因為所謂的“中心”,實際上是自我的一種需要的產物,如果沒有一個中心,我們必然失去對自身存在的理解進而喪失自我意識,因此“中心”的中心是“主體”。按照西方傳統思想中的主體性,主體應該是統一、完整、自足的實體。因此,人,主體,意識這個三位一體的存在成為最終的絕對的“在場”。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后結構主義對西方傳統思想的顛覆實驗在“主體”問題上進入最後一個環節。而對“主體”的消解必然意味著對中心敘事的排斥,也就不可能採取某種固定的價值立場,這樣的結果是我們很難在這一理論的範圍內找到某種合乎總體觀念的存在,這是后殖民主義在立場問題上不可迴避的。
后殖民理論在中國語境中運用的再考察
限於理論研究者的知識範圍與結構,在薩義德或者斯皮瓦克那裡,后殖民理論都是根植於某一個特定的社會的。例如近東的伊斯蘭世界,遠東的大英帝國印度殖民地等,薩義德自己在其《東方學》中所說的,這裡的“東方”(the Orient)是指伊斯蘭世界的東方,而非遠東的中國,印度或日本所在的“遠東”(the East),因此單純地移植其後殖民理論肯定會產生諸多謬誤,這不僅因為地域與民族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殖民方式與中國的殖民程度與上述的國家或地區有巨大的差別,很多在後殖民理論中平常的事實,對於中國的特殊歷史而言並不完全適用,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后殖民理論在中國傳播存在諸多誤區。因此,對於后殖民語境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必須經過審慎的再次考察。
后殖民主義與女權主義
一致性
后殖民主義與女權主義之間無論在實踐上還是理論上都呈現出既相聯繫又相衝突的十分複雜的關係。它們之間一致性是顯而易見的:這兩種文化理論都關注對於在統治結構中被邊緣化的"他者"的研究,自覺維護他們的利益;都以顛覆性別的、文化的、種族的等級秩序為己任,並利用后結構主義來否定男權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共同基礎──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
斯皮瓦克
在當今的美國學術理論界和文化研究界,斯皮瓦克( Gayatri C. Spivak ) 的名字變得越來越引人注目, 尤其是在後殖民主義理論思潮突破了西方中心的模式並完成了從 邊緣步入中心的步驟后, 斯皮瓦克更是被當作僅次於賽義德的當代最有影響、同時也是最有爭議的一位后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知識分子, 或后殖民批評家。
作為一位有著強烈的女性挑戰意識的女權主義批評家, 斯皮瓦克對女權主義的態度是矛盾的, 她既不像肖瓦爾特那樣致力於建構一種女權主義詩學, 也不像法國的女權主義理論家克里斯蒂娃和西克蘇那樣深深地受惠於拉康式的精神分析理論。應該說, 她的女權主義批評既包含了從女性本身的視角出發進行的文學和文化批評, 同時也包括對女權主義理論本身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