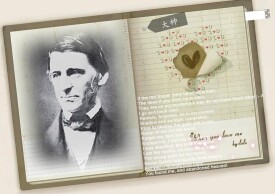共找到11條詞條名為大神的結果 展開
大神
美國詩人愛默生的詩作
《大神》是美國思想家、文學家、詩人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寫的一首詩歌,該詩發表在1857年1 1月份的《大西洋月刊》上,是愛默生最優秀的詩篇之一。本詩通過對《奧義書》中的“梵我一如”說的形象化闡釋來宣揚他的“超靈”論。
Brahma
If the red Slayer think he killed a man,
The dead if you think he is slain,
They are on my mysterious way do not know much about - A
I go and back road.
Remote, forgotten, as in my current;
Shadow and sunlight completely;
Prior to destroy the gods still in me;
Honor to me are the same.
Forget me, he's lost;
Escape me, I was his two wings;
I was skeptical, but also the doubt,
I am the monks, he also sang hymn.
The strong gods for my home,
Seven Saints are equally fond dream;
But you -- humble love man!
You found me, and abandoned heaven!
大神
血污的殺人者若以為他殺了人,
死者若以為他已經被殺戮,
他們是對我玄妙的道了解不深—一
我離去而又折回的道路。
遙遠的,被遺忘的,如在我目 前;
陰影與日光完全相仿;
消滅了的神祇仍在我之前出現;
榮辱於我都是一樣。
忘了我的人,他是失算;
逃避我的人,我是他的兩翅;
我是懷疑者,同時也是那疑團,
而我是那僧侶,也是他唱誦的聖詩。
有力的神道渴慕我的家宅,
七聖徒也同樣痴心妄想;
但是你——謙卑的愛善者!
你找到了我,而拋棄了天堂!
①原題Brahma,為印度教中最高之神,所以譯作“大神”,也就是“一切眾生之父”,故本詩中也充滿了東方宗教的思想。
《大神》一詩最初發表在1857年1 1月份的《大西洋月刊》上,是愛默生最優秀的詩篇之一,可以說是對其“超靈”( Oversoul)思想的形象化闡釋。愛默生的“超靈論”近可以追溯到柯爾律治的萬物關聯說和謝林的精神實體說,遠可以溯源於柏拉圖、斯多葛派和普羅提諾的自然哲學,同時也與印度的宗教哲學有內在的密切關聯。早在《論自然》一文中,他就認為自然萬物是精神的象徵,它們共同屬於一個包羅萬象的靈魂,“萬物各異,其實共通”。
後來在《論超靈》一文中,愛默生則詳盡地闡述了他的“超靈論”,他說:“古往今來,對錯誤的最高批評家,對必然出現的事物的唯一預言家,就是那大自然,我們在其中休息,就像大地躺在大氣柔軟的懷抱里一樣;就是那‘統一’,那‘超靈’,每個人獨特的存在包含在其中,並且跟別人的化為一體。”“我們一點點地看世界,如看見太陽、月亮、動物、樹木;然而,這一切都是整體中觸目的部分,整體卻是靈魂。”這種超驗的“超靈論”思想試圖突破一切的經驗局限,達到一種超越時空、超越主客界線的整體論智慧,從而引導人們以一種全新的眼光來反觀世界、個體和每一個事件。
愛默生閱讀過一些印度宗教的經典著作,尤其是《奧義書》對他影響極大,他所說的“超靈”與婆羅門教的“梵”( Brahman)有著深刻的相似性。“梵”一詞最早出現於吠陀文獻《梵書》中,后在《森林書》和《奧義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闡釋,它在梵文中原有“聖智”、“咒力”、“祈禱”等意思,後來引申為由祈禱而得的神秘的力量,又引申為世界的主宰,在《奧義書》中被描述為一切事物的本體,宇宙的最高實在。它是永恆的,無法描述亦無法限定,愛默生的“超靈”即具有“梵”的屬性。
其實,他的《大神》(Brahmn,又譯“梵天”)一詩正是通過對《奧義書》中的“梵我一如”說的形象化闡釋來宣揚他的“超靈”論。在《奧義書》中,“我”一方面意味著“小我”,即個我、自我、個體靈魂以及個體肉身,另一方面又指“大我”,即“梵”。“梵我一如”或“梵我同一”即是指作為宇宙本體的“梵”(大我)和作為人的主宰體的“我”(小我)在本質上是同一的,梵是一切的根本,是個我的本質,因此世間萬物雖表現為多種多樣,但這一切僅是現象,真正實在的只有最高的梵,萬物同一於梵,這也正是愛默生說的“萬物各異,其實共通”的含義。
作為一種超驗的學說,無論是“梵我一如”說還是愛默生的“超靈”論都是對經驗世界的極大挑戰與否定。所以,在《大神》一詩的開頭,愛默生寫到“血污的殺人者若以為他殺了人/死者若以為他已經被殺戮/他們是對我玄妙的道了解不深”,殺人者和被殺者,以及下文提到的遙遠的與眼前的,被遺忘的與被銘記的,榮與辱等等,在經驗理性的層面上是相對立的,具有相反的本質,但是在超驗的層面上,它們共同屬於一個包容一切精神現象以及自然現象的超靈,在本質上是“同一個”。
殺人者在殺別人的同時也殺掉了自己的靈魂,而被殺的人則以另一種形式存在於殺人者和其他人的靈魂中,被遺忘的東西像那些被銘記的東西一樣在生命中留下痕迹,成為靈魂的祭奠品或紀念物,只是不能被輕易地覺察到而已。因此,一切在超靈之內,而在超靈之內的一切是平等的,永存的,“忘了我的人,他是失算;逃避我的人,我是他的兩翅”,外在的形式無法改變內在的本質,或者說內在的本質超越了一切的形式規定性,我、你、他和它們都是一體的,彼此互為影子,互為肉體,互為心靈,所以,對象與主體的區分在超驗的意義上是沒有必要的,“我是懷疑者,同時也是那疑團,而我是那曾侶,也是他唱誦的聖詩”。人們如果領悟到這些,領悟到超靈的存在,也就領悟了自身作為超靈之載體的屬性與歸屬,成為尊重和愛戴一切生靈的“謙卑的愛善者”,從而拋棄那個不必要的來世的天堂,在現世中構建美好的天堂。
在這首詩以及愛默生論述超靈的其他篇章中均可以看出他的良苦用心,他把包括人在內的一切事物歸為同一個超驗的靈魂,是對人以及其他生靈的充分肯定,在經驗的現實中,沒有完美之物,但是就超靈而言,就這個永恆的涵蓋全部的“一”而言,一切都是美的,都是善的,“善良是絕對的,而邪惡是短缺而致,不是絕對的”,靈魂存在著,而“存在就是巨大的肯定”,所以,“我儘管不完美,卻崇拜我自己的‘完美,每個人只要意識到自己內在的這種神聖性與完美性,就會對生活充滿熱情。愛默生的這種觀點是對美國傳統加爾文教性惡論的否定與挑戰,極大地鼓舞了人們對自我、對生活的信心,為創造人間天堂奠定了內在的人性基礎。另外,在普遍意義上而言,愛默生肯定超靈的存在和人的超靈屬性也為打破文化與制度中現有的一切鄙陋開拓了道路,文化制度往往是經驗的產物,它以種種的秩序性和規定性表現出來,並最終衍生出各種各樣阻礙人性健康成長的羈絆之物,而作為超靈之器官的個體或群體應該衝破一切障礙,在追求創造和自由的道路上建造更符合靈魂需求的新文化。畢竟,文化是為人服務的,而不是人服務於文化。
愛默生為首的超驗主義運動興起於19世紀30年代後期,直接為美國的文藝復興(1830-1860)乃至整個美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愛默生由此成為美國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被林肯稱為“美國的孔子”。愛默生的重要性不但在於提出擺脫傳統桎梏建立美國自己的文化,而且在於從理論上為新文化的建立指明了方向從而確立了它的基本精神,這種精神概而言之就是堅持自立、自助、自信、自強並最終實現自我完善的一種倫理個人主義信念。
愛默生始終把自己看作是一位詩人,而且常常在準備演講辭和寫作隨筆時產生作詩的衝動。他的詩風像他的散文一樣不事雕琢,言辭銳利,帶有一定的哲理性和訓誡味道。愛默生賦予詩人極高的地位,認為詩人在異化成局部之人的現代人中間代表著完整的人。詩人是“真正的唯一的導師”,他們能夠通過一種秘而不宣的智力知覺或者說直覺發現事物中的思想和象徵,領悟事物的靈魂,並把它明確表達出來,從而成為“解救萬物的諸神”,同時也賦予他人一種新思想,打開人類的精神鎖鏈,指引人們進入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