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齊亞·黛萊達
義大利自然主義流派作家
格拉齊亞·黛萊達(義大利語:Grazia Deledda,1871年9月27日-1936年8月15日),義大利薩丁島自然主義流派作家,1926年憑作品《邪惡之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03年出版的《EliasPortolu》標誌著黛萊達正式踏上成功之路,她的代表作品有《灰燼》(Cenere,1906年)、《母親》(LaMadre,1920年)、《離婚之後》(Naufraghiinporto,1920年)、《科西瑪》(Cosima,1937年)等。其中《灰燼》曾啟發一部由埃萊奧諾拉·杜塞演出的電影。

格拉齊亞·黛萊達
和撒丁島上其他女孩女比,格拉齊亞·黛萊達算是受到相當的教育了。但在努奧羅城,她十歲之後就再沒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了。沒有親戚和老師的指導,她開始自學。她孜孜不倦地廣泛閱讀各種經典作品和普通文學作品,包括沃爾特·司各特、拜倫、亨利希·海涅、維克多·雨果、夏多布里昂、歐仁·蘇、奧諾雷·德·巴爾扎克、喬蘇埃·卡爾杜齊、喬萬尼·維爾加、列夫·托爾斯泰、伊萬·屠格涅夫和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她的文藝創作風格介於批判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之間,主張對社會現實作精細、不加修飾的描寫。她以美麗的撒丁島的自然風光為背景,以耳聞目睹的傳說和真實生活為素材,創作了樸實、動人,帶有戲劇性的作品,如《撒丁島的傳說》、《正直的靈魂》、《邪惡之路》、《山中老人》等。

格拉齊亞·黛萊達
1927年黛萊達被發現患了乳腺癌,並逐漸擴散到全身。她就這樣走完了她平平淡淡的一生。1936年8月15日,在接受了最後的宗教儀式后,她被葬在羅馬。后應努奧羅城居民的要求,她的遺體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移至她家鄉附近的一個教堂里。
《風中蘆葦》
《撒丁島的傳說》
《正直的靈魂》
《邪惡之路》
《山中老人》
《灰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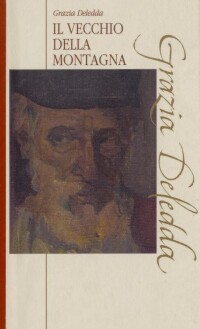
《山中老人》
《鴿子和老鷹》
《風中蘆葦》
《孤獨的秘密》
《生者的上帝》
《飛過埃及》

格拉齊亞·黛萊達
黛萊達是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第二位獲獎的女作家。早在一九一三年,當她四十二歲時,她就已被提名,經過多年的角逐,直到十三年後的一九二六年,她才獲得這一殊榮。她的獲獎是因為“她那為理想所鼓舞的作品,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繪了她海島故鄉的生活,並以同情的態度處理了一般人類問題”。
從二十年代開始,黛萊達的創作有了新的突破,更注重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寫和挖掘,而且背景也由撒丁島逐步轉向更廣闊的天地。在她後期的創作中,重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母親》(1920)、《孤獨者的秘密》(1921)、《逃往埃及》(1925)、《阿納萊娜·比爾希尼》(1927)及短篇小說集《森林中的笛聲》(1923)、《為愛情保密》(1926)等。

格拉齊亞·黛萊達
格拉齊婭·黛萊達不屬於那類圍繞主題討論問題的作家。她總是使自己遠離當時的論爭。當艾倫·凱伊試圖引她加入那種爭論時,她回答說:“我屬於過去。”也許她的這種表態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格拉齊婭·黛萊達體會到她與過去、與其人民的歷史有緊密的聯繫。但是,她也懂得如何在她自己的時代生活,知道該怎樣給予反映。雖然她對理論缺乏興趣,但她對人生的每個方面都有著強烈的興趣。她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們的最大痛苦是生命之緩慢的死亡。因此,我們必須努力放慢生活的進程,使之強化,賦予它儘可能豐富的意義。人必須努力凌駕於他的生活之上,就像海洋上空的一片雲那樣。”準確地講,正因為生活對於她來說是那樣地豐富和可愛,因而她從不參與當今在政治、社會或文學領域的論爭。她愛人類勝過愛理論,一直在遠離塵囂之處過著她那平靜的生活。她在另一封信中寫道:“命運註定我生長在孤僻的撒丁島的中心。但是,即使我生長在羅馬或斯德哥爾摩,我也不會有什麼兩樣。我將永遠是我——是個對生活問題冷淡而清醒地觀察人的真實面貌的人,同時我相信他們可以生活得更好,不是別人,而是他們自己阻礙了獲取上帝給予他們在世上的權力。現在到處都是仇恨、流血和痛苦;但是,這一切也許可以通過愛和善良加以征服。”
這最後的話表達了她對生活的態度,嚴肅而深刻,富有宗教的意味。這種態度雖然是感傷的,卻絕不悲觀。她堅信在生活的鬥爭中善的力量最終會獲勝。在小說《灰燼》的結尾,她清楚明確地表達出她的創作原則。安納尼亞的母親受到污辱,為了不影響兒子的幸福,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躺在兒子的面前。當兒子還在襁褓中時,她曾送給他一個護身符。現在他將護身符打開,發現裡邊只是包著灰燼。“是啊,生命,死亡,人類,一切都是灰燼,這就是她的命運。而在這最後的時刻,他站在人類最悲慘的屍體面前。她生前犯了錯,也受到惡行的各種懲罰,現在為了別人的幸福而死去。他忘不了在這包灰燼中,常常閃爍著燦爛而純凈的火花。他懷著希望,而且仍熱愛著生活。”

格拉齊亞·黛萊達

格拉齊亞·黛萊達
這種環境培養了格拉齊婭·黛萊達非常坦率質樸的生活觀。在努奧洛城,做強盜並不令人可恥。黛萊達一篇小說里的一個農村婦女說:“你認為那些強盜是壞人嗎?啊,那你就錯了。他們只是想顯示他們的本事,僅此而已。過去男人去打仗,而現在沒有那麼多的仗好打了,可是男人需要戰鬥。因此他們去搶劫,偷東西,偷牲畜,他們不是要做壞事,而是要顯示他們的能力和力量。”所以,那裡的強盜得到的更多是人們的同情。如果他被抓住關進監獄,那裡的農民有句意味深長的話,叫做他“碰上麻煩了”。一旦他獲得了自由,惡名也就與他無關了。事實上,當他回到家鄉時,他聽到的歡迎詞是:“百年之後讓這樣的麻煩來得更多些吧!”
家族間的仇殺仍然是撒丁島的習俗,向殺害親人的兇手報仇雪恨的人,受到人們的尊敬。因而,出賣復仇者被看成是犯罪。一個作家寫道:“即使能獲得比他的頭值錢三倍的獎賞,在整個努奧洛地區也找不到一個人肯出賣復仇者。那裡只有一條法律至高無上:崇尚人的力量,蔑視社會的正義。”
格拉齊婭·黛萊達成長時期所在的那個小城,當時受義大利本土的影響甚微,周圍的自然環境有如蠻荒時代那樣美麗,她身邊的人民像原始人那樣偉大,她住的房子具有《聖經》式的簡樸特色。格拉齊婭·黛萊達寫道:“我們女孩子,從不許外出,除非是去參加彌撒,或是偶爾在鄉間散步。”她沒有機會受高等教育,就像這個地區的其他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一樣,她只上了當地的小學。後來她跟人自學了一些法語和義大利語,因為在家裡她家人只講撒丁島的方言。她所受的教育,可以說並不高。然而她完全熟悉而且喜歡她家鄉的民歌,她喜歡其中的讚美聖人的讚歌、民謠和搖籃曲。她也熟知努奧洛城的歷史傳說,而且,她在家裡有機會讀到一些義大利文學著作和翻譯小說,因為按照撒丁島的標準,她家算得上是相當富裕的了。但是也就僅此而已。然而這個小姑娘熱愛學習,她十三歲時就寫出了一篇想像奇特的帶有悲劇特色的短篇小說《撒丁島的血》(1888),成功地發表在羅馬的雜誌上。可努奧洛城的人們並不喜歡這種顯示大膽的方式,因為女人除了家務事之外不應過問其他事情。但是格拉齊婭·黛萊達並不依附於習俗,她反而全身心地投入了小說的寫作:第一部小說《撒丁島的精華》發表於一八九二年,之後是《邪惡之路》(1896)、《深山裡的老人》(1900)和《艾里亞斯·波爾托盧》(1903)等,她以這些作品為自己贏得了名聲,漸漸得到公認,成為義大利最優秀的年輕女作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