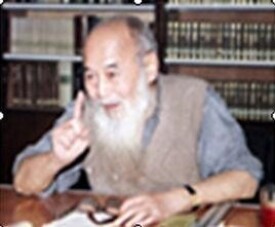蒙思明
蒙思明
蒙思明(1908—1974),原名爾麟,又名弘毅,四川鹽亭金鼎場人。著名史學家蒙文通教授,即先生之長兄。少年時代先生一直在鄉下和縣城讀私塾,一九二二年離開家鄉,就讀於重慶江北治平中學。適逢共產黨員、革命烈士惲代英、蕭楚女來川傳播革命思想,在革命先烈和進步書刊的影響下,先生逐漸對政治問題發生興趣,開始走上追求真理和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五年初中畢業后,先生到上海,就讀於上海立達園高中部。在大革命時代的推動下,先生憤然投身於工農革命潮流。於一九二六年夏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選任立達園高中部書記。隨後參加周總理親自領導的上海三次工人大暴動。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蔣介四發動反革命政變,在上海製造白色恐怖,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先生亦難倖免。在國民黨反動派日益殘酷的政治迫害下,先生避難於法租界,后更名為弘毅,到杭州,就讀於之江大學社會系。一九二七年秋,先生不幸被捕,後由伯父蒙裁成(公甫)、長兄蒙文通多方營救出獄。一九二八年春,先生亡命國外,就讀於日本東京大岡山日語補習學校。不兩月,山東濟南發生“五三”慘案,為抗議日本帝國主義殘酷屠殺中國人民的暴行,先生憤然輟學歸國,在上海參加“留日學生抗日大同盟“,積極宣傳抗日,其愛國熱情灼然可見。后因“抗日大同盟”的革命活動不容於當局,不久便遭取締解散。先生被迫於一九二八年秋返回故鄉鹽亭。其時,伯父先逝,家道衰落,學業荒廢,先生有感於社會黑暗,時政之腐敗,欲明未來之發展,幡然為當時國史界興起的社會史研究的潮流所吸引,遂改名為思明,開始了他的治史生涯。
一九二九年秋至三三年,先生就讀於華西大學社會及歷史系。三三年至三五年,先生在華西大學及華西協和高中任教,在講授西洋歷史和中外地理的同時,間作哈佛研究學社的研究工作。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先生入北京燕京大學研究院歷史部專門進修中國歷史。載譽史壇之《元代社會階級制度》一書,即先生之畢業論文。
縱觀這一時期先生所發表的文章,其中有可稱道的代表作和著名論斷如下:
發表於一九三八年四月《燕京大學學報》專號第十六期的《元代社會階級制度》一書,是先生研治元史的代表作。全文共分五章,附小注一千七百四十八條。在當時史壇把元代稱為“征服朝代”,把元代視為民族矛盾居統治地位的社會,把元末革命視成為種族革命的潮流下,先生能力排眾議,創建新說,斷然認定:(一)蒙古入住中土,並為破壞宋、金以來的以“貧富懸隔”為特徵的社會組織和經濟結構;(二)蒙古所創立的種族四等制,其“世紀區分,則仍本之於實力之強弱”;(三)元末革命雖以驅逐蒙人為結果,“而發軔則基於貧民乏食”,“參與革命者皆貧苦農民”,“抗拒革命者,一漢人富室”,故“非純粹漢人反抗蒙人之種族革命如一般之所解釋者”。這些論斷,與馬克思主義在觀察民族問題時強調其階級實質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先生能夠在當時成就此說,與他早期所受的馬克思主義影響是分不開的。至於該著“取材既較豐富,組織亦極完整,立論尤其審慎”,頗受當時史壇稱讚.“尤其對於元代社會能從動的方面去看它的轉變的經過,更覺可貴”。(見西門評論,《燕京大學學報》第二十三期,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學者鈴木正推薦說,相信該著應該作為中國社會機構研究者的“必備必讀之書”。先生成就此書,時年三十,因是書而獲燕京大學文碩士學位。魏晉南北朝歷史是先生重點研究並有所成就的另一個領域。《元魏的階級制度》一書,對“由古代社會轉向中古社會的一個樞紐”的元魏社會的各階級的地位和情況,作了詳盡的考證和論述;《六朝士族形成的經過》一文,則偏重於從統治集團的角度出發,考察了兩漢以來的地主階級的發展演變過程和魏晉南北朝的特點,提出“魏晉南北朝應當叫做士族統治時代”。在《曹操的社會改革》一書中,先生針對當時普遍流行的“曹操乃權奸之雄”的成見,通過對東漢末年政治經濟衰相及曹操改革的成敗剖析,肯定曹操是一個輝映東漢末年的“傑出人物”;在他“被污名千載之後”,“本文沒有任何企圖,要為曹操個人剖白”。曾經在五十年代末期史學界引起軒然大波的“為曹操翻案”的那些論點,其實早在二十年前先生早已發之,先生研究魏晉南北朝歷史多所心得,抗戰期間積捲成稿,但未付梓;后又曾於解放后與魏晉南北朝史專家繆鉞教授合議,共同編寫《魏晉南北朝史》,亦未能如願。至今仍留存當年遺稿一部,名曰《魏晉南北朝的社會》。先生研究這段歷史的精闢論述,統統匯聚其中。
注重史學方法的研究和運用,是先生治學的一個重大特點。在當日史壇考據史料之風興盛一時,甚至認為“史料即史學”,“無史料斯無歷史”的氣氛之中,先生立揚史學方法之論,前後著書,凡是論歷史研究的對象、史學方法的任務、研究題目的選擇、史料的搜集、以及考據在史學上的地位。他系統地指出,“歷史研究的對象,是過去的人類活動”;史料只是了解歷史本身的中介之一種;史學則是研究歷史所用的方法和理論。史學方法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躋歷史研究於科學之林”。所謂科學的研究方法,就是指考訂史料,重建史實的方法;根據史實,構建哲學的方法;訂立體例,寫為史著的方法;這三種方法都必須是科學的。先生尖銳抨擊那種“抱殘守缺,用陳腐不堪的方法,以臆度、推想、輕信、泥古、妄解、欺枉的方法治史”的人,痛斥他們的怪論“是光天化日下的妖孽,學術進步中的障礙”。他大聲疾呼,史學方法的第一任務,就是要“以掃除史學研究中的腐化勢力為職責”。這些論點在當時無不具有進步的戰鬥意義。
一九四四年,先生由華西大學赴美國留學,在哈佛大學選習德、法、日等國文字,並繼續進修俄國史、美國史、日本史和中國近代史。留美期間,先生研究學問非常認真,在留學諸生中,給人以和藹、篤實、持重的印象。先生充分利用美國所藏的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檔案材料,撰寫題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組織和功能》的學術論文,因此而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此外,另有《北京俄羅斯使館考》和《璦琿條約的簽訂》兩文交付哈佛大學。一九四九年底,成都宣告解放,先生興奮之情溢於言表,見諸行動。懷著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激情,先生當即辦理歸國手續,幾經周折,終於和夫人魏志統女士在一九五零年回到成都。
此後,先生一直在高等學校從事教育工作。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先生歷任華西大學教授、哲世系教授、文學院院長兼外文系代主任,為開設蘇聯史、唯物論和聯共黨史等新課和史學方法課積極工作,備受辛勞。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以後,先生歷任四川大學副教務長、教務長和歷史系教授,先後在歷史系兼任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史資料整理和史學方法等課程。先生勤於學習鑽研,凡有心得則筆錄為文,積高達數冊之多,不幸散失於“文革”動亂之中。
先生教學認真,經驗豐富,頗受學生之愛戴。先生晚年雄心猶存,戰鬥不已,專門講授元史,並招收研究生,培養青年教師,認真研究元史中的重大問題,為再版《元代社會階級制度》一書重新搜集史料,撰寫前言,真可謂苦心孤詣,鞠躬盡瘁。“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殘酷迫害廣大知識分子,先生雖然身患重病,仍未能倖免,遭受種種折磨,於一九七四年二月三日含恨去世,終年六十六歲。先生逝世前留下遺願,仍不忘將其所藏之歷史、哲學等外文書籍贈送四川大學,其關懷教育事業之心赤誠可見,足以激勵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