雌性的草地
嚴歌苓創作小說
《雌性的草地》是旅美作家嚴歌苓創作的中篇小說,該作品創作於1989年。《雌性的草地》描寫了在20世紀那個“紅色的年代”女性知青像男人一樣放牧軍馬的艱苦生活,展現了她們遭受人性摧殘的悲涼人生和不幸命運。雖然女知青們都相繼成了“崇高”理想的祭品,但是在被“雄化”、“物化”過程中,她們仍舊錶現出對女性身份的渴望,悲情地呼喚著“雌性”。
嚴歌苓以悲劇的方式寫人性的殘缺與幻滅,同時又在精神與肉體的爭鬥中彰顯著“性”,並由此引發了關於“雌性”的意義——既柔弱又勇敢,既兇狠又善良,既有容納一切的母性、愛情,又有毀滅一切、催生一切的慾望。複雜的人性在雌性的種種爆發中得到了展示,極致的殘缺本身反而蘊藏著一股召喚悲憫的聲音:對女性力量和自由的吶喊與尊重。
一個由七個女孩子組成的“鐵女子牧馬班”,在軍區首長的一聲號召下來到了草原牧馬。在那個紅色年代,她們肩負了以領導為代表的“集體”重託,趕著軍馬來到青海與西藏交界的海拔三千米的高原草場,這裡一年四季不是烈日就是雨雪冰雹,即使是當地牧人也很難堅持下去,而且在這塊草地上還遊盪著狼群、不懷好意的土著牧人等等。七個年輕的女兵在嚴酷的自然環境下堅持當初的誓言,將英雄主義旗幟下的革命理想看做高於一切的崇高使命。她們的姣好的面容也因為風吹雨打冰雹寒潮而結了一層痂。草原上物質十分匱乏,每個月配的米的分量只夠女孩子們吃三天,接下來的日子就是東拼西湊找食物過日子。一年到頭就只有冬宰才能吃到肉。不僅吃不飽,在衣著上,她們也沒有自己的制服,穿的都是不合身的男式舊軍裝。她們住的是隨時可以遷徙的,沒有廁所和澡堂的帳篷。她們本能的慾望在嚴酷的自然和極致的生存環境面前被迫壓抑,並通過變態的形式表現出來。班長柯丹的雌性慾望通過與叔叔生下一個怪異的孩子布布而釋放,毛婭絕望中通過嫁給土著牧民生養一大堆孩子而釋放本能,而杜蔚蔚卻通過將馬鞍故意弄得不舒服而磨出血來感到快意,通過跟班長打架讓班長狠揍一頓釋放自己的本能。
當地牧民經常覬覦她們的身體,毛姆就差點被當地牧民強姦。為了嚇跑躲在帳篷外面的牧民,她們甚至會穿上男性的衣服,偽裝成叔叔。她們變成一群似男似女的人。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她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從始至終,“鐵女子牧馬班”的成員都以放牧出軍馬為榮。但是她們的付出是無用的,她們放牧出一匹符合軍馬標準的馬——紅馬逃回了草原。而到最後,“鐵女子牧馬班”被人遺忘,連編製都不復存在。甚至就連騎兵制度也被取消,國家再也不需要軍馬。 《雌性的草地》共13章。
時代背景
1966年,正當中國基本完成調整經濟的任務,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發生了。當時的領導者倡導革命理想的信念,號召年輕人深入農村、邊疆等偏僻地區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了培養年輕人不怕吃苦的精神,當時社會中樹立了一些英雄模範。這些英雄人物在國家的宣揚下成為了許多年輕人的偶像。他們懷著對偶像的崇拜以及成為英雄的渴望到了條件極為艱苦的地方工作。《雌性的草地》描寫的是軍旅生活中的女性,以及她們在“文化大革命”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畸形生存狀態。
成長經歷
嚴歌苓12歲參軍,經歷了長達十三年的軍旅生活,並於1979年主動請纓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以戰地記者的身份直面戰爭的殘酷與生命的脆弱。這段不同於以往生活體驗的軍旅生涯,不僅使嚴歌苓飛快地由涉世未深的少女成長為一名意志堅定的士兵,更豐富了她的性別體驗,使她產生一種非女人式的,比較雄壯的,近乎雄性的氣質。作者產生寫《雌性的草地》的衝動是在1974年,嚴歌苓16歲的時候,她隨軍隊的歌舞團到川、藏、陝、甘交界的一片大草地去演出,聽說了一個女子牧馬班的事迹。這是作者創作小說的最原初動機。
沈紅霞
沈紅霞,是一個年輕的知識青年。她被下放到一個自然環境極其惡劣的地方。她更固執,對自我的要求更高,很少展現女性脆弱的一面。沈紅霞甚至睡覺的時間都捨不得花費,她認為牧馬可以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深化,使自己達到一種偉大的實現。她把放馬這件事情,當做一種聖神的、崇高的事業來做,為了馴服紅馬,她差一點丟掉了自己的生命,她隨時準備著為牧馬這一“崇高”的事業奉獻自己年輕的生命。她討厭和自己在同一牧馬班的女孩,所流露出來的女性特徵,她覺得她和她們沒辦法交流。只能和本應該不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革命幽靈芳子姐和陳黎明交流,把她們當做自己革命應該學習的榜樣,非常苛刻的對待自己。同時,她輕視男女之情,覺得男女之情褻瀆了軍人的榮譽和天職。她年輕的生命從來都沒有享受過美麗的愛情,自己的雙腿也不靈活了,眼睛也瞎了,嗓子也不好使了。
女主 人公沈紅霞是一個被超常化、神秘化了的人物。她是“女子牧馬班”中的一名成員,得了夜盲症,“根本看不見馬群,憑一種神秘的知覺控制每一匹馬。整群馬猶如一盤棋那樣在她的知覺里。
柯丹
女子牧馬班的班長柯丹,土生土長的牧工,有著和男人一樣寬厚的肩膀、強 壯的羅圈腿,這強壯里有著草原游牧人世代相傳的經驗和辛勞。這個有著強壯身體的女子,在一個初春飄雪的早晨,在野地的草窪子里生下了一個男嬰——布布。她雖然有著男人般雋永的前額、寬闊的背,但這絲毫不影響她作為一個雌性所具有的天然的母性。當她得知自己懷孕后,她並沒有驚慌失措,也沒有怨恨肚子里的小黑戶。布布出生后,為了能使兒子留在自己的身邊,柯丹一改往日的粗暴蠻橫,變得沉默寡言、溫良恭讓。柯丹開始終日緘默,和氣中露出了奴性,往日動輒便和其他人大打出手,如今為了給別人撿一盒掉在床鋪底下的大頭針,她會在寒冬臘月里脫光衣服,肚皮貼著地爬進鋪下去尋找,即使擦破了額角也毫無怨言。虎背熊腰的柯丹為了兒子變得恭順無比。
杜蔚蔚
杜蔚蔚又稱老杜,是個丑姑娘,老杜被戰友們稱作是驢,她將柯丹作為了性幻想對象,糾纏著柯丹。柯丹對她罵道: “你比驢皮阿膠還粘手。”杜蔚蔚彷彿有受虐的渴望。青春的躁動、合理的生命慾望得不到釋放,自己又長得丑,她只能用自虐的方式滿足自己,她把自己的馬鞍弄得不合適,使自己的腿不舒服,以致出血,享受痛的快感。其間夾雜著她通過與班長柯丹激烈的身體接觸獲得的某種隱秘的性滿足,那張時時出現的長驢臉就是她不正常情慾的外化。
主題思想
最美麗的喪失是對理想的閹割
《雌性的草地》小說中的“受難主體”——“女子牧馬班”,只是由於一位“老首長”喜歡馬,並且說了這樣的一句話:“男娃女娃都一樣,女娃也可以牧馬。”“老首長”這一句隨意的話,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在那個“軍裝的海洋”中,既應和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最高指示”,也巧合了“男女平等”的“時代精神”。因此,很快就被當做重要“指示”落到實處。於是,一批十七、八歲的美麗、柔弱的姑娘們,被安排到了川、藏、陝、甘交界的一個連當地牧民也無法放牧的高原“草地”。她們干著她們的身體所不能承受的重活,時時忍受著飢餓、嚴寒、惡狼、洪水、沼澤以及不懷好意的各色男人的欺凌、騷擾、攻擊。而且,人們並不拿她們的生命當回事,她們所受的肉體、情感之苦都不在話下,只要有可能完成一個試驗。這個“試驗”是“老首長”那句隨意的話能否實現——能否在三五年內,由一群“女娃”在“大草地”上將“老首長”喜歡的馬“牧”出,並且交到“老首長”管轄的部門中。為此,“女子牧馬班”的全體成員——七個正值青春的少女,必須乾和男人一樣的體力活,過與男人完全一樣的生活,連情感也打磨得和男性一樣粗獷、粗糙。她們犧牲了青春、美麗、戀情,甚至犧牲了親情、親人與自己的生命,終於把馬“牧”成了——可以把馬交到“老首長”的手中。可是,“老首長”的部門已經撤消了騎兵的建制,不再需要馬。 “老首長”也最多只需要一匹馬,作為自己的業餘消遣。 “試驗”完成了,“女子牧馬班”的目的與她們本身卻成了一個虛幻——她們奉獻了一切、完成了一切、犧牲了一切,卻發現一切本來都應該沒有。一切都不過是假借了一個虛幻 的“革命”的名義。
以一個荒謬的“平等”的名義:“老首長”不僅喜歡馬,“老首長”還說了“男娃女娃都一樣,女娃也可以牧馬”這樣一句話;這個“試驗”,也就具有了在特殊區域——“大草地”,爭取“男女平等”的名義與意義——也就是在牧馬的同時,“女娃”的“自牧”也具有了至高無上的意義。因此,“女子牧馬班”也曾經以“自牧”自詡;並且,也因此,無限風光、威風,擁有許許多多的榮譽與花環。但是這種榮譽與花環,是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的——犧牲女人的生理、心理特徵與需要,要做到比男人還要男人。在沉重的“榮譽與花環”的擠壓下,“女子牧馬班”也整體性的由“被動轉為主動”,她們視喂馬為天下最大之事,寧願犧牲自己和犧牲親情——寧願餓死,不吃馬料;寧願孤獨,不交男友;寧願傷損自己的身體,不去照顧自己的女性生理特徵。這種僅僅滿足於挑戰體力極限的絕對平等努力,顯然只是性別平等和女性解放的誤區;但是,極大地滿足了“時代”、“革命”、“平等”對她們提出的“自牧”要求;也極大地滿足了她們在外界的強烈刺激下發自於自身的“自牧”要求。不考慮女人的需要和利益,名義上的男女平等,實際上是另一種不平等,或者說是在遮蓋另一種不平等。“女子牧馬班”的“女子”作為女人,在“身體”層面上力圖與男人平等——“男性化”的同時,她們在“精神”層面上卻步步退縮——成為十足的“小女人”,不得不在男人的庇護、保護、調教、欺負下“討”生活。她們之所以“存在”的“創意者”——“老首長”是個男性;她們的直接領導、生命的“保護傘”——“指導員”是個男性。
“老首長”,在遙遠的地方,關注著她們,期待她們為“老首長”的“原創”爭氣;“指導員”隨時隨地“貼身”“指導”著她們;每有重大事情,必由他拿主意,每有危難必由他解救。他是她們的精神領袖和情感上的依託,他的智慧果敢、勇猛威武徹底從精神上征服了她們;她們只有依附於——從身與心兩方面——“指導員”。於是,“指導員”,自然地成為了她們的主心骨和精神支柱——甚至情感上的支柱、主動或被動的“性夥伴”;一個既是領導,又是救星;既是長輩(被稱為“叔叔”),又是同輩(性慾的對象)的偉人。於是,“她們”不僅只有“男性化”后才能夠被認同,而且,“她們”還必須以男人的思想和行動為標準,甚至以男人的要求為要求——包括性的要求,才能夠被“大草地”這個“環境”所認同。所以,在一個荒謬的、被假借的“革命”性的“平等”名義之下,“她們”的“自牧”——實際上是在一個被毀滅的過程之中的代名詞——精神極度危險、處境極度艱難。
“她們”沒有未來:在“雌性的草地”的深處,不斷閃爍著一雙“眼睛”、一盞“紅燈”,那就是——“權力”。有著旺盛生命力與生殖力的女性,不應該沒有權力;有著博大的胸懷與奉獻精神的女性,更不應該沒有權力。但是,在 《雌性的草地》中,女子牧馬班的女人,都沒有“權力”。在《雌性的草地》中,職務、地位、傳統,代表權力;“信物”,如“槍”也代表著“權力”;但是,職務、地位、傳統和“槍”——尤其是“槍”,都只能掌握在男性——成年男性,甚至未成年男性手中。女子牧馬班的女人,都沒有擁有“槍”的“權力”。作為指導員的“叔叔”有“槍”,正是有了“槍”,“叔叔”能在任何危急關頭充當英雄——解決一切問題、克服一切困難:征服自然、征服“土著”、征服姑娘們的心——包括順奸和誘姦女子牧馬班的數個女人。女子牧馬班的班長柯丹與“叔叔”所生的兒子布布——這個只有三四歲的男孩子,居然也有“槍”——他拿了他父親的槍出走,還開槍打傷了他的母親柯丹。“叔叔”有“槍”與“布布”拿“槍”這兩個細節,隱喻了女人的生存困境產生於她們被剝奪了建構和擁有自己“文明”的權力,她們只是男權文化中的客體;隱喻了未成年男性通過繼承父親的“權力”,而對“自然”的母親的背叛。 “叔叔”有“槍”與“布布”拿“槍”,這兩個細節,也是一個預言:預言“她們”女子牧馬班的“女人”,沒有未來——“她們”血緣上的後代,很可能是她們的反叛者、剝奪者,甚至是謀殺者。由於沒有“權力”,女子牧馬班的“女人”,既沒有了此在,也沒有了未來。儘管她們拼盡了身心的一切。實際上,當老母狗“姆姆”作為女人的象徵——惟一的價值只在於它的生育功能,只剩下“肚皮和奶子”時,女子牧馬班的“女人”就同母馬、母狗這些雌性的生命一樣,沒有了未來。嚴歌苓出發於“雌性的草地”的有關母性無私神聖的讚歌,最終還是帶來了讓人失望的結果;最終還是要在各種“名義”與“權力”面前碰得粉碎。女人、母馬、母狗這些雌性的生命,雖然頑強生存著,但是,她們已經沒有了未來——她們已經從“被牧”走到了“自牧”;只剩下一副軀殼,甚至連一副軀殼也無 法久存於世間。
藝術特色
敘述視角
《雌性的草地》 中,嚴歌苓運用第一人稱“我”來講述女子牧馬班的經歷,但開篇便是與讀者的直接對話,“假如說以後的一切都是這個披軍雨衣的女子引起的,你可別不信。正像有人說,草地日漸貧乏歸咎母牲口,它們繁衍生養沒個夠,活活把草地給 吃窮了,你可別信。“嚴歌苓作為故事的講述著,開門見山,拉近了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在該故事的進程中,嚴歌苓不時地運用第一人稱“我”的敘述來發出“原本的我”的聲音,這一女性主義敘事視角表現了作者自主掌控故事發展的能力和慾望,人物的命運似乎也掌握在作者手中。第一人稱“我”在與讀者交流之外,甚至會時不時的出來與作品中的人物進行交談,與讀者分享作者自己作為旁觀者對故事的看法和對人物的情 感。例如作者在談到該小說中關於小點兒的一段隱情節時與朋友的爭論,“一個朋友直言說不好,不真實。一個少女怎麼能去參加殺人?‘我’說,那是20世紀60年代末。”跳出故事情節與讀者的交流,不僅使作者的觀點得以直接抒發,也間接地映射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現況。
多重敘述視角的轉換,能使讀者全方位地審視該小說中女性群體的現狀。嚴歌苓在作品中採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努力構建女性的話語權。一方面,在作者敘述的聲音下,對該小說中各類人物進行特色描寫,映射時代背景下被異化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通過多重敘述視角的轉換,表現了女性作家在作品創作過程中言說慾望的迫切。《雌性的草地》 中的女性主義敘事,體現了文學作品中女性自主意識的樹立,為保障社會中女性的主體地位起到了積極作用。
文紅霞(河南理工大學副教授):《雌性的草地》揭開了知青運動內在的荒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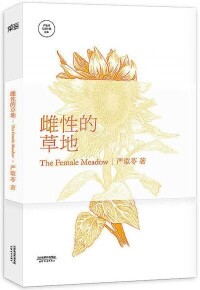
雌性的草地圖書
嚴歌苓,1958年11月16日出生於上海,美籍華裔女作家、編劇。

嚴歌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