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書
大王書
“大王書”系列為曹文軒歷時八年精心構思而成,它是曹文軒迄今為止花費心血最多、最為重要的作品,幻想與文學融為一體,既具有作者一貫的美學風格,又內容新奇獨特,極富探索之風,目前,第一部《黃琉璃》第二部《紅紗燈》已經出版。其餘兩部分別為《紫河車》和《白紙坊》。
“大王書”圖書系列分四部,分別是《黃琉璃》、《紅紗燈》、《紫河車》和《白紙坊》。
《黃琉璃》為曹文軒多卷本長篇小說“大王書”系列的第一部。作家調動非凡的想象,描繪了一個風煙瑟瑟、撲朔迷離的陌生世界,演繹出千軍萬馬攻城、追擊、迎戰的宏大戰爭場面,刻畫了一個少年王波瀾起伏的成長曆程。在血流漂杵的戰爭中,心靈的呼吸、生命的搏動永無停歇。第二部《大王書·紅紗燈》現已上市。
第三部已完稿,準備發行!(曹文軒在江蘇睢寧新世紀中學給學生作報告時親口所說)
剝奪光明,剝奪聲音,剝奪語言,剝奪靈魂……出逃自地獄的熄,在篡奪了這個疆域無邊的大國王位之後,陰險無所不用其極。即便如此,熄仍被心頭隱患所糾纏,他擔心智慧而美麗的文字總有一天會讓人覺醒,為此,熄呼風喚雨,又發動了一場毀滅文字的浩劫……
可他萬萬沒有想到,有本書從萬丈火焰中騰空而出,飛上了夜空。它是書中之書,是大王書。它的新主人是牧羊少年茫——茫是一個沐浴天地靈氣而長大的少年,在危難時刻被成千上萬的難民擁立為王。
於是,在刀光劍影的漫漫長夜裡,茫帶領他的軍隊與熄及巫師團展開了殊死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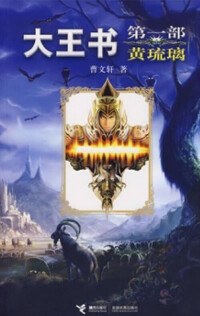
大王書
第一章 哭泣的火焰
第二章 岩石上的王
第三章 瑤
第四章 食金獸
第五章 公石之城
第六章 迷谷
第七章 流血的劍
第八章 三影人
讓幻想回到文學(代後記)
曹文軒出版年表
曹文軒主要得獎記錄
曹文軒,著名作家、學者。1954年1月生於江蘇省鹽城市農村。1974年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中國作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和現當代文學博士生導師。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當代文學教研室主任,兒童文學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客座教授。代表作有《草房子》《紅瓦》《天瓢》等;曾獲國際安徒生獎提名獎、宋慶齡兒童文學獎金獎、冰心文學大獎、國家圖書獎等四十多種獎項。
曹文軒是中國少年寫作的積極倡導者、推動者。主要作品有文學作品集《憂鬱的田園》、《紅葫蘆》、《薔薇谷》、《追隨永恆》、《三角地》等。長篇小說:《埋在雪下的小屋》《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天瓢》、《紅瓦》、《根鳥》、《細米》、《青銅葵花》、《大王書》等。主要學術性著作《中國80年代文學現象研究》、《第二世界——對文學藝術的哲學解釋》、《20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小說門》等。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曹文軒文集》(9卷)。作品大量被譯介到國外,《紅瓦黑瓦》、《草房子》以及一些短篇小說分別翻譯為英、法、日、韓等文字。獲省部級以上學術獎、文學獎30餘種。其中有宋慶齡文學獎金獎、冰心文學大獎、國家圖書獎、金雞獎最佳編劇獎、中國電影華表獎、德黑蘭國際電影節“金蝴蝶”獎、北京市文學藝術獎、中國台灣《中國時報》年度開卷獎、“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小說獎等獎項。2004年獲得國際安徒生獎提名獎。曹文軒的作品以莊重憂鬱的風格、詩情畫意的意境、充滿智慧的敘述方式,呈現給了我們一個真善美的藝術世界———這裡有厄運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獨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脈脈溫馨和殷殷情懷……這些內容在童年情懷的關照下呈現出的精神之光,感動著所有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們,讓我們的心為之震動。
文學,詩意地幻想——讀曹文軒《大王書》第一部/路文彬
時下的文學正以遠遠超乎人們想象的速度刷新著歷史。然而,捫心想來,這過快的速度與過遠的距離似乎已無法讓我們再從其中看到什麼文學。曾經,我們為自己的文學在想象層面所暴露出的拮据家底深感羞愧;而今,懸疑、驚悚以及奇幻等繁多小說名目的瞬間湧現,卻使我們被個中那鋪天蓋地、盛氣凌人的奇思異想壓迫得喘不過氣來。紛亂的想象已經不是想象,而是奢侈和放縱的表徵;它直接昭示著寫作者對於現實及歷史的傲慢與無情。小說也不再是小說,而是病歷,活生生地記錄著這一時代中人心靈上的疑難雜症。由於疏遠了歷史,人們也就必然地疏遠了文學,因為文學終歸屬於歷史性的存在。但即便如此,想象的快車還是毫不理會極速所帶來的失重後果,依然不知節制地讓人們在刺激快感的享樂中親近著死亡的幻覺,並且輕易就迷失和墮落於這樣的幻覺。正在這個想象幾乎促使我們將文學徹底遺忘的緊要關頭,曹文軒先生的《大王書》及時趕到,令我於剎那間甚至想到了“驚現”一詞。
一古典精神之路的守護者形象,決定了曹文軒先生總是樂於把目光投向過去。因此,《大王書》仍然不是一部未來的“大王書”,而是一部歷史的“大王書”。儘管它不打算告知我們確切的歷史時間,但僅憑“熄”、“蚯”、“柯”、“茫”、“瑤”這些人物的名字,我們的思緒便可當即回到軒轅與蚩尤所盤踞的那個久遠年代。至於大王熄針對文字開始的殘忍屠戮,則直接觸痛的是我們關於焚書坑儒的歷史記憶。不過,曹文軒先生想象的歷史性還不單限於他所想象的內容,它同樣也活躍在其始終迷戀的文學風骨上。至少,我能夠從《大王書》里清晰聽到來自安徒生和博爾赫斯兩位巨匠身上的歷史迴響:前者的質樸與悲情、後者的狡黠與詭譎。女主人公瑤彷彿就是“海的女兒”、“賣火柴的小女孩”們的姐妹,她那令人心碎的柔美使我從一開始便相信了她將註定要有著與姐妹們相同的命運。大王熄那無以計數的國土,讓我聯想到的是博爾赫斯那本永遠數不清頁碼的“沙之書”;而使茫軍受困的迷谷,則又讓我重遊了這位神秘大師精心營造的“交叉小徑的花園”。安徒生、博爾赫斯,想必這是曹文軒先生鍾愛著的兩位作家吧,他的幻想世界里時常會閃現出這麼兩個偉岸的身影。也正是憑藉這樣的身影,曹文軒先生的幻想一刻亦未曾偏離過文學。這是一種真正屬於文學的幻想,它以詩意的方式存在著。這種詩意的幻想拒絕停留於嬉戲,它不是純粹的消耗,而是創造——在歷史的追憶中創造。海德格爾說過:“作詩就是追憶。追憶就是創建。”由此看來,不管是曹文軒先生選擇的歷史,還是他所選擇的詩意,他的想象指向的皆是創造的本質。其實,選擇了歷史亦便選擇了承擔,就像選擇了唯美便選擇了悲劇一樣。曹文軒先生的古典主義堅持當屬道道地地的創造,它向來與自戀和消極沒有絲毫干係。那麼,我們就別再指望《大王書》會是一場多麼輕鬆的遊戲。當然,也不要以為它又會有多麼的複雜。複雜從來就不合乎古典美學理想的實質,因為聽覺嚮往的總是與沉靜接近的單純之音;唯有現代性的視覺慾望里才洶湧著破解複雜的執拗衝動。說來簡單,這不過又是一個有關善惡較量的故事。然而,如何呈示和理解這樣的較量卻絕不簡單,要不,它又怎麼敢叫做“大王書”呢?
許多朋友都知道,在很多年前我就有寫一部幻想類作品的念頭,但就在躍躍欲試準備進入情況時,卻見此類作品在一些有識之士的張揚與推動下忽然於一天早晨便在中國大地上鑼鼓喧天地熱鬧了起來,它們成了寵兒,成了許多出版社竟相出版的主打作品,一時間,五顏六色,斑斕多彩,紛紛揚揚地飄落在中國人的閱讀空間里。加之“哈利·波特”、《指環王》、《加勒比海盜》等作品與電影之全球性的滾滾熱浪對中國的大肆席捲,中國的作家、批評家、出版家以及廣大讀者終於徹底地認同了一種叫做“幻想文學”的文學,並義無反顧地迷戀上了它。在如此波瀾壯闊的情形之下,我想我就沒有必要再湊這個熱鬧了,於是便暫時放棄了這個曾經洶湧在心的念頭,依然很平靜地去寫我的《草房子》、《紅瓦》、《細米》、《青銅葵花》式的作品去了。
然而,就在這幾年裡,寫著寫著便會有一種企圖再度涉足此類作品的衝動,但與從前的情形卻有了不同。衝動的原因,不再僅僅是來自難以壓抑的內心渴望,而更多的是來自對當下所謂幻想文學的猶疑和擔憂:這就是幻想嗎?這就是文學嗎?這就是幻想文學嗎?
我從豪華的背後看到了寒磣,從蓬勃的背後看到了荒涼,從炫目的背後看到了蒼白,從看似縱橫馳騁的瀟灑背後看到了捉襟見肘的局促。
上天入地、裝神弄鬼、妖霧瀰漫、群魔亂舞、舌吐蓮花、氣貫長虹……加之所謂“時空隧道”之類的現代科學的生硬摻和,幻想便成了決堤的洪水,汪洋恣肆,現如今已經有點兒泛濫成災的意思了。這種無所不能而卻又不免匱乏精神內涵和審美價值的幻想,遮掩的恰恰是想象力的無趣、平庸、拙劣乃至惡劣。“幻想”在今天已經成了“胡思亂想”的代名詞,成了一些寫作者逃避“想象力貧乏”之詬病而瞞天過海、欺世盜名的花槍。所謂“向想象力的局限挑戰”的豪邁宣言,最後演變成了毫無意義、毫無關感並且十分吃力的耍猴式的表演。
當然,我說的肯定不是全部。我在林林總總申還是看到了一些讓我著迷的幻想類作品,它們在經典性方面,可以與一切通常的經典平起平坐,絕不在其下。但令人遺憾的是,其中大部分卻不是出自國人之手,而是來自國外。
我一直以為,想象力只是一種純粹的力,這種力是否具有價值,全看是否能夠得到優良知識和高貴精神的發動和牽引。如果得不到,這種力就很有可能如一頭蠻橫的怪獸衝出拘圃它的柵欄,橫衝直撞,進行一種沒有方向、沒有章法的癲狂,甚至會踐踏人群、踐踏草木。這種所謂的創造,若沒有意義與價值,倒還算是好的了,最糟糕的情況是:它所創造出來的可能是一些光怪陸離、歪門邪道的東西,甚至還會創造出使人走火入魔、迷失本性的東西。當年黑格爾稱這種想象為“壞想象”。在人類的記憶中,這世界上有許多場災難就是由那些壞想象所導致的。將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趕進焚屍爐,以為可征服並統治整個世界的希特勒的想象,也是一種想象,並且是一種“驚世駭俗”的想象。
所以,我們不可不設前提、毫無反思和警覺地泛泛而談所謂想象。
在文學這裡所談的壞想象,當然還不至於禍國殃民、慘絕人寰,但它們同樣會給我們帶來傷害——精神上的、心智上的傷害。它們會使我們煩躁不安、憂心忡忡,會使我們陷入迷狂和痴心妄想,會使我們被恐懼所籠罩而虛汗淋漓。
我們曾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想象力而汗顏,至今仍在汗顏。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絕大部分,至今也未能有所升騰,依然匍匐於灰色的土地。我們的能耐似乎只有坐在那兒照著生活中的那堆爛事依樣畫葫蘆。所謂寫作,就是將眼前所見,照單全收,用於想象的心和腦卻閑置著,幾乎到了荒廢的程度。正是有感於此,這些年我們才對想象、想象力那樣熱衷地呼喚。然而,當終於有一天想象竟滿地跑馬時,我們所看到的情形卻又是令人哭笑不得:那想象,並不是我們所企盼的可以提升中國文學品格、將中國文學帶出乎庸而狹長地帶的那種想象——藝術的想象。
當然,我對當下幻想文學的猶疑與擔憂,還不僅僅因為幻想本身的質量,更重要的是因為我深刻地感覺到了文學在這裡的缺席與放逐。
所謂“幻想文學”,其實“文學”是沒有的,剩下的就只有“幻想”了——“文學”只是浪了個虛名。
“文學”、“文學性”、“藝術”、“藝術性”,這些字眼在這些年裡一直糾纏著我,搞得我很煩躁。有時我會很不自信地質疑自己:你是否成了一隻迷途的羔羊?有時我甚至對自己的寫作感到害怕,怕自己的認定是一種迷亂,一種偏激,一種膚淺,進而還會懷疑自己的社會責任:人家在談歷史、文化、社會、世界、人類、制度、底層、下崗女工、分配的不平等,而你總是在談什麼文學、文學性之類的話題,你是否犯了本末倒置的大錯?可是,心虛歸心虛,終了還是被這些字眼牽著鼻子走了,還是忘不了去對與我對話或傾聽我言語的人們訴說那一套都長了老繭的話題。
我至今還是冥頑不化地認為,一部既然叫“文學”的作品,天經地義文學就是它的屬性,就是它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石;丟了文學、文學性,那可憐的文字就活不下去;一切都可丟掉,唯獨那文學性決不可丟掉——丟掉了文學性,就是丟掉了腦袋。
我虛弱的心的底部,還是執著地信奉:文學才是永遠璀璨多芒的鑽石,而其他都會衰亡——其他東西即使很有價值,價值連城,也必須將其安放在文學的空間里,如果不是這樣,所有這些東西都將會在歲月中風化,最終變成粉末隨風飄逝。
基於這些冥頑不化的見解,我決定涉足幻想文學,更何況我在此之前許多年就已經寫過一部標準的幻想文學長篇《根鳥》,並且得到很多榮譽。
我對自己說:去做吧,讓幻想回到文學!
為了寫好它,我做了自我寫小說從未做過的案頭工作。我認真地看了大約二十部關於人類方面的皇皇大著。其中,弗雷澤的《金枝》、斯特勞斯的《野性的思維》、泰勒的《原始文化》、布留兒的《原始思維》等經典性著作,這一次都是重讀。它們給了我太多的靈感與精妙絕倫的材料。我對這些著作,深懷感激。
如此處心積慮地寫“大王書”,其動機自然不在改變局面,我也深知自己沒有如此能力,只是想對不盡如人意而卻又風風火火的幻想文學這麼攪合一下。
一石激起千層浪,如果這世界上真能發生如此神奇的物理效應,那麼這塊無名而愚直的石頭即便是被沖入大海,沉入洋底,它也會心甘情願——它定會安然沉睡。
我能夠報答的就是儘力修改和寫作餘下三部。
2007年六月六日深夜於北京大學藍旗營
(摘自《大王書》第一部《黃琉璃》代後記)
地獄之舞
熄是在山頭狂歡中得知茫軍已經順利走出迷谷的消息的。起初,他根本不相信,將那個報告這一消息的城防將軍劈頭蓋臉地罵了一頓。“胡說八道!”他大聲咆哮,嚇得那個城防將軍渾身哆嗦。“呸!”他往城防將軍的腳下狠狠啐了一口,轉身去參加正處在高潮之中的狂歡去了。
他從地獄帶來了一種叫做“黑魂靈”的舞蹈。
這是地獄里的一種最豪華也是最美的舞蹈,只有在盛大的節日,才會跳這一舞蹈。那時,黑幽幽的大廳里,到處點著以上等的動物油脂作為燃料的油燈,空氣里飄散著的香料味與腐爛的氣息混雜在一起,那氣味使每一顆靈魂都感到迷醉。與之相配的音樂,彷彿是從狹長的石縫裡吹來的遠風,有時尖鳴,有時嗚咽,有時像從枯黃的草尖上吹過。舞蹈的動作極其考究,有成百上千個節奏與動作,或似野貓躡手躡腳猶疑不前,或似月桂樹下的蝙蝠輕盈飛翔於藍色的月光之下,或似烏蛇潛游於草叢之中,或似猛獸正從黑色的山崗上俯衝而下,忽起忽落,忽揚忽抑,忽徐忽疾,忽猙獰忽嫵媚,千姿百態,但都朝著一個“輕”字,一個“飄”字。一顆顆黑色的魂靈,猶如天空中無數的落葉旋轉於一股忽強忽弱的旋風裡。
這是千年之舞,是舞中之舞,熄要求他的全部將士們必須學會這一舞蹈,因為只有這樣的舞蹈才能使他領略到盛大節日的快意,並且能讓他回憶起遠去的地獄生活—那裡的生活刻骨銘心。
為了逼真地營造地獄的氛圍,他讓軍需機構為他的將士們每人發放了一套黑色的衣服,到時都必須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