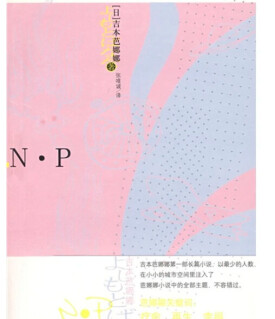N.P
n.p
《N.P》是2008年8月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日]吉本芭娜娜。故事圍繞著一部名為《N·P》的小說集展開。活躍在舞台上的是四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迦納風美是整個故事的目擊者和講述者,她多年以前認識了孿生姐弟阿笑和乙彥,後來在日本重逢,並由此牽引出一系列驚世駭俗的故事。阿笑和乙彥曾同父母一起旅居美國,在他們十四歲時父親高瀨皿男自殺身亡。高瀨死後留下了招致多人死亡的短篇集《N·P》和兩篇神秘的、未發表的遺作。小說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帶著已知身份登場亮相的,只有箕輪萃不是。在大量鋪墊之後箕輪萃的真實身份被層層揭開:她是阿笑和乙彥同父異母的姐姐,因父親高瀨的“一夜情”而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不可思議的是,她與作品中出現過的所有男性都發生了親密關係,在這個人物身上糾結著小說最重要的主題之一:近親亂倫。而且,她的亂倫故事發生在與最難以置信的人之間———自己的父親和弟弟。
吉本芭娜娜(1964-),本名吉本真秀子,生於東京,日本大學藝術系畢業。畢業后一度在餐廳當服務員。1987年以《廚房》獲海燕新人文學獎,次年再度以《廚房》獲泉鏡花文學獎,后陸續獲山本周五郎獎、紫式部獎等文學大獎。1993年獲義大利SCANO獎。作品暢銷不衰,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備受世界各地讀者關注,掀起“芭娜娜熱”。重要作品另有《泡沫*聖所》、《哀愁的預感》、《斑鶇》、《白河夜船》、《N·P》、《蜥蜴》及《甘露》等。
吉本芭娜娜(Banana Yoshimoto),超人氣日本當代文壇天后,與村上春樹、村上龍齊名。因酷愛香蕉花而取筆名為“芭娜娜(Banan a)”。憑藉處女作《廚房》一舉拿下“海燕新人文學獎”等諸多獎項.在文壇閃亮登場。作品已被譯介到30多個國家和地區,受到歐美和亞洲各國讀者高度關注,在世界各地掀起“芭娜娜熱潮”。
芭娜娜的文字純凈輕盈,富有夢幻色彩,流淌著青春的迷惘、憂鬱、哀愁,契合現代都市年輕人無從述說的微妙心緒和敏感情懷,在我國港台地區擁有大批忠實擁躉,深得少女們的追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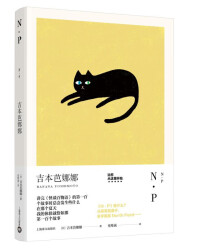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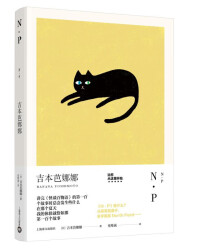
n.p
1.N·P
2.後記
N·P
據我所知,這個叫高瀨皿男的人是位憂鬱的作家,住在美國,在他那憂鬱的生活中抽空寫寫
小說。
四十八歲自殺身亡。
和已經離婚的妻子育有兩個孩子。
小說集成一冊,曾在美國紅過一陣。
書名叫《N?P》。
書中收錄了九十七個短篇,都極短,散文一般地依次羅列,大概這位作家是個沒長性的人。
這些事是從我昔日的戀人庄司那裡得知的,他發現了這位作家未曾發表的第九十八篇小說,並且把它翻譯了過來。
講完怪談百物語的第一百個故事時總會發生些什麼,而在那個夏天,我的體驗就恰如那第一百個故事,彷彿真切地經歷了那種事情。濃烈的空氣,宛若被夏日的天空吸進去的心情,不錯,那就是一個發生在那些短暫時日里的故事。
是哦,回想起來,我是在高中時見到高瀨皿男的兩個孩子的。只有一次,距離現在五年多了。
那天,庄司帶我去參加出版社的聚會。會場很大,碩大的餐桌上擺滿銀制的餐具和各色菜肴,很多人聚在幾個蘭花形小吊燈下談笑風生。
其他幾乎看不到什麼年輕人,所以當我發現他們時,心中湧起一陣喜悅。
庄司正同別人聊得起勁,我悄悄挪動了一下位置,來到一個可以更方便觀察他們的地方。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彷彿已在夢中和這兩個人見過好多次。不過很快我便回到了現實中,我明白,不論是誰見到他們倆,都會產生和我同樣的感覺。
不經意間誘發鄉愁的男女。
見我出神地盯著他們,庄司說:“那兩位就是高瀨先生的遺孤。”
“兩人都是?”我問。
“聽說是異卵雙胞胎。”
“挺想和他們聊聊的。”
“我來介紹一下吧?”
“我在這兒就是以年滿二十的身份出現的,瞧你小心翼翼的樣子!”我笑道。
“那就好。走吧,我為你介紹。”庄司也笑了。
“算了吧,還想再看看他們。”我覺得以現在的距離觀察恰到好處,搭起話來就難以細細打量了。
關於這兩個人,我只知道他們是高瀨皿男年輕時結婚生下的孩子,年齡和我相仿。他們很小時高瀨皿男就離開家了。高瀨皿男去世后,他們和母親一起搬到了高瀨在日本的家中。
我望著他們心想,這兩個人一定經歷了很多事情。
兩人都是高挑個兒,棕色頭髮。女孩肌膚嬌嫩,光滑飽滿,雙腿緊緻,腳蹬一雙黑色高跟鞋,寬肩敞領的禮服配上天真無邪的臉蛋,透出令人新奇的明快氣息。
男孩長得也很帥氣,雖然目光有些暗淡,但身上洋溢著充滿希望的健康,眼神中有一點天生的狂野,讓人感覺得到遺傳的痕迹。
兩人似乎很愛笑。自始至終都在聊著什麼,滿臉笑意地望著對方。
看到這情景,我想起自己也有過類似的心境。
那是我去附近一個植物園散步時的事情。一對母子在草地上隨意而卧。植物園很大,幾乎沒有人,碧綠的草地上灑滿金色的夕陽,年輕的母親將六個月大小的嬰兒放在一方白色毯子上,既沒逗孩子玩,也沒有笑,只是愣愣地注視著嬰兒,不時若有所思地抬頭看看天空。
陽光穿過母子倆的鬢髮,那鬢髮在風中輕柔地飄動,這有著濃重陰影的光景頗像一幅魏斯的圖畫定格在我心中。
我的目光突然變得很遙遠,彷彿成了神的視線,幸福和憂傷融在一起,匯成一幅夕陽下永恆的風景。
高瀨姐弟的周圍似乎也瀰漫著類似的氛圍,那是明媚夕陽下的憂鬱。即使再年輕,再快樂,那憂鬱也無法消散,也許這就是流動在血液中的才華在顯現吧。
我問庄司:“你要譯高瀨皿男的小說?”
“是啊。”他看著我,有點得意地回答。
“題目叫什麼來著?好像是什麼的首字母。”
“是《N?P》。”
“《N·P》是什麼?”
“Nonh Point的縮寫。”
“是什麼意思?”
“從前有首曲子,名字就是NoAh Point。”
“是首什麼樣的曲子呢?”
“嗯……非常憂傷的曲子。”庄司說。
那天,電話鈴聲將我從睡夢中突然吵醒。
“……喂?”我從被窩裡伸出手,拿起話筒,耳邊傳來姐姐低低的聲音:“風美嗎?是我,你好嗎?”國際長途特有的斷斷續續的聲響讓我清醒過來。
“有什麼……有什麼事嗎?”
屋裡幽暗恬靜,看看錶,清晨五點鐘。透過窗帘的縫隙能看到外面黎明的天空還罩著沉重的灰色。梅雨還沒結束呢,我怔怔地想。
“沒什麼事,就是打個電話。”姐姐說。
“又忘記時差了吧,現在這裡是早上五點。”
“抱歉抱歉。”姐姐笑起來。她嫁到了倫敦。
“那邊是什麼時間?”
“夜裡八點。”
想想時差,總覺得不可思議。難得相通的那條電話線也顯得珍貴起來。
“你還好嗎?”我問。
“我夢見你了呢,”姐姐道,“在我們家附近,你在走路,挽著一個比你年長很多的男人。”
“附近?你是說倫敦?”
“是呀,就在我們家後面的教堂那裡。”
“真是那樣就好了。”我高興地說。姐姐的夢總是很准,一直以來都是。
“可是總感覺兩個人挺難過的,也不跟我打招呼。那男的個子挺高,有些神經質的樣子,穿一件白毛衣,而你不知道為什麼穿著水兵服,所以呢,給我的印象倒像一對偷情的男女呢。”
“我沒有!”
雖然嘴上那麼說,但我還是吃了一驚,姐姐在夢中看到的一定是我和庄司。
可是姐姐並不認識庄司。
“這麼說,我的直覺也不準咯。”
“嗯,沒猜中。”
我一面答話一面想,這是否是某種前兆呢?這陣子我想起他的次數的確多起來,每次只一瞬間,而且方式也不同於回憶。在雨中,在黝黑潮濕的柏油路上,在街角閃光的窗戶上,那面容會忽地一下閃現出來,儘管我一直在努力忘掉他。
“姐夫好嗎?”
“嗯嗯,很好,入冬后要和我回日本呢,你和媽媽碰面了沒有?”
“嗯,常見面,她也想你呢。”
“代我問她好。吵醒你啦,對不起,回頭再打吧。”
“把時差弄清楚再打。”
“明白了,你也要當心,不要陷入悲哀的不倫之戀哦。”姐姐笑了。
我“嗯嗯”應著掛斷了電話。
放下話筒,屋裡的寂靜真真切切地向我壓來,這是一天開始前的時刻,新的一天還沒有真正到來。
我心裡有事,下了床,打開桌子下面的合葉拉門,裡面有個匣子,我並不常動。打開匣子,裡面有一包陳舊的《N?P》手稿、活頁封面和一塊沉甸甸的勞力士手錶。
這些是庄司的遺物。
他是四年前服安眠藥自殺的,自從我拿到這些東西以後,它們便在我心中的某個地方安頓了下來。
即使是白天,在我工作的大學研究室里,當遙遠的警笛聲掠過街市,引得我突然凝神靜聽的時候,我總是覺得那聲音離我家很近。每當這時,那些東西便會浮現在心頭,對我而言它們是如此沉重。
彷彿要確認一下似的,我拿起它們,又放回原處。然後鑽進被窩,再次進入夢鄉。
在我十九歲之前,我們一家三口:母親、姐姐和我住在一起。
我九歲、姐姐十一歲那年,父母離婚了,因為父親喜歡上了別的女人。
母親原來是一名口譯工作者,經常飛來飛去。為了照料我們,開始做書面翻譯,這樣可以在家裡工作。從初稿翻譯到會議紀要,什麼工作她都攬來做。
父親離開家以後,生活雖然寂寞,但還是挺有意思的。三個人住在一起,年齡和角色似乎每天可以轉換好多次。一個人哭泣,另一個人就來安慰;一個人說沮喪的話,另一個人就進行鼓勵;一個人撒嬌,另一個人就親切地給予擁抱,一個人生氣,另一個人知錯就改。
慢慢地,我們習慣了這種生活。
母親說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不多了,決定教我們英語。一過晚上十點,大家就把筆記本攤在廚房的餐桌上,開始一個小時的學習,內容是發音、單詞和簡單的會話。幼小的我們常在心裡嘀咕:這不是鬧著玩嗎?但為了母親,還是耐著性子參加。
因此,對我們來說,母親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並不是廚房裡的背影,而是戴著銀邊眼鏡教英語時那用力的面龐和飛快翻閱厚重的辭典時那自皙的手指。她在教我們的同時,似乎是要再一次把那些淺顯得不能再淺顯的英語銘記在心,重新描繪出自己的人生線條,那盡心竭力的樣子非常美麗。
現在,母親和我們都各自獨立生活了,但每每聚首,母親總會將我在英美文學研究室工作以及姐姐和外國人結婚歸結於她的教育,“能走到這一步還是因為跟著媽媽領略到了英語的樂趣啊。”她笑著說。在我心中,那時的母親比任何時候都可愛。
那天早上,我突然睜眼醒來,最初映入眼帘的是從窗帘縫隙處透進來的澄澈的夏日天空,那色調似乎與夢中所見非常相似。
夢裡我哭了。感覺好像是把從清湛的河水中淘到的砂金帶回了家。
“是因為悲傷而哭泣?”我怔怔地想,“還是因為在悲傷中得到了寬恕而哭泣?總之無論哪種情況我都不願醒來啊。”
涼爽的風穿過虛掩的窗吹進房間里來。
去研究室上班后,我的心依然平靜不下來。
茶杯被打碎,複印紕漏不斷。
“奇怪。”我不住地嘀咕。今天的確不正常。
宛若將夢中的感覺帶到了現實。
察覺到自己的反常后,我一直在琢磨,那是一個怎樣的夢呢?
接電話心不在焉,有時接晚了,有時掛早了,整個上午出了十幾次錯。這次教授乾脆自己拿起話筒, “喂,”他一面對著話筒打招呼一面滿臉無奈地望著我,到這時我才清醒過來。
“迦納小姐,找你的。”教授苦笑著將話筒遞過來。
道聲抱歉,我接過話筒。
“喂?”
電話斷了。
“對方報姓名了嗎?”我疑惑地問教授。
“沒有,只問迦納小姐在嗎,是個女人的聲音。”教授回答。
“我看,迦納小姐,今天你累了,去午休吧。”教授說。
“可是,才十一點呀。”
我的話音剛落,辦公室里一直佯裝不知的同事們便紛紛在各自的座位上向我示意,是啊是啊,去休息吧,大家眾口一詞地說。
於是,我被趕出門似的離開了辦公室。
今天的我有那麼奇怪嗎?我這樣想著,穿過無人的操場出了校門。這是我沒有料到的事,眼前的景物都很新鮮,彷彿自己還沒有完全回到現實中來,莫非那是我降生於世時的夢境?
學校後面有一條坡道,坡道中間有一家書店。想到午休時間有兩個小時,我便走上坡道,決定去那家店裡買點什麼。
我就是在那條坡道上碰到乙彥的,這是我平生第二次見到他。
那時我正在穿越坡道旁的一條老商業街,我怔怔地望著街道,沉醉在眼前的景物里,藍天,流雲,街上裝飾鋪面的銀色和粉紅的花。我清楚地記得當我們見面時,那些躍動的影像還在我的眼角殘留不去。
猛抬頭,看到一個似曾相識的人從坡道上走下來。
“啊,是你嗎?”我條件反射似的脫口而出,“你是高瀨先生的公子吧。”
“是呀。你是?”
他眼裡充滿驚訝,這是很自然的。我連忙自我介紹:“我曾在H出版社的聚會上見過你一面,我叫迦納風美。”
他愣愣地打量我。“哦哦,”他說,“當時你和翻譯家戶田莊司在一起吧。”
“記得很清楚呀。”我說。
“那時只有我們幾個比較年輕,很顯眼。”他笑道。
“你住在這附近?”我問。
“哦,我家在橫濱,現在住姐姐那裡,就在這坡道上頭,T大學心理學研究院裡面。”
“哎?T大?”
“是呀。”
“還真巧了,我就在那裡的英美文學研究室工作。”
“是嗎?我姐姐就是那次聚會上和我一起的同伴,她叫咲。”
“那一定在路上遇到過。”
“有時間嗎?一起喝茶怎樣?”
我有大把大把的時間。
“嗯,行啊。”我說。
臨近中午的咖啡店很冷清,我們面對面坐下來喝咖啡。對我來說,他是一個本應只存在於故事中的屬於過去的人物,我根本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感覺很奇特。我仔細地重新審視他,發現和過去大不一樣了,雙眼黯淡無光,和那白色馬球衫以及光滑的面龐給人的印象很不協調。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不曾有的感覺。
“乙彥,你變了很多啊。”
“是嗎?”
“看上去像年齡大了許多,其實你只比我大兩歲,你的事我都知道呢。”
“那麼,你今年二十二?”
“是呀。”
“這麼說來,那時你還是高中生吧。”
“是的。”
“五年……自己一點也不覺得歲數大了多少,大概是去了國外的緣故吧。”
“什麼地方?”
“波士頓。四月份剛回來。”
難怪在他身上有那麼一種朦朧的封閉傾向,這種傾向是歷經命運壓迫卻仍要拚命保持自尊的人所特有的,這是我以前見到他時不曾有過的感觸。
“你一直住在日本吧。”
“嗯,在橫濱的祖父母家。”
“你父親一去世就去了那兒么?”
“是啊,我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已經不在家住了,但他的戶口沒遷走。後來祖父母感到寂寞,就把我們叫了去。”
“那時你多大?”
“十四歲吧。父親的死似乎對母親打擊很大,我們就奠名其妙地像大人似的勸母親出去旅行,於是大家就在外面四處轉了一圈,回來后卻不知道以後該怎麼辦。正在這個時候,祖父母問我們是否願意回日本。當時母親很猶豫,但我們都勸她去。祖父母對母親的將來……也就是是否再婚之類很寬容,而且他們認為我們三個人一起生活母親會承擔不起。那時候,儘管我們不願意離開已經住慣了的國家,但還是裝出想去的樣子,挺不容易的。”
“這個我理解,我們家也是這樣,父母離婚後,我們姐妹倆和母親三個人一起生活。”
“那樣待在一起是不健全的呀。”
“就是,父親離開后的存在感還是很強。”
“就沒有一點精神緊張方面的問題嗎?”
“有啊。”我說,“有一段時間,我失聲了。”
“因為這個么?”他很感興趣地問。
“好像是吧,毫無理由地不能說話,又毫無理由地恢復過來。”
“在你幼小的心中一定存在激烈的衝突。”他說。
是啊,父親離家后的第三個月,彷彿為了使精神緊張的母親不受傷害,我突然變得說不出話來。
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放學后我在外面玩得太野,到了晚上便發起高燒。昏睡了好幾天,沒去上學。身上痛,喉嚨也腫脹起來。
我發著燒,迷迷糊糊地躺著,聽到母親和姐姐正在說話。
“……怎麼這樣想?”母親的聲音。
“不知道,可我就是這樣想的。”姐姐說。
“你說風美髮不出聲了?”母親說,聲音中明顯帶著歇斯底里的味道。
“嗯,我覺得是。”姐姐淡淡地回答。
姐姐的感覺一直很靈。比如誰來的電話,天氣變好還是變壞,這類事姐姐總能猜得准,那種時候她總是超乎尋常地從容,像個大人似的。
“這話可不能在風美面前說。”母親似乎有點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