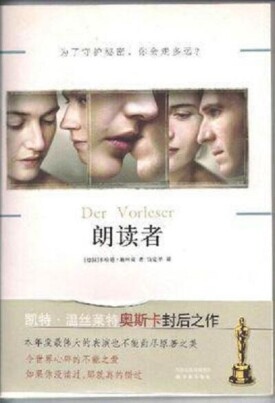共找到4條詞條名為朗讀者的結果 展開
- 央視綜合頻道播出欄目
- 德國、美國2008年史蒂芬·戴德利執導電影
- 人民文學出版社圖書
- 本哈德·施林克著長篇小說
朗讀者
本哈德·施林克著長篇小說
《朗讀者》是德國法律教授和法官本哈德·施林克於1995年撰寫的長篇小說。作品1995年在德國出版,1997年由卡露·布朗·珍妮維(Carol Brown Janeway)翻譯的英語版本於美國發行。
《朗讀者》講述男孩米夏和女人漢娜之間充滿激情的忘年戀,而故事的深層含義則是近代德國人對於歷史、暴行與原罪的自我鞭笞式的反思。
《朗讀者》是第一本登上《紐約時報》冠軍的德語書籍,先後獲得漢斯·法拉達獎、“世界報”文學獎等獎項。
![朗讀者[本哈德·施林克著長篇小說]](https://i1.twwiki.net/cover/w200/m6/b/m6b9beed8eb11b86923c46a74e8942408.jpg)
朗讀者[本哈德·施林克著長篇小說]
在米夏的朗讀中,漢娜像個孩子似的時而痛哭,時而
大笑,那個夏天,是他們一生中最短暫最快樂並最終影響了後來歲月的時光。不久后一天,漢娜突然不辭而別,8年後再次見到漢娜的時候,米夏作為一名實習生在旁聽,漢娜成了一名站在法庭上的納粹罪犯,她曾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女看守。漢娜並沒有像其他一同被指認的罪犯一樣,否認自己的罪行,而是堅定異常地坦誠一切。直到審判席上,漢娜不願提筆在白紙上寫下黑字做筆跡比較,並因此背負罪名被判終身監禁時,米夏終於明白了原因,明白了漢娜為什麼不看他的旅行計劃,為什麼會在拿到菜單時神色緊張,為什麼總是不厭其煩地聽他朗讀,漢娜是一個根本不會認字讀書的文盲,但她拒絕向任何人袒露自己的缺陷,即使替他人受過而終身監禁,也要隱藏她是文盲這個秘密。
米夏是可以說出真相替她減輕罪與罰的,但卻最終選擇了和漢娜一樣,用生命去捍衛這個卑微的秘密。兩人的故事並沒有因為漢娜的入獄而終結,在隨後的人生中,米夏慢慢體會到了漢娜的想法。他開始給獄中的漢娜寄去各種錄著自己朗讀聲音的錄音帶,漢娜也開始了識字,並給米夏寄去了一封又一封的信件,但米夏卻始終沒有回信。十八年過去了,在獄中表現良好的漢娜獲得了假釋,終於能夠和米夏見面了,可是面對這一機會,漢娜卻喪失了勇氣,她以上吊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1995年,施林克在創作了大量偵探小說之後,嘗試新的文學創作,開始寫純文學作品。在這種背景下創作了《朗讀者》。
漢娜
漢娜在小說中出場時已經36歲了,生理上已經完全成熟,但是心理上還一直處於停滯的蒙昧狀態。這種蒙昧狀態的主要表現為她不諳生活中的道德底線和遊戲規則,其生活是在別人的指令和引導下進行的,不具備辨別是非善惡、輕重緩急的能力,更不要說自我反思和糾正的能力。她21歲時身先士卒,做了奧斯維辛及其附近集中營的女看守。為了掩蓋自己是文盲的秘密,在西門子公司要升遷她時,她毫不猶豫地選擇從事殺人幫凶這一職業,而絲毫沒認識到這一工作的罪惡性。在集中營中她選擇一些體弱的女子在晚上來為自己朗讀,為了不被人發現自己是文盲,她若無其事地第二天又將她們送到奧斯維辛的煤氣室,絲毫沒認識到她們和自己一樣擁有溫熱的血肉之軀,擁有作為一個人存在的尊嚴和權利。在集中營中她“選擇”犯人,即每個月從1200名犯人中選擇60名送到奧斯維辛這個殺人工廠,明知這些人要去送死,但因為是上級命令所以感覺這是理所應當的,絲毫沒想到如果這些人是自己的親人和朋友,她絕對不會如此無動於衷。在那個烈火衝天的夜晚,500名婦女被鎖在教堂中活活燒死,而她卻因為沒有得到上級的命令,害怕犯人逃脫和造反,寧可犧牲數百人的性命,也要烙守職責,堅守到底。一言以蔽之,她的生活如果沒有他人的引導、命令和指示,就會處於完全混亂的狀態。導致她不成熟的核心因素則自己是文盲這一事實,她無法克服自己的這一弱點,所以就竭盡全力地來掩蓋這一事實。文盲不是她的錯誤,但她因此犯下了一個又一個罪惡。
米夏
作為朗讀者,米夏的朗讀可分為兩個時期。在第一時期里,他是應漢娜的要求而被動地、無自我意識地朗讀。之後他逐漸變為“乘著情慾而來”,而漢娜卻很“頂真”,他必須先為她朗讀半個小時,她才會為他沐浴,滿足他的要求。後來,他也漸漸地喜歡上朗讀,並將其納入他們二人世界的固定節目之中,一起享受這一過程。他為她朗讀《奧德賽》、《愛米麗亞·迎洛蒂》、《陰謀與愛情》、《一個窩囊廢的生涯》和《戰爭與和平》等,在朗讀中,他的情慾“漸漸退潮”,在漢娜的熱忱參與中,他感到無限滿足“沉浸在一片無邊的幸福之中”。這一時期的朗讀,對米夏來說,書目的選擇是隨意的,大多屬於學校教科書範圍,而且對書的理解和漢娜一樣只是一種感性的認識,屬於一個中學生正常的認知漸進過程,但它對米夏的影響是深遠的,這種文學素養的積澱在他主體性格的形成過程中成為一個難以磨滅的胎記,幾乎暗中引導著他的人生走向。
在第二時期,米夏主動地為漢娜朗讀。在漢娜服刑的第八年,他又開始為漢娜朗讀。出於對妻子和女兒的歉疚感,出於沒有揭露漢娜真相的負罪感,出於對第三帝國這段歷史的“眩暈麻木”感,米夏夜不成眠,無奈之餘,再一次開始為漢娜而朗讀。他秉燭夜讀,再一次從《奧德賽》開始,朗讀凱勒、馮塔納、海涅和默里克,朗讀卡夫卡、弗里茨、巴赫曼和倫茨,甚至還朗讀自己所寫的作品。朗讀使他與漢娜的距離時而遙遠,時而親近,這種若即若離感不僅使他獲得了心靈上的安靜,開始直面自己,而且也促使他重新思索他與漢娜的關係,重新思索第三帝國那段黑暗的歷史。
歷史反思
《朗讀者》是個寧靜而又深層的愛情故事,但也是施林克就德國人對罪責、對罪行的看法所作的犀利獨白。小說中的麥克象徵了德國無辜的新一代,在同聲譴責戰時納粹的同時,卻也發覺無法自外於殘暴年代的歷史責任。
在小說中,豐腴的中年美婦漢娜的身份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看守,二十年後站在了被告席上,因為一起猶太囚徒的死亡慘劇。“愛上女看守”,似乎又是一個“制服誘惑”的故事,作者在小說中也詳細地描述了漢娜身著“制服”的情景。然而,已經成為青年的米夏認識到,對於站在歷史被告席上的漢娜來說,穿“制服”上法庭是一個致命的“政治正確”上的錯誤。同時,美婦漢娜還是一個肉感、強悍、執拗、笨拙、邊緣化的人物,她來自農村,不識字,有著旺盛的性慾,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在漢娜的一生,在她與米夏的愛情中,漢娜處處表達出她對米夏及其家庭所代表的城市文明生活的渴望,同時,因為擔心被“文化”遺棄,而選擇保守自己的隱秘出身,選擇暴力與逃離。米夏對漢娜的愛,來源於漢娜的成熟與肉感的性誘惑力;而漢娜對米夏的愛的漸進,除了最初的性挑逗之外,更多地來自於米夏為她朗讀文學經典的過程。“朗讀”是這部小說的核心。在集中營中,漢娜每天晚上都要叫柔弱的猶太女孩為她朗讀,然後目送她們走進毒氣室,漢娜宛若“一千零一夜”里的暴君,一個掌握生死權柄、習慣使用暴力而迷戀“文化”的人。米夏與那些猶太女孩宛若山魯佐德,不知道明天的命運如何。擔任朗讀者角色的猶太女孩們,走進了毒氣室。而米夏,一生籠罩在漢娜的陰影之下,失去了愛的能力。
如同山魯佐德一樣,在小說的最後部分,二人的角色發生了轉換。暴君漢娜被判處無期徒刑,住進了監獄。處於“安全”但是無愛狀態的米夏,繼續承擔著朗讀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成為啟蒙者,一年年為漢娜寄磁帶。在米夏的朗讀磁帶的帶動下,漢娜學會了拼讀和拼寫,開始閱讀關於大屠殺的書籍。小說中尤其提到了漢娜·阿倫特的名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個關於惡的平庸報告》。艾希曼的身份和小說中的漢娜類似。阿倫特提出,艾希曼是有罪的,是“平庸的惡”,就像木偶,充當了極權社會的犯罪中介。漢娜的這一轉變,固然是由於米夏的愛,更多的則是由於對自身的惡的反省。
《朗讀者》是本複雜的小說。這是一部關於歷史與個人、情慾與道德、愛與罪的小說,這些東西統統被壓在小說敘述者、主人公米夏的身上,當這些東西無法拋棄、無法剝離、無法逃避的時候,它帶來的感動無疑也是相當沉重的。現在有一個詞常被引用,叫“歷史的人質”。而《朗讀者》告訴我們,這個辭彙遠比我們想像中要複雜得多。尤其是這個“歷史”跟我們的靈魂和肉體都發生關係的時候,這個“歷史”跟我們的父母和愛人都發生關係的時候。雖然我說這本書的兩個層面和我這個“異國讀者”有些“隔”,但是類似的歷史、類似的境遇,在我們這個“異國”絕非沒有,然而我們這裡似乎缺乏這樣“直面歷史”的作品,甚至在近來的影視和圖書里,僅僅剩下一些“懷戀”了。如果這本書仍能關乎我們自己的話,大概就是這點感慨和惋惜。
在《朗讀者》的謎中,無疑漢娜的認罪之謎最令人費解。一個女人在戰爭期間放棄自己安定的生活,入伍做了集中營女看守;繼而又在審判期間放棄自己辯護的權益、寧願認罪被判無期徒刑,這一切僅僅是因為要掩蓋自己是文盲,不認識字而已!施林克用這個多少有些奇崛的故事文本,告訴我們雖然罪行是無可爭辯的,但是對於犯罪者是無法簡單判定的。對於個人與歷史的關係,《朗讀者》做出了這樣一種值得警醒的反思。而在這部小說的后兩部分,我們接觸到最多的辭彙,是“麻木”二字,在漢娜一案中:審判者是麻木的;旁聽者是麻木的;甚至證人——集中營的倖存者也是麻木的。反而倒只有漢娜這個站在被告席上的人表現出豐富的性格:時而倔犟、時而驕傲,甚至有些天真——尤其是她反問法官(只有職業表情的人)“換了您會怎麼做呢?”這無疑是對自認是無罪的人、自認是正義者的拷問。在我看來,這句拷問,就是《朗讀者》的核心。
當然,任何一種簡單讀解《朗讀者》的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它本身的多義,是它的吸引力之一。實際上對這本書的閱讀體驗和讀者個人的歷史應該是有相當聯繫的。但是在“愛情”這個層面上的感動,普天下都有著同一性。《朗讀者》寫的愛情,毫不諱言是包裹著情慾的,是關乎身體的——尤其是漢娜的氣味,令米夏一生都想在別的女人身上“重逢”;當然他們之間的愛還有“神聖的”儀式,那就是朗讀,在性愛之後,米夏照例要給漢娜讀書,各種名著,甚至在漢娜入獄之後。雖然“朗讀”對於漢娜的意味極為複雜,但這無疑是這段愛情在米夏心中得以延續的重要動力。據說,《朗讀者》要被拍成電影,其實所有讀過這本書的人,肯定在心中對漢娜已經有許多形象的投射。按米夏的話來說“她有很多寫照”:比如在廚房拉上長筒襪、騎著車賓士時裙邊在車子帶起的風中飄浮、站在書架前手指滑過書脊,等等。這是這本小說最感性的地方,在初戀結束之後,對那些“寫照”的懷念——尤其是對於有“負罪感”的戀人來說,那些在分離之後,那些畫面、那些氣味、那些場景、那些話語,當你在心頭又和它們不期而遇的時候,無疑會令魂魄為之一顫。或許也可以說,正是他們之間的情感令讀者“魂魄為之一顫”,從而更加深了對這本小說政治性的反思。
在《朗讀者》中,施林克對於納粹暴行的批判一直沒有停過。漢娜在獄中服刑的漫長歲月中,通過自學逐漸可以閱讀,從一個聆聽者蛻變成一個能夠獨立閱讀和書寫的人。漢娜閱讀關於納粹暴行的書籍越多,就越發為自己的過去感到懊惱。在十幾年的監禁生活即將結束的時候,漢娜向米夏進行了一次靈魂深處告白:“我一直覺得沒有人能夠理解我。你知道如果不能被人理解,我永遠不會想到要懺悔,即便是在法庭上。然而現在,那些無辜死去的人們,他們能夠理解我。在監牢里,我和她們呆在一起的時間更長,不論我是否願意,他們晚上都會來。在被審訊之前,我甚至在夢中就可以將他們逐走”。
朗讀成了他們約會時的必備節口,十五歲的少年“一遍遍地為心愛的女人朗讀學校要求學生朗讀的文學作品:荷馬史詩、西塞羅的演講和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老人怎樣與魚、與海搏鬥一。”這段發生在年齡相差21歲的中年婦女漢娜和年僅巧歲的中學生米夏之間的感情糾葛不僅僅探討了一段跨越年齡的愛情,也透視了代溝這個更為廣大的社會現象。
在小說的第一章,十五歲的少年因病在街邊嘔葉,得到中年婦女漢娜的照顧。“她旋開水龍頭,用兩隻手掬著清水潑在我的臉上算是給我洗了臉。”她粗糙的舉動即使在表達著關懷和母性,也透露著粗暴的本性。漢娜和米夏開始戀愛關係的時已經是36歲的婦人了,年齡大的足可以做米夏的母親。這種不能被社會承認的,在當時看來甚至是違法的關係映射出米夏這代青年人與他們父輩的關係:戰後德國的青年人如何理解他們的父輩在戰爭期間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他們是否應該原諒他們所深愛的父母,還是應該站出來毫不留情地譴責他們?正如成年米夏而對作為納粹戰犯在法庭上被審訊的昔日愛人漢娜時心底里流淌出來的感覺:“我想要一邊理解漢娜的罪過一邊詛咒她的過錯,但是這卻太可怕了。我試圖要理解她的罪過,但是我無法同時對她進行她應該受到的批判;當我批判她怨恨她的時候,我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理解她的空間。我強迫自己在理解的同時去譴責,然而我根本無法同時做到兩者。”米夏對漢娜既愛又恨,欲罷不能的感情,恰恰是施林克這一代戰後德國年輕人父輩的感情。“我因為對漢娜的愛而註定經受痛苦,這是我這一代人的痛苦,是所有德國人的痛苦。”戰後德國兩代之間難以互相融入,無法互相理解的尷尬,通過這段忘年戀細緻地反映了出來。
在小說第二部分,已經長大的米夏再次見到漢娜時是法律系參加法庭實習的大學生。對而站著的漢娜,是接受審判的納粹戰犯。米夏明白了一個秘密:原來,曾當過集中營女看守的漢娜是個文盲。因此她與少年米夏約會時一再要求米夏為她讀書。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掩蓋這個令她感到羞恥的秘密,漢娜放棄了西門子公司的工作跑去當了納粹黨衛軍女看守一一因為這個活兒不需要識宇。為了避免暴露自己是文盲,漢娜在法庭上拒絕被辨認筆跡,直接攬下被指控的所有罪行。文盲是本書中最為重要的象徵,它象徵著納粹統治下的德國和德國人民像文盲一樣生活在黑暗和無知當中,既無法辨別是非也無法在是非而前保護自己,大多數人只能選擇麻木地接受。漢娜認真聆聽少年米夏的朗讀,強烈的求知慾望正代表了第三帝國時期一部分試圖尋求正義和光明並希望擺脫納粹統治的德國人的心態。朗讀者一直圍繞著文盲這個核心思想:因為漢娜不認識字,我才為他朗讀。施林克將這個主題作為推動器來幫助情節的發展。
故事不僅僅推動得完關,故事中隱藏的內涵更加深刻,那就是尊嚴。透過這層尊嚴,讀者聞到了殘忍,無奈,懺悔與寬容的味道。米夏知道了漢娜的過去和她納粹的身份,他感到受了欺騙,感到恥辱和羞憤。當他意識到昔日的情人原來是不認識字的文盲,他的內心掙扎了,應該尊重漢娜的選擇,還是將這個秘密揭露給法庭來洗脫漢娜的罪名米夏猶豫了。真正的問題已經不在於漢娜是否是文盲,而是米夏是否有勇氣承認自己和漢娜的過去,是否有勇氣正視漢娜戰爭中的罪過,是否有勇氣正視上一代人犯下的滔天大罪。他替自己找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借口維護漢娜的尊嚴,尊重漢娜的個人意願,最終選擇了漠視和麻木。“為了這個尊嚴,既是漢娜的也是我的,我參與了謀殺。這與納粹在戰爭中的暴虐行為有什麼區別呢?我也參與了對漢娜的謀殺,把罪不至此的她推進了終身監禁的大牢。我也是有罪的,這是罪人對罪人的審判,是用罪過審判罪過。”這無疑是對第三帝國的深刻反思,也是對生活在那個時期的兩代人的深刻反思。
批判法律
在對漢娜的審判中,作者描寫了法庭的麻木,“審判剛開始,他們還帶驚恐和剋制的表情,到後來,法官和陪審團們的面部表情就恢復常態了,他們開始露出微笑,交頭接耳,在討論到要去以色列出差取證時,他們又齊發旅遊之豪興,爭先恐後起來。”
作者辛辣地諷刺了律師的毫無原則和趨利避害,“當其他被告的辯護律師發現,這些策略都因為漢娜的心甘情願而落了空,他們就掉轉方向,採取一種新的對策,盡量利用漢娜對法庭的順從態度,把什麼事都推到她身上,以便為其他被告開脫罪責。”
作者還描寫了法庭審理中人性的惡的運用,而法律對此一樣無可奈何。“一旦漢娜承認了報告是她所寫,其他被告就順水推舟、得寸進尺了。他們齊聲說,凡不是一個人幹得了的事,漢娜就硬要他們一起去做,她擔任指揮,一切事情都出自她的決定。”
小說中,審判長並不能主持正義,連漢娜不會寫字也甄別不了,卻號稱熱愛“法學家和法官的事業”,這真是一種諷刺。當看到人性中的麻木、推諉、陷害、怯懦、逃避都不約而同地披著正義與和平的外衣,來對付一個裹挾在歷史洪流中只是想隱瞞文盲和私情秘密的女人時,法律與屠刀根本沒有什麼分別。法律原本是為保護私人的利益而存在,但不可避免地,竟然也會因它所要保護的私人利益而使其公正性受到踐踏。
人的尊嚴是神聖、純潔的,無論在哪個時代,只是用量化的法條來判斷是非對錯,是極其可笑可怕的,即使無可否認現階段我們是如何地離不開法條。人的尊嚴應該依靠更純潔的人性的呼喚來洗滌,而不是萬千的法條。
從藝術性上來說,《朗讀者》並沒有特別出眾的地方。它的語言似乎談不上優美。它的形式也很簡單,全書以三個章節來劃分米夏人生的三個階段:少年米夏與漢娜的相識和相處,青年米夏與漢娜在審判期間的重逢,審判之後十多年間的滄桑變化。敘事方式也是單一的,整個敘述是以米夏的視角、用回憶的手法、依照時間順序來推進的,因此也貫穿了統一的腔調。作為德國人的作者,在行文中保持著一種德國式的沉穩、嚴肅、冷靜和直率。他不慌不忙地從容道來,一邊回憶一邊講述,一邊感受一邊表達,一邊提問一邊分析。米夏的歡愉和痛苦、疑惑和追問,都被講述得理性而直白,還時時透出一種浸在骨子裡的沉痛之感。因此,《朗讀者》不僅不是華美精巧的,也不是輕鬆愉悅的。
但它卻有種讓人肅然心動的力量。這力量可能部分來自它的真誠和莊重。面對那樣駭人聽聞的道德災難和人性罪惡,真誠和莊重是最自然也最得體的態度。從一開始,米夏就自剖其心,他對漢娜的熾熱的情和欲,他因為愛上有罪之人而捲入其罪的羞恥和自責,他不知道對愛人的罪行是該理解還是該譴責的矛盾和迷惑,他因為自己對漢娜的背叛和拒絕而產生的內疚與懷疑,還有他對一代人的罪責該如何面對和評判的追問與思考,他對麻木不仁和沉默不語的警醒與質疑,都以一種坦誠、敞開又真切的態度朗聲說了出來、問了出來。作者把米夏的所感、所思和所察,從個體最細微的心思、到人心最深處的幽暗,從最簡單的愉悅、到最痛切的責問,都不加修飾地攤在我們眼前,一絲不苟,也一絲不掛。作者,或者說米夏,不為人諱言,也不為己諱言;不為有罪的一代諱言,也不為清算上一代的這一代人諱言。他只是認真地觀察,鄭重地思考,沉痛地詰問,既不舉重若輕,也不避重就輕。正是因為如許的真誠和莊重,米夏與漢娜不合倫理的情愛糾葛才能不帶有一絲淫邪和輕浮。
小說採用全知的第一人稱敘述方式,極大地增加了文章的真實感,讓讀者一直有親歷其境的感覺,同時也使作品增添了不少自傳的色彩。但是,小說這一體裁特徵又包含一定的虛構性,所以施林克對第三帝國這段歷史的看法只能從其敘述態度和小說中的評論解讀出來。此外,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只能將視角限制在“我”之內,不能體會他人的心理,因而讀者就只能通過米夏的視角來解讀其他人物,在此基礎上探討施林克是如何看待第三帝國這段歷史的。
作為戰後一代的代表,米夏對歷史的看法一直是變化著的。最初作為不知情者,他愛上了一個納粹女看守,從一個旁觀者、局外人忽然間變成了參與者、劇中人,本來可以與納粹歷史擦肩而過,卻被漢娜牽扯進來。施林克設置的兩代人在面對第三帝國歷史時對峙的巧妙之處,在於不是簡單的“父輩文學”中的“父子關係”的對峙,而是難以自拔且糾纏不體的情人關係。如果說父子關係是上天註定的,那麼情人關係則是人可以選擇的,這樣米夏埃爾在與歷史的對峙中於被動之中又有一定的主動。米夏在一個青春動蕩的年代不知情中選擇了漢娜;在大學的法學課上,參與了“集中營討論小組”,義不容辭地把自己的父輩推上了歷史的審判席;法庭上與漢娜相遇之後,譴責的手指轉了180度,從漢娜陡然轉向了自己,從自我反思到整個民族的反思,從煎熬糾纏到解脫釋懷,一條自我拯救和逍遙的啟蒙之路走得無比艱難和辛苦。
《朗讀者》1995年問世以後已經被譯成40餘種語言,被引領美國閱讀潮流的“奧普拉讀書俱樂部”推薦。
《朗讀者》2006年1月在北京圖書訂貨會上推出,已重印10餘次,位列《新京報》等數十家有影響力的傳媒之圖書暢銷榜;是民營書店北京萬盛書園、上海季風書園、南京先鋒書店等的上榜暢銷書。榮登卓越網2006年文學類十大好書之首,噹噹網2006年度中國圖書暢銷榜、新書專家榜,《中華讀書報》2006年百部好書推薦榜;入選《2006知識工程推薦書目》;是2006年度“全行業優秀暢銷品種”和“引進版優秀暢銷書”。其老書重做被評為《中國圖書商報》"2006優秀圖書營銷案例”。
2008年,作品由英國導演史蒂芬·戴德利拍攝成同名電影,電影相繼榮獲金球獎和奧斯卡獎等獎項。截至1999年4月,該書的發行量在德國已達50萬冊、法國10萬冊、英國20萬冊。
德國作家漢斯·布赫:“小說描繪的故事畢竟是不真實的,是在想象的基礎上虛構出來的,比如說漢娜是個文盲,不會讀寫,這讓人難以置信,就像阿Q只是一個象徵性的人物,不代表現實。在文學奇迹中建築出來的故事雖然講述真理,卻無法反映現實生活。”
作家肖復興:“這部小說是一個在為了不能夠忘卻的記憶中,戰後新一代人如何成長的寓言。”
作家曹文軒:“在我為他人開出的所有書單中,無一沒有這本書的名字。這樣一本書,正合我的閱讀趣味與文學理念。在20世紀的文學普遍放棄感動的文章而一味——甚至變態追求思想深刻的當下,再一次閱讀這樣令人感動的小說,我們在感動中得到了深華。”
《紐約時報書評》:“感人至深,幽婉雋永!小說跨越國與國之間的樊籬,而直接同人類的心房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