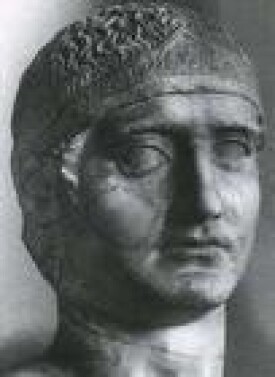費邊
費邊
費邊,全名為“拖延者”昆圖斯·費邊·馬克西姆斯·維爾魯科蘇斯(拉丁語:QVINTVS·FABIVS·Q·F·Q·N·MAXIMVS·VERRVCOSVS·CVNCTATOR),(約公元前280~公元前203),一譯法比烏斯或菲比爾。古羅馬政治家、軍事家,傑出的統帥。曾五次當選為執政官(前233年、前228年、前215年、前214年和前209年),兩次出任獨裁官(前221年、前217年),並擔任過監察官(前230年)。費邊以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採用拖延戰術對抗漢尼拔,挽救羅馬於危難之中而著稱於史冊。
費邊出身於羅馬最顯赫的貴族氏族之一的費邊氏族,屬於該氏族的馬克西姆斯分支。他的祖父昆圖斯·費邊·馬克西姆斯·古爾格斯(前292年的執政官)和父親昆圖斯·費邊·馬克西姆斯·古爾格斯(前265年的執政官,與父同名)都擔任過執政官職務。普盧塔克說,童年時代的費邊性情溫順、說話緩慢,以致於被稱為“奧維庫拉”(Ovicula),意為“羊羔一樣的人”。不過這些性格上的弱點並沒有阻礙費邊的政治事業,尤其是他還出身名門。
費邊於前233年第一次當選為執政官。他在任上打敗了利古里人(高盧人的一支),把他們趕進了阿爾卑斯山,因此被授予一次凱旋式。之後他又於前230年當選為監察官,前228年第二次當選執政官。在這一時期,羅馬與迦太基的關係日趨緊張,因為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擴張活動取得了巨大進展。但羅馬還面臨著更迫在眉睫的北方高盧人問題,因此無力在西班牙採取強硬立場。前226年,羅馬向迦太基駐西班牙的軍事統帥哈斯德魯巴爾(此人是哈米爾卡的女婿,漢尼拔的姐夫)派遣使團。雙方簽訂了一項條約,根據該條約,羅馬實際上默認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勢力範圍。這一妥協沒有維持多長時間:前221年哈斯德魯巴爾在打獵中被其奴隸所殺后,漢尼拔接手了他在西班牙的職務,並開始實行更具侵略性的政策。漢尼拔決心迫使羅馬向迦太基宣戰,遂於前219年率軍越過伊伯魯斯河(條約中規定的雙方在西班牙的界河)進攻羅馬人的盟友薩貢圖姆城(今薩貢托)。羅馬元老院得知此事後,派遣以費邊為首的使團前往迦太基,要求對方解釋漢尼拔的行動是否得到了迦太基元老院的授權。據蒂托·李維記載,迦太基元老院用一段冗長的話表示他們拒絕對此事負責,而羅馬人應該承認現狀。這時費邊折起了袍子的一角說道:“我們帶來了和平與戰爭兩種選擇;你們自己選吧。”迦太基人用同樣專橫的態度回答:“你們羅馬人自己挑。”於是費邊放下袍子,說:“羅馬選擇戰爭。”迦太基人異口同聲地回答:“我們接受;並且,我們還將以和接受時同樣堅決的態度來實行它(指戰爭)。”費邊立刻率領使團返回羅馬,第二次布匿戰爭就這樣開始了。
第二次布匿戰爭爆發后,漢尼拔出人意料地翻越阿爾卑斯山進攻義大利本土,完全打破了羅馬人原有的戰爭計劃(以兩支軍隊分別進攻西班牙和迦太基本土)。漢尼拔不久即在特雷比亞戰役和特拉西梅諾湖戰役中取得了兩次輝煌的勝利。羅馬人在這兩次戰役中損失了大量兵力,而且通往羅馬城的道路已經被打開,使羅馬本身面臨被圍攻的危險。在這種緊急形勢下,元老院於前217年任命費邊為獨裁官(第2次任期)。
漢尼拔在特拉西梅諾湖戰役之後並沒有進軍羅馬,而是縱兵蹂躪義大利各地,以瓦解羅馬對義大利的統治。他先是向東推進到亞得里亞海沿岸,稍事休整后即向南前往普利亞,並將路過的地區洗劫一空。費邊也率領4個軍團前往普利亞,並在阿爾皮附近追上了漢尼拔。但他在追上漢尼拔之後卻避免與其正面作戰,而是讓自己的軍隊與漢尼拔保持一段距離,同時伺機騷擾。這就是所謂費邊戰術。費邊的策略是:漢尼拔的軍隊久經戰陣,戰鬥力極強,其騎兵部分更是羅馬根本不能抗衡的,因此與之決戰並不划算,反而會加劇損失。但漢尼拔孤軍深入,補給困難,而羅馬在本土作戰,兵員和糧草都易於補充,從長遠看優勢在羅馬一方。所以只要拖住迦太基軍,保存己方實力,並注意援助同盟城市,避免其倒向漢尼拔,則我方越來越強,敵方越來越弱,最終必能獲勝。在這種策略的指導下,費邊率軍尾隨漢尼拔,但卻避免與之發生接觸。漢尼拔因之受到了很大牽制,由於始終面臨費邊的大量軍隊的威脅,他難於分出兵力去洗劫義大利城市,而那正是他想做的。漢尼拔顯然也理解了費邊的策略,為了打破這種局面,他多次嘗試引誘費邊與其對決;但即使當他的軍隊在義大利最富有的坎帕尼亞地區破壞掠奪時,費邊仍只是保持距離地尾隨著,始終不與他進入決戰。
費邊的戰術在軍事上是有用的,但在政治上卻對他十分不利。縱容漢尼拔的結果是農村地區受到迦太基軍嚴重破壞,因此這種策略必然導致農民的強烈不滿。同時,漢尼拔在義大利境內來去自如,可能動搖各同盟城市對羅馬的忠誠(這種忠誠往往建立在對羅馬軍事能力的敬畏之上)。元老院中也有許多反對費邊的人。這些反對情緒日趨強烈,使費邊的聲望嚴重受損,人們諷刺他為“拖延者”(CVNCTATOR)。隨著戰爭的持續,費邊的消極戰術在羅馬越發不受歡迎。他在卡西利努姆戰役(前217年)中的失誤更是使自身面臨困境。這次戰役的背景如下:漢尼拔決定在冬天前離開被他破壞殆盡的坎帕尼亞,返回普利亞地區。為此他準備先攻克途中的卡西努姆,以補充給養。但他的嚮導聽錯了地名,把迦太基軍帶到了一個叫卡西利努姆的地方。該地四周都是山地,又多沼澤,極容易被圍困。當漢尼拔進抵該地時,發現所有退路都已被費邊的軍隊堵住:前面是由4000名羅馬士兵把守的狹窄隘口,後面是費邊親自率領的羅馬軍主力。漢尼拔在這種困境之下想出一條妙計。他的軍中帶有許多牛隻,於是他下令將火把綁在牛角上。入夜之後,漢尼拔下令熄滅其它燈火,只點燃牛身上的火把,然後把牛從費邊軍與隘口之間的山坡上趕出去。兩邊的羅馬軍看見山腰上火光衝天,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把守隘口的軍隊以為漢尼拔要從山腰方向突圍,於是冒失地沖了出去,把隘口空了出來。漢尼拔抓住機會佔領隘口,然後全軍從隘口撤退。當時費邊在另一側也看見了火光,但他懷疑這可能是漢尼拔的詭計,於是按兵不動;這種選擇雖然謹慎,但卻使羅馬人在佔盡優勢的情況下被敵人安然逃走,喪失了一次可能的勝利。漢尼拔離開坎帕尼亞的消息傳到羅馬後,費邊的聲望嚴重受挫,他的政敵公開指責他懦弱無能。漢尼拔進一步打擊費邊的名譽,他派軍隊攻擊費邊的地產,燒光附近的農舍和田地,單單留下費邊的莊園,甚至還派士兵守衛它。這事被羅馬人得知后造成了很惡劣的影響。元老院終於決定剝奪費邊的軍權。祭司們用舉行宗教儀式的借口把他召回羅馬,軍隊則交給騎兵長官馬爾庫斯·米努基烏斯·魯弗斯指揮。米努基烏斯是費邊的政敵之一,他激烈反對拖延戰術。此時漢尼拔正屯兵普利亞地區的革羅尼烏姆。米努基烏斯趁敵軍出城搜集糧草時發動了一次成功的偷襲,在這次戰鬥中他避開了迦太基騎兵,結果給敵軍造成了巨大損失。消息傳回羅馬,米努基烏斯聲望大增,公民大會特別通過決議讓他與費邊共同指揮軍隊。當費邊返回軍中后,米努基烏斯建議由兩人輪流掌握軍隊的指揮權,但費邊拒絕了,代之以將軍隊一分為二,兩人各領其一。不久漢尼拔髮動反攻(革羅尼烏姆戰役),米努基烏斯所部遭到伏擊,傷亡慘重,幸虧費邊及時援救,才免於被迦太基軍殲滅。這一戰雙方最終打成平手。戰役結束后,米努基烏斯感於救命之恩,對費邊心悅誠服,稱呼他為“父親”。
革羅尼烏姆戰役之後費邊的獨裁官任期已滿,軍權被交還給當選的執政官盧基烏斯·埃米利烏斯·保盧斯與蓋烏斯·特雷恩蒂烏斯·瓦羅。此時漢尼拔在義大利境內作戰已久,各同盟城市和農民的忍耐已達極限。社會上的所有力量都主張儘快剷除漢尼拔,結束戰爭。在這種輿論支持下,保盧斯與瓦羅於前216年8月2日在坎尼附近與漢尼拔進行決戰。羅馬人最大程度地動員了軍隊(可能多達8~10萬人),企圖畢其功於一役;然而結果卻是羅馬軍在兵力優勢下被漢尼拔擊敗,而且大部分士兵被殺。坎尼戰役給羅馬帶來的打擊極為巨大,但漢尼拔在獲勝后仍然沒有冒險攻擊羅馬城,而是分兵南下,使義大利南部的城市紛紛投降,包括人口規模僅次於羅馬的卡普阿。在這種絕望的局勢中,羅馬人終於認識到與漢尼拔進行決戰是愚蠢的行為;他們再次想到了費邊,於前215年選舉他為執政官。費邊當選後繼續執行他的拖延戰術,主要進攻那些背叛羅馬的義大利城市,而避免與漢尼拔正面交鋒。從這時起,“拖延者”從諷刺語變成了一個榮譽稱號。前214年費邊連任了執政官。
前209年費邊再次當選為執政官(最後一任),進行了他一生中的最後一次重大戰役。漢尼拔在義大利南端的他林敦建立了一個堅固的根據地(前212年),費邊受命奪回這座城市。費邊採用佯攻策略,先派出一支他準備當成犧牲品的軍隊(多半由逃兵和違反軍紀者構成)進攻他林敦附近的另一座迦太基控制下的城鎮,然後趁漢尼拔前去援救時拿下了他林敦。城破后,居民遭受了可怕的洗劫和屠殺,多達3萬人被賣為奴隸。費邊在返回羅馬時又獲得了一次凱旋式。普盧塔克記載了一件趣事:有一個叫馬爾庫斯·李維烏斯的人在漢尼拔最初用計奪取他林敦時堅守陣地,並在其工事里一直堅持到費邊把城市奪回。此人認為自己沒有得到應有的獎賞,因而對費邊十分嫉妒,甚至對元老院宣稱攻克他林敦的功績不應歸於費邊而應歸於他。費邊得知后揶揄道:“你說的對,要不是你把城市丟了,我怎麼有機會去收復它呢?”
在前209年之後,費邊沒有擔任過公職。他在元老院里擁有巨大的勢力,是所謂保守派的代表。費邊開始反對新冒頭的少壯派,尤其是大西庇阿。這些年輕精英們認為反擊的時刻已經到了,而大西庇阿確實已在西班牙取得了巨大成功。費邊竭力壓制西庇阿的影響,一部分是出於他對漢尼拔(此時仍在義大利境內)的畏懼和天生的謹慎,但是更多的是對以西庇阿為代表的改革派的擔憂,最終這個派系讓希臘文化擊垮了羅馬的舊道德,讓羅馬漸漸颳起了靡靡之風。不過,他終於沒能阻止西庇阿進軍非洲。正是西庇阿最後於扎馬戰役中決定性地擊敗了漢尼拔。費邊沒有看到這次勝利,他大約在漢尼拔返回非洲的同時去世。
費邊在世時以其卓越的演說著稱,不過他的演講在普盧塔克的時代就已僅存一篇,即其子小費邊在執政官任上去世時他對公眾發表的一篇頌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