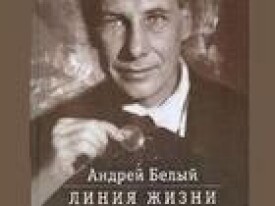別雷
別雷
安德列·別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1880——1934)是俄羅斯象徵主義文學中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在詩歌以及小說方面成就很大,代表作品有長詩《交響曲》等,長篇小說《銀鴿》、《彼得堡》、《莫斯科》以及《頭面像》等,此外還有詩集《灰燼》、《藍天澄金》等。他是20世紀俄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他的長篇小說《彼得堡》被著名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列為20世紀西方四大名著之一(另外三部是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卡夫卡的《變形記》)。

別雷
和當時的許多同時代人一樣,和其前後的許多俄國思想家一樣,別雷也對俄國究竟是東方還是西方,俄國究竟該往何方行,這一問題進行了嚴肅、獨特的思考,並試圖通過他的小說三部曲來表達他的思想。三部曲由《銀鴿》、《彼得堡》和《無形的城堡》構成,《銀鴿》和《彼得堡》相繼寫成並出版,而第三部卻未最終完成,《無形的城堡》 后更名為《我的一生》《我的一生》也未寫完,具有自傳意味的《科吉克·列達耶夫》等被視為《我的一生》的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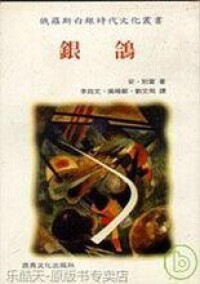
別雷
《銀鴿》仍舊帶有十九世紀俄羅斯小說的特點,濃厚的思想性、沉鬱的語調和對終極問題的思考。不過,小說的體格卻並不笨重。篇幅只有28萬字。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俄羅斯知識分子,他不斷地對自我的命運、實際上也就是俄羅斯的現代命運進行著探尋。這個知識分子叫達雅爾斯基。他受到了當時俄羅斯一些知識分子發起的“到民間去”運動的影響,準備深入生活。到社會底層去,體驗和發現俄羅斯的社會本質,去體察俄羅斯人民的真實生活。但是,當他真正進入到底層的生活中的時候,橫亘在他面前的,是俄羅斯城市和鄉村的分裂、宗教和科學知識的斷裂、貴族階層和窮人之間的分裂,同時,帶有鄉野氣息的農婦對他的誘惑,貴族女人對他的吸引,這些都使達雅爾斯基感到了難以抉擇。

別雷
二十世紀的俄語文學,如果以現實主義為基本的參照,那麼也還存在著一條非現實主義的流脈。這條非現實主義流脈有待人們作系統的研究。它的起點,無疑是那活躍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國文壇上的象徵主義文學。
俄國象徵派文學在藝術上的建樹,不僅局限於詩的藝術。俄國象徵派詩人所建立的小說詩學、戲劇詩學、理論詩學與其詩歌藝術共同構成了俄國象徵主義文學的藝術個性,使俄國象徵主義文學與其他民族的象徵主義文學區別開來。

大詩人勃洛克
在典型的俄國象徵派小說作品中,作家的審美對象,已經不是被折射於心靈中的世界,而直接是涵納著世界投影的心靈;作家的審美取向,已經不再局限於橫向地觀照人生即人在社會關係網路中的政治的、社會的、倫理的、心理的,意識形態的層面,而更多的是透視人生即考察人的“類本質”,心理與生理機制,意識系統(顯意識與潛意識諸層)在特殊情境中的狀態,情感世界的非正常或“超常”狀態,理智世界中的形而上的層面;作家的敘述不再是或不僅僅是以社會現實生活風云為主要客體,甚至也不再以對人物內心的心理生活的詳盡描繪為首要任務。這樣,生活與生存,塵世與彼岸,外在世界的萬千氣象,內心生活的風雨波濤,都融匯於“半明半暗”的象徵形象的迷離夢幻之中,在象徵派的小說世界中構成一種令人神往與回味的特別景觀。作家有意識地裸露自己編織情節描寫場景顯現情境的獨特匠心,不時地向讀者提醒藝術世界的虛構性,讓讀者感覺到是在接受文學作品,讓讀者體味出對存在的審美觀照本身的愉快與娛樂。作家在敘述方式上不再以塑造典型環境與典型性格為目標,而是以有意識地“打碎情節”,“弱化性格”來呈現某種“超常情境”,渲染某種特別的“情緒氛圍”。文學創作中最根本的“寫什麼”與“怎麼寫”的問題,在俄國象徵派小說藝術探索中得到了一次自覺自為的革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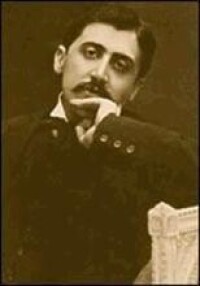
普魯斯特
別雷在西方被看成是二十世紀俄羅斯小說家中最傑出的天才。一些國外文藝學家把別雷的小說視為“劃時代”的現象。一九六五年,捷克學者雅·尚達就在標題為《安德列·別雷——具有世界意義的小說家》的文章中,把別雷與普魯斯特、喬伊斯、卡夫卡相提並論,認為他們四位是實驗家型的作家,是現代小說的改革者。一九六七年,匈牙利女學者列娜·西拉爾德在《論別雷的第二交響曲》一文中指出,別雷的早期作品開闢了二十世紀長篇實驗小說的時代。她把別雷的交響曲看成是蘊含著巨大創作能量的嶄新的小說作品形式,它的生成,立足於別雷對詩、音樂甚至當時剛剛問世的電影手段的借鑒。七十年代中期以來,西方對別雷小說的研究興趣方興未艾。到了八十年代,一個席捲全球的“別雷創作研究熱點”已然形成,以歐洲——日本——美國為據點的“國際別雷學”也已構成。如今,“別雷學”的發祥地從義大利、西德、匈牙利、波蘭等國擴展到法國、西班牙、斯堪的那維亞半島諸國。這種“第二次發現”,正是“文學萬有引力”的作用,在幾十年的沉默、失落與遺忘之後,在“第一次發現的匆忙”之後,西方學者對別雷創作的興趣再次勃興。

喬伊斯
別雷在《交響曲》(1901-1906)、《銀鴿》(1909)、《彼得堡》(1913)、《柯吉克·列達耶夫》(1922)、《頭面像》(1932)和《莫斯科》(1926-1932)這樣一些最典型的象徵主義小說作品中,有意識地嘗試交響樂作曲中一些結構原則移植入文學創作之中,把情節打碎成鏈節,再把那些鏈節通過“深層的、內在的”“主導主題”聯繫起來,使小說文本“節奏化”,使那些隱在於文本之中的層面被“語義化”,進而實現“詞形——詞音——詞義”全面“象徵化”,即使節奏作為一種潛在的聲音積極地工作起來,使詞語本身由“形象”轉化成“音象”,進而實現那種於敘述之中聽見節奏,於節奏之中悟出意義的目標,以新的方式,使小說的文本密度大大增加,創造出帶有意義的節奏。在詩學理論上,則是使形式賦有意義,成為“有意味的形式”或“內容性的形式”之有趣的試驗。
別雷把小說文本結構作為一種自足自立的現實結構裸露出來。實現這種結構裸露的主要手段是詩學意義上的“戲耍把玩”,即使戴上不同面具的各種敘述者彼此發生衝突,對各種不同的文體風格作諷擬性的展示。別雷作為小說作者好像是在千方百計把讀者的注意力,由“小說在敘述什麼”這種習慣定向,轉移到“小說怎樣在敘述”,並且暗示讀者:“怎樣在敘述”這一形式本身又正傳達著“敘述著什麼”這個內容。
別雷十分傾心於“意識的屏幕”。在致力於觀照“意識的生命”時,別雷不僅廣泛運用內心獨白、夢境、幻覺這些假定性手法,而且還在小說詩學實驗中來了個“質的飛躍”:別雷在其小說創作中實際上是把整個客觀世界僅僅當作人物意識的“室內裝飾”——意識世界的內景畫,而人物的意識生命活動,則成了統攝一切的審美對象。他的那些主人公或那些戴上各種面具的敘述者的意識流變,成了他小說藝術世界的主體。也就是說,“意識生命”的呈現取代了客觀世界原來在傳統小說中的地位。

卡夫卡
別雷根據“神智學”學說向人們顯示:人存在十多重世界的交合點上,存在狀態的多重層面在人身上同時得到反映:生理層面,心理層面,精神層面,性靈層面,星相層面(“人正是通過星辰實現於‘宇宙空間’的聯繫”)等等。別雷的這種觀念,自然在小說的形象體系的構成中有所顯現。《彼得堡》的象徵世界,在結構上類似於某種晶體。例如,小說事件發生的時間是一九○五年十月九日和十日這兩天,可是在這個時間段里的敘述卻投射著整個世界歷史的過去與未來。小說的“外在的情節”是由三個主要人物所分別代表著的三種力量的衝突而構成,它們都追逐主宰俄羅斯命運的權力。其一是沙皇政府的參議官阿波羅·阿波羅諾維奇·阿勃列烏霍夫為代表的沙皇官僚力量,其二是由杜德金為首的恐怖主義分子所組成的反對派黨徒,第三種力量是以大學生尼古拉·阿勃列烏霍夫這個智力型知識分子為化身,這種力量在兩種極權主義暴力的夾縫中生存,實際上成了沙皇國家政權與恐怖主義黨徒之間鬥爭的工具。推動整部小說的情節運行,使各種力量發生衝突,人物之間發生傾軋的最初動因,是尼古拉不經意地說出來的“要殺死父親”這一允諾。整個情節的波折環繞著尼古拉如何實現這一允諾而展開。初看上去,這似乎是一部偵探小說。但這僅僅是作品象徵世界的最表層。並且,這個偵探故事的情節在小說中被別雷打成了碎片。小說的中心事件“爆炸”,在外在情節上是一個鬧劇。那個自製的炸彈是一怪誕形象的具象化。外在情節上的“爆炸”,十分可笑。但是,尼古拉心靈中的爆炸後果卻是嚴重的,尼古拉把自己等同於一枚炸彈——相應於酒神狄奧尼斯的受難,相應於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尼古拉來到了他這個人註定要走的那條十字路口。正是尼古拉的“天路歷程”,這個人物心靈上的爆炸,構成了小說的內在情節。別雷在建構這一內在情節時,把偵探小說的諷擬筆法與鬧劇中的滑稽噱頭糅合於一體,在亦諧亦庄的氛圍中讓主人公在小說結尾走出“魔圈”。
而主人公尼古拉心靈中的爆炸,又與一系列的象徵意蘊相疊印。例如這個人物在兩種不同形式的極權主義暴力的夾縫中生存,與俄羅斯文化在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兩大板塊的撞擊中生存,就構成一種象徵,這個人物的“潛在的弒父情結”,與家庭衝突、歷史衝突、文化衝突等各個層面的象徵意蘊,又是層層相印,其意義可以在“滾雪球”似的聯想中向無限延伸。這種形象系統中的疊印,正是“大千世界物物相印”,“普遍參與”、“普遍映照”這一象徵主義世界觀,在象徵主義者別雷的敘事詩學上的顯現。正是這種物物相印,作為一種內在邏輯力量,把聯想之鏈上的所有環節連接起來,把敘述文本中各種主題的跳躍組織起來,把文本世界的各種成分聯接起來。如同外在的經驗世界一樣,別雷小說的藝術世界由“物物相印、相互體現”的內在邏輯,構成一個自足自立的實體。
別雷象徵主義小說藝術的詩學個性,不僅僅體現在《彼得堡》這一部作品中。在後來的長篇小說《柯吉克·列達耶夫》(1922)中,別雷試圖把人的孩提時代的意識,甚至嬰兒期的思維情態與宇宙本體的存在狀態“同晶”地顯示出來,十分有趣。在別雷的小說中,世界以一種被打成碎片然而卻是深切完整的系統呈現在讀者面前。這是一種看上去雜亂無章然而卻是內在地物物相印的系統。這種系統,已不是可見的、栩栩如生的、可從各個角度去審視去欣賞的油畫,而是形體性極弱節律性極強的無形之象——一種獨特的視象,一種與宇宙同構與萬象同晶,處於永不間歇的變奏與轉化的運動狀態的象徵世界。敘事藝術在“能指簡化、所指擴大”的航道上逼近音樂藝術,小說的結構為音樂性所貫穿,閱讀這種小說的速度必須加快,以跟上小說文本的節律,也就是說,這種小說的閱讀本身接近於對音樂作品的欣賞,譬如說,聽交響樂。它可以使讀者進入一種“大象無形”、“大音希聲”的境界。只要讀進去,便可品味,可感悟,可體驗其中的無窮意趣。這是俄國象徵派小說中一個獨特的類型。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別雷
希望者 清淚處處顫動 鮮明。清淚打濕玫瑰 鮮紅。粉紅的玫瑰變成 大紅。閃電照亮玫瑰 火紅。玫瑰歡快地吟起 讚美歌。它們的詩琴發出 頌歌。它們的長裾五光十色 蔌蔌作響。它們的桂冠金碧輝煌 十分明亮。朝霞顫動著火焰 蔌蔌…… 朝霞舞動著紅旗 嘩嘩。 1901年 張冰 譯
太陽 答《我們將像太陽》的作者 太陽溫暖人心。太陽企求永恆的運動。太陽是永恆的窗口 通向金色的無窮。玫瑰頂著金色的發叢。玫瑰在溫柔地顫動。一道金色的光線刺進花心 紅色的暖流溢滿全身。貧乏的心中只會惡念叢生 一切都被燒光砸扁、一個不剩。我們的心靈是一面鏡 它只反映赤色的黃金。 1903年 張冰 譯
窗下
目光伸向春天的遠方:那裡是蔚藍色的穹蒼…… 而攤開在我眼前的是《批判》 它們有皮製的封面……· 遠方是另一種生存 星星的眼睛是那麼明凈…… 於是,我乍然一驚,心念一閃 原來空間是那般虛幻。 1908年莫斯科 張冰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