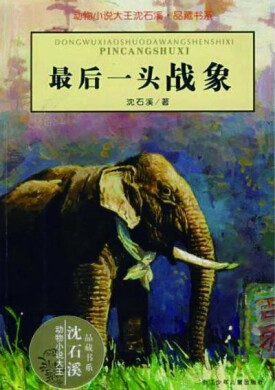共找到3條詞條名為最後一頭戰象的結果 展開
- 沈石溪所著小說
- 2014年杜子名主演的電影
- 人偶舞台劇
最後一頭戰象
沈石溪所著小說
《最後一頭戰象》是一部由作家沈石溪在2008年創作的圖書,作品介紹了動物小說之所以比其他類型的小說更有吸引力,是因為這個題材最容易破人類文化的外殼和文明社會種種虛偽的表象,可以毫無遮掩地直接表現醜陋與美麗融於一體的原生態的生命。
西雙版納曾經有過威風凜(lǐn)凜的象兵。所謂象兵,就是騎著大象作戰的士兵。士兵騎象殺敵,戰象用長鼻劈敵,用象蹄踩敵,一大群戰象,排山倒海般地撲向敵人,勢不可當。
1943年,象兵在西雙版納打洛江畔和日寇打了一仗。戰鬥結束后,鬼子扔下了七十多具屍體,我方八十多頭戰象全部中彈倒地。人們在打洛江邊挖了一個巨坑,隆重埋葬陣亡的戰象。
在搬運戰象的屍體時,人們發現一頭渾身是血的公象還在喘息,就把它運回寨子,治好傷養了起來。村民們從不叫它搬運東西,它整天優哉(zāi)游哉地在寨子里閑逛,到東家要串香蕉,到西家喝筒泉水。
它叫嘎(gǎ)羧(suō),負責飼養它的是波農丁。
二十多年過去,嘎羧五十多歲了。它顯得很衰老,整天卧在樹陰下打瞌(kē)睡。有一天,嘎羧躺在地上拒絕進食,要揪住它的鼻子搖晃好一陣,它才會艱難地睜開眼睛,朝你看一眼。波農丁對我說:“太陽要落山了,火塘要熄滅了,嘎羧要走黃泉路啦。”
第二天早晨,嘎羧突然十分亢(kàng)奮,兩隻眼睛燒得通紅,見到波農丁,嘔(ōu)嘔地輕吼著,象蹄急促地踏著地面,鼻尖指向堆放雜物的閣樓,像是想得到閣樓上的什麼東西。
閣樓上有半籮谷種和兩串玉米。我以為它精神好轉想吃東西了,就把兩串玉米扔下去。嘎羧用鼻尖鉤住,像丟垃(lā)圾(jī)似的甩出象房,繼續焦躁不安的仰頭吼叫。破篾(miè)席裡面有一件類似馬鞍的東西,我漫不經心地一腳把它踢下樓去。沒想到,嘎羧見了,一下子安靜下來,用鼻子呼呼吹去上面的灰塵,鼻尖久久地在上面摩挲(suō)著,眼睛里淚光閃閃,像是見到久別重逢的老朋友。
“哦,原來它是要自己的象鞍啊。”波農丁恍然大悟,“這就是它當年披掛的鞍子,給它治傷時,我把象鞍從它身上解下來扔到小閣樓上了。唉,整整二十六年了,它還記得那麼牢。”
象鞍上留著彈洞,似乎還有斑斑血跡,混合著一股皮革、硝煙、戰塵和血液的奇特氣味;象鞍的中央有一個蓮花狀的座墊,四周鑲著一圈銀鈴,還綴著杏黃色的流蘇。二十六個春秋過去,象鞍已經破舊了,仍顯出凝重華貴;嘎羧披掛上象鞍,平添了一股英武豪邁的氣概。
波農丁皺著眉頭,傷感地說:“它要離開我們去象冢(zhǒng)了。”
大象是一種很有靈性的動物,每群象都有一個象冢,除了橫遭不幸暴斃(bì)荒野的,它們都能準確地預感到自己的死期,在死神降臨前的半個月左右,會獨自走到遙遠而又神秘的象冢里去。
嘎羧要走的消息長了翅膀似的傳遍全寨,男女老少都來為嘎羧送行。許多人泣不成聲。村長在嘎羧脖子上系了一條潔白的紗巾,四條象腿上綁了四塊黑布。老人和孩子捧著香蕉、甘蔗(zhè)和糯(nuò)米粑(bā)粑,送到嘎羧嘴邊,它什麼也沒吃,只喝了一點水,繞著寨子走了三圈。
日落西山,天色蒼茫,在一片唏(xī)噓(xū)聲中,嘎羧開始上路。
我和波農丁悄悄地跟在嘎羧後面,想看個究竟。嘎羧走了整整一夜,天亮時,來到打洛江畔。它站在江灘的卵石上,久久凝望著清波蕩漾的江面。然後,它踩著嘩嘩流淌的江水,走到一塊龜形礁(jiāo)石上親了又親,許久,又昂起頭來,向著天邊那輪火紅的朝陽,歐──歐──發出震耳欲聾的吼叫。這時,它身體膨(péng)脹起來,四條腿皮膚緊繃繃地發亮,一雙眼睛炯(jǒng)炯有神,吼聲激越悲壯,驚得江里的魚兒撲喇喇跳出水面。
“我想起來了,二十六年前,我們就是在這裡把嘎羧抬上岸的。”波農丁說。
原來嘎羧是要回到當年曾經浴血搏殺的戰場!
太陽升到了檳(bīng)榔(láng)樹梢,嘎羧離開了打洛江,鑽進一條草木茂盛的箐(qìng)溝。在一塊平緩的向陽的小山坡上,它突然停了下來。
“哦,這裡就是埋葬八十多頭戰象的地方,我記得很清楚,喏(nuò),那兒還有一塊碑。”波農丁悄悄地說。
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荒草叢中,果然豎著一塊石碑,鐫刻著三個金箔(bó)剝落、字跡有點模糊的大字:百象冢。
嘎羧來到石碑前,選了一塊平坦的草地,一對象牙就像兩支鐵鎬(gǎo),在地上挖掘起來。它已經好幾天沒吃東西了,又經過長途跋涉,體力不濟,挖一陣就喘息一陣。嘎羧從早晨一直挖到下午,終於挖出了一個橢(tuǒ)圓形的淺坑。它滑下坑去,在坑裡繼續挖,用鼻子卷著土塊拋出坑;我們躲在遠處,看著它的身體一寸一寸地往下沉。
太陽落山了,月亮升起來了,它仍在埋頭挖著。半夜,嘎羧的脊背從坑沿沉下去不見了,象牙掘土的冬冬聲越來越稀,走到坑邊查看。土坑約有三米深,嘎羧卧在坑底,側著臉,鼻子盤在腿彎,一隻眼睛睜得老大,凝望著天空。
它死了。它沒有到祖宗留下的象冢。它和曾經並肩戰鬥的同伴們躺在了一起。
威風凜凜:形容聲勢或氣派使人敬畏、恐懼。
勢不可當:來勢迅猛,不可抵擋。
優哉游哉:形容從容不迫、悠閑自得的樣子。
亢奮:極度興奮。
焦躁不安:著急、煩躁、坐立不安的樣子。
漫不經心:隨隨便便,不放在心上。
摩挲:撫摩;撫弄、摸索,用手輕輕按著並一下一下地移動。
泣不成聲:哭得噎住了,連聲音也發不出來,形容極度悲傷。
唏噓:哭泣后不由自主地急促呼吸。
震耳欲聾:聲音很大,耳朵快被震聾了。指聲音特別大,特別吵。
炯炯有神:炯炯:明亮的樣子。形容人或動物或其他事物的眼睛明亮,很有精神。
長途跋涉:長途:形容詞,路途遠的;遠距離。跋:翻越。跋涉:翻山越嶺、趟水過河。指遠距離的翻山渡水。形容路途遙遠,行路辛苦。
排山倒海:推開高山,翻倒大海。形容力量強盛、聲勢浩大。
鐫刻:即雕刻之意;把銘文刻或畫在某種堅硬物質上或石頭上。
浴血搏殺:形容戰鬥或鬥爭的激烈、殘酷。
![最後一頭戰象[沈石溪所著小說]](https://i1.twwiki.net/cover/w200/m4/8/m4862623a3dcf3719b62499c591e5ca6c.jpg)
最後一頭戰象[沈石溪所著小說]
久別重逢:分別很久后再次見面。
英武:英俊勇武。
暴斃:突然死亡。
箐溝:山間大竹林的溝。竹木叢生的山谷上的溝。
①沒想到,嘎羧見了,一下子安靜下來,用鼻子呼呼吹去上面的灰塵,鼻尖久久地在上面摩挲著,眼睛里淚光閃閃,像是見到久別重逢的老朋友。
真的是沒有想到,一件象鞍竟然使急躁的嘎羧頓時安靜下來!作者對嘎羧動作、神情的描寫,細膩生動,寥寥幾筆卻清晰地表達出一頭英勇的戰象積澱在心中的深沉的感情:“呼呼吹去”“久久地”“摩挲”“淚光閃閃”,使讀者深刻地感受到嘎羧見到象鞍時內心涌動的對輝煌過去的深深留戀與回味!
②二十六個春秋過去,象鞍已經破舊了,仍顯出凝重華貴;嘎羧披掛上象鞍,平添了一股英武豪邁的氣概。
象鞍破舊,卻仍然凝重華貴;嘎羧年邁,卻仍然英武豪邁!二十六個春秋,彈指一瞬間。而今,戰火不再,血腥不再,但積滿灰塵的象鞍上記載著凝重的歷史,記載著嘎羧的英勇;紛亂不再,年輕不再,但垂暮的英雄,博大的胸懷仍在,勃勃的雄心仍在!對稱的並列句式增強了語勢,此句通過對象鞍和嘎羧的簡練描繪,深情地讚頌了嘎羧的英雄形象與氣概。
③它站在江灘的卵石上,久久凝望著清波蕩漾的江面。然後,它踩著嘩嘩流淌的江水,走到一塊龜形礁石上親了又親,許久,又昂起頭來,向著天邊那輪火紅的朝陽,────發出震耳欲聾的吼叫。
“親了又親”的礁石,也許是嘎羧曾經奮力殺敵的一處戰場,也許是曾灑滿戰友鮮血的一處傷心之地;“震耳欲聾的吼叫”,也許是嘎羧在深情呼喚戰友們的靈魂,也許在訴說它對戰友的深深懷念,也許在告訴戰友,它也將來陪伴它們……這樣的悲壯,這樣的深情,這僅僅是一頭戰象嗎?這是一位讓人滿懷敬仰的英雄,這是一位讓人飲淚歌頌的英雄!
④土坑約有三米深,嘎羧卧在坑底,側著臉,鼻子盤在腿彎,一隻眼睛睜得老大,凝望著天空。
有誰能如此坦然地面對死亡?有誰能如此完善地走完一生?嘎羧靜靜地為自己挖掘了墓地,靜靜地躺在那裡,那“睜得老大”“凝望著天空”的眼睛,讓人揣想:它在告訴我們歷史不能忘懷嗎?它在期盼和平嗎?……
⑤它死了。它沒有到祖宗留下的象冢。它和曾經並肩戰鬥的同伴們躺在了一起。

最後一頭戰象
![最後一頭戰象[沈石溪所著小說]](https://i1.twwiki.net/cover/w200/m0/f/m0fd283820efe8e4a28e48b9d8d0d3f41.jpg)
最後一頭戰象[沈石溪所著小說]
在抗日戰爭中倖存下來的最後一頭戰象嘎羧,自知生命大限已至,便再次披上象鞍,來到打洛江畔緬懷往事,憑弔戰場,最後在埋葬著戰友們的"百象冢"旁刨開一個坑,莊嚴的把自己掩埋了的故事。
沈石溪(1952年10月-),自稱沈一鳴,生於上海,祖籍浙江慈溪市。現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職稱文學創作2級,任中國兒童文學委員會委員、雲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專業作家。
1969年初中畢業赴西雙版納插隊,插隊期間學會捉魚、蓋房、犁田、栽秧,積累了豐富的野外生活經驗。他作過水電站民工、山村男教師,在雲南邊疆生活了18年。1975年應徵入伍,擔任過宣傳股長。1984年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92年調任成都軍區創作室。80年代開始從事文學創作,他的第一篇動物小說是《象群出沒的山谷》,發表於1980年的《兒童文學》雜誌。他已經出版500多萬字的作品。1997年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與沈石溪簽約,以6位數的價碼買斷沈石溪未來十年動物小說的出版權,並出版了囊括沈石溪前期所有動物小說的《中國動物小說大王沈石溪文集》十卷本。

沈石溪
給大象拔刺
最後一頭戰象

最後一頭戰象
憤怒的象群
象警
死亡遊戲
動物檔案——象
野豬跳板
野豬囚犯
野豬王
動物檔案——豬
與狗熊比舉重
智取雙熊
棕熊的故事
動物檔案——熊
闖入動物世界
獲獎記錄
珍藏相冊
一頭即將步入墳墓的戰象,奮力披掛上當年的象鞍,跋山涉水趕往百象冢,要與曾和自己浴血奮戰的夥伴們葬在一起。精明的獵手覬覦百象冢里幾百根價值連城的象牙,一路悄悄尾隨在老戰象身後。蒼茫暮色中,老戰象用盡生命中最後的力量,與同伴們會合,與這片曾經灑滿熱血的土地會合……
西雙版納曾經擁有一隊威風凜凜的象兵。所謂象兵,就是騎著大象作戰的軍隊。象兵比起騎兵來,不僅同樣可以起到機動快速的作用,戰象還可用長鼻劈敵,用象蹄踩敵,直接參與戰鬥;一大群象,排山倒海般地撲向敵人,戰塵滾滾,吼聲震天,勢不可當。
1943年,日寇侵佔緬甸,鐵蹄跨進了和緬甸一江之隔的西雙版納邊陲重鎮打洛。象兵在打洛江畔和日寇打了一仗。戰鬥異常激烈,槍炮聲、廝殺聲和象吼聲驚天動地;鬼子在打洛江里扔下了七十多具屍體,我方八十多頭戰象全部中彈倒地,血把江水都染紅了。戰鬥結束后,召片領在打洛江邊挖了一個長寬各二十多米的大坑,把陣亡的戰象隆重埋葬了,還在坑上立了一塊碑:百象冢。曼廣弄寨的民工在搬運戰象的屍體時,意外地發現有一頭公象還在喘息,它的脖頸被刀砍傷,一顆機槍子彈從前腿穿過去,渾身上下都是血,但它還活著。他們用八匹馬拉的大車,把它運回寨子。這是倖存的戰象,名叫嘎羧。好心腸的村民們治好了它的傷,把它養了起來。
我1969年3月到曼廣弄寨插隊落戶時,嘎羧還健在。它已經50多歲了,脖子歪得厲害,嘴永遠閉不攏,整天滴滴嗒嗒地淌著唾液;一條前腿也沒能完全治好,短了一截,走起路來躓躓顛顛;本來就很稀疏的象毛幾乎都掉光了,皮膚皺得就像脫水的絲瓜;歲月風塵,兩根象牙積了厚厚一層難看的黃漬。它是戰象,它是功臣。村民們對它十分尊敬和照顧,從不叫它搬運東西。它整天優哉游哉地在寨子里閑逛,到東家要串香蕉,到西家喝筒泉水。
我和負責飼養嘎羧的老頭波農丁混得很熟,因此和嘎羧也成了朋友。我插隊的第3年,嘎羧愈發衰老了,食量越來越小,整天卧在樹蔭下打瞌睡,皮膚鬆弛,身體萎縮,就像一隻脫水檸檬。
波農丁年輕時給土司當了多年象奴,對象的生活習性摸得很透,他對我說:“太陽要落山了,火塘要熄滅了,嗄羧要走黃泉路啦。”幾天後,嘎羧拒絕進食,躺在地上,要揪住它的鼻子搖晃好一陣,它才會艱難地睜開眼睛,朝你看一眼。我覺得它差不多已處在半昏迷的狀態中了。
可一天早晨,我路過打穀場旁的象房,驚訝地發現,嘎羧的神志突然間清醒過來,雖然身體仍然衰弱不堪,但精神卻處在亢奮狀態中,兩隻眼睛燒得通紅,見到波農丁,歐歐歐短促地輕吼著,鼻子一弓一弓,鼻尖指向象房堆放雜物的小閣樓,象蹄急促地踢踏著地面,好像是迫不及待想得到小閣樓上的什麼東西。開始波農丁不想理它,它發起脾氣來,鼻子抽打房柱,還用龐大的身體去撞木板牆。
象房被折騰得搖搖欲墜。波農丁拗不過它,只好讓我幫忙,爬上小閣樓,往下傳雜物,看它到底要什麼。小閣樓上有半籮谷種、兩串老玉米和幾條破麻袋,其它好像沒什麼東西了。我以為它精神好轉起來想吃東西了,就把兩串老玉米扔下去,它用鼻尖勾住,像丟垃圾似地丟出象房去;我又將半籮稻穀傳給波農丁,他還沒接穩呢,就被嘎羧一鼻子打翻在地,還賭氣地用象蹄踩踏;我又把破麻袋扔下去,它用象牙把麻袋挑得稀巴爛。
小閣樓角落裡除了一床破篾席,已找不到可扔的東西了。嘎羧仍焦躁不安地仰頭朝我吼叫。“再找找,看看還有啥東西?”波農丁在下面催促道。
我掀開破篾席,裡面有一具類似馬鞍的東西,很大很沉,看質地像是用野牛皮做的,上面蒙著厚厚一層灰塵。除此之外,小閣樓里真的一樣東西也沒有了。我一腳把那破玩意兒踢下樓去。奇怪的事發生了:嘎羧見到那破玩意兒,一下安靜下來,用鼻子呼呼吹去蒙在上面的灰塵,鼻尖久久地在破玩意兒上摩挲著,眼裡淚光閃閃,像是見到了久別重逢的老朋友。
“哦,鬧了半天,它是要它的象鞍啊。”波農丁恍然大悟地說,“這就是它當戰象時披掛在背上打仗用的鞍子,我們當年把它從戰場上運回寨子,它還佩戴著象鞍。在給它治傷時,是我把象鞍從它身上解下來扔到小閣樓上的。唉,整整26年了,我早把這事忘得一乾二淨,沒想到,它還記得那麼牢。”嘎羧用鼻子挑起那副象鞍,甩到自己背上,示意我們幫它捆紮。我和波農丁費了好大勁,才將象鞍置上象背。
象鞍上留著彈洞,似乎還有斑斑血跡,混合著一股皮革、硝煙、戰塵和鮮血的奇特的氣味;象鞍的中央有一個蓮花狀的座墊,四周鑲著一圈銀鈴,還綴著杏黃色的流蘇,26個春夏秋冬風霜雨雪,雖然已經有點破舊了,卻仍顯得沉凝而又華貴。嘎羧披掛著象鞍,平添了一股英武豪邁的氣概。
“它要披掛象鞍幹什麼?”我迷惑不解地問道。“恐怕不是什麼好兆頭。”波農丁皺著眉頭傷感地說,“我想,它也許要離開我們去象冢了。”
我聽說過關於象冢的傳說。大象是一種很有靈性的動物,除了橫遭不幸暴斃荒野的,都能準確地預感到自己的死期。在死神降臨前的半個月左右,大象便離開象群,告別同伴,獨自走到遙遠而神秘的象冢里去。每群象都有一個象冢,或是一條深深的雨裂溝,或是一個巨大的溶洞,或是地震留下的一塊凹坑。凡這個種群里所有的象,不管生前浪跡天涯海角漂泊到何方,最後的歸宿必定在同一個象冢;讓人驚奇的是,小象從出生到臨終,即使從未到過也未見過象冢,卻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憑著一種神秘力量的指引,也能準確無誤地尋找到屬於自己種群的象冢。
果然被波農丁說中了。嘎羧準備告別曼廣弄寨,找它最後的歸宿了。它繞著寨子走了三圈,對救活它、收留它並養活它26年的寨子表達一種戀戀不捨的心情。
嘎羧要走的消息長了翅膀似地傳遍全寨,男女老少都涌到打穀場來為嘎羧送行。大家心裡都清楚,與其說是送行,還不如說是送葬,為一頭還活著的老戰象出殯。許多人都泣不成聲。村長帕琺在象脖子上系了一條潔白的紗巾,四條象腿上綁了四塊黑布。老人和孩子捧著香蕉、甘蔗和糯米粑粑,送到嘎羧嘴邊。它什麼也沒吃,只喝了一點涼水。日落西山,天色蒼茫,在一片唏噓聲中,嘎羧上了路。送行的人群散了,波農丁還站在打穀場上痴痴地望。我以為他在為嘎羧的出走而傷心呢,就過去勸慰道:“生老病死,聚散離合,本是常情,你也不要太難過了。”不料他卻壓低聲音說:“小夥子,你有膽量跟我去發一筆財嗎?”見我一副茫然無知的神態,他又接著說:“我們悄悄跟在嘎羧後面,找到那象冢……”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是要我跟他合夥去撿象牙。在熱帶雨林里,大象的軀體的骨頭會腐爛,象牙卻永遠閃耀著迷人的光澤;象冢由於世世代代埋葬老象,每一個象冢里都有幾十根甚至上百根象牙,毫不誇張地說,找到一個象冢就等於找到一個聚寶盆;聰明的大象好像知道人類覬覦它們發達的門牙,生怕遭到貪婪的人類的洗劫,通常都把象冢選擇在路途艱險人跡罕至的密林深處,再有經驗的獵人也休想找得到;但如果採取卑鄙的跟蹤手段,悄悄尾隨在死期將臨的老象後面,就有可能找到那遙遠而又神秘的象冢。我猶豫著,沉默著,沒敢輕易答應。波農丁顯然看穿了我的心思,說:“我們只撿象冢里其它象的象牙,嘎羧的象牙我們不要,也算對得起它了嘛。”這主意不錯,既照顧了情感,又可圓發財夢,何樂而不為?我倆拔腿就追,很快就在通往崇山峻岭的小路上追上了踽踽獨行的嘎羧。
天黑下來了,它脖頸上那塊標誌著出殯用的白紗巾成了我們摸黑追蹤的路標。它雖然跛了一條腿走不快,卻一刻也沒停頓,走了整整一夜,天亮時,來到打洛江畔。“我想起來了,這兒是水晶渡的上游,26年前,我們就是在這裡把嘎羧給抬上岸的。”波農丁指著江灣一塊龜形的礁石說,“幸虧有這塊礁石擋住了它,不然的話,它早被激流衝到下游淹死了。”
這麼說來,這兒就是26年前抗日健兒和日寇浴血搏殺的戰場。這時,嘎羧踩著嘩嘩流淌的江水,走到那塊龜形礁石旁,鼻子在被太陽晒成鐵鏽色的粗糙的礁石上親了又親;許久,才昂起頭來,向著天邊那輪火紅的朝陽,歐--歐--發出震耳欲聾的吼叫。它突然間像變了一頭象,身體像吹了氣似地膨脹起來,四條腿的皮膚緊繃繃地發亮,一雙象眼炯炯有神,吼聲激越悲壯,驚得江里的魚兒 撲喇喇跳出水面。我想,此時此刻,它一定又看到了26年前驚天地泣鬼神的一幕:威武雄壯的戰象們馱著抗日健兒,冒著槍林彈雨,排山倒海般地沖向侵略者;日寇鬼哭狼嚎,丟盔棄甲;英勇的戰象和抗日將士也紛紛中彈跌倒在江里。
我對嘎羧肅然起敬,它雖然只是一頭象,被人類稱之為獸類,卻具有很多稱之為人的人所沒有的高尚情懷;在它行將辭世的時候,它忘不了這片它曾經灑過熱血的土地,特意跑到這兒來緬懷往事,憑弔戰場!
我們跟在它後面,又走了約一個多小時,在一塊平緩向陽的小山坡上,它突然又停了下來。“哦,這裡就是埋葬八十多頭戰象的地方,我參加過挖坑和掩埋,我記得很清楚。喏,那兒還有一塊碑。”波農丁悄悄說道。
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荒草叢中,果然豎著一塊石碑,鐫刻著三個金箔剝落、字跡有點模糊的大字:百象冢。莫非嘎羧它……我不敢往下想,斜眼朝波農丁望去,他也困惑地緊皺著眉頭。
嘎羧來到石碑前,選了一塊平坦的草地,一對象牙就像兩支鐵鎬,在地上挖掘起來。它已經好幾天沒吃東西了,又經過長途跋涉,體力不濟,挖一陣就站在邊上喘息一陣,但它堅持不懈地挖著,從早晨一直挖到下午,終於挖出了一個橢圓形的淺坑來;它滑下坑去,在坑裡繼續深挖,用鼻子卷著土塊拋出坑來。我們在遠處觀看,只見它的身體一寸一寸地往下沉。太陽落山了,月亮升起來了,它仍在埋頭挖著。半夜,嘎羧的脊背從坑沿沉下去不見了,象牙掘土的咚咚聲越來越稀,長鼻拋土的節奏也越來越慢。雞叫頭遍時,終於,一切都平靜下來,什麼聲音也沒有了。
我和波農丁耐心地等到東方吐白,這才壯著膽子,走到坑邊去看。土坑約有3米深,嘎羧卧在坑底,側著臉,鼻子盤在腿彎,一隻眼睛睜得老大,凝望著天空。
它死了。它沒有到遙遠的神秘的祖宗留下的象冢去,它在百象冢邊挖了個坑,和曾經並肩戰鬥過的同伴們葬在了一起。
作為一頭老戰象,它找到了最好的歸宿。土坑裡彌散著一股腐爛的氣息,看得見26年前埋進去的戰象的殘骸,紅土裡,好像還露出了白的象牙。嗄羧那對象牙,因挖掘土坑而被沙土磨得鋥,在晨光中閃爍著華貴的光澤。波農丁牙疼似地咧著嘴苦著臉說:“要是我們在這裡撿象牙,只怕是蓋了新竹樓要起火,買了牯子牛也會被老虎咬死的啊!”“對,是要遭報應的。”我說。望著戰象嗄羧高貴的遺體,我感到我這個人的靈魂的猥瑣。我和波農丁一起動手,將土推進坑去,把土坑填滿夯實,然後,空著手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走回寨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