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5條詞條名為悉達多的結果 展開
- 201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書籍
- 赫爾曼·黑塞創作中篇小說
- 古印度系族名稱
- 赫塞創作小說
- 黑塞作品譯林出版社2015年出版
悉達多
赫爾曼·黑塞創作中篇小說
徠《悉達多》是黑塞的第九部作品,1922年在德國出版,通過對主人公悉達多身上的兩個“自我”——理性的無限的“自我”和感性的有限的“自我”——的描寫,黑塞探討了個人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無限的、永恆的人生境界的問題。讀者從中既可以洞察作家對人性的熱愛與敬畏,對人生和宇宙的充滿睿智的理解,又能夠感受到他對傳統的人道主義理想的呼喚和嚮往,同時,還可以領略到作為西方人的作者對東方尤其是中國思想智慧的接受與借鑒。
《悉達多》講述了古印度貴族青年悉達多英俊聰慧,擁有人們羨慕的一切。為了追求心靈的安寧,他孤身一人展開了求道之旅。他在舍衛城聆聽佛陀喬答摩宣講教義,在繁華的大城中結識了名妓伽摩拉,並成為一名富商。心靈與肉體的享受達到頂峰,卻讓他對自己厭倦、鄙棄到極點。在與伽摩拉最後一次歡愛之後,他拋棄了自己所有世俗的一切,來到那河邊,想結束自己的生命。在那最絕望的一剎那,他突然聽到了生命之河永恆的聲音……經過幾乎一生的追求,悉達多終於體驗到萬事萬物的圓融統一,所有生命的不可摧毀的本性,並最終將自我融入了瞬間的永恆之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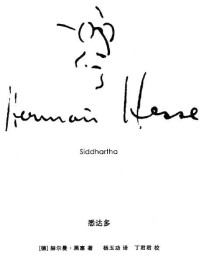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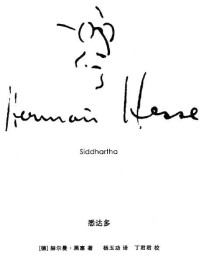
封面
| 目錄 |
第一部 婆羅門之子 沙門 喬答摩 覺醒 第二部 伽摩拉 人世間 輪迴 在岸邊 船夫 悉達多之子 噸 僑文達 |
赫爾曼·黑塞對小說《悉達多》(Siddhartha——Eine indische Dichtung)的創作始於1919年12月,在此之前,已過不惑之年的作者在個人生活上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困難時期。1919年4月,黑塞結束了在德國戰俘救濟所的工作之後,幾乎一貧如洗,只能靠費舍爾出版社給他提供的資助勉強維持生計;家庭生活也陷入了困境,妻子由於精神分裂症而不得不一再住進精神病院,他被迫將三個兒子送到朋友處寄養,他本人也多次接受了精神分析的治療。與此同時,時代的大環境對作家的內心也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和震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們帶來巨大的精神創傷,每一位飽受戰爭之苦煎熬的人都在思考著一個相同的問題:如何才能使剛剛發生過的悲劇不在未來重演?而對於始終關注著人類和世界前途與命運的人道主義作家黑塞來說,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則顯得尤為迫切。
無論從個人際遇和時事的影響,還是從作者本人的創作經歷來看,黑塞又寫出一部描寫個人發展的小說《悉達多》就不足為奇了,同時,黑塞在這部作品中如何針砭時弊,如何發展他已有的思想就自然而然地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小說一開頭,作者就把讀者帶到了古代印度,帶到了一個對於大多數人來講充滿異國情調的環境當中。主人公悉達多的形象也直接進入了讀者的視野,他是個英俊瀟灑、受人喜愛和尊敬的年輕婆羅門——古印度最高的精神貴族。正當所有人都能從他那裡獲得快樂和欣喜,都堅信他會擁有一個美好未來的時候,他自己卻由於某種不滿足而深感苦惱。為了探尋這種不滿足的根源,他對自己提出了一連串問題: “難道創造世界的果真是生主嗎?難道就不是那獨一無二的阿特曼嗎?難道神明不也是像你我一樣被創造出來的受時間約束的暫時的形象嗎?何處可以找到阿特曼,它在哪裡,它永恆的心在何處跳動,除了在每個人身上那最內在的不可摧毀的自我中之外,還會在何處呢?可是,這個自我又在哪裡,在哪裡,這最內在的最後的自我?滲入它,滲入這個自我,滲入我自己,滲入阿特曼——是否存在另一條值得去尋找的道路呢?
透過這些問題,就會發現,首先,主人公之所以感到苦惱,是因為作為一個婆羅門之子的他所要追求的最終目標——“阿特曼”還沒有達到。“阿特曼”這個詞漢語可以譯為“自我”和“我”,是印度哲學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它指人本身的永恆核心,是人一切活動的基礎;它是“梵”(brahman)的總體的一部分,可以同這一總體相通甚或融合;而“梵”在印度哲學里則是最高存在的意思,是永恆的、無限的和無所不在的,因此,悉達多渴求的這個“自我”也是一種超驗的、絕對的、完滿的存在。在這裡,黑塞做了兩點暗示。一方面,他已經為小說的內容和情節搭建了發展的框架,即這樣一部發展小說所要描寫的就是主人公悉達多如何最終達到這個永恆的“自我”的過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黑塞給他小說的主人公起一個與傳說中的佛陀相同的名字,因為在黑塞看來,傳說中的佛陀無疑達到了這個永恆的“自我”,成了完美的存在,所以主人公的名字暗示著他最終一定能夠如佛陀一樣達到“覺悟”,達到永恆而完美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既然“阿特曼”可以與宇宙中無限的最高存在同一,那麼人達到這個“自我”也就意味著個人也可以達到與宇宙和世界同一的境界。
既然主人公追求的目標已經明確,那麼接下來的問題自然就是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從悉達多的問題中可以看出,他不僅還沒有“找到”永恆的自我“阿特曼”,而且,他對另一個“自我”,即這裡提到的“各自的自我”——智者們認為可以找到永恆的“阿特曼”的地方——也缺乏認識和了解,顯然,這個“各自的自我”指的就是每個個人,即每個單獨存在於物質世界中的生命個體。關於這兩個“自我”的關係,黑塞在1943年5月給一個年輕人的信中做過更加詳細的闡述:“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兩個自我,誰始終知道,其中的一個從哪裡開始,另一個在哪裡結束,他就是不折不扣的智者。我們主觀的、經驗的、個體的“自我”——如果我們對其稍加思考——總是變化多端,隨心所欲,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外界,受外界影響。這個自我教給我們的——如《聖經》中經常講到的那樣——無非是,我們是一個相當孱弱的、固執的、沮喪的種姓。然而,接下來就是另一個自我,它隱藏在前一個之中,與之相融合,但絕不能與之相混淆。這第二個崇高的、神聖的自我(印度人的阿特曼,您將它與梵相提並論)不是個體,而是我們在神明、在生命、在整體、在非我和超我中所佔據的那一部分。”
眾所周知,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人們心靈中所造成的精神創傷,很多人在戰後都不同程度地產生了悲觀厭世的情緒,而黑塞在這裡反覆強調人不能逃避“自我”,應該面對現實,重新鼓起勇氣去追求美好的理想,可謂用心良苦。既然個人尋求永恆的“自我”必須假道個體的“自我”,那麼,主人公(作者)所思考和要“解決”的歸根到底也就是人如何從低級階段的感性的人發展成為高級階段的理性的人的問題。但正如黑塞本人已意識到的那樣,兩個“自我”之間既存在著不可割斷的聯繫,又存在著本質上的矛盾和對立。一方面,永恆的“自我”是主人公追求的目標,個體的“自我”是以永恆的“自我”為其存在的前提的,因為後者是人的本質核心,所以只有以達到後者為最終目標,個體“自我”的發展才具有意義;另一方面,一旦感性的個體“自我”朝著達到永恆“自我”的方向發展,它就必然會對理性的永恆“自我”有所“侵犯”,兩者便會處於對立面的無休止的鬥爭之中,也就永遠無法最終“統一”於理性。正因為如此,席勒才會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後在“人格”和“狀態”中間建立起一個假想的“審美的王國”。所以,黑塞才會借主人公之口一再表達了自己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在大徹大悟的那一時刻”在人身上發生的事是人“無法用語言和教義”表達的,這充分說明,作者正在為在不破壞感性和理性兩者任何一方的前提下達到兩者的統一尋找“答案”,但那“答案”究竟是什麼,恐怕連作家本人也還沒有完全瞭然。
小說中有四個證悟的人。第一個是喬達摩。他就是佛,小說沒有寫他的修行過程,高高在上,無懈可擊。第二個是悉達多,悉達多的學習和漫遊是對喬達摩的模仿,最後兩者合而為一。另外還有兩個人,一個是僑文達。僑文達聽釋迦牟尼講經,在佛教中是聲聞。另一個是船夫,他從傾聽河水而來,在佛教中是緣覺。小乘佛教分為聲聞、緣覺,緣覺比聲聞程度高。所謂緣覺就是從萬事萬物中傾聽和體會,《莊子·人間世》所謂“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緣覺另外的翻譯是獨覺,也就是緣覺的另一面,他不依靠老師的指導,是一個人自己悟出來的。喬達摩和悉達多是一對,喬達摩是已經證悟的,悉達多演繹了喬達摩的修行過程。僑文達和船夫是一對,僑文達是聲聞,船夫是緣覺。從小說中可以看出黑塞的佛教觀念,他當時在西方了解的就是聲聞、緣覺兩條路,沒有其他了。可以指出的是,在佛教中這還是小乘,還沒有到大乘菩薩行。
帶著認識和發展個體“自我”的強烈願望,主人公悉達多開始了全新的生活——他從未經歷過的世俗生活。在這裡,黑塞對悉達多世俗生活的描寫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一方面,他結識了名妓卡瑪拉,在她那裡第一次接觸到了男女之間的性愛,並成為她的朋友和情人;另一方面,他從商人卡瑪斯瓦密那裡學會了做生意,從世俗的人們那裡學會了物質享樂,並沉湎於其中。總而言之,悉達多將物質生活,即感性的個體“自我”發展到了極致。另一方面,由於主體內部那種追求永恆“自我”的趨向的存在,主人公對這種世俗生活日益感到厭倦,逐漸把它當作了一種痛苦,並希望能從中擺脫出來。根據已掌握的有關小說創作過程的材料,黑塞在尋求“自我”的終點的問題上顯然是百思不得其解,於是,小說的創作在持續了九個月後中斷了,而且一停就是18個月。1922年2月,也就是在重新開始寫作《悉達多》之前,他在致菲利克斯·布勞恩的信中提到了小說的結尾與中國哲學的關係:“赫拉克勒斯的道路我也很熟悉,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在創作一些與此類似的東西,它們裹著一層印度的外衣,起源於梵和佛陀,而終止於道。”而在1922年8月致海蕾娜·威爾蒂的另一封信中,他又一次重複了類似於上面的看法:“《悉達多》的結尾與其說是受了印度的影響,毋寧說具有道家哲學的色彩”。
徠1922年3月,黑塞重新拿起筆,在幾個星期內一氣完成了《悉達多》這部作品。那麼在小說最後幾章里他又是如何“解答”自己提出的問題的呢?悉達多終於逃離了那個世俗的世界,來到了多年前他曾經橫渡過的那條河的河邊,作者終於為主體如何解決變與不變、有限與無限的問題找到了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事物——河水。
主人公留在了河邊,開始從河水那裡“學習”他想要了解的“秘密”。首先,他看出了河水的一個特點——它既是“不變”的,又是“常新”的:“這河水流啊流,永不停息,卻又總是在這裡。它在任何時刻都是一個樣,但在每個瞬間又是全新的!”顯而易見,河水的這一特點已將兩個“自我”的特性都“包容”了進去,說其“不變”,是因為作為人的本質,永恆的自我始終如一;而說其“常新”,是由於個體自我無時無刻不在變化,正如席勒所說:“人只有在變化時,他才存在;只有保持不變時,他才存在。”於是,河水儼然已成為人的生命的象徵,成為個體的自我和永恆自我的“結合體”。
瞬間即永恆,時間是一切變化與不變的“結合點”,一旦主體不再意識到時間的存在,那麼他也就在主觀觀念上,在思維的層面上,既在自身當中使對立的兩個自我合而為一,又使世間萬物之間的區別不復存在,也就是說,在每一時刻,世界在他眼中都是一個和諧統一的整體。但是,這一切都不過是主人公從河水那裡得到的認識,他還要面對的一個問題便是:他能否把這一認識在現實中真正地實現?換句話說,當主體思索著世界是一個和諧的整體的時候,他實際上已假定自己是站在一個更高的觀點上看待世界,就是說他處在世界萬物的對立面,自身並不在其中;而另一個不爭的事實卻是,主體又的的確確存在於這個整體的世界之中,因此,要消除這個“自相矛盾之處”,主體就必須將自身“重新”納入到世界的整體之中並“證明”其自身的確是這個和諧世界的一部分,而這一切只有在現實的層面上才能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