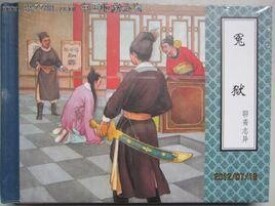共找到4條詞條名為冤獄的結果 展開
- 漢語詞語
- 聊齋志異篇目
- 1991年保羅·溫杜斯執導的電影
- 1991年上映的電影
冤獄
聊齋志異篇目
《冤獄》是清代小說家蒲松齡創作的文言短篇小說。
朱生,陽穀人。少年佻達,喜詼謔。因喪偶,往求媒媼。遇其鄰人之妻,睨之美。戲謂媼曰:“適睹尊鄰,雅少麗,若為我求凰,渠可也。”媼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為若圖之。”朱笑曰“諾。”
更月余,鄰人出討負,被殺於野。邑令拘鄰保,血膚取實,究無端緒;惟媒媼述相謔之詞,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令又疑鄰婦與私,搒掠之,五毒參至。婦不能堪,誣伏。又訊朱,朱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既使冤死,而又加以不節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何忍乎?我實供之可矣:欲殺夫而娶其婦,皆我之為,婦實不知之也。”問:“何憑?”答言,“血衣可證。”及使人搜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復甦者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證據死我耳,待自取之。”因押歸告母曰:“予我衣,死也;即不予,亦死也。均之死,故遲也不如其速也。”母泣,入室移時,取衣出付之。令審其跡確,擬斬。再駁再審,無異詞。經年余,決有日矣。
令方慮囚,忽一人直上公堂,努目視令而大罵曰:“如此憒憒,何足臨民!”隸役數十輩,將共執之。其人振臂一揮,頹然並仆。令懼,欲逃。其人大言曰:“我關帝前周將軍也!昏官若動,即便誅卻!”令戰懼悚聽。其人曰:“殺人者乃宮標也,於朱某何與?”言已,倒地,氣若絕。少頃而醒,面無人色。及問其人,則宮標也。搒之,盡服其罪。
蓋宮素不逞,知其討負而歸,意腰橐必富,及殺之,竟無所得。聞朱誣服,竊自幸。是日身入公門,殊不自知。令問朱血衣所自來,朱亦不知之。喚其母鞠之,則割臂所染。驗其左臂刀痕,猶未平也。令亦愕然。后以此被參揭免官,罰贖羈留而死。年餘,鄰母欲嫁其婦;婦感朱義,遂嫁之。
異史氏曰:“訟獄乃居官之首務,培陰騭,滅天理,皆在於此,不可不慎也。躁急污暴,固乖天和;淹滯因循,亦傷民命。一人興訟,則數農違時;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產:豈故之細哉!余嘗謂為官者,不濫受詞訟,即是盛德,且非重大之情,不必羈候;若無疑難之事,何用徘徊?即或鄉里愚民,山村豪氣,偶因鵝鴨之爭,致起雀角之忿,此不過借官宰之一言,以為平定而已,無用全人,只須兩造,笞杖立加,葛藤悉斷。所謂神明之宰非耶?
每見今之聽訟者矣: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攝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牌。蒙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將盡矣!而儼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拔救耶!然在奸民之凶頑,固無足惜;而在良民株累,亦復何堪?況且無辜之干連,往往奸民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於奸民。何以故?奸民難虐,而良民易欺也。皂隸之所毆罵,胥徒之所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暴。
身入公門,如蹈湯火。早結一日之案,則早安一日之生;有何大事,而顧奄奄堂上若死人,似恐溪壑之不遽飽,而故假之以歲時也者,雖非酷暴,而其實厥罪維均矣。嘗見一詞之中,其急要不可少者,不過三數人;其餘皆無辜之赤子,妄被羅織者也。或平昔以睚眥開嫌,或當前以懷璧致罪,故興訟者以其全力謀正案,而以其餘毒復小仇。帶一名於紙尾,遂成附骨之疽;受萬罪於公門,竟屬切膚之痛。人跪亦跪,狀若烏集;人出亦出,還同猱系。而究之官問不及,吏詰不至,其實一無所用,只足以破產傾家,飽蠹役之貪囊;鬻子典妻,泄小人之私憤而已。深願為官者,每投到時,略一審詰,當逐,逐之;不當逐,芟之。不過一濡毫、一動腕之間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養多少元氣。從政者曾不一念及此,又何必桁楊刀鋸能殺人哉!”
據《聊齋志異》鑄雪齋抄本
陽谷:縣名,今屬山東省。
佻達:輕薄。
雅少麗:十分年輕美麗。雅,甚。
渠,她。
若:你。
討負:猶討債。負,欠債。
鄰保:此指鄰里。保,戶籍編製單位。始於北來,明清相沿。初設時十家為一保,五十家為一大保。每兩人出一保丁;保年人犯法,保丁須檢舉、揭發。參見《文獻通考·乒考》五和《清文獻通考·職役》。
血膚取實:謂企圖通過烤打刑訊,令其供出實情。血膚,打得皮破血流。
五毒參至:極言施刑慘烈。五毒,五種酷刑,所指不一,此泛指各種酷刑。《後漢書·隗囂傳》:“(王莽)冤系無辜,妄族眾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灌以醇醯,裂以五毒。”參,雜。
駁:駁勘,上司駁回複查。《宋史·刑法志》三:“景定之年,乃下詔曰:比詔諸提刑司,取翻異駁勘之獄,從輕斷決。”
慮囚:審查核實囚犯的罪狀。前、后《漢書》作“錄囚”。《漢書·雋不疑傳》“錄因徒還”顏師古註:“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否)也。今雲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
努目:猶怒目。
憤債(kuìLuì潰潰):昏憒、糊塗。
大言:大聲說。
關帝前周將軍:即周倉,傳說為三國蜀關羽的部將。舊時關廟中有其塑像,持大刀立於關羽之後。
從“於朱其何與”至“則宮標也”,此據山東省博物館本增補,原無此八句。
素不逞:平素為非作歹。不逞,本謂不滿意、不得志。見《左傳·隱公十一年》。此用引申義,即為非作歹。《後漢書·史弼傳》:“外聚剽輕不逞之徒。”
參揭:彈劾、揭發。
罰贖羈留而死:罰其以金自贖,並在被羈留期間死去。
“培陰騭(zhì 至)”三句:謂積養陰德,還是滅絕天理,全表現在如何處理訟獄方面。陰騭,猶言陰德。天理,天性。
“躁急”四句:謂急於結案而濫施刑罰,固然有違自然祥和之氣;而長期拖延,消極不辦,也常常傷害百姓性命。乖,違。大和,自然的祥和之氣。語出《莊子·知北游》。污暴,猶貪暴,言貪術賄賂而濫施刑罪。淹滯,停止不前,此謂拖延不辦。因循,謂不事進取,持消極態度。
違時:謂違背農時,使農民錯過耕種和收割的季節。《孟子·梁惠王》上:“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
故之細:事之小者,即小事。故,事。細,小。
羈候,羈留候審。
鵝鴨之爭;指鄰里因小事發生爭執。
雀角之忿:喻指赴官爭訟。雀角,喻忿爭。《詩·召南·行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兩造:指爭訟雙方,即原告和被告。《書·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傳》:“兩謂囚、證;造,至也。”
葛藤悉斷:謂訟訴糾葛,全部剖斷分明。葛藤,葛和藤,均為纏樹蔓生植物,因喻事務糾纏不已。此喻民事訟訴糾紛。
“攝牒者”四句:謂經辦案件的捕役、書吏填滿私囊之後,才允許見官候審。攝牒者,指奉命捕系犯人的人。承刑者,指主辦文案的官吏,即刀筆吏。潤筆,本指舊時給予寫字繪畫者的報酬,此指文吏借人訴訟而從中敲詐的餞財。“見官之票”,此據二十四卷抄本,“票”原作“到”。
長吏:此泛指聽訟的主管長官。
僵息在床:卧在床上養息。語出《詩·小雅·北山》,原作“息偃在床”。
水火獄中:水深火熱的牢獄之中。
株累:因受牽連而致罪。株,樹根,此謂株連。一人有罪而牽連別人,猶如樹根向四處延伸一樣。
干連:猶牽連。干,關涉。
胥徒:古代官府中的小吏及奔走服役的人。此泛指官府衙役。
“而顧”句:謂卻只是因循之官長在大堂之上有氣無力像將死的人。極言官之拖沓,辦案不力。
溪壑之不遽飽:喻指如溪似壑之貪慾不能很快填滿。溪壑,本謂溪谷溝壑,見《國語·晉語》八,此以之喻無厭的貪慾。
歲時:此從二十四卷抄本,原無“時”字。
厥罪維均:謂拖延對日以勒索訴訟者與刑罰酷暴之罪相同。厥,其。維,語中助詞,無義。均,等。
詞:訟詞。
羅織:捏造罪名,陷害無辜。《唐會要·酷吏》:“時周興、來俊臣等,相次受制,推究大獄……共為羅織,以陷良善。又造《羅織經》一卷,其意旨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海內震驚,道路以目。”
以睚眥(yázì 牙自)開嫌:謂以小忿而產生仇怨。睚眥,怒目而視,借指小怨小忿。語出《史記·范雎列傳》。開,啟。嫌,仇怨。
以懷壁致罪:謂或因富有遭到嫉恨而獲罪。《左傳·桓公十年》:“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
正案:猶主案。
以其餘毒復小仇:以其餘恨對小的仇怨進行報復。毒,恨。
“帶一名”四句:謂狀詞上妄加一人,便使其如骨生惡瘡難以擺脫;使其在官府遭受種種苦難,竟是因為讒害所致。紙,狀紙。附骨之疽,骨上生的惡瘡。此謂一旦牽連入案,就如瘡生骨上難以割除一樣擺脫不掉。萬罪,猶言萬般苦難。切膚之痛,猶切身之痛。此指因遭受讒害而吃官司、受折磨。切膚,切身。虞集《道園學古錄·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邃深蔽雲,群讒切膚。”
“人跪”四句:極言官府不分青紅皂白,凡受案件牽連的人都須陪著打官司、受折磨。烏集,如群鴉集於一處,黑壓壓一片。猱(náo 撓)系,如同系猱。猱:猴屬。
蠹役:害民的吏役。
投到時:案中有關人員到公堂之時。
逐:斥出。言將無事生非者趕出公堂,不予受理。
芟:除去,言將關涉案件的一般人員除名,只留審必要的當事者。
元氣:人的精神,生命力的本原。此言不害民即保全社會元氣。
“從政者”二句:謂今之為官者從不念及保全百姓,培養社會元氣,這種淹滯因循的作風也一樣可以殺人,並不只是靠殘酷的刑具。曾,竟。桁(háng 杭)楊刀鋸,均指刑具。桁楊,加在犯人頸上或腳上的大型刑具。《莊子·在宥》:“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成玄英 疏:“桁楊者,械也。夾腳及頸,皆名桁楊。”刀鋸,《國語,魯語》上:“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韋昭註:“割劓用刀,斷截用鋸。”
朱生,是陽谷縣人,年齡不大,卻性情輕薄、好開玩笑。一天,他因為死了妻子,去求一個媒婆給自己說親。路上碰到那媒婆鄰居的妻子,朱生瞟了一眼,見那婦人很美,便跟媒婆開玩笑說:“剛才碰見你的鄰居,真是既文雅又秀麗,你若為我求偶,她就可以。”媒婆也開玩笑說:“你先殺了她男人,我再替你想辦法。”朱生笑著說:“說定了。”
過了一個多月,媒婆的鄰居出去討債,被人殺死在野外。縣令拘拿了死者的鄰居和地保,拷問實情,卻仍無頭緒。只有那個媒婆招供了她和朱生開的玩笑話,縣令因此懷疑到了朱生頭上,將他逮捕了,朱生卻堅決不承認。縣令又懷疑死者的妻子跟朱生私通,謀害親夫,將那婦人抓了去,用盡了各種酷刑拷打。婦人忍受不了折磨,胡亂招認了。縣令又拿婦人的供詞審問朱生。朱生說:“她一個柔弱婦人,受不了刑罰,她說的全是假的!既然她將要冤死,還要被加上不貞潔的名聲;縱使鬼神無知,我又於心何忍呢?我實招了吧:想殺死她的丈夫再娶了她,都是我一個乾的,她實在不知情!”縣令問:“你有什麼憑證嗎?”朱生說:“有血衣可以作證。”縣令便派人到朱生家搜取血衣,搜來搜去,卻怎麼也找不到。縣令再次拷打朱生,打得他幾次死去活來。朱生便說:“這是我母親不忍拿出物證來讓我去死,等我自己去取!”縣令命衙役押著他回到家中。朱生告訴母親說:“給我血衣,我是死;不給我也是死。反正都是死,還不如快點死去,也免得多受折磨。”他母親聽了,哭著進了內室。不一會兒,取出一件衣服來交給他。縣令檢查到衣服上確有血跡,人證、物證俱在,便判了朱生死刑。以後經兩次複審,也都沒有不同的證詞。過了一年多,朱生馬上就要被處決了。
一天,縣令正在審案,忽有一人徑直衝上公堂,瞪著眼大罵縣令道:“你如此昏庸糊塗,怎麼治理老百姓!”幾十名衙役見狀,一擁而上,想綁起他來,那人振臂一揮,衙役們呼啦啦倒了一片。縣令大驚,站起身想逃,那人大喊道:“我是關帝跟前的將軍周倉!昏官敢動,立即要你的狗命!”縣令渾身顫抖,一動不敢動。那人說:“殺人的是宮標!與朱某有什麼關係?”說完就一下子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樣。過了會兒才蘇醒過來,還面無人色。等詢問他的姓名,才知他就是宮標。縣令拷打他,宮標招供了全部殺人罪行。
原來,宮標本是個無賴,知道那鄰居討債回來,以為他腰包里一定有很多錢,就在野外殺了他,沒想到竟什麼也沒有。後來聽說朱生被屈打成招,他暗自慶幸。這天,他稀里糊塗地衝進縣衙,自己也不知是怎麼回事。縣令又問朱生那件血衣是哪裡來的,朱生也不知。叫他母親來詢問,才知是他母親割破自己的胳膊染的!檢查朱母的左臂上,果然刀傷還沒好,縣令也大吃一驚。後來,縣令因為這個案子被告發罷官,罰款贖罪,在羈留時死在獄中。
過了一年多,死者的母親讓媳婦改嫁,那婦人感激朱生的義氣,便嫁給了他。
異史氏說:訴訟決獄是為官者的首要任務,積陰德,滅天理,都在於此,不可不慎重。急躁貪暴,固然有悖天理;然而因循拖延,也會損傷人民的性命。一個人訴訟,則好幾個農民將難以務農;一案既成,則十家人傾家蕩產,難道這是小事嗎!我曾經說那些當官的,不要隨便接受別人的訴訟,就是最大的德行。如果不是重大的事情,不要把人長久羈押;如果不是疑難的案件,何必徘徊不決?即便是有的鄰里愚民,山村野夫,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起了紛爭,結果鬧上公堂,這也不過是想借官府一句話,為他們來做一個評判,不用全部人等,只要原告和被告,加以杖刑,什麼事都解決了。這難道不是所謂的神明一樣的官宰嗎?
如今每每見到那些審案,傳票一出,就好象什麼都忘了。拘捕者的賄賂不得到滿足,那麼那些傳票就不會消除;書吏賄賂不得到滿足,那麼就不讓你見到官宰。蒙蔽拖延,動輒經年累月,還沒有升堂斷案,則被告的皮骨都快被壓榨乾凈了!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宰,安然躺在床上,好象沒事一樣。難道不知道水深火熱的監獄中,有無數的冤魂,都伸長了脖子延長著氣息,企望你的拯救嗎!固然那些凶頑的刁民,死不足惜;但是那些受牽連的良民,又怎堪承受?況且無辜的牽連,往往都是奸民少但是良民多,良民所受的傷害,則更加倍於那些奸民。這是什麼原因呢?奸民難以施虐,但是良民卻容易欺壓。那些官吏的毆打,衙役的勒索,都是選擇良民來進行的。
一旦入了公門,如同在滾水與烈火中一般。早一天結案,早一天安生,有什麼大事,看看堂上那些奄奄一息垂死之人,恐怕自己的私囊不能填飽,於是借故拖延時日經年累月!雖然看似不殘酷凶暴,但這種拖延和殘酷凶暴又有什麼差別呢?曾經看到一案中,真正緊要的人不過三人許,其餘都是無辜收到牽連的清白之人,妄被羅織罪名羈押在案。有的是平日里小忿而產生仇怨,有的則是因富有遭到嫉恨而獲罪,所以那些原告全力以赴於主案,順便攜報私仇。謂狀詞上妄加一人,便使其如骨生惡瘡難以擺脫;使其在官府遭受種種苦難,竟是因為讒害所致。極言官府不分青紅皂白,凡受案件牽連的人都須陪著打官司、受折磨,就像烏鴉,猴群一樣的聚集。而細究那些官宰詢問不及,官吏詰問不至,其實都沒什麼用處,只是導致傾家蕩產,飽了那些污吏的私囊,賣了老婆孩子,只不過因為那些小人要泄私憤而已。深深希望那些當官的,每有告狀的,稍微詢問一下,那些無理取鬧的直接趕走,那些關涉案件的一般人員除名,只留審必要的當事者。不過一揮筆、一抬手之間,就能保全多少人的身家性命,保護了社會多少元氣啊!從政者沒有這種觀念,那麼殺人真的不必用那些酷烈的刑具啊!
蒲松齡(1640-1715),清代傑出的文學家,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山東淄川(今山東淄博市)人。他出身於一個沒落的地主家庭,父親蒲槃原是一個讀書人,因在科舉上不得志,便棄儒經商,曾積累了一筆可觀的財產。等到蒲松齡成年時,家境早已衰落,生活十分貧困。蒲松齡一生熱衷功名,醉心科舉,但他除了十九歲時應童子試曾連續考中縣、府、道三個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外,以後屢受挫折,一直鬱郁不得志。他一面教書,一面應考了四十年,到七十一歲時才援例出貢,補了個歲貢生,四年後便死去了。一生中的坎坷遭遇使蒲松齡對當時政治的黑暗和科舉的弊端有了一定的認識,生活的貧困使他對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和體會。因此,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寫了不少著作,今存除《聊齋志異》外,還有《聊齋文集》和《詩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