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23條詞條名為暴風雨的結果 展開
暴風雨
紀伯倫散文詩集
《暴風雨》成書於1920年,全集收集了紀伯倫在一次大戰前後所寫的31篇短文,其中一篇《蘇爾班》為短劇形式。《暴風集》是紀伯倫最有力度的散文詩集。紀伯倫把這個集子定名為《暴風集》並不是偶然的。紀伯倫特別喜歡象徵著反叛、革命、翻天覆地變化的暴風雨。在大自然的狂風暴雨中,他的內心激蕩之情能夠得到共鳴與抒發。紀伯倫是馳譽世界的東方詩人。他在黎巴嫩出生,在歐洲學過繪畫,在美國組織過阿拉伯第一個海外父子團體。創作出一系列小說和散文詩作品。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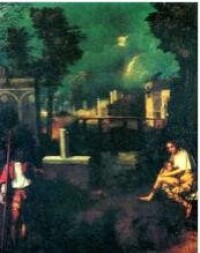
暴風雨
正是在這樣的熾熱中,一篇篇充滿激情的散文詩誕生了。這個集子薈萃了許多名篇,大都是針對東方特別是阿拉伯世界的社會、政治問題而寫的。作者簡介 紀伯倫是馳譽世界的東方詩人。他的散文詩集《先知》等被譽為“東方贈予西方的最好禮物”。他既是“破壞者”,又是“建設者”;既要做埋葬活屍的“掘墓人”,又要做醫治民族“靈魂”的“醫生”。他把整個世界當作“祖國”,把全人類當做“鄉親”。他為人類提出的目標是“神性的人”。這本評傳將向您介紹這位東方詩人兼畫家的一生,他的生命哲學、藝術性趣的主要作品,他的愛情,以及他孤獨的原因。詳細介紹《掘墓人》《掘墓人》是闡釋紀伯倫性格人生最典型的一篇。紀伯倫以超現實的筆法,描繪了一個敢於“褻瀆太陽”“詛咒人類”、“嘲笑自然”的“瘋狂之神”的形象。他沒有什麼偶像,只膜拜自己,並大聲宣稱“我是自己的主!”在這個阿拉伯文學史上,這是一個空前大膽的藝術形象,實際上正是紀伯倫人的理想具體化,是消除一切奴性痕迹的自立自強的人。紀伯倫在《掘墓人》中提出了“埋葬活屍”的口號。他借“瘋狂之神”之口說出,世界上存在著許多苟且偷安的人,他們沒有獨立的思想,“在風暴面前戰慄而不與它一同前進”,這些人無異於行屍走肉。紀伯倫由此為詩人們找到了最合適的工作,即帶領大家挖掘墳墓,埋葬“死人”與“活屍”。紀伯倫本人無疑是一直致力於這工作的。關於東方,東方痼疾的論述,是《暴風集》中最有價值、最具普遍意義的部分。紀伯倫在《麻醉劑和解剖刀》一文中坦率地指出,“東方是一個病夫”。不僅如此,東方在“災病輪番侵襲”下,竟已“習慣了病痛”,甚至把自己的災難和痛苦看成是“某種自然屬性”。紀伯倫一針見血地指出,東方人太愛聽甜言蜜語,以為一切揭病灶、下良藥、動手術的行為都近於瘋狂。對於這一點紀伯倫是深有感觸的。東方的“病人”是如此,東方的“醫生”又如何呢?紀伯倫發現,東方的醫生很多,但大多數只開些能減弱而不能治癒疾病的“臨時麻醉劑”。從文中所舉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紀伯倫以這些只開“麻醉品”的庸醫來影射那些政客、宗教家、學者,甚至普通教師、鄰人與親朋。他們自己也是病人,又怎能治癒他人呢?紀伯倫形象地描述了阿拉伯乃至東方世界的現狀:由於麻醉劑的效力,“東方”在柔軟的床榻上可以沉睡一輩子,而當一個清醒者向他大喊,希望他能擺脫這種狀態時,他卻認為這是一個“粗魯的,自己不睡也不讓別人睡的傢伙”,並且對自己的靈魂說,這是一個叛教者,正在敗壞著青年一代的道德,用毒箭傷害著人類。可見,這些醫生的麻醉劑非但不能根治東方的病症,而且使東方的病情惡化了,以致病夫低制一切的治療,敵視那些企圖將其從昏睡中喚醒的人。紀伯倫在《齲齒》一文中發揮了這一思想,他借牙科醫生對東方民族的齲齒僅僅進行表面修補,裹上金殼的無用之舉,將粉飾太平的行為與民族的衰亡聯繫起來。《暴風集》
紀伯倫是馳譽世界的東方詩人。他的散文詩集《先知》等被譽為“東方贈予西方的最好禮物”。他既是“破壞者”,又是“建設者”;既要做埋葬活屍的“掘墓人”,又要做醫治民族“靈魂”的“醫生”。他把整個世界當作“祖國”,把全人類當做“鄉親”。他為人類提出的目標是“神性的人”。這本評傳將向您介紹這位東方詩人兼畫家的一生,他的生命哲學、藝術性趣的主要作品,他的愛情,以及他孤獨的原因。詳細介紹《掘墓人》《掘墓人》是闡釋紀伯倫性格人生最典型的一篇。紀伯倫以超現實的筆法,描繪了一個敢於“褻瀆太陽”“詛咒人類”、“嘲笑自然”的“瘋狂之神”的形象。他沒有什麼偶像,只膜拜自己,並大聲宣稱“我是自己的主!”在這個阿拉伯文學史上,這是一個空前大膽的藝術形象,實際上正是紀伯倫人的理想具體化,是消除一切奴性痕迹的自立自強的人。紀伯倫在《掘墓人》中提出了“埋葬活屍”的口號。他借“瘋狂之神”之口說出,世界上存在著許多苟且偷安的人,他們沒有獨立的思想,“在風暴面前戰慄而不與它一同前進”,這些人無異於行屍走肉。紀伯倫由此為詩人們找到了最合適的工作,即帶領大家挖掘墳墓,埋葬“死人”與“活屍”。紀伯倫本人無疑是一直致力於這工作的。關於東方,東方痼疾的論述,是《暴風集》中最有價值、最具普遍意義的部分。紀伯倫在《麻醉劑和解剖刀》一文中坦率地指出,“東方是一個病夫”。不僅如此,東方在“災病輪番侵襲”下,竟已“習慣了病痛”,甚至把自己的災難和痛苦看成是“某種自然屬性”。紀伯倫一針見血地指出,東方人太愛聽甜言蜜語,以為一切揭病灶、下良藥、動手術的行為都近於瘋狂。對於這一點紀伯倫是深有感觸的。東方的“病人”是如此,東方的“醫生”又如何呢?紀伯倫發現,東方的醫生很多,但大多數只開些能減弱而不能治癒疾病的“臨時麻醉劑”。從文中所舉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紀伯倫以這些只開“麻醉品”的庸醫來影射那些政客、宗教家、學者,甚至普通教師、鄰人與親朋。他們自己也是病人,又怎能治癒他人呢?紀伯倫形象地描述了阿拉伯乃至東方世界的現狀:由於麻醉劑的效力,“東方”在柔軟的床榻上可以沉睡一輩子,而當一個清醒者向他大喊,希望他能擺脫這種狀態時,他卻認為這是一個“粗魯的,自己不睡也不讓別人睡的傢伙”,並且對自己的靈魂說,這是一個叛教者,正在敗壞著青年一代的道德,用毒箭傷害著人類。可見,這些醫生的麻醉劑非但不能根治東方的病症,而且使東方的病情惡化了,以致病夫低制一切的治療,敵視那些企圖將其從昏睡中喚醒的人。紀伯倫在《齲齒》一文中發揮了這一思想,他借牙科醫生對東方民族的齲齒僅僅進行表面修補,裹上金殼的無用之舉,將粉飾太平的行為與民族的衰亡聯繫起來。《暴風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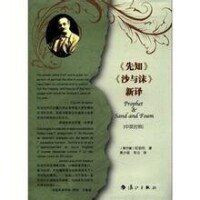 紀伯倫在《暴風》一文中道出了真正想為東方治病的醫生們的悲劇。顯然紀伯倫對此是有切膚之痛的。他主張用“解剖刀”挑開東方遮掩的病灶,用果斷的“手術刀”切除那危險蔓延的癰疽,從而達到治標治本的目的。紀伯倫本人是一貫如此行事的,這才是真正的愛與忠誠。但他得到的卻是嘲罵和詛咒,被宣布為“人道主義的敵人”!因此,紀伯倫在文中形象地描寫出了“時代病夫”竟然從被子里伸出手掐死醫生的可怕情景。在這篇文章中,紀伯倫所表現的憤怒超過了痛心。但這種憤怒終究也是以愛為出發點的。《奴性》也是《暴風集》中的名篇。紀伯倫尖銳地指出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都不自覺地通過某種形式,成為某種物質的或精神的奴隸。他站在人類歷史的高度寫道:“自我降生始,七千年過去了,我所見到的儘是屈辱的奴隸和帶鐐銬的囚犯。”然而這些奴隸們卻順從地跪在偶像面前,被奴性支配而不自知,因此紀伯倫寫道:“我發現奴隸主義昂首闊步於各地的祭悼隊伍之中,人們奉之為神靈”。紀伯倫看出一種奴性從屬於奴性,存在著一個奴性的階梯:“勞工是商賈的奴隸,商賈是大兵的奴隸,大兵是官宦的奴隸,官宦是國王的奴隸,祭司是偶像的奴隸。”而偶像不過是“堅立在骷髏堆上”的“一把泥土”而已!紀伯倫列舉了奴性的種種表現形式,有“啞巴式”,“聾子式”,“佝僂式”,……不一而足,而“其最出奇者,則是將人們的現在與其父輩的過去拉在一起,使其靈魂拜倒在祖輩的傳統面前,讓其成為陳腐靈魂的新軀殼,一把朽骨的新墳墓。”喋喋不休,誇誇其談,喜歡坐而論道,不願起而行道,這是紀伯倫發現和憎惡的另一個東方社會現象。他揭露“那些政治家們”言辭娓娓動聽,說得天花亂墜,完全是為了蒙蔽公眾耳目,那些神父、教士們口口聲聲訓誡別人,而自己從來並不身體力行”。在《言語與誇誇其談者》一文中,紀伯倫發展了這一思想。他指出,真理的聲音淹沒在誇誇其談的汪洋大海之中,令有思想的人分外苦惱。紀伯倫嘆道:“我的思想就丟在言語和誇誇其談者中間”了!他忍無可忍地喊出:“我已厭煩了言語和誇誇其談的人!”在《致大地》一文中,紀伯倫強調了民族自我更新的意義,他針對東方民族沉溺以往光榮,總愛誇耀自己悠久歷中的心理與行為,說出“准不把自己往昔的功績忘卻,必將元所創新”,這一名句。紀伯倫指出,“誰不用自己的力量扯下自己的腐葉,必將日益衰亡。”因此,紀伯倫呼喚暴風雨,目的是“用風暴武裝,以現代戰勝過去,以新的壓倒舊的,以強大征服軟弱。”紀伯倫在《雄心勃勃的紫羅蘭》一文中,以寓言的形式表現了一個重要的主題,即“存在的目的在於追求存在以外的東西”——理想。一株纖弱的紫羅蘭想變成高大燦爛的玫瑰,以了解自己“有限天地”之外的事情。她超越了“知足”這難以超越的障礙,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儘管她的奮鬥最後以悲劇靠終,但她帶著“勝利的微笑”死而無憾。其它平庸的紫羅蘭們對此是大不以為然的。但對於“野心勃勃的紫羅蘭”來說,她已經歷過一生中最美麗的時光,再無遺憾了。《暴風集》是紀伯倫最優美的散文詩集之一。他一改往日語言纖細柔弱的風格,而以火、以風暴鍛鑄出簡潔、有力的文字。紀伯倫呼喚著摧枯拉朽的變革風暴的到來。可以說他就是一個舊世界的“掘墓人”,一個號召人民擺脫奴性,反抗壓迫的革命者。這本書出版后,不僅再次衝擊了海外阿拉伯僑民界,也給阿拉伯本土同胞帶來很大震動。《珍趣篇》
紀伯倫在《暴風》一文中道出了真正想為東方治病的醫生們的悲劇。顯然紀伯倫對此是有切膚之痛的。他主張用“解剖刀”挑開東方遮掩的病灶,用果斷的“手術刀”切除那危險蔓延的癰疽,從而達到治標治本的目的。紀伯倫本人是一貫如此行事的,這才是真正的愛與忠誠。但他得到的卻是嘲罵和詛咒,被宣布為“人道主義的敵人”!因此,紀伯倫在文中形象地描寫出了“時代病夫”竟然從被子里伸出手掐死醫生的可怕情景。在這篇文章中,紀伯倫所表現的憤怒超過了痛心。但這種憤怒終究也是以愛為出發點的。《奴性》也是《暴風集》中的名篇。紀伯倫尖銳地指出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都不自覺地通過某種形式,成為某種物質的或精神的奴隸。他站在人類歷史的高度寫道:“自我降生始,七千年過去了,我所見到的儘是屈辱的奴隸和帶鐐銬的囚犯。”然而這些奴隸們卻順從地跪在偶像面前,被奴性支配而不自知,因此紀伯倫寫道:“我發現奴隸主義昂首闊步於各地的祭悼隊伍之中,人們奉之為神靈”。紀伯倫看出一種奴性從屬於奴性,存在著一個奴性的階梯:“勞工是商賈的奴隸,商賈是大兵的奴隸,大兵是官宦的奴隸,官宦是國王的奴隸,祭司是偶像的奴隸。”而偶像不過是“堅立在骷髏堆上”的“一把泥土”而已!紀伯倫列舉了奴性的種種表現形式,有“啞巴式”,“聾子式”,“佝僂式”,……不一而足,而“其最出奇者,則是將人們的現在與其父輩的過去拉在一起,使其靈魂拜倒在祖輩的傳統面前,讓其成為陳腐靈魂的新軀殼,一把朽骨的新墳墓。”喋喋不休,誇誇其談,喜歡坐而論道,不願起而行道,這是紀伯倫發現和憎惡的另一個東方社會現象。他揭露“那些政治家們”言辭娓娓動聽,說得天花亂墜,完全是為了蒙蔽公眾耳目,那些神父、教士們口口聲聲訓誡別人,而自己從來並不身體力行”。在《言語與誇誇其談者》一文中,紀伯倫發展了這一思想。他指出,真理的聲音淹沒在誇誇其談的汪洋大海之中,令有思想的人分外苦惱。紀伯倫嘆道:“我的思想就丟在言語和誇誇其談者中間”了!他忍無可忍地喊出:“我已厭煩了言語和誇誇其談的人!”在《致大地》一文中,紀伯倫強調了民族自我更新的意義,他針對東方民族沉溺以往光榮,總愛誇耀自己悠久歷中的心理與行為,說出“准不把自己往昔的功績忘卻,必將元所創新”,這一名句。紀伯倫指出,“誰不用自己的力量扯下自己的腐葉,必將日益衰亡。”因此,紀伯倫呼喚暴風雨,目的是“用風暴武裝,以現代戰勝過去,以新的壓倒舊的,以強大征服軟弱。”紀伯倫在《雄心勃勃的紫羅蘭》一文中,以寓言的形式表現了一個重要的主題,即“存在的目的在於追求存在以外的東西”——理想。一株纖弱的紫羅蘭想變成高大燦爛的玫瑰,以了解自己“有限天地”之外的事情。她超越了“知足”這難以超越的障礙,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儘管她的奮鬥最後以悲劇靠終,但她帶著“勝利的微笑”死而無憾。其它平庸的紫羅蘭們對此是大不以為然的。但對於“野心勃勃的紫羅蘭”來說,她已經歷過一生中最美麗的時光,再無遺憾了。《暴風集》是紀伯倫最優美的散文詩集之一。他一改往日語言纖細柔弱的風格,而以火、以風暴鍛鑄出簡潔、有力的文字。紀伯倫呼喚著摧枯拉朽的變革風暴的到來。可以說他就是一個舊世界的“掘墓人”,一個號召人民擺脫奴性,反抗壓迫的革命者。這本書出版后,不僅再次衝擊了海外阿拉伯僑民界,也給阿拉伯本土同胞帶來很大震動。《珍趣篇》 1923年,《暴風集》的延續——《珍趣篇》出版了。這本書不是作者本人與出版商聯繫編定、出版的,而是由一位叫尤素福·托瑪·布斯塔尼的阿位伯出版家在埃及阿拉伯人書局編輯出版的。由於它是從散見各處的紀伯倫的作品中選輯的,所以最初的版本在內容上與紀伯倫的某些集子有重複。《珍趣篇》是一個內容豐富、體裁多樣的綜合性集子。它包括三十六篇作品,其中散文詩十六篇,韻詩十四首,文學論文與評論五篇,劇本一個。這些作品也大都寫於一次大戰前後,在內容與主題上與《暴風集》有異曲同工之妙。就散文詩而言,此集中最重要的篇章首推《你有你們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這是一篇立意深刻、氣勢壯闊、形式新穎、文采璀璨的妙文。通篇以大體相近的句式,對應重複,一氣呵成,淋漓盡致地表現出紀伯倫的愛國主義和美好的社會政治理想。紀伯倫採取敘述加對比的手法,描繪出兩個迥然不同的黎巴嫩。你有你們的黎巴嫩及其難題,我有我的黎巴嫩及其瑰麗。紀伯倫指出,他的敵對者締造的黎巴嫩,是解不開的“政治死結”。針對在土耳其殘酷統治下的黎巴嫩,被政客出賣,被教會欺騙的現狀,紀伯倫寫道:“你們的黎巴嫩”是“宗教首領、軍隊司令的棋盤”,是“形形色色的教派和政黨”,是無休止的“謊言”和“辯論”。這樣的黎巴嫩不會長久,它很快將走向滅亡,就象奄奄一息的朽翁。紀伯倫心目中的黎巴嫩,則是瑰麗無比的大自然,是“悠遠的思想”、“熾勢的感情”、“神聖的語言”,是“青年抱負,中年的決心,老年的睿智”,是“樸素而袒露的真理”。在紀伯倫心中,這些都是被黑暗一時遮蓋了的黎巴嫩的本色,這樣的黎巴嫩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光輝的前途的,就像是“生氣勃勃的青年”。在紀伯倫看來,黎巴嫩的兒女應能代表黎巴嫩“岩石中的意志,巍峨中的高貴,流水中的甘美,空氣中的芳馨”,即具有黎巴嫩人傳統的優秀品格,他們應該讓自己的生命成為“黎巴嫩血管里的一滴血”。這些兒女們包括為黎巴嫩作出貢獻的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也包括“把自己的靈魂傾注於新杯中的詩人”,他們是“風吹不滅的燈,時蝕不腐的鹽”,是邁著堅定步伐奔向真善美的人。這篇散文詩表達了紀伯倫熱愛祖國的一顆拳拳之心,具有無比的生命力,至今仍具現實意義,並將顯示出跨世紀的魅力。《珍趣篇》中還有許多篇章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獨立與紅氈帽》,通過一位同胞為了強調自己的“獨立”和“尊嚴”,拒絕在法國客輪餐廳脫下他的紅氈帽這件小事,引發出紀伯倫對民族心理的深刻透視和剖析。他指出,“精神上和心智上均受奴役的民族,是不能靠他們的衣著、習俗成為自由的”,同胞們的不幸正在於“他們反對結果而未曾注意到原因”。紀伯倫呼籲同胞不要在小事上盲目爭“獨立”,要爭“技術獨立”與“工業獨立”。他說這是“懸於每個人頭上”的問題。在當時,能這樣清醒地看到並大膽指出民族奮起的先決條件的人是不多的。可見紀伯倫是注重事物的本質的。在《皮殼與內核》一文中,紀伯倫把他的這個觀點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他指出,生命不在於它的“表象”,而在於它的“內蘊”,事物不在於它的“皮殼”,而在於它的“內核”,人不在於他的“面孔”,而在於他的“內心”。對於宗教、藝術、社會與個人,也應首先看到它(他)們的內部本質。這些在今天看來,不見得有多少讓人特別驚奇的地方,但在那時,宗教家、政治家、“學者”都唱著動聽的歌曲,糟糠與精華難辨,對於那些東方人,尤其輕信的阿拉伯人,的確是一種及時而可貴的忠告嗎。紀伯倫在同胞中一直是一個孤獨者。他的孤獨是果實累累無人採摘的孤獨,是一個慷概的給予者找不到接受者的孤獨,是缺乏知音、缺少理解者的孤獨。在《我的心重負著累累果實》一文中,紀伯倫向人們披露了作為精神富有的孤獨者的秘密。文章情真意切,使人們更深地了解紀伯倫本人。通過《我的心靈告誡我》、《完美》、《孤獨》、《更遼闊的海洋》等文,紀伯倫引導讀者進入一個遼闊而深邃的精神世界。在這裡,紀伯倫時而是哲學家,談論現象與本質;時而是道德家,表達無私給予者的煩惱;時而是美學家,探討“完美”的終極意義;時而是心理學家,尋求詩人孤獨的原因和心靈溝通的道路……他和他的心靈為伴,巡視著這個世界,希望找到一個滌盪污垢的大海,他們找到了,但海灘上充斥了世間的俗人與各式各樣的裝腔作勢者,於是他們離開那裡,又去尋找“更遼闊的海洋”。《珍趣篇》的確是名副其實的“珍聞與趣談”。在這裡紀伯倫展示了他豐富的精神世界,提出許多新穎而有價值的見地,令人深思而有所得。可以看出,這時紀伯倫的筆已不像過去那樣鋒芒畢露、咄咄逼人了。隨著一次大戰的結束,紀伯倫的主題也漸漸從“破壞”轉移到“建設”上來。
1923年,《暴風集》的延續——《珍趣篇》出版了。這本書不是作者本人與出版商聯繫編定、出版的,而是由一位叫尤素福·托瑪·布斯塔尼的阿位伯出版家在埃及阿拉伯人書局編輯出版的。由於它是從散見各處的紀伯倫的作品中選輯的,所以最初的版本在內容上與紀伯倫的某些集子有重複。《珍趣篇》是一個內容豐富、體裁多樣的綜合性集子。它包括三十六篇作品,其中散文詩十六篇,韻詩十四首,文學論文與評論五篇,劇本一個。這些作品也大都寫於一次大戰前後,在內容與主題上與《暴風集》有異曲同工之妙。就散文詩而言,此集中最重要的篇章首推《你有你們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這是一篇立意深刻、氣勢壯闊、形式新穎、文采璀璨的妙文。通篇以大體相近的句式,對應重複,一氣呵成,淋漓盡致地表現出紀伯倫的愛國主義和美好的社會政治理想。紀伯倫採取敘述加對比的手法,描繪出兩個迥然不同的黎巴嫩。你有你們的黎巴嫩及其難題,我有我的黎巴嫩及其瑰麗。紀伯倫指出,他的敵對者締造的黎巴嫩,是解不開的“政治死結”。針對在土耳其殘酷統治下的黎巴嫩,被政客出賣,被教會欺騙的現狀,紀伯倫寫道:“你們的黎巴嫩”是“宗教首領、軍隊司令的棋盤”,是“形形色色的教派和政黨”,是無休止的“謊言”和“辯論”。這樣的黎巴嫩不會長久,它很快將走向滅亡,就象奄奄一息的朽翁。紀伯倫心目中的黎巴嫩,則是瑰麗無比的大自然,是“悠遠的思想”、“熾勢的感情”、“神聖的語言”,是“青年抱負,中年的決心,老年的睿智”,是“樸素而袒露的真理”。在紀伯倫心中,這些都是被黑暗一時遮蓋了的黎巴嫩的本色,這樣的黎巴嫩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光輝的前途的,就像是“生氣勃勃的青年”。在紀伯倫看來,黎巴嫩的兒女應能代表黎巴嫩“岩石中的意志,巍峨中的高貴,流水中的甘美,空氣中的芳馨”,即具有黎巴嫩人傳統的優秀品格,他們應該讓自己的生命成為“黎巴嫩血管里的一滴血”。這些兒女們包括為黎巴嫩作出貢獻的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也包括“把自己的靈魂傾注於新杯中的詩人”,他們是“風吹不滅的燈,時蝕不腐的鹽”,是邁著堅定步伐奔向真善美的人。這篇散文詩表達了紀伯倫熱愛祖國的一顆拳拳之心,具有無比的生命力,至今仍具現實意義,並將顯示出跨世紀的魅力。《珍趣篇》中還有許多篇章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獨立與紅氈帽》,通過一位同胞為了強調自己的“獨立”和“尊嚴”,拒絕在法國客輪餐廳脫下他的紅氈帽這件小事,引發出紀伯倫對民族心理的深刻透視和剖析。他指出,“精神上和心智上均受奴役的民族,是不能靠他們的衣著、習俗成為自由的”,同胞們的不幸正在於“他們反對結果而未曾注意到原因”。紀伯倫呼籲同胞不要在小事上盲目爭“獨立”,要爭“技術獨立”與“工業獨立”。他說這是“懸於每個人頭上”的問題。在當時,能這樣清醒地看到並大膽指出民族奮起的先決條件的人是不多的。可見紀伯倫是注重事物的本質的。在《皮殼與內核》一文中,紀伯倫把他的這個觀點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他指出,生命不在於它的“表象”,而在於它的“內蘊”,事物不在於它的“皮殼”,而在於它的“內核”,人不在於他的“面孔”,而在於他的“內心”。對於宗教、藝術、社會與個人,也應首先看到它(他)們的內部本質。這些在今天看來,不見得有多少讓人特別驚奇的地方,但在那時,宗教家、政治家、“學者”都唱著動聽的歌曲,糟糠與精華難辨,對於那些東方人,尤其輕信的阿拉伯人,的確是一種及時而可貴的忠告嗎。紀伯倫在同胞中一直是一個孤獨者。他的孤獨是果實累累無人採摘的孤獨,是一個慷概的給予者找不到接受者的孤獨,是缺乏知音、缺少理解者的孤獨。在《我的心重負著累累果實》一文中,紀伯倫向人們披露了作為精神富有的孤獨者的秘密。文章情真意切,使人們更深地了解紀伯倫本人。通過《我的心靈告誡我》、《完美》、《孤獨》、《更遼闊的海洋》等文,紀伯倫引導讀者進入一個遼闊而深邃的精神世界。在這裡,紀伯倫時而是哲學家,談論現象與本質;時而是道德家,表達無私給予者的煩惱;時而是美學家,探討“完美”的終極意義;時而是心理學家,尋求詩人孤獨的原因和心靈溝通的道路……他和他的心靈為伴,巡視著這個世界,希望找到一個滌盪污垢的大海,他們找到了,但海灘上充斥了世間的俗人與各式各樣的裝腔作勢者,於是他們離開那裡,又去尋找“更遼闊的海洋”。《珍趣篇》的確是名副其實的“珍聞與趣談”。在這裡紀伯倫展示了他豐富的精神世界,提出許多新穎而有價值的見地,令人深思而有所得。可以看出,這時紀伯倫的筆已不像過去那樣鋒芒畢露、咄咄逼人了。隨著一次大戰的結束,紀伯倫的主題也漸漸從“破壞”轉移到“建設”上來。

紀伯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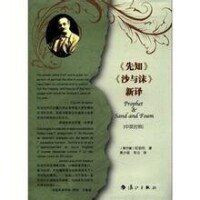
暴風雨

暴風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