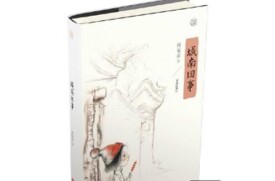共找到9條詞條名為城南舊事的結果 展開
城南舊事
青島出版社插圖本
《城南舊事》是2015年01月青島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圖書,作者是林海音。
《城南舊事》是林海音的自傳體小說,以她的七至十三歲的童年記憶為線串起五個童年的故事。
《城南舊事》寫出一個小女孩的焦急、迷惑和淚水。她要分出好人和壞人。她要寫愛情、婚姻中的女人的命運,她為秀貞、蘭姨娘、媽媽哭。敏銳,使得她傷心、憂傷。智力,使她擺脫自己不喜歡的人和事,比如為了媽媽和自己,使得蘭姨娘離開了爸爸。
冬陽童年駱駝隊(代序)
惠安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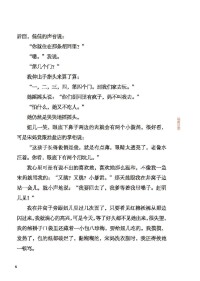
城南舊事插圖本
驢打滾兒
爸爸的花兒落了
後記
它們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寫著它們的時候,人物卻不斷地湧現在我的眼前:斜著嘴笑的蘭姨娘,騎著小驢回老家的宋媽,不理我們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樹衚衕的瘋女人,井邊的小伴侶,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兒。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舊日京華的所在地。父親好動到愛搬家的程度,綠衣的郵差是報告哪裡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們住過的椿樹衚衕、帘子衚衕、虎坊橋、梁家園,儘是城南風光。
——林海音
童年是不易寫的主題。由於兒童對人生認識有限,童年的回憶容易陷入情感豐富而內容貧乏的困境。林海音能夠成功地寫下她的童年且使之永恆,是由於她選材和敘述有極高的契合。
林海音的文筆最善寫動作和聲音,而她又從不濫用渲染,不多用長句,淡淡幾筆,情景立現。因此看似簡單的回憶,卻能深深地感動人。有了這樣的核心,這些童年的舊事可以移植到其他非特定的時空里去,成為許多人共同的回憶了。——齊邦媛
上海是張愛玲的,北京是林海音的。——余光中
Part 1:
“你要聽什麼故事兒?”
“你弟弟的,你的。”
![城南舊事[青島出版社插圖本]](https://i1.twwiki.net/cover/w200/m9/0/m901e5721f1e271b974148597f66de2db.jpg)
城南舊事[青島出版社插圖本]
“英子。”
“英子,英子,”他輕輕地念著,“名兒好聽。在學堂考第幾?”
“第十二名。”
“這麼聰明的學生才考十二名?應當考第一呀!準是貪玩兒分了你的心。”
我笑了,他怎麼知道我貪玩兒?我怎麼能夠不玩兒呢!
他又接著說:
“我就是小時候貪玩兒,書也沒念成,後悔也來不及了。我兄弟,那可是個好學生,年年考第一,有志氣。他說,他長大畢了業,還要飄洋過海去念書。我的天老爺,就憑我這沒出息的哥哥,什麼能耐也沒有,哪兒供得起呀!奔窩頭,我們娘兒仨,還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呢!唉!”他嘆了口氣,
“走到這一步,也是事非得已。小妹妹,明白我的話嗎?”
我似懂,又不懂,只是直著眼看他。他的眼角有一堆眼屎,眼睛紅紅的,好像昨天沒睡覺,又像哭過似的。
“我那瞎老娘是為了我沒出息哭瞎的,她現在就知道我把家當花光了,改邪歸正做小買賣,她不知道我別的。我那一心啃書本的弟弟,更拿我當個好哥哥。可不是,我供弟弟念書,一心要供到讓他飄洋過海去念書,我不是個好人嗎?小英子,你說我是好人,壞人?嗯?”
好人,壞人,這是我最沒有辦法分清楚的事,怎麼他也來問我呢?我搖搖頭。
“不是好人?”他瞪起眼,指著自己的鼻子。
我還是搖搖頭。
“不是壞人?”他笑了,眼淚從眼屎後面流出來。
“我不懂什麼好人,壞人,人太多了,很難分。”我抬頭看看天,忽然想起來了。“你分得清海跟天嗎?我們有一課書,我念給你聽。”
我就背起《我們看海去》那課書,我一句一句慢慢地念,他斜著頭仔細地聽。我念一句,他便點頭“嗯”一聲。念完了,我說:
“金紅的太陽是從藍色的大海升上來的嗎?可是它也從藍色的天空升上來呀?我分不出海跟天,我分不出好人跟壞人。”
“對,”他點點頭很贊成我,“小妹妹,你的頭腦好極了,將來總有一天你分得清這些。將來,等我那兄弟要坐大輪船去外國念書的時候,咱們給他送行去,就可以看見大海了,看它跟天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看海去!我們看海去!”我高興得又念起來。
![城南舊事[青島出版社插圖本]](https://i1.twwiki.net/cover/w200/mc/b/mcb3b49cfbf8f991b1c945f79bfa9de87.jpg)
城南舊事[青島出版社插圖本]
“金紅的太陽,從海上升起來……”
我一句句教他念,他也很喜歡這課書了,他說:
“小妹妹,我一定忘不了你,我的心事跟別人沒說過,就連我兄弟算上。”
Part 2:
我含著眼淚,大大地倒抽了一口氣,為的不讓我自己哭出來,我揪揪秀貞褲腿叫她:
“秀貞!秀貞!”
她停止了哭聲,滿臉淚蹲下來,摟著我,把頭埋在我的前胸擦來擦去,用我的綿綿軟軟的背心,擦乾了她的淚,然後她仰起頭來看看我笑了,我伸出手去調順她揉亂的劉海兒,不由得說:
“我喜歡你,秀貞。”
秀貞沒有說什麼,吸溜著鼻涕站起來。天氣暖和了,她也不穿綁腿棉褲了,現在穿的是一條肥肥的散腿褲。她的腿很瘦嗎?怎麼風一吹那褲子,顯得那麼晃蕩。她渾身都瘦,剛才蹲下來伏在我的胸前時,我看那塊后脊背,平板兒似的。
秀貞拉著我的手說:
“屋裡去,幫著拾掇拾掇。”
小跨院里只有這麼兩間小房,門一推吱吱扭扭的一串尖響,那聲音不好聽,好像有一根刺扎在心上。從太陽地里走進這陰暗的屋裡來,怪涼的。外屋裡,整整齊齊地擺著書桌,椅子,書架,上面滿是灰土,我心想,應該叫我們宋媽來給撣撣,準保揚起滿屋子的灰。爸爸常常對媽說,為什麼宋媽不用濕布擦,這樣大撣一陣,等一會兒,灰塵不是又落回原來的地方了嗎?但是媽媽總請爸爸不要多嘴,她說這是北京規矩。
走進裡屋去,房間更小一點,只擺了一張床、一個茶几。床上有一口皮箱,秀貞把箱子打開來,從裡面拿出一件大棉袍,我爸爸也有,是男人的。秀貞把大棉袍抱在胸前,自言自語地說:
“該翻翻添點棉花了。”
她把大棉袍抱出院子去曬,我也跟了去。她進來,我也跟進來。她叫我和她把箱子抬到院子太陽底下曬,裡面只有一雙手套、一頂呢帽和幾件舊內衣。她很仔細地把這幾件零碎衣物攤開來,並且拿起一件條子花紋的褂子對我說:
“我瞧這件褂子只能給小桂子做夾襖裡子了。”
“可不是,”我翻開了我的夾襖里給秀貞看:“這也是用我爸爸的舊衣服改的。”
“你也是用你爸爸的?你怎麼知道這衣服就是小桂子她爹的?”秀貞微笑著瞪眼問我,她那樣子很高興,她高興我就高興,可是我怎麼會知道這是小桂子她爹的?她問得我答不出,我斜著頭笑了,她逗著我的下巴還是問:
“說呀!”
我們倆這時是蹲在箱子旁,我看著她的臉,劉海兒被風吹倒在一邊,她好像一個什麼人,我卻想不出。我回答她說:
“我猜的。那麼——”我又低聲地問她:“我管小桂子她爹叫什麼呀?”
“叫叔叔呀!”
“我已經有叔叔了。”
“叔叔還嫌多?叫他思康叔叔好了,他排行第三,叫他三叔也行。”
“思康三叔,”我嘴裡念著,“他幾點鐘回家?”
“他呀,”秀貞忽然站起來,緊皺著眉毛斜起頭想,想了好一會兒才說:“快了。走了有個把月了。”
說著她又走進屋,我也跟進去,弄這弄那,又跟出來,搬這搬那,這樣跟出跟進忙得好高興。秀貞的臉這時粉嘟嘟的了,鼻頭兩邊也抹了灰土,鼻子尖和嘴唇上邊滲著小小的汗珠,這樣的臉看起來真好看。
秀貞用袖子抹著她鼻子上的汗,對我說:“英子,給我打盆水來會不會?屋裡要擦擦。”
我連忙說:
“會,會。”
跨院的房子原和門房是在一溜沿的,跨院多了一個門就是了,水缸和盆就放在門房的房檐下。我掀開水缸的蓋子,一勺勺地往臉盆里舀水,聽見屋裡有人和秀貞的媽說話:
“姑娘這程子可好點了嗎?”
“唉!別提了,這程子又鬧了,年年開了春就得鬧些日子,這兩天就是哭一陣子笑一陣子的,可怎麼好!真是……”
“這路毛病就是春天犯得凶。”
我端了一盆水,連晃連灑,潑了我自己一身水,到了跨院屋裡,也就剩不多了。把盆放在椅子上,忽然不知哪兒飄來炒菜香,我聞著這味兒想起了一件事,便對秀貞說:
“我要回家了。”
秀貞沒聽見,只管在抽屜里翻東西。我是想起回家吃完飯,還要到橫衚衕去等妞兒,昨天約好了的。
又涼又濕的褲子,貼在我的腿上,一進門媽媽就罵了:
![城南舊事[青島出版社插圖本]](https://i1.twwiki.net/cover/w200/m2/6/m2661a22cbb12e3bbf344cbc6c235dd71.jpg)
城南舊事[青島出版社插圖本]
“還早呢,急什麼。”
“不送進學堂,她滿街跑,我看不住她。”
“不聽話就打!”爸的口氣好像很兇,但是隨後卻轉過臉來向我笑笑,原來是嚇我呢!他又說:“英子上學的事,等她叔叔來再對他說,由他去管吧!”
吃完飯我到橫衚衕去接了妞兒來,天氣不冷了,我和妞兒到空閑著的西廂房裡玩,那裡堆著拆下來的爐子、煙筒,不用的桌椅和床鋪。一隻破藤箱子里,養了最近買的幾隻剛孵出來的小油雞,那柔軟的小黃絨毛太好玩了,我和妞兒蹲著玩弄箱里的幾隻小油雞。看小雞啄米吃,總是吃,總是吃,怎麼都不停啊!
小雞吃不夠,我們可是看夠了,蓋上藤箱,我們站起來玩別的。拿兩個制錢穿在一根細繩子上,手提著,我們玩踢制錢。每一踢,兩個制錢打在鞋幫上“嗒嗒”地響。妞兒踢時腰一扭一扭的,顯得那麼嬌。
這一下午玩得好快樂,如果不是又到了妞兒吊嗓子的時候,我們不知要玩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