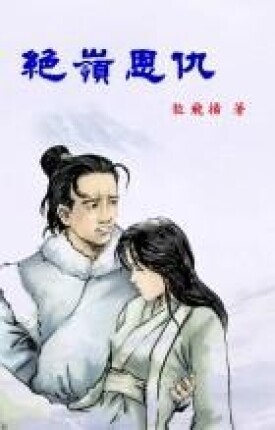敖飛揚
敖飛揚
敖飛揚原名劉惠軍,在香港出生及接受教育。現任香港小說網網站版主、香港小說網出版社社長。 1996年秋季因病退休,並開始業餘小說寫作。
1999年 10月,以“敖飛揚”為筆名在台灣(大梁出版社)出版長篇武俠小說一套四冊《魔劍傳說》。
2000年10月,以“敖飛揚”筆名在香港(高碧有限公司)出版長篇武俠小說一套四冊《魔劍傳說》。
2000年10月,以“張華”筆名在香港(當代文藝出版社)出版長篇文藝愛情小說一冊《宜昌的雪》。
2002年4月,以“敖飛揚”筆名與香港武俠漫畫家合作,在香港(創慧文化出版社)出版短篇武俠插畫小說一冊《小狂兒》。
2003年1月,以“敖飛揚”筆名在台灣(角色扮演出版社)出版長篇武俠小說一套兩冊《如來佛掌》。
2003年4月起,在香港成立出版社“香港小說網”,與朋友們合作出版武俠小說集《我們筆下的武林》及《我們筆下的武林2》,並以“敖飛揚”筆名出版個人武俠小說《赤煉鷹王》、《絕嶺恩仇》、《正義風雲錄》、《武林爭霸戰》、《熱血丹心》、《飛揚的武俠世界》、《飛揚的武俠世界2》、《飛揚的武俠世界3》、靈異小說《生死約》,並以《張華》筆名出版愛情小說《渴望》及工具書《推銷員基本法》。
1998年起,以“敖飛揚”及“張華”筆名在中、港多家小說雜誌如香港《當代文藝》雙月刊、香港《年青人雙周報》半月刊、香港《武俠世界》周刊、中國上海《大俠與名探》季刊、中國武漢《今古傳奇武俠版》期刊、中國廣州《武俠世界》周刊發表十多個長、中、短篇(包括武俠小說、文藝小說及散文)作品。
孤身走江湖:敖飛揚
文:鄧炯榕 Nico .
武林中人皆知新派江湖五絕為金庸、古龍、梁羽生、溫瑞安及黃易,五大名家自成一派叱吒風雲萬人迷。他們推波助瀾使武俠熱潮翻雲覆雨。然則幾十個寒暑消逝,五大名家前後封筆仙游歸隱,江湖霎時風平浪靜。後起之秀頓感前路茫茫無所適從,武俠狂熱份子反而要比刀光劍影的日子付出更多的氣力,才能找到一條登上華山論劍之路。孤身上路才發現沒有人的江湖原來更可怕,只因一切都殺人於無形。
拜訪武俠小說作家敖飛揚當日遇上颱風明珠襲港,聽著他數說今天寫武俠小說的血淚故事,配合窗外風聲颼颼山雨欲來的背景音樂,為此番江湖對談增添幾分凄楚的味道。
[武俠上網]
敖飛揚是近十年興起的新一代武俠小說作家,可算是出道於武俠熱潮飄渺時。在兩岸三地正在撤離這個江湖的尾聲,敖飛揚還在努力地尋找出路,雖不至於是上山下海尋求天山雪蓮,卻足以令人筋疲力盡要回家閉關。兜兜再轉轉,最後敖飛揚決定吧武俠上網,結果另闢了一片新天地。
「我在1996年尾開始寫第一個武俠小說,1997年初完成了一部份後便投稿去《武俠世界》雜誌,但《武俠世界》沒有刊登,我打電話給他們的社長沈西城,問他有沒有收到我的稿,為甚麼不刊登?他就跟我說:『細路,你咁寫野唔系可得呀。』之後他就教了我一段時間,我開始跟著來改,終於我改好之後,他們就刊登了出來。」在報紙連載已經銷聲匿跡的今天,武俠雜誌尚且為作者保留一口真氣。可是在刊登過後,除了稿費袋袋平安之外,似乎不會再有下文。剛好當時敖飛揚的弟弟正在搞網頁生意,近水樓台順便把他的武俠小說UPLOAD上網,在虛擬世界展開另一段江湖奇緣。
「我想把那個故事放在網上,就算不能出書也會有多些人看。後來,在網路上我認識到台灣一些與我有類似經歷的人,透過其中一個網友《莫愁兄》的介紹,我把那個故事交給台灣一間叫《大梁》的出版社,結果就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魔劍傳說》。但因為當時我只完成了四份之一,見有人願意幫我出書,便立即把它寫完。年半後,我終於順利完成整部小說,1999年底,一套四冊的《魔劍傳說》才正式在台灣面世。」敖飛揚在台灣出書的故事很快就在網上流傳開去,其他網友見到網上的小說原來有機會出版成書,亦紛紛效發他開始將武俠小說上網,亦有很多人把自己的作品頭稿給我敖飛揚的網站,慢慢就形成今天這個由敖飛揚主持的《香港小說網》。
「我是第一個在香港網路寫作而能在台灣出書的香港武俠小說作者,整件事可以說是因緣際會。我在台灣出完書後,香港(高碧出版社)立即也有人來找我出了香港版,香港出完之後,大陸就有人幫我翻版。哈哈。不過,自從台灣的傳統武俠出版業開始萎縮後,就沒有人再幫我出了。後來的作品都是我自己掏錢出版的,我自己也順道成立了自資出版公司,並以《香港小說網》為名。」
[俠客與博客]
率先投身網路洪流以為佔盡先機,站在那個完全赤裸公開的平台,敖飛揚其實還念念不忘書本的重量。「我始終覺得拿著一本書比上網看書好,我當時決定把文章放上網只是出於無可耐奈何,因為除了《武俠世界》願意刊登之外,我已經無其他辦法投稿給其他出版社。當初我把我的小說寄給香港所有有出版小說的出版社,大概有四、五十間,卻沒有任何一間覆過我。我覺得很無意思,所以才會放上網。」走投無路把心一橫,結果柳暗花明,就像張無忌跳落山崖跌入崑崙仙境練成九陽神功。
可是,小說中仙境不會變,網路世界卻爭分奪秒幻化百千。文字發布由以前FORUM變為現在人人都寫BLOG,當身邊任何一個人都成為部落格博客,敖飛揚這位第一代的網上人卻不以為焉,並沒有參與其中、不上前湊湊熱鬧。「現在我寫好一個故事就會立即投稿給《武俠世界》,也沒有時間把它放上網,或寫BLOG。除非是徇眾要求,加上那個故事又已經在《武俠世界》刊登過,我才會把它放上網公開給大家看。不過我很少會這樣做,因為我的網站已經給很多大陸的其他網站CAPTURE了。即是網址是別人的,裡面所有的內容卻是我的,我UPDATE十萬字,他就會立即自動跟著UPDATE。但正因如此,在大陸反而很多人知道我的名字,特別是上網看書的人。所以說是有好可有壞。」
對於一個作者把作品發表給讀者看,網路無疑是最方便直接的方法,但同樣也面對著被人抄襲的風險。敖飛揚手上那套大陸版《魔劍傳說》,相信也是被人從網上抄出來翻版。幸好這本書的翻版商算是有良心,肯用回他的名字出版他的書。而隨著網路的發展,網上生活愈來愈多元化,真正上網看小說的人亦逐漸減少了。
「我比較幸運,當初上網的選擇還不多,我把小說放上網真的有人看,他們有些還會寄EMAIL給我意見。但這幾年真的少了,現在的人多是上網看MV、看電影、交友、CHATROOM、MSN、或者BLOG,沒有人有耐性看你作的故事,因為名人明星寫的BLOG都有排看。當網上可以選擇的內容豐富了,小說自然邊緣化。就算有人寫,通常也是一些未完成正在連載的故事,很少人將我這樣吧整個故事放上去。」
敖飛揚表示,《香港小說網》起初有一半投稿的是香港作者,另一半是台灣人及大陸人,而現在大陸作者已經佔了七成多,台灣的佔了兩成,香港的只有不足一成。因為他堅持作者要把一個故事完成才交給他,無論長到50萬字,或者短到500字,總之一定要完整才會放上網。
「不過,也不是沒人會寫小說,尤其是現在BLOG這樣流行,我估計由學生開始計算,起碼有兩、三萬人會寫小說,只是在這兩、三萬人當中真正能夠完成一部數萬字以上長篇作品的,應該不會多過兩千人;而這兩千人當中,可以見得下人的應在不會超過五百人;而這五百人裡面,有機會或者夠膽自己出書的應該不會超過一百人。」
[情意結]
成長於七十年代的敖飛揚,正值武俠小說的黃金歲月,很自然就會跟武俠結緣走上江湖路。不過,原來敖飛揚第一次迷上的並不是武俠小說,而是粵語長片。「對我影響最大的其實是諸葛青雲寫的《奪魂旗》及卧龍生的《天劍絕刀》。《奪魂旗》就是以前粵語殘片那個石堅蒙住塊面拿著支旗殺人的那套,我的《魔劍傳說》有些角色的造型也是找石堅借鏡的。《天劍絕刀》則是陳寶珠與蕭芳芳那套。還有,我們這一代寫武俠小說的人,未看過《如來神掌》一定會被人噓。《如來神掌》的影響力都幾大,我認識的港澳武俠小說作者中,很多個也是因為看《如來神掌》這套電影而投身江湖。我們小時候就是看這些武俠電影大的,所以才建立了這份對武俠的情意。」
敖飛揚十歲八歲的時候就是看這些電影,之後就有李小龍及邵氏的電影:「《獨臂刀》、《十三太保》等,我們小時候便扮大俠來玩,玩玩下長大了才看小說,看看下才開始自己寫。通常喜歡寫武俠小說的人都是這樣長大的,那時候有很多武俠的媒體浸著我們。現在後生的人應該是看漫畫吧,《中華英雄》、《風雲》、《小流氓》等,不過現在的漫畫都拖得太長,我十幾歲的時候,十來歲的王小虎在打,現在我四十五歲,仍是二十歲的王小虎還在打,王小龍也死了兩次。哈哈。現在的電視都沒有武俠劇,全是歷史劇來的,台灣的武俠劇更加不知所謂。所以,現在新一代的人寫武俠,條件是差了,因為沒有以前那樣好的武俠氣氛去充實你的想像力。」
在眾多武俠小說人物中,敖飛揚最喜歡金庸《連城訣》里的丁典。「丁典是一個有情有義有智慧又勇敢冷靜決斷、應該狠的時候狠、應該溫柔的時候溫柔的人。雖然他是個悲劇人物,但我的確很喜歡他。還有早期的令狐沖,即是未失戀之前的令狐沖,瀟灑有智慧,正義又有點陰濕,他做的事是正義,但用的手段是陰濕,好聽點是不拘小節。老實說,我自己寫的人物,很多時也是參照丁典和令狐沖。但我的書裡面永遠不會有郭靖,永遠不會有楊過。女角方面比較少喜歡的,古龍寫的女主角大部份都是淫婦。嗯,也有一個喜歡的,叫蘇櫻,喜歡她的聰明和堅持,金庸寫不到這種角色,金庸寫的人物太過經典,太過唔似真人。」
「我還喜歡古龍的一套小說叫《歡樂英雄》,我次次看都會感動落淚。我很喜歡裡面的王動這個角色,其他兩個角色郭大路及燕七也不錯。不過這個故事寫得不太真實,真實的還是丁典最喜歡。《多情劍客無情劍》里的阿飛也不錯,還有《邊城浪子》的傅紅雪,不過古龍小說里的人物大多都有缺陷,沒有金庸的完整。」
由小學時開始,敖飛揚看了廿多年武俠小說,七十年代那時的武俠小說差不多都看過。「以前都是看金庸、古龍、梁羽生、卧龍生、柳殘陽等等,看完之後,很自然就會很想去寫,因為每個人對正義、正道、人生道理都會有自己的看法。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什麼不公平、憤怒、不滿的事,慢慢就會把這些事代入小說中,我的第一個故事《魔劍傳說》就是這樣寫成的。這個故事我想了十年,廿年前我做SALES的時候見盡人面,之後就將現實中遇到的偽君子真小人放在小說里,現實中法律不能制裁這些壞人,在小說中我則可以一刀把他殺死。所以寫小說是一個很好的發洩方法,我不喜歡李柱銘,便可以將他化入小說里;不喜歡董建華,我又將他放入小說去。在你的故事裡,你可以打他、斬他,任由你控制,好過癮!」
「你可以想像到,放在網上有讀者追住來看,寫完《武俠世界》又會登,雖然他們並不是太普及,但都有幾千個讀者,這是很令人興奮的。我想,所有有看小說習慣的人,心裡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故事,都會有自己落筆寫的衝動,只是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及勇氣去寫。喜歡看漫畫的人,看得多也會自己畫吧。當然,有沒有勇氣寫出來?你有沒有耐性吧故事完成?你寫出來的故事好不好看?這是另一回事。」
[投奔怒海]
在1990年,敖飛揚曾經患上鼻咽癌,原因的一半是遺傳,一半是他以前做SALES的時候吸了太多二手煙及小時候食得太多鹹魚鹹蛋梅菜之故,幸好現在已經康復。之後他還打了五、六年工,但發覺身體愈來愈差才退休在家裡照顧剛上小學的女兒和年邁的外母。當他沒工作後,那個想了十年的故事便來了。可惜當時武俠小說熱已經退卻,當台灣也停止出版傳統武俠小說的時候,像他這樣喜歡武俠小說的作者,忽然都變了滄海遺珠失去所有依靠,而他就憑著心中一股豪情壯志及不服氣的心態,毅然自資搞出版社孤身向怒海投奔。
「像我這樣的人,真的愛寫武俠小說愛到顛。出版一本書要二萬五,一次印一千本,一套書兩冊就要四萬五。四萬五齣一套書,可能收回來也不到二千元,然後全間屋都放滿回書,香港有幾多人願意做?我至今共花了廿多萬,其他人可能認為這是把錢丟到鹹水海去。但在我作為一個作者的立場看來,《香港小說網》很都人認識啊,起碼你們(號外雜誌)也來訪問我,《明周》、《香港經濟日報》也有訪問過我,《亞洲電視》也訪問過我,《香港電台》都去過兩次直播節目,雖然說我不是真的很有名,但在目前這個環境,這一點點成就也叫我可以自得其樂。是的,幾年下來我是蝕了廿多萬,但可能在很多人眼中,廿萬算得上什麼?有人食一餐飯開一支好的紅酒都可能用了四萬多了。」
「很多人都說搵食艱難,一個月萬多元的收入要養屋企有要養自己,還要拿幾萬元來出書,的確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但我覺得作為一個熱愛寫作、熱愛書的作者,這幾萬元的投資是值得付出的,這才算是對得住自己。我覺得一個作者,一生起碼要出一本書。」雖然是自己掏錢出版,但能夠擁有自己的書,的確是很多寫作人的夢想理想。敖飛揚說自己有時會到圖書館CHECK自己的書,知道自己的書的借出率並不低,便是證明了自己還有一班讀者,也知道自己雖然不致是寫得很好,但也不算是差,算是很不差了。「其實我出書的時候已經打定輸數,預計圖書館買二十本,街上一本也賣不出,結果現在賣了百多本,都算超標了。」
[荊棘滿途]
為了堅持自己的心愿,敖飛揚的確是奮不顧身,付上畢生積蓄去圓一個武俠夢。作為一個過來人,敖飛揚深深體會到今天閱讀氣氛正不斷淡然消卻,其實不只是武俠小說,人們對書的興趣都大不如前了。而弱勢的新作者群,站在利益掛帥的出版商場,除了眼甘甘作一次WINDOW SHOPPING之外,唯有搖頭嘆氣黯然離場。
「我出版第一本小說的時候寫了篇文章,批評香港人不願意提攜後輩。我是有感而發:為什麼香港人在香港寫作,卻要找台灣人幫手出書?為什麼系香港出唔到書呢?據我所知,很多出版社都不會理會新作家。寫完一個作品,你周圍投稿,人家看也不看便會落籃(即棄掉),如果你看完覺得差才落籃是一件事,連一眼也不看便會落籃,身為作者就會覺得很憤怒。」
敖飛揚認為,要提高大家對閱讀的興趣,起碼先要有些好的新作品給人看,但現在看來看去都是張小嫻、李敏、亦舒這幾個,看得多讀者都會悶。他們本本書都一樣,風格又接近,看一本等如看十本。「讀者是很需要新作者的,但當市場提供不到新作者的時候,他們沒有選擇,唯有繼續看會舊作者的書;書店又以為新作者的書賣不去而不賣,出版社又以為新作者的書賣不去而不出版,惡性循環怎會不死?所以,如果有些名牌大出版社願意提拔新人,情況就會好得多。」
的確,提拔一個新作者是一個長遠的投資,不可能一出版就賣個滿堂紅,而現在新作者式書賣得不好的話,根本不會有出第二本的機會。「這樣根本稱不上是提拔新作者,根本不是培訓人材。作者不是歌星明星,不會拍一部戲就一炮而紅,出書是第一本賣500本,第二本好些,第三本更好些,才能慢慢成名。而且,大出版社有很大的網路,他們可以幫到新作者在其他媒體如報紙、雜誌找到寫作的地盤,作者的曝光率才會高。」
現在的情況反而是等作者成了名,出版社才高價挖角,當普遍都擁有這種想法時,大家便不願意先行踏出第一步,雖說在商業的角落看無疑是一門策略,但在這樣的氛圍下,新作者便唯有自求多福了。「我的《香港小說網》網站早期有很多人投稿,很多人寫得很好,但他們投一次投兩次,以後就沒有寫了。因為縱使他們在網路上寫,仍然找不到出路,沒有人願意為他們出書,由於他們都要生活,寫作又不能維生的時候,便只可以當興趣,而當寫完還要自己掏錢出書的時候,怎會不失去動力?」
除了被出版社忽視之外,現在的世界物質豐富了也帶來很大的影響。「好似我個女,我寫的武俠小說她都不會看,年輕人通常都上網打機,在MSN吹水,去YOUTUBE睇手機短片,很少人會看書。現在人們太著重享樂主義,精神生活反而薄弱了。你看台灣那些玄幻書大熱,這些書可以打到去異次元空間,上太空落地獄都無問題,就是因為看這類書不需用腦,我們寫傳統武俠小說的則不同,始終需要著重故事內容起承轉合,要有角色心理要有事故發生,有時還有一些哲學成份,於現在的人看來,可能會覺得悶。而且現在新一代寫小說的人,他們的文章也寫得不太深入,多數都是寫些好表面的文章出來,好似寫了一套徐克的電影出來,砰砰碰碰打一輪,啊,睇完!等如你看徐克的電影跟看李安的不同,徐克的電影里的角色說話快一陪,動作快兩陪半,而且廢話特別多,一邊打一邊說很多廢話。但現在的年輕人卻很喜歡看這類型,不需要用腦的,總之一開始就刺激刺激刺激,之後就睇完。」
過於追求觀感上的刺激,內容反而成了次要,這樣的文字創作有什麼辦法不被邊緣化?照敖飛揚說,武俠小說尚算是通俗讀物,寫文學的則死得更快。「寫作在香港可以說已經死,香港太勢利,太過現實,太過短視。你看我在台灣出了套小說,香港就立即有人來找我,你說現實不現實?」
[復興武林]
依照敖飛揚不服輸的性格,他當然曾經想過儘力去復興武俠小說的熱潮。幾年前,他就集合了一班新一代的港澳武俠作家們,一人出一些錢出版《我們筆下的武林》一書,希望可以藉此重振江湖。「我們初初都有很大的理想,希望可以把武俠小說做旺。結果現在我們都失望,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自己的定位,我們只能為自己的興趣、為我們的理想努力,做好自己本份,對得住自己就算了。出面市場好不好唔緊要,書賣得好不好唔緊要,起碼圖書館會幫我們買幾十本,而且這些書在未來兩年的借出率起碼有八成,所以我知道一定有人在看,只不過他們都去了圖書館借。」
「我們的書,除了大眾、三聯會擺之外,商務都沒有了,二樓書店更加沒有。二樓書店當初都是很有理想的,他們會為新作者找出路,把他們的書擺出來賣,以前的二樓書店都是這樣的,像洪葉等等。但有理想都要有實力才行,洪葉現在也倒閉了。我們也有理想,但沒有實力,既然知道自己沒有實力,便唯有將規範降低。OK,現在我們出書是為了自得其樂,我們純粹為自己的興趣而創作,直到有一日,失去興趣就算了。」
《我們筆下的武林》初初共有八位武俠小說作者一起籌辦,出了兩集。但寫寫下,當中有些作者意興闌珊地退出了,現在只剩下四個,而第三集的《我們筆下的武林》也胎死腹中。「我相信剩下的這四個人會繼續堅持的,不過已經很疏了,以前我們可能一年出三、四本書,現在可能三、四年才出一本,因為真的很窮了。」
如果說要振興武俠小說,就需要有實力有名氣的人出來帶頭,那麼誰可擔此重任?敖飛揚認為只要金庸可以出一句聲就可以了:「你最近有沒有看蘇民峰在有線電視的『峰生水起精讀班』節目?蘇民峰話收徒弟,嘩!市面上的羅盤呀、堪輿術數書呀馬上大賣。如果有一個像金庸這樣的大師級走出來,不要說收徒弟,只說收徒孫,或者搞個比賽,我想最少有幾百人應聲參加,全香港精英盡出。加上傳媒炒作,全世界的華人都注目,武俠小說即刻翻生呀!其實金庸有今日的地位,也不用出面,只要出句聲呼籲一下,已經有很大的影響力。如果說要振興武俠小說,金庸是很關鍵的人,他肯出聲就可以了。」
「大約在1999年到2000年的時候,曾經有很多文人出來說:香港寫作的人愈來愈少,香港的出版氣氛愈來愈差,讀者愈來愈少,然後又說後繼無人呀等等,很多名家都出來說這些晦氣話,在我們聽來實在很難受。不是我們不寫,而是你們不給我們出版的機會。我幸運些,我硬頸,你不給我出版機會嗎?我找台灣出,連台灣也不能出的時候,我自己掏錢出。這是因為我硬頸,但並不是人人都好似我這樣硬頸,也不是人人可以拿幾萬元出來出書。我想,有很多人寫寫下就無心機了,算了,不寫了,但當中可能有很多人是比我寫得好的。我覺得這是很浪費,很可惜。出版社是一門生意,他們不幫我們出書是理所當然,但那些名家大師請不要出來說那些晦氣話,我們聽到真的很難受,因為我們曾經努力過,但由於我們不夠名氣,不夠錢才會失敗。」
現在敖飛揚寫武俠小說也是從興趣出發,動力來自寫成後可在《武俠世界》雜誌刊登。然而,香港就只剩下《武俠世界》這一本唯一的武俠雜誌,敖飛揚說,如果連《武俠世界》都結束的話,他可能也會就此封筆。
跟他談了近三個小時,只有一份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又如何的無可奈何。
面對武俠的式微,寫小說的人該何去何從?真希望尚有下回可以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