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克里瑪
伊凡·克里瑪
伊凡·克里瑪(Ivan Klima,1931——),捷克籍猶太裔作家。
1931年9月14日,伊凡·克里瑪出生於布拉格一個猶太人家庭,10歲時隨父母關進納粹集中營,直到二戰結束被解救。1956年大學畢業后在一家出版社做編輯,業餘創作小說和劇本,1960年開始發表作品。其主要作品有《布拉格精神》、《一日情人》、《沒有聖人,沒有天使》等,曾獲得捷克共和國傑出貢獻獎章與“卡夫卡文學獎”,與瓦茨拉夫·哈維爾、米蘭·昆德拉並稱為“捷克文壇三駕馬車”。

伊凡·克里瑪
1939年,納粹佔領捷克,接下來的兩年中,克里瑪被禁止去上學,全家被迫穿上黃色六芒星,開始得知自己祖上具有猶太血統。
1941年,10歲的伊凡·克里瑪隨父母被關進納粹設立的泰里茨集中營,在那裡度過三年時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親眼目睹了自己祖父母的死亡,所有兒童時代的同伴都死於毒氣室。
1945年,蘇軍解放集中營,克里瑪及其家人均倖存。
1956年,克里瑪畢業於布拉格大學文學語言系,在一家出版社任編輯,同時開始小說和劇本的創作。
1958年,克里瑪迎娶了心理治療師海倫娜,他們生了兩個孩子邁克和漢娜,邁克是位報社編輯,漢娜是位藝術家。
1960 年,開始發表小說與戲劇。
1964 至 1968 年期間,伊凡·克里瑪主編捷克作家聯盟(the Czech Writer’s Union)的刊物。

伊凡·克里瑪
1969年,伊凡·克里瑪謝絕了朋友們的勸告回到捷克,隨即失去了工作。為了生計他做過救護員、送信員、勘測員等工作,同時作為自由撰稿人寫作。有20年時間他的作品在捷克完全遭到禁止,只能以“地下文學(薩米亞特)”的形式在讀者中流傳。克里瑪經常被警察總局叫去談話,不過從來沒有被逮捕。
1989 年,發生的“天鵝絨革命”使伊凡·克里瑪的作品重新得以出版,此後他開始擔任國際筆會中心捷克分會主席,后改任副主席。他堅決地拒絕進入議會,拒絕任何行政職務,只當作家。
2002年,克里瑪獲得捷克共和國傑出貢獻獎章,此後又獲得“卡夫卡文學獎”,成為該獎的首位捷克藉獲獎者。
2009年,出版回憶錄《我的瘋狂世紀》。
| 作品名稱 | 作品類型 | 創作時間 |
| 《我快樂的早晨》 | 小說 | 1985年 |
| 《我的初戀》 | 短篇小說集 | 1986年 |
| 《我的金飯碗》 | 小說 | 1992年 |
|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 | 小說 | 1994年 |
| 《布拉格精神》 | 小說 | 1994年 |
| 《終極親密》 | 小說 | 1997年 |
| 《一日情人》 | 短篇小說集 | 1999年 |
| 《沒有聖人,沒有天使》 | 小說 | 1999年 |
| 《我的瘋狂世紀》 | 傳記 | 2003年 |
以上參考

伊凡·克里瑪
克里瑪的作品有兩個基本點:情慾和死亡。情慾是宣洩口,是真實生活和生活意義的具體體現,也是調劑品。他小說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有無數個情人,而且基本上一見面就做愛,做愛成為情人對話的特殊方式。死亡則是前提,是背景,是潛在的敵手,是壓艙物,也是悲觀或樂觀的最好理由,甚至還涉及到克里瑪最初的寫作動機:用創作來抗衡死亡,許多思考也都圍繞著這一前提展開。情慾與死亡兩個點恰恰最能反映人的微妙心理和精神風貌,它們既互相依賴、互相襯托,又互相抵觸、互相瓦解,形成一種張力。

伊凡·克里瑪
克里瑪早期“地下文學(薩米亞特)”最重要的價值是有勇氣衝破檢查制度的高牆,表現出文學應有的尊嚴,即對人類自由精神的維護。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的幾部長篇小說,如《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仍然是一部關於逃跑的小說,邊界的主題再次出現。故事始於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通過穿插回憶,將極權體制下的生活與轉型后的生活聯繫在一起。由於每天都要應付被監視的生活,缺乏思考的時間,“地下文學(薩米亞特)”時期克里瑪的作品大都是短篇小說,採用的多是新聞報道式的記事手法,似乎只是想要如實記錄下尋常遭遇,作為時代的見證。但由於太過於對自我日常生活的寫實,因而也缺乏有深度的刻畫。只是在捷克制度轉型后,克里瑪才有了充裕的時間和距離感,去思考制度與人性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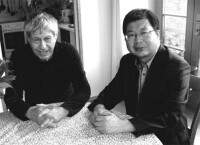
伊凡·克里瑪
克里瑪不像昆德拉那樣講究作品的結構、形式和哲學意味,不像哈維爾那樣注重文學的使命、職責和鬥爭性,也不像赫拉巴爾那樣追求手法的創新和前衛;他顯然更看重質樸和自然,要在質樸和自然中貼近世界、生活和人性的本質。克里瑪的小說手法簡樸,敘事從容,語調平靜,講述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整體上看,作品似乎都很平淡,但平淡得很有韻味,是一種大劫大難、大徹大悟后的樸實、自然和平靜。克里瑪總是千方百計地隱藏自己,他誠懇地給讀者講幾個故事或一段生活,然後完全由讀者自己去回味、去琢磨。他能從第一刻就消除同讀者之間的距離,作品無疑更加接近生活和世界的原貌。他筆下的人物一般都有極強的幽默感,有極強的忍耐力,喜歡尋歡作樂又不失善良的本性。而這些正是典型的捷克民族特性。沒有這樣的特性,一個弱小民族在長期的磨難中,恐怕早就消亡了。克里瑪相信捷克民族早就練就了一套應付生存的超級本領。
| 榮譽類 |
| ▪ 2002 捷克共和國傑出貢獻獎章(獲獎) |
| 文學類 |
| ▪ 2002 卡夫卡文學獎(獲獎) |
以上參考
一顆鮮為西方賞識的文學瑰寶……一位巔峰時期的捷克大師。——《波士頓環球報》

伊凡·克里瑪
克里瑪先生所塑造的角色如此真實可信——充滿瑕疵、脆弱、迷茫、生活化。在他們取得真知灼見或終於能夠溝通彼此那一刻,我們由衷感到意義非凡。就像契訶夫,作家克里瑪先生有能力向我們展示平凡生活的不凡之處。——《華盛頓時報》
不輸於任何人,克里瑪重構了二十一世紀小說。巧妙結合了散文和小說的長處,他創造出具有莎劇人物般影響深遠的角色……《沒有聖人,沒有天使》是一部並不張揚的傑作。——湯姆·戴夫林《普羅維登斯報》
從壓抑舊制度下的生活,到自由新紀元下的問題和令人失望之處,克里瑪筆下的人物演繹貫穿了整個區間……克里瑪在探索過去的同時仍然聚焦當下。——《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