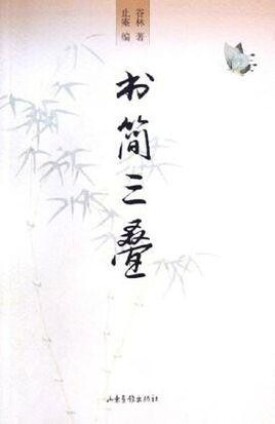書簡三疊
谷林先生所著書信
十來年間寫過不少信。偶與幾位舊友提起,都說成疊留存著。經一番分頭檢點,揀選了匯交在止庵處。經止庵的再整理,共得一四五通,計揚之水五十三通,止庵四十九通,沈勝衣四十三通。字數約計十三萬雲。
止庵寫信給我說,整理“揚之水(所存)信殊麻煩”。因信上“多不寫年月”,排比就須仔細查對。“不寫年月”的責任在我,只是揚之水收到沒加補註,以後留存又不免失序吧。
但止庵信上掉轉話頭又道:“麻煩一辭,似乎略有怨意,其實完全相反,覺得時有樂趣,好比科學發現一般。”還說列印以後,與原信“校對起來也有趣”,總結是“這幾天過得非常快活”。
前人有詩云:“老病難為樂,開眉賴故人。”又云:“得書劇談如再少。”聖陶先生更把晚歲與故人來回寫信視作“暮年上娛”。止庵蓋深會此意。這件小事如果借電話一說,豈不簡省,但像來信蘊涵的那般頓挫環盪情味必致全部消失。我讀止庵來信自然較之接聽電話高興,堅信他自述“非常快活”也非虛誑。
揚之水與我曾在國家博物館共事,卻不相識。她在司機班,我在文獻組。以後《讀書》雜誌創刊,她逢伯樂,成為該刊編輯部五朵金花之一;我則自稱只是它的“編外打雜工”,但去信提意見或偶寄補白小品,適巧歸她處置,日久乃傳聞“閣樓人語”,指說我們“知己”。鄙人預流光寵,別無勝業可言。張中行先生《負暄三話》中有她的畫像,最能傳神。
止庵以著撰豐茂,聲聞盛播,我認為其編校功德或尤在著作之上。他所校訂的整套知堂“自編文集”可供佐證。我的那本很不成器的《答客問》,承他挺身而出,加工編校,宛如“法酒調神氣,清琴入性靈”,恍然音色一新,最出望外。眼下這冊《書簡三疊》,又讓我坐享其成,他說的“非常快活”無疑是他從自身的“非常辛勤”中萌發。
至於沈勝衣則別是一奇。我讀他文字多不自報刊,幾乎悉數是他伴同手簡用“憶水舍箋”一般規格的大張素紙列印寄來。博觀深情,自是一絕。好法書名畫,每以彩色縮印於箋紙一角。對港台影劇歌詠,又獨具心眼,自稱有“聲色之好”。以後方知他聯繫廣泛多由網路,三年前曾寄我一份他收錄的《“谷林”典故》,共計七大張,統為素所未聞。新近見告已編就列年作品共得五本,首兩本下月可望出書,則無俟我在此絮叨了。
以上依照三位收信人的年齒挨個略事介紹,實皆不得要領,末后卻必須補上幾句,記下《書友》老總黃成勇栽植玉成的厚惠。他寬容我多年在報端嘵舌,還發了代我徵集書翰的啟事,陸續收到寄回來的“冷藏”,使這個漸在“淡出”的糟老漢頓悟他竟被如許和洽慈祥的同調呵護在深心之中,叫他怎樣始克盡其餘年小有報役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