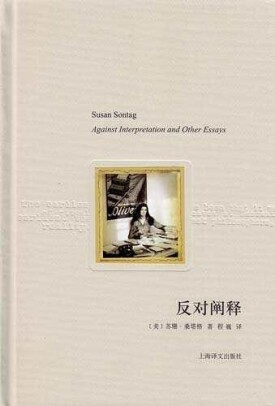反對闡釋
反對闡釋
《反對闡釋》是美國文藝評論家蘇珊·桑塔格創作的文集,該作彙集了桑塔格於1961-1965年間在《黨派評論》、《紐約書評》、《常青評論》等重要刊物上發表的26篇文章。
該作中,評論的鋒芒遍及歐美先鋒文學、戲劇、電影,集中體現了“新知識分子”“反對闡釋”與以“新感受力”重估整個文學、藝術的革命性姿態和實績。
桑塔格以一種輕鬆的語調諷刺闡釋泛濫的本質與根源,指出林林總總的闡釋不過“是以修補的方式保留那些被認為太珍貴以至不可否棄的古老文本的極端策略。”不但沒有再創造,反而使得原本就很貧瘠的世界變得更加的貧瘩。闡釋中有誤解,有重複,它是對作者本意的蒙蔽、侵犯還有掠奪。她以《沉默》為例,認為“這種方式的闡釋暴露出闡釋者對作品的不滿(有意或無意的不滿),希望以別的東西取代它。”桑塔格進一步指出,事實上,“闡釋者並沒有真的去除掉或重寫文本,而是在改動它,但他不能承認自己在這麼做。他宣稱自已通過揭示文本的真實含義,只不過使文本變得可以理解罷了。不論闡釋者對文本的改動有多大,他們都必定聲稱自己只是讀出了本來就存在於文本中的那種意義。”她認為,造成這種單一闡釋的根源是內容說,即“形式”與“內容”的劃分.並指出,“內容說”本身在今天就是這種情況,無關內容說以前是怎樣的,它在當今看來主要是一種妨礙,一種累贅,是一種精緻的或不那麼精緻的庸論。”而且, “對內容說的過分強調帶來了一個後果,即對闡釋的持續不斷、永無止境的投入。”
在剖析了闡釋的本質之後,桑塔格將其主要的批評火力集中指向了那種極度簡單化的對等式的“權威”闡釋。她明確提出“如果我反對釋義,我也不是這樣反對釋義本身,因為所有的思考都是某種釋義。我實際上是反對簡化的釋義。我也反對花巧地把意念及名詞調換作粗淺的對等。即,X其實是A,Y其實是B,z其實是c的替換。”顯然,桑塔格其實不否認藝術作品是可以被描述或闡釋的,只是應該是服務於原作而不是奪取他的位置。因此,她認為應更多關注藝術的形式,而不是其所謂的“內容”。與此相關,她還認為需要一套為形式配備的描述性的辭彙,而不是規範性的辭彙。由此,桑塔格提出“新感受力”的概念來倡導一種更加直接的,不加偽裝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並主張在欣賞藝術作品的時候,不是去理解和分析,而是去感覺。
| Ⅰ | Ⅱ | |
| 英國版自序 | 反對闡釋 | 作為受難者之典範的藝術家 |
| 致謝 | 論風格 | 西蒙娜·韋伊 |
| 加繆的《日記》 | ||
| 米歇爾·萊里斯的《男子氣概》 | ||
| 作為英雄的人類學家 | ||
| 喬治·盧卡奇的文學批評 | ||
| 薩特的《聖熱內》 | ||
| 納塔麗·薩洛特與小說 |
| Ⅲ | Ⅳ | Ⅴ |
| 尤內斯庫 | 羅貝爾·布勒松電影中的宗教風格 | 沒有內容的虔誠 |
| 論《代表》 | 戈達爾的《隨心所欲》 | 精神分析與諾曼·O·布朗的《生與死的對抗》 |
| 悲劇的消亡 | 對災難的想象 | 事件劇:一種級端並置的藝術 |
| 劇場紀事 | 傑克·史密斯的《淫奴》 | 關於“坎普”的札記 |
| 馬拉 / 薩德 / 阿爾托 | 雷乃的《慕里埃爾》 | 一種文化與新感受力 |
| 關於小說和電影的一則札記 |
桑塔格反對闡釋觀點的產生離不開美國20世紀60年代反文化的時代背景。加利福尼亞公立大學歷史學教授西奧多·羅斯扎克將“原文化”的特徵歸結為60年代發生在美國社會政治、文化領域的育年人抗議運動,並將反文化運動定義為60年代發生在美國社會的一切抗議運動,既包括校園民主運動、婦女解放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反戰和平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同性戀者權利運動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搖滾樂、性解放、吸毒、嘻皮文化,及神秘主義和自我主義的復興等方面的文化“革命”。反文化運動的展開促成了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的對立,更確切的說是主文化與反文化的對立是對現存社會秩序的不同態度的對立,主文化擁護支持現存秩序,反文化則保有抵制與對抗的態度。桑塔格所做的努力其實是在試圖為反文化的非主流闡釋的合法化尋求支持,是刻意與主流文化的對抗,不過,她所採取的路線是“革命性的”,或激進式的。她試圖從根本上對闡釋重新進行審視。
1963年,在紐約,桑塔格開始了寫作生涯。她給當時頗有影響的文藝評論雜誌《黨派評論》撰寫文章。《關於坎普的札記》一文使她一夜之間聲名鵲起。這篇隨筆與其他幾篇這個時期的文藝評論後來被收入標題為《反對闡釋》的文集,成為她最重要的著作。
從字面上來看,桑塔格似乎是闡擇人類學的當然反對者,她直言要”反對闡釋“,並試圖去除所有外加的闡釋,而回歸事物本來的樣式。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她所真正反對的並不是闡釋的行為本身。因為她承認“我們誰都無法回歸到當初在理論面前的那種天真的狀態。”換言之,她很清楚地意識到,對事物的解釋是無法免除的人類行為。事實上,她所反對的是過度闡釋,是對事物原意的漠視而強加以意義的行為。是那種簡單化的將A對等於B的武斷做法。
桑塔格的反對闡釋觀點具有鮮明的後現代性,其產生除了社會文化背景因素,還有眾多文化和理論思潮碰撞與交流的結果。可以說,“反對闡釋”的思想並不能歸於桑塔格一入名下,阿蘭·羅伯—格里耶、羅蘭·巴爾特、福柯、德里達、讓·波搞里亞等法國著名作家和理論家,都是對反對闡釋理論發生過重要影響的後現代主義大家,甚至可以說,反對闡釋理論的崛起可以一直追溯到後現代思想的先驅尼采那裡。周憲曾就桑塔格與後現代主義談到:“桑塔格堅信後現代主義開創了一種‘新感性’,她尤其從意義及其解釋角度分析了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區別。在她看來,現代主義者相信在符號表層之下隱含著某種深層意義,而後現代主義者則堅信意義就在表層,根本不存在什麼深層意義。
闡釋的產生即意味著意義的缺失,其更深的根源則是由柏拉圖開始的對於真實世界與現實世界、理性與情感、思維與肉體的區分,這種區分殖面著絕對的價值判斷會因時間的流逝而變得面目全非,也就無法找到永恆的意義。大眾生活的世界,反而變成了虛假的存在,被輕蔑的拋擲在人類理智的視野之外。對於桑塔格來說,作品的闡釋使得知識分子固執的將活生生的藝術作品拋在腦後,而在聞釋中傾注了過分的精力。更為重要的是,闡釋逐漸變成某些人獨享的權力被牢牢的控制在那些社會精英手中,普通的大眾則養成了跟隨他們指引的習慣。這種闡釋權力的佔有,產生了社會象徵領域中的統治與被統治。在極左派的知識分子看來,西方的知識分子埋頭學術研究,希圖在思想領域中展開他們的鬥爭無疑是一種失效,然而,桑塔格堅信這種鬥爭的意義,她所做的即是徹底揭穿這幻象的本質。
桑塔格在“反對闡釋”中並不是專斷的,相反卻是非常辯證的。她明確說:“我並沒有說藝術作品不可言說,不能被描述或詮釋。問題是怎樣來描述或詮釋。”闡釋不是(如許多人所設想的那樣)一種絕對的價值,不是內在於潛能這個沒有時間概念的領域的一種心理表意行為。闡釋本身必須在人類意識的一種歷史現中來加以評估。在某些文化語境中,闡釋是一種解放的行為。它是改寫和重估死去的過去的一種手段,是從死去的過去逃脫的一種手段。在另一些文化語境中,它是反動的、荒謬的、懦怯的和僵化的。桑塔格反對對文本進行簡單的、符碼對應式的單一闡釋,並且這種闡釋多是道德說教式的,尤其是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觀點,全部被當作闡釋的契機。她“呼籲批評家暫停對隱含意義、象徵形態進行急切的挖掘,並宣稱就像格特魯·斯泰因所宣稱的那樣,“玫瑰就是玫瑰”,而不是闡釋者所聞釋的那種特定的道德符碼。因此,針對“大體上是反動的和僵化的闡釋行為”,桑塔格旗幟鮮明地反對將文本的闡釋單一化。這種單一化簡直就是“闡釋”建立起了對文本的殘酷的專制統治,這種闡釋的單一化將藝術等同於道德說教或心理分析的符碼甚或別的東西。這種等問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惟一正確的”,以致於當人們面對藝術作品時,首先想到的就是藝術的“道德意義”或暗示的是什麼,忽略的恰恰就是藝術(形式)的本身。這種闡釋簡直就是對藝術的扼殺,也正是桑塔格所堅決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