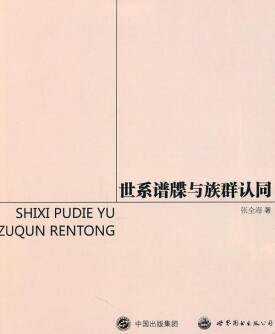族群認同
族群認同
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就是族群的身份確認,是指成員對自己所屬族群的認知和情感依附。關於族群的認同理論,最有影響的就是根基論和工具論。
在當今世界,“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日益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社會政治困境。不管在西方世界,還是在東方世界,族群的衝突和對立都變成了一個極端令人困擾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儘管形形色色思想家、學者和專家一直在絞盡腦汁地思考問題的答案,儘管大大小小的政治領袖和政治家們也在不斷地尋找各種具體的對策和解決方案,但是時至今日,甚至在可預見的將來,族群的衝突和對立非但不會變得緩和,反而有越來越惡化的趨勢。更有甚者,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族群問題往往並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同宗教、階級、意識形態等一系列其他社會政治問題糾纏在一起。族群的衝突和對立如同一個導火索,往往在一個甚至多個國家引起一種“多米諾骨牌”似的連鎖反應。它們輕則引起政治和社會動蕩,重則導致社會分裂和國家解體,甚至最終演變成為大規模的種族屠殺和血腥戰爭。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族群的衝突和對立並不是現代社會才有的現象。在前現代或傳統社會之中,諸如此類的衝突同樣是比比皆是。譬如說,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古人就已經清醒地看到了這樣一個事實:“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由此可見,族群的衝突和對立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人類社會的常態。
不過,在現代社會的情況完全不同的是,在傳統社會中,族群的衝突和對立雖然無處不在,但它本身並沒有對既定的社會政治秩序構成根本的挑戰,因此並不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對於傳統社會來說,所謂的族群認同並不是一個獨立自在的問題,在大多數時候甚至根本不構成一個問題。傳統社會相信,在族群之上,還存在著某種更高的、神聖的秩序,譬如“天”(中國)、“宇宙”(古希臘)、“上帝”(猶太教和基督教)或“真主”(伊斯蘭教)等。從政治的層面來說,帝國(或其他准帝國的政體形式)就是這種神聖秩序的具體化身。作為一個具有“差序格局”的大一統政治秩序,帝國本身容納了許多異質性的亞層次或低層次認同,諸如血緣、宗族、地域、階層、人種和族群等。在這種大一統的政治秩序中,族群之間的差異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而相對於帝國這一最高和終極的認同,包括族群在內的低層次認同也不具有多少緊迫性。
但是,在現代社會,族群認同不僅變成了一個獨立自在的問題,甚至變成了一個無法解決的致命問題。這首先是因為,構成現代社會的政治實體不再是帝國,而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民族國家的核心當然不是國家,而是民族(nation)。儘管在中文語境中,“民族”的含義同族群(ethnos)非常相近(正是這種表面的相近導致了許許多多不必要的誤解和混淆),但實際上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因為族群是自然形成的共同體,而民族則是人為的和理性建構的產物。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那句流行的行話說,民族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
關於族群的認同理論,最有影響的就是根基論和工具論。
根基論也叫原生論,代表人物是西爾斯(Edward Shils)、葛慈(Clifford Geertz)、伊薩克(Harold P. Isaacs)與克爾斯(Charles Keyes)等,認為族群認同主要來源於根基性的情感聯繫,這種族群情感紐帶是“原生的”,甚至是“自然的”。對於個人而言,根基性的情感來自親屬傳承而得的“既定資賦”(givens)。基於語言、宗教、種族、族屬和領土的“原生紐帶”是族群成員互相聯繫的因素,強調這些共同特徵是整個人類歷史上最基本的社會組織原則,而且這樣的原生紐帶存在於一切人類團體之中,並超越時空而存在。對族群成員來說,原生性的紐帶和情感是根深蒂固的和非理性的、下意識的。
工具論也叫場景論,代表人物是德斯皮斯(Leo A. Despres)、哈爾德(Gunnar Haaland)及柯恩(Abner Cohen)等。他們基本上把族群視為一種政治、社會或經濟現象,以政治與經濟資源的競爭與分配,來解釋族群的形成、維持與變遷。工具論認為族群認同是族群以個體或群體的標準特定場景的策略性反應,是在政治、經濟和其他社會權益的競爭中使用的一種工具。它強調族群認同的場景性、族群性的不穩定性和族群的成員的理性選擇,強調在個人認同上,人們有能力根據場景的變遷對族群歸屬做出理性選擇,認為認同是不確定、不穩定的,是暫時的、有彈性的,群體成員認為改換認同符合自己利益時,個體就會從這個群體加入另一個群體,政治經濟利益的追求常常引導人們的這種行為。
就族群認同理論中的根基論和工具論,中國學者對二者進行了綜合性的理解。一般認為,族群認同的產生,與其說是自覺,不如說是外人所區分的類別所致。而這種類別的創造是國家形成過程中的一個普遍特徵,更與殖民地擴張存在密切關係。族群認同是人們與不同起源和認同的人們之間互動中的產物,地理上與其他人群完全隔離的孤立的小人群是不可能構成族群的,特定個體取決於社會情景而有著一些不同的族群認同;認同既可以是自己選擇的,也可以是強加的,如政治社群對成員的歸屬感和共同目標的灌輸。族群認同並非簡單地將世界劃分為“我們”與“他們”,而是劃分為不同的層級性的、等級化的“我們”和“他們”類別。在這方面,孫九霞提出了族群認同產生的條件是族群間存在的互動關係,並提出了族群認同必須具有的要素。
如所周知,構成族群有兩大元素,一是血統,另一是以語文為核心的文化(包括歷史、文學、藝術、宗教、風俗、習慣,等等)。因此,族群認同感必須同時含有血統與文化兩種成分。單憑血統而產生的族群認同是不完善、不牢固的,對於強化族群或國家的凝聚力,也不能產生持久的、可靠的作用。
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都屬於個體對整體的認同,但是二者除此共性之外,亦有差異。
首先是認同的對象不同。族群認同的對象是“族群”。關於“族群”的內涵,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最早將其界定為“體型或習俗或兩者兼備的類似特徵,或者由於對殖民或移民的記憶而在淵源上享有共同的主觀信念的人類群體,這種信念對群體的形成至關重要,而不一定關涉客觀的血緣關係是否存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族群“是想象的共同體”。享有共同信念的人群因各自的神話、歷史、文化屬性、種族意識形態而互相區別。班頓(Banton)將族群界定為“具有共同血統與文化所構成的人群種類”。著名學者郭洪紀則認為:“族群主要建立在共同的名稱、神話、價值和風俗習慣之上,以祖先的居住地、歷史敘事、民間傳說為文化根源。它具有建基在種族、血統、語言、宗教、風俗、鄉土一類的文化要素,以及歷史傳統之上的心理情感和非政治行為。族群作為某種共同體的象徵符號,既有自己的生存空間和與之有關的傳統,包括宗教組織和神職人員,像神廟、儀式、教義等,又有懷舊母題及認同符號系統,像民族英雄、宗教領袖、效忠意識150以及草原、森林、山巒、族源地等。”
與此相對應,國家認同的對象則是“國家”。關於“國家”的內涵,西塞羅將其定義為:“國家乃人民之事業,但人民不是人們某種隨意聚合的集合體,而人民是許多人基於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結合起來的集合體。”馬克思主義在深入研究國家產生的原因及其發展變革的規律,概括了各種類型國家的特點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礎上,為國家提出了一個全面的科學的定義: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階級受一個階級控制的機器。這是列寧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觀點最全面、最準確的概括。
應該說,國家是社會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當在一個固定的領土範圍內居住著一個人民(經常是同一族群或有共同的認同感),而在這個人民中又行使著一個合法的政治權力時,便存在著國家。所謂人民,在過去,特別是在西歐,首先是指一個族群。在現代,則是指所有服從於一個主權權力的人民。它可以是一個族群,也可以包括若干族群。在國內政治的領域中,人民更多地是被定義為公民,即有權參加政治事務的人。這是一個法律政治意義上的概念。它超越了人們在經濟地位、文化、職業上的不同,使人們有了一個新的共同身份。
族群認同建立在血緣和文化基礎上。他們強調文化原初情感的重要性。所謂原初的聯繫或情感指的是起源於被假定的傳統。族群力量的獲得來自族群共同的基本文化特質。這些基本的文化特質包括源自父母基因上的生物遺傳,也就是個人生理上的特徵,例如:膚色、臉部輪廓等;還包括經由所屬家庭的中介而取得社會性的特徵,例如:語言、國籍、宗教、歷史及起源。這些原初的情感聯繫構成了身份與認同的基礎。由於人類屬於固定的族群共同體,由於遺傳進化和血緣關係,族群總的來說是一種優先的、既定的而且是強有力的社會約束。族群聯繫具有邏輯和時間上的優先權,具有強制的力量和情感。族群約束壓倒了其他的忠誠。這種源於血統的強烈認同感和團結一致的態度,即原生的認同,可能會產生一些障礙,妨礙甚至破壞國家建設的進程。
國家認同則更多地建立在以憲法為準則的公民基礎上,是確認自己國家歸屬的心靈性活動,是一種抽象性的、哲學性的思考。國家認同主要是指個體對自己政治共同體歸屬的確認以及個人對自己意欲歸屬的政治共同體有何期待。在某種意義上說,國家認同是所有集體認同中最重要的認同。國家具有道德意義上的優越性。國家認同首先要有共同的連接基礎,一種是血緣和歷史記憶,一種是透過與他人共享某一公共空間或人際關係而形成的一體感。厄內斯特·勒南認為“在記憶與遺忘之間,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尋求一個平衡……”“國家預設一段歷史,這段歷史到了現在便化約成一項明顯的事實,那就是國家認同。”國家對不同的國民來講,可能是族群國家,也可能是文化國家或政治國家。這三個層面通常會合在一起,但也可能以某一層面為主要依據。公民認同國家的標準可以分為三類:族群血緣關係、歷史文化傳統與政治社會經濟體制。國家認同相應地可以在這三個層面探討: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從這個視角來看,國家認同當中實際上已經內在地包含著族群認同。
由於族群與國家屬於兩個不同層次的認同取向,多族群國家有時會面臨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失諧狀態(以下簡稱“認同失諧”),這種失諧狀態的存在原因除了族群與國家固有的差異以外,還有經濟與文化心理因素。
首先是經濟因素。經濟因素主要是指經濟不平等心理誘發的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失諧。這種不平等心理既有可能在經濟不發達的邊緣地區存在,也有可能在經濟水平較高的邊緣地區存在。“族群認同被有意識地操作和應用於經濟競爭中。”“族群組織實際上類似於一種政治組織,社會的相互影響和組織實質是雙重現象,政客也是符號的人,族群性就是為特殊目的開發這種雙重性的一種組織形式。”
一般來說,非主體族群或少數族群的邊緣化表現為它們傳統的封閉性與自主性小型社會,被融入到更大的社會中而成為其邊緣成分(主體族群和發達族群則處於更大的社會中心);表現為他們原先的自然經濟開始轉向商品經濟,而在全國性的商品經濟體系中他們的轉型經濟又處於依附的、不平等的地位。由於中心與邊緣在經濟地位上是相對不平等的,因此客觀上容易滋生不滿情緒而導致認同失諧。這種相對不平等與相對剝奪理論有關。相對剝奪理論強調並非是客觀的不平等造成了族群心理失衡,而是一種挫折或相對剝奪的感覺,促進了認同失諧的發生。相對剝奪的感覺被界定為:人們認為其應該擁有的生活物質及條件之權利,與他們實際上所能得到或維持的生活物質及條件有著他們心理感覺上的相對差異。關於相對剝奪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有過很好的解釋。它的基本觀點是:社會群體及其成員一般僅僅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和其他群體或個人比較它們的位置和命運,而且通常只在社會規模的意義上。儘管可能地位、物質和社會在絕對意義上都在進步,但它們還是很在意相對於其他群體而言,它們的進步如何。社會運動和政治行為是部分成員或群體感受到挫敗的結果,感受到它們遭到相對剝奪,在財富、地位、服務與權力競爭方面受到阻礙。根據這個觀點,認同失諧是地區相對剝奪感的結果。這種認同失諧一般發生在典型的落後地區,有時也發生在經濟水平比中心地區發達的地區,譬如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拿大的魁北克。
其次是文化心理因素。文化心理因素引發的族群失諧更多地伴隨著現代化的進程。關於現代化,經濟學家將其定義為“人類逐步提高其對外部環境的控制能力並利用它來提高人均產出的一個過程”。社會學家則認為現代化包括“喚醒和激發大眾對現在和未來生活的興趣,認為人類生活是可以理解的而不是受制於超自然的力量,以及直至目前才樹立起的對科學和技術的信賴”等特徵。其實,現代化不僅僅是一個同質的過程,它還具有分化的一面。現代化不僅不是造成同質,消解多元,而且正好相反,它時常造成異質和多元。
“現代化的發展打破傳統的生產與生活模式,社會的變遷給人們帶來不安全感。”伴隨現代化而來的政治和文化的演進,雖然把更廣泛的群體納入中心領域,但同時又相當矛盾地產生了這些群體與中央的政治社會體制疏遠的潛勢,以及不可名狀及與社會異常隔絕之感不斷發展的潛勢。而這些又隨著他們參與中心領域期望的增高而更加強烈。然而,所有這些演進不僅造成了各種各樣的解體局面,而且還增加了主要群體和階層的相互依賴和影響,因而又增加了他們之間衝突的可能性,各種群體和階層被納入相對共同的框架,以及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加強,能夠極大地增加它們之間的裂痕和衝突。不同的群體更加相互依賴和相互了解,不僅增加了他們之間衝突的範圍和次數,而且還增大了其感受和強度。”一些族群在進入現代化階段之際,不斷感受到社會結構和傳統文化解體的危機,從而產生對外來先進文化一體化的情緒化抗拒。強烈的族群認同也就自然成為宣洩痛苦情緒的一種表達方式。結果,為保持自身族群文化傳統的純潔性、連續性及優越感,形成了對族群同一性的強烈追求。“儘管多民族國家的中央政府力圖把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在儘可能廣泛的意義上傳輸給全體國民,但這種理想在中央政府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外的一些邊緣地區總是難以實現……日後的外來因素即使在構成對邊緣文化自下而上的危險的同時,也作為一種刺激,促進邊緣地區民族集團採取相應的集團行動來保衛傳統文化和地方慣例。”
因此,伴隨著現代化的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就是“族群民族主義並沒有伴隨著政治與經濟發展而枯萎。實際上,高度的政治參與與迅速擴展的GNP常常在給予民族主義集團新生活的同時,使得他們更加尋求發展過程中的利益”。因此,現代化對於多族群國家而言,較容易催化其內部族群的分離傾向。因為現代化導致不同族群團體間的接觸急遽增加,發生衝突的機會也比以往有所增加。雖然現代化可能會使得不同的團體更加聚合在一起,但是現代化的影響由於族群團體的差別而有所不同。現代化的過程也許對一些族群團體是有利的,對另一些族群團體可能就是不利的。這些不同影響往往激起某些族群團體有遭受相對剝奪的感覺,這種感覺又因為現代傳媒技術及人際間的良好溝通而擴大。族群團體隔閡隨之加大,最後導致認同失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