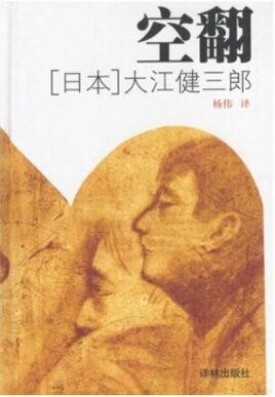空翻
大江健三郎長篇小說
《空翻》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空翻》是大江健三郎歷時4年創作的長篇小說,於1999年出版,是他對日本的靈魂和精神狀態的反思。直接促使該部小說的誕生的原因,是東京地鐵中發生的沙林毒氣事件和日本奧姆真理教的產生,大江健三郎作為一個對日本負有責任的作家,立即用文學的手段,進行了自己的反應,探索了產生奧姆真理教這個怪胎的日本社會的現實狀態。
作者運用極為豐富的想像力,以虛構和現實相結合的手法對反人類、反社會的邪教活動以及對日本人的靈魂和日本人的精神危機等問題進行思索。
兩個具有爭議的人物“師傅”和“嚮導”曾創立一個宗教團體。在信徒中的激進派準備採取炸毀核電站的恐怖行動之際,“師傅”和“嚮導”來了個“空翻”,宣布自己的教義是虛假的、愚蠢的,是個鬧劇,於是教會宣布解散,激進派的運動宣告流產。十年後,兩位原領袖籌劃東山再起,然而突發事件接連發生,“師傅”沒有新的建樹。也就在此時,一個“新人”教會悄然興起。
| 《空翻》 | |
| (上) | |
| 序章 | 狗一般面龐上的美麗眼睛 |
| 第一章 | 百年 |
| 第二章 | 再會 |
| 第三章 | 空翻 |
| 第四章 | 講解R.S.托馬斯 |
| 第五章 | 莫斯布魯加委員會 |
| 第六章 | 嚮導 |
| 第七章 | 聖痕 |
| 第八章 | 選出新嚮導 |
| 第九章 | 一本裡面什麼都寫著,但活著就得續寫下去的大書 |
| 第十章 | 守夜狂躁病無限地延續(一) |
| 第十一章 | 守夜狂躁病無限地延續(二) |
| 第十二章 | 新信徒的入教儀式 |
| 第十三章 | 追悼集會上的哈利路亞 |
| 第十四章 | 師傅為何現在復歸 |
| 第十五章 | 鬱積多年的疲勞 |
| 第十六章 | 臨床專家 |
| (下) | |
| 第十七章 | 地方的魔力 |
| 第十八章 | 接受與拒絕(一) |
| 第十九章 | 接受與拒絕(二) |
| 第二十章 | “安靜的女人們” |
| 第二十一章 | 孩童的螢火蟲 |
| 第二十二章 | 約拿 |
| 第二十三章 | “技師團” |
| 第二十四章 | 眾人是如何接受聖痕的? |
| 第二十五章 | 以天窪為舞台的戲劇 |
| 第二十六章 | 像未編輯過的錄像帶似的人 |
| 第二十七章 | “新人”的教會 |
| 第二十八章 | 奇迹 |
| 第二十九章 | 教育 |
| 第三十章 | 關於嚮導的回憶 |
| 第三十一章 | 夏季的集會 |
| 第三十二章 | 為了師傅 |
| 尾聲 | 永遠的一年 |
1995年,東京地鐵出現了奧姆真理教散播沙林毒氣,造成大量乘客和行人中毒傷亡的惡性事件。奧姆真理教的主要成員大都是高學歷的年輕人。奧姆真理教產生的精神背景是“宗教的空白”。大江曾指出:二戰后,出於對戰前戰時天皇崇拜的逆反心理,宗教意識普遍淡薄,這使奧姆真理教乘虛而入。正是奧姆真理教的沙林事件使一度決定在小說這種形式上封筆的大江再一次解除了自己的禁令,作家的良心使他不能不通過奧姆真理教事件,對這一完全異質的共同體的產生進行精神背景上的追究,從而對日本人的信仰、靈魂等問題展開深層的探索,《空翻》正是大江健三郎對日本人的靈魂和日本人的精神等問題進行思索的產物,用來探索現代日本人的靈魂拯救之路。
大江創作《空翻》的四年間(1995年—1999年),正值日本經濟輝煌后的蕭條時期,新國家主義的風潮和對戰後民主主義的否定勢頭乘機抬頭,正是針對這種傾向,大江特彆強調對“自我靈魂”的關注,希望人們通過自我靈魂的構築來與右翼勢力所倡導的“國家主義”相抗衡。而在上述時代背景下,一般日本人——特別是年輕人——的心中出現了精神和信仰上的空白狀態。資本主義使家庭、共同體及國家變得軟弱無力。在一個已經弱化了的共同體中,極端國家主義很可能在某一天復活,而且,人們也很容易湧起對完全異質的共同體的執著追求。
“師傅”
小型宗教團體主要領導人;年齡:四十;性別:男。“師傅”能在冥想世界中幻視到神的影像般的話語,而“嚮導”則負責將“師傅”的所視所云用常人的語言整理記錄下來。
“師傅”的一些信徒認為,教會嘛,就是打造人靈魂的地方。追隨者們在與“師傅”探討宗教間題的過程中發現,“師傅”的宗教思想卻是別有洞天,他其實真正追求的是一種無限遠離宗教的宗教。
該宗教團體曾經有過一次潰滅的經歷。在教團日益壯大之時,團體內部的一個高學歷精英集團“技師團”為讓社會感受“懺悔”,計劃奪取核電站,策動恐怖事件,“師傅”和“嚮導”見局面難以控制,決定與日本的警方、傳媒聯手,力圖阻止這一危險的發生。
“師傅”與“嚮導”二人在電視上發表講話,聲稱“以前在教團里跟信徒們宣講的那些都是胡謅八扯,都是惡作劇”。這樣,“技師團”的恐怖活動流於未遂,教團本身也趨於解散。教團首領自行放棄自己原創的教義,無異於殺了自己的回馬槍。這一事件被傳媒戲稱為“空翻筋斗”,“師傅”和“嚮導”也像是在空中翻了一個大跟斗,落回原地,又跌進深不見底的地獄。“師傅”最後也死掉了,他的死與其說是殉教,不如說是與神的斷絕。 “師傅”最後之死,未能完成精神思想的根本統一。
“嚮導”
“嚮導”是一個五大三粗的大塊頭男人。“嚮導”給人的印象:和藹可親但難於接近、成默寡言。他也是反人類、反社會宗教團的二號人物。患有腦動脈瘤。“嚮導”死於內部紛爭。
“童子”
“童子”即傳奇少年阿基,“孩童的螢火蟲”首領。“童子”計劃成立“孩童的螢火蟲”來建設獨立於外部世界的共同體。因為,依靠外部世界的“舊人”是無法使日本度過危機,只有寄希望於象徵著純潔無垢和美好未來的“新人”,即“童子”來拯救出現令人擔憂“徵兆”的世界。
“木津”
在美國東部大學藝術系任教。癌症患者。後到日本度假數年。在度假期間,在東京某研究所從事管理工作,負責講課和研究班的工作,還承擔一些雜務工作。他漸漸地遠離了真正的繪畫創作工作。
“木津”與“育雄”他們把性行為當成一種思想探索、哲學思考的方式。在個性受到威脅的時代,他們試圖以此來體驗個體存在的強度,探尋人的性的真實存在,將人在現代社會中對自己生存狀態的不安與焦慮用性的障礙與性的焦慮狀態來表現,成為一種廣義衝動的宣洩。
“育雄”
“育雄”曾是大學建築專業的學生。他也是“木津”繪畫的模特,後來成為“木津”的同性戀伴侶。
育雄從孩提時代起就思考著世界末日。一直渴望著再次聽到神的聲音,因此他把自己與周圍的一切都對立了起來:從大學里退學、離開格格不入的家庭、遊離在社會的邊緣……而在他與木津相互扶持的生活當中,他逐漸找到了生活的方向,最後打消了再次傾聽神的聲音的念頭,在“師傅”以悲壯的方式完成與神的決絕後,小說以育雄的一句話結束了全篇,教會嗎,以他說,就是打造人靈魂的地方。
“青年荻”
“青年荻”他那約莫二十四五歲的年輕肉體所充溢的美感,還有他那整個身姿所瀰漫著的獨特風采,無不強烈地吸引著木津。
主題思想
《空翻》的主題思想即如何“構築靈魂”。《空翻》探討的是如何建立一個“構築靈魂的場所”,以拯救“激蕩不休”的年青靈魂。
在《空翻》中,諸如木津、育雄、舞女、青年荻、立花和森生姐弟、古賀醫生、與“師傅” 、“嚮導” , 還有原先教會的幾路人馬,他們本來都有自己的生活,其生活軌跡幾乎很難發生交叉的,但是大江卻讓他們在“轉向”的主題下,聚攏到一道,在一種奇異的聯繫中,他們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隨後,大江又讓他們走出東京,走到森林山莊,在那裡,苦苦掙扎的“舊人”與充滿活力的“新人”、都市的主流文化與峽谷的邊緣文化、當代人的信仰危機與傳統文化的宗教習俗,在大江的導演下,發生了戲劇性的大碰撞,從而隆重地推出了如何“構築靈魂”這一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命題。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真實的靈魂是生活和生命的根本之所在。
作為教會靈魂人物的“師傅”,一直也沒有提出明確的教義,直至最後才發現,原來他所追求的,竟然是一種遠離宗教的宗教!小說中很多情節是通過畫家木津的視角展現的,而木津是追隨在“師傅”身邊的人中唯一一個對神沒有任何希求的人,他只是為了融入同性戀的對象育雄的生活而加入教會的,進而一步步深入教會之中。他認識到自己在教會中的角色就是:“一個站在宗教外面的人把一個站在宗教內部的人神聖化”,所謂“旁觀者清”,所以他才會在臨終前感悟地說出:“育雄,你還是非要聽到神的聲音不可嗎?……我呀,就是沒有神,也會說rejoice(喜悅)的啊!在木津的這些話中,“沒有神”是十分重要的。就是說,一部看似以宗教為主題的小說,最後的落腳點卻落在了“無神” 、“無神的宗教” 、“無神者的靈魂拯救上”,這的確是該作品的大膽之處。“師傅”最後也死掉了,他的死與其說是“殉教”,不如說是與神的決絕。小說想要告訴讀者的是:真正能夠拯救人類的,不是什麼神,而是人類自己。因為神是沒有自由的一種存在,而沒有自由的東西與自由的人之間不存在可以共生的時間和場所,也就無法給有自由的人以拯救;倒是在沒有神的世界里,人們更容易找到真正自由的根據。也就是說,大江健三郎認為沒有神的宗教或許才有可能使人獲得拯救,而這種大膽設想的根基則是人的想像力,以及想像力所帶來的無限可能。
敘事方式
大江健三郎在構想《空翻》長篇小說在敘事方式創作上則表現為一種結構中的解構與解構中的結構的並舉。大江健三郎在與薩伊德的對談中強調,作為最後的作品,把很多不同的事物,超越時間和空間,聚攏在一起的構思已經有,但是還找不到敘事方式。不如先在心裡創作出反敘事一類的東西。
大江健三郎曾接受過結構主義的影響,並撰文“稱自己是‘遲到的結構主義者’”,後來他又表示,如果說在日本存在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混雜在一起的現象,那麼他恰恰是對這種狀態感興趣的人。他倒是積極地把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混合到一起來理解。而“反敘事”的提法,其實已經暗示著大江健三郎正在“積極地把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混合到一起”,以熔鑄其後期作品獨特的敘事風格,那是一種把結構中解構與解構中結構並舉的敘事方式,即作品的敘事往往是對某一已有定論的事件的重新解讀(解構),在解構過程中,不僅獲得了重新的認識,事件本身也在繼續推進(結構),而最後則是以一種具有自我解構傾向的結局(結構),使作品呈現為一種具有不確定性的開放性結構。
在《空翻》里,整個敘事的出發點是“師傅”十年前的“轉向”,當下圍繞著“師傅”的復出並重建“教會”所展開的敘事,顯然是通過對當年“轉向”的解構而實現的新的“結構”,而“教會”的重建(結構),則是以“師傅教會”的徹底解體(解構)而告終結,在“師傅教會”的廢墟上浮現出來的是“新人”教會的輪廓(解構與結構的並存)。同時,小說整個敘事主要是以身患絕症的畫家木津為視角,其中又時時迴響著一個反敘事的旋律——木津的自我反省及其與他人之間質詢式的對話。其實,小說書名已經暗示了結構與解構並舉的敘事方式,“翻”本身意味著解構式的結構,而“空”則是對“翻”之結構的解構,整個“空翻”便是一個由雙重的解構所形成的結構。
正是採用這種層層疊疊的解構又結構、結構復解構的敘事方式,大江健三郎的後期作品通過對於人物靈魂的剝筍式的拷問,達到了對於全球化背景下的人類靈魂及其境況,進行了深刻的探究。
象徵意義
生存的荒誕感、存在的虛無
日文中“空翻”既有翻筋斗之意,也指到某地后馬上折返。大江健三郎從象徵意義上使用了“空翻”該詞,不僅是教主的“空翻”,更是社會意義上隱喻的“空翻”,這一形象的詞語即帶給讀者清晰的荒誕感。
《空翻》中描述了一個新興宗教團體領袖人物的“轉向”。這個團體在近十幾年間網羅了大批年輕信徒,形成了強大的勢力。面對領袖們宣稱的“世界末日”的到來,這個教團的年輕成員們最終試圖採取政治上的過激行動,想以此喚起人們的改悔之心。於是,激進派分子進入了實際行動的準備階段。在這種情況下,教主及其搭檔不得不在電視鏡頭前發表聲明,說他們創立的教會教義乃是信口雌黃,通過電視媒體宣告了教會的解散,並聲明激進派的行動缺乏依據,以便瓦解激進派的恐怖計劃。
教團解散了,“轉向”的首領們從社會的表層銷聲匿跡,他們的“轉向”被記者們戲稱為“空翻”,在社會上留下了強烈的餘震。就這樣,教會的領袖殺了自己一個回馬槍,就像在原地翻了一個筋斗一樣。這一戲劇化的過程無疑是荒謬的:就在教會成員對教義篤信不疑,甚至要為此奉獻自己生命的時候,創出教義的教會領袖——“師傅”與嚮導卻將這一切都推回了原點,這樣的“空翻”,帶給了讀者強烈的荒誕感受。
在經歷了十年的心靈煉獄后,“師傅”與嚮導決定再創新教。然而,由於“師傅”在建立新教會時,並沒有從辯證法的角度去超越當初的失敗,所以沒有樹立起新的理念,這也就註定了這一次的努力嘗試又變成了再一次的“空翻”——徒勞翻騰。通過這樣一些描寫,薩特存在主義關於人的行為的徒勞性的思想,就具有了極大的具象性和直觀性,更讓讀者深刻體會到了世界的荒誕與存在的虛無。
薩特認為,人是被逼而自由的,人也是被逼而成為強者的。人生唯一的出路,就是行動,是介入,是通過行動來超越來適應世界簡單穩定的決定論,並且在世界的物質性中改造世界。如果說存在先於本質,那麼行動和介入就使人能夠創造自己真正的本質,只有行動,才賦予了人的一生以意義。
在這一點上,大江健三郎受薩特的影響至深。作為一個專修法國文學的學生,大江健三郎從薩特那裡學到了參與社會。的確,大江健三郎很好地實行了薩特關於“介入文學”的主張,他強烈的社會參與意識使得他的文學創作超越了個人化的局限,體現出高度的使命感、責任感。大江在接受芥川獎時強調,他是通過文學參與政治的,只有在這點上他才更清楚自己選擇文學所要承擔的責任。用想象力的語言在兩個世界之間架起一座橋,使小說世界走向政治世界。
《空翻》中的反社會的性行為描寫——如木津與育雄的性取向、青年荻與建築師夫人的婚外情等,他們把性行為當成一種思想探索、哲學思考的方式。
《空翻》對存在主義的超越
大江健三郎《空翻》的意義並不在於對存在主義的簡單詮釋和吸收,而在於對存在主義的超越。
(一)想像力——超越“存在”的媒介
“奧姆悲劇決不可重演。為此,有必要在領導者和信徒雙方的心中驅動想像力。”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採訪時,大江表述了創作《空翻》的動機,這恰恰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解讀《空翻》的角度。
作為“小說理論家”的大江健三郎,在創作的不同階段,先後接受了薩特的存在主義、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文化人類學以及怪誕現實主義理論的影響。這些影響,最後都彙集到“想像力”這一文學創作的根本問題上。
大江說,在薩特的引導下思考作為小說方法論基礎的想像力論的過程中,他發現了一個更能夠讓我透徹理解想像力理論的新嚮導,他就是加斯東·巴什拉。首先是薩特的“存在——虛無——自由” 、“形象——想像——自由”,其次是巴什拉的“想像力是改變形象的能力”,最後是布萊克的“想像力就是人的生存本身”。由此,大江健三郎對想像理論的認識就有了一個質的飛躍,以想像力為媒介,實現了對薩特存在主義的超越。
《空翻》乍看上去感覺像是一本宗教小說,通篇都可見有關信仰與神的問題。《空翻》傳達給讀者這樣一個理念:“人的想像力才是超神的,才是自由的,想像力就是人的生存本身!”
(二)“新人”——尋求“存在”的希望
在《空翻》作品里,作者為讀者描述了一個這樣的世界,聚集在“師傅”身邊的信徒們,也都是那些被黑暗、憂鬱和絕望控制著的人,試圖在教會中得到新生。然而,在對複雜的社會現象進行細緻入微的剖析之後,作者毫不客氣地指出,這種反人類、反社會的邪教活動,只能是原地空翻筋斗的瞎折騰,最終仍然指向虛無。
大江沒有像薩特存在主義那樣讓人們就此沉淪,而是積極為人們尋求著“存在”的希望,在為人們所共同面臨的精神危機開藥方時,這位質樸的作者將烏托邦建立在了他的生養之地——四國島上的那片森林裡。他給出了讀者這個問題的答案,那就是:“期盼並呼籲一代新人的出現,呼籲那種沒有受到污染,象徵著人類的良知、純潔和美好未來的新人的出現。”就此,大江健三郎超越了薩特存在主義的虛無觀。
《空翻》的故事情節是圍繞著教會的領袖——“師傅”與嚮導重建教會的活動展開的,而在這一困難叢叢的過程中,“師傅”發現了一個關鍵辭彙——“新人”,並且,這“新人”又成為了宗教活動的中心,教會也被命名為“新人”教會。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大江通過“師傅”的舉動告訴讀者:小說的主人公與其說是身為教主的“師傅”和“嚮導”,不如說是育雄和“孩童的螢火蟲”的頭領——一個名叫阿基的森林少年。這些“新人”一出場,就帶給讀者與“舊人”完全不同的感受:他們對過去與現在有著清晰的認識,同時擁有著縝密的思維與堅定的意志以及無窮的想像力,在“孩童的螢火蟲”所承襲的當地的習俗中,“生活在谷間的人類靈魂在肉體死亡之後,仍舊駐留在能夠俯瞰谷間的森林之中,而且三番五次地降臨到谷間”,“生者的世界和死者的世界在這塊地形中形成了一種完美的組合。”
就這樣,在神秘的四國森林中,通過新人們的努力,死者與生者實現了“共生”,為人們帶來了無窮的“存在”的希望。
在閱讀《空翻》的過程中,讀者隨時都能感覺到作家對人類靈魂的憂慮和這種對“新人”的期待。大江健三郎作為一個文學家,而不是作為一個宗教信徒,自始至終站在人本主義的立場上呼籲著人們進行改悔,反省自己的罪孽,並構築起自己的靈魂。無疑,《空翻》就是大江呼喚的載體。
(三)仁愛——帶來“存在”的光明
薩特存在主義的名言“他人即是地獄”表明,人應該有絕對的自由,因而“他人”就成了人自為存在的障礙,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而《空翻》之所以吸引了眾多讀者,原因之一就是感人的人物形象,而除了人物形象的豐滿與生動外,更主要的還在於以“仁愛”完成的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融合。這是《空翻》能夠超越薩特存在主義的最根本之處。
在小說的最後,一度被與津金夫人婚外戀折磨著的荻,終於在離開教團后與津金夫人正式結合;他回到教團所在地,才知道為獲得拯救而試圖集團自殺的婦女們吃下的是被師父偷換的瀉藥而不是青酸毒,結果一群人在樹林里拉了個天昏地暗,並接受“師傅”的遺托,打消了集體自殺的念頭;木津在眾人的幫助下與病魔進行了不懈的鬥爭,最終遺憾地離開人世;
從《空翻》的人物形象中體現出來的超越了薩特存在主義的觀念與中國儒學中的“仁”的觀念極為相似。“仁”是指人與人之間的心意相通的關係。“仁者愛人”,愛即“推愛”,從親愛與自己有血緣親情的親人開始,推而擴充到對自己所有的同類均保持一種溫情與同情。儒家文化追求人與自我身心、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天(道)的普遍和諧。這種普遍的和諧不是不承認現實的差異與矛盾,而是把現實的差異與矛盾看作是事物非本然的狀態,是事物在尚未到達理想境界前所呈現出來的不圓滿,但事物在發展過程中是可以通過自我調節而達到圓滿和諧的。就這樣,大江健三郎用“仁愛”為讀者帶來了“存在”的光明,從而使作品從眾多變相的人與事物中產生純人文主義的理想形象。
《空翻》作品通過描寫一個新興宗教團體的再生與幻滅來思考、探索現代日本人的靈魂拯救之路。
——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