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
早年經歷
安妮出生於德國的法蘭克福,為奧托·弗蘭克(Otto Frank)一家的小女兒,家中還有母親艾迪斯·弗蘭克(Edith Frank)和姐姐瑪戈特·弗蘭克(Margot Frank)。由於當時納粹德國排斥猶太人風氣日盛,父親奧托便放棄於德國的事業而將家庭移至
荷蘭阿姆斯特丹,一家過著較為平順的生活。她出生時名為安內莉澤·瑪麗(Anneliese Marie),但家人和朋友都以昵稱“安妮(Anne)”來稱呼她. 有時其父也會叫她“小安妮(Annelein)”。弗蘭克一家住在一個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雜居的同化小區中,而安妮和其它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小孩一樣,經常接觸到不同信仰的人士(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以及其它猶太裔人。弗蘭克一家信奉
猶太教的一分支—猶太教改革派,此教只遵守部分原猶太教條,而忽略及摒棄了大量原猶太教傳統。安妮的母親艾迪斯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奧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出仕於德國政府,並且獲授勛。性格上奧圖熱衷於追求知識,所以對安妮及其姊瑪格特也經常鼓勵她們多閱讀。
其夫奧托開設了一家名為“Opekta Works”的公司,負責批發由各種水果提煉出來的果膠。他在阿姆斯特丹近郊的梅爾韋德廣場(Merwedeplein)替家人找到了新住所。1934年2月,艾迪斯帶著安妮與瑪格特搬到新住所,而且也重新為兩姊妹安排學校。姐妹同就讀於蒙特梭利學校,.兩姊妹在學業上各有專長,瑪格特比較精於算術及數學,而安妮在讀寫上比較優異。其中一個當時安妮的朋友哈娜·哥斯拉(Hannah Goslar)憶述,安妮在作業時經常會用手蓋著答案,以不被其它同儕借故抄襲,而且也不會跟其它同學一起討論。但是這些作業後來卻沒有保留下來。同時,安妮和瑪格特在個性上也有著明顯差別。瑪格特在舉止上較文靜,保守和勤奮,而安妮則較健談,外向和充滿活力。
1933年3月13日,在法蘭克福進行了市議會選舉,由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勝出。
反猶太主義在此時便迅速擴張起來,使弗蘭克一家開始擔心繼續留在德國會對自身安全構成危險。在接近年尾時,艾迪斯便帶著安妮與瑪格特到亞琛的外母家中居住,而奧圖則繼續留在法蘭克福,直至他收到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開設公司的邀請,便決定搬到那邊去打理生意和為家人安排新住所。弗蘭克一家是1933年至1939年離開德國的300,000猶太人之一。
1938年,奧托與一個由德國奧斯納布呂克舉家搬來,與名叫赫爾曼·雲佩斯(Hermann van Pels)的肉販合夥建立了另一家公司。1939年安妮的祖母也搬到阿姆斯特丹來居住,她之後一直住在這裡直到1942年1月逝世。1940年5月,德軍入侵併迅速佔領荷蘭,新成立的親納粹政府開始透過差別對待及嚴格的執法迫害猶太人。政府對猶太人實行了強制登記及隔離,所以即使瑪格特與安妮在學校表現優異,但新制度卻規定她們只可在指定的猶太學校讀書,她們只好離開原校。之後,她們被編入猶太學園繼續學習,此時安妮12歲。

可愛的安妮·弗蘭克
1942年6月12日,當安妮正慶祝她的13歲生日時,她收到一份之前在逛商店時,曾向父親央求過的小簿作為 生日禮物。這是一本配有紅白彩格封面,並附上一個小鎖的簽名簿。但安妮之後還是決定把這本小簿作為日記使用。她開始在日記中記載著在日常生活上的各種瑣事,如自己,家人和朋友,校園生活,鄰居,甚至與一些男孩嬉戲的情況。這些早期的日記都記錄了她的生活,其實都像其它同學一樣大同小異。同時,安妮也把一些在德國佔領下,周遭發生的變化記錄下來。當中有些是在表面上難以察覺的。但在之後的日記,安妮也透露了納粹對猶太人的壓迫正急速膨脹,而且也記錄了一些詳細數據。其中一個例子是日記中有關強迫猶太人在公眾場合攜帶“黃星”的記錄。她也列舉了一系列在阿姆斯特丹風行,針對猶太人的禁制及迫害措施。同時,她也在日記中表示對年初祖母的離世感到難過。
躲藏在隱密之家后
1942年7月,瑪戈特收到了一份由猶太移民局中央辦公室(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所發的徵召通告,命令她的父親到附近的勞動營報到。由於納粹當局捕捉猶太人的行為日益嚴重,而且瑪戈特也收到納粹當局的勞動通知,於是安妮一家決定移居到更為隱密且安全的居所。然後安妮便得知其父奧圖在與自己公司的僱員"溝通"后,決定把她們藏到公司里去,而其母與其姊亦早得知此事。於是一家人便搬到了位於阿姆斯特丹王子運河(Prinsengracht)河畔的公司內一間隱蔽的房間。

安妮
在1942年7月6日早上,安妮一家搬到隱密之家暫避。他們故意把房子弄得很亂,嘗試營造他們已經離開的樣子。奧圖法蘭克留下了一張字條,暗示他們要去瑞士。他們被逼留下了安妮的貓“莫蒂”。因為猶太人不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們從家門走了幾公里,每個人都穿了幾層的衣服,因為害怕被人見到他們拿著行李。房子秘密增建的部分,在日記中叫“Achterhuis”,在荷蘭文中意即後座。這是一個在房子後座三層高的空間,可以從地面進入。第一層有兩間細房,相連的洗手間;樓上是一間大的開放式房間,旁邊有一間細房。細房可以通往閣樓去。通往這隱密之家的門被一個書架蓋住,保證不會被發現。主建築在Westerkerk教堂的一個街口外,表面上跟阿姆斯特丹其它的房子沒甚兩樣。
"庫格勒"、"克雷曼"、"米普"、"愛麗(真名貝普)"是唯一幾個知道這裡有人隱藏的僱員,"米普"的丈夫、愛麗的父親都是幫助他們藏身的人。他們是屋內的人和外界的唯 一聯繫,也會告知他們戰爭的情況和政局發展。他們保證屋內人的安全,照顧他們的起居飲食——一個隨時間而變得艱難的任務。安妮寫下了他們在最危險的時期對提升屋內士氣的貢獻。他們都知道,一旦被發現,幫助猶太人都會令他們落得死刑的下場。
在七月尾,凡佩爾斯一家加入了弗蘭克一家,他們包括:和安妮父親奧托·弗蘭克共事的凡佩爾斯(日記中稱為凡·達恩先生),其妻子奧古斯特·凡佩爾斯(日記中稱為“凡·達恩夫人”)、和他們十六歲的兒子彼得,十一月時斯佩普·普佩弗(日記中稱為“杜塞爾先生”),一位牙醫和凡佩斯家的朋友,也加入了。安妮寫下了跟新朋友說話的興奮,但很快,狹小的居住環境引起了衝突。安妮跟普佩弗同住一間房,她很快就覺得他很難以忍受;她又跟奧古斯特凡佩爾斯衝突,她認為她愚蠢。她跟她母親的關係亦日漸緊張,安妮說她與她母親沒有什麼共同點。她有時也跟瑪格特吵架,她最親的還是父親。過了一段日子以後,成長之後的渴望聊天的安妮和密室唯一的男孩“彼得”,萌生了感情。
安妮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讀書和學習上,閑時也寫日記。除了記下生活上經歷的事情外,她也寫下自己的感受,信念和希望,一些她覺得她不能再談的東西。後來她對寫作的信心增強了,人又成熟了,她開始寫一些抽象的東西,例如對神的信念,又或是她怎麼了解人性。她一直都在寫,直至1944年8月1日的最後一篇為止。1944年8月4日大約上午10點,有人打電話舉報王子運河263號藏有猶太人,隨後納粹警察帶人突襲了密室。
被捕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國警察闖入了他們的隱密之家,告密者的身份至今未明。在西爾弗鮑爾的帶領下,當中總共有至少三個德國警察的成員。屋裡的人都被貨車帶走了,幫助他們的克雷曼和庫格勒也被帶走。其它所有人都被帶到了蓋世太保的基地,被盤問了一整晚。8月5日,他們被轉送到拘留所,一個極度擠逼的監獄中。兩日後八個猶太囚犯又被轉送到荷蘭的韋斯特博克——一個臨時營地。隨後很快被轉運到奧斯維辛集中營。
米普和愛麗(貝普)沒有被帶走。他們後來回到隱密之家,找到安妮散落在地上的紙張;把它們連同家庭相簿收起,打算戰後把它們還給安妮。
被送入集中營與逝世
9月3日,他們被移轉,由火車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去。他們在三日後到達,以性別分開,再也無法會面。到達集中營時,火車上的男人和婦孺被強行分開,奧托就此與家人分開。弗蘭克姊妹被迫拖運岩石和挖草皮;晚上她們都塞進十分寒冷的營房中。後來有人作證說安妮每當看見有小孩被送到毒氣室,都會變得僻靜和流淚。

“希望可以永遠保持著這張相片中的樣子”
549個人(包括所有15歲以下的小孩)被直接送到毒氣室殺害。安妮躲過了這一命運,因為她看起來比別的孩子稍大一些。脫光消毒,剃頭,被紋上一個識別碼。因為集中營中男女完全被隔離,安妮自此再沒見過父親,所以當時安妮相信50多歲不很強健的父親已在他們分開后不久已經死亡。白天,她們被逼做奴隸式的苦工,晚上她們都擠在冷得要命的營房中。疾病非常猖獗,由於集中營衛生太過惡劣,導致各種疾病蔓延猖獗,弗蘭克姐姐的皮膚也受疥癬嚴重感染,二人被送到醫療室治療,那裡是持續黑暗的環境,有很多老鼠出沒。那時候她們的媽媽艾迪特不進食,把每一口的食物留下給兩個女兒,並鑿穿醫療室底部的牆,把食物傳送過去。1944年10月,弗蘭克家的婦孺被選定加入波蘭上西里西亞的勞動營,但安妮被禁止去那裡,因為她受到
疥癬感染,而她的母親和姐姐選擇與她留下。
1944年10月28日,軍方開始選移轉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多於8000個女人,包括安妮、瑪戈特和愛吉斯·凡佩尓斯,被轉送到該集中營;因為大量囚犯被送進來,要開始用營帳收留,安妮和瑪戈特就是其中二人,人口增加了,同時使死亡率不斷上升。安妮跟朋友短暫地重遇——漢妮和蘭特,她們在戰爭中活下來了。蘭特形容安妮為:禿頭,瘦弱,又在顫抖。漢妮說雖然安妮自己也在生病,她卻更擔心瑪戈特,因為她的病更嚴重,而且已經不能走動,常常在帆布床中躲著。佩爾斯太太跟安妮與瑪戈特在一起,並照顧瑪戈特,因為她當時病得很嚴重,虛弱得不能下床。

安妮與瑪戈位於集中營舊址的紀念碑
1945年3月,斑疹傷寒在營中散播,17,000人因此死亡。後來有目擊者指瑪戈特的身體已非常虛弱,她因為休克,從帆布床掉下來就死了,大約兩天後安妮也死去了。漢妮她們的見面是在1945年1月底至2月初。幾個星期後,英軍於1945年4月15日解放這個集中營,但確實日期並沒有紀錄,安妮的死亡時間是介乎2月底和3月中。安妮和她的姐姐瑪戈特她們倆都同時在1945年2-3月死於斑疹傷寒。當時距離該集中營被英軍解放還不足兩個月的時間。
其他隱居的成員,除了安妮的爸爸奧托外,全都死於集中營。於安妮的日記經常提及的桑妮·雷德曼,已跟她的父母弟弟送到毒氣室,而她的姐姐,芭芭拉,跟瑪戈特很要好的朋友,則生還了。而安妮倆姊妹在學校認識的朋友,有幾個生還了。至於奧托與艾迪特的延伸家庭,他們在1930年已逃離德國,分別定居在瑞士、英國及美國。
解放后,營地被全力燒毀,以防止疾病蔓延,而瑪戈特和安妮被埋葬於萬人冢,屍體下落不明。
安妮與瑪戈特位於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舊址的紀念碑,伴隨著的是人們悼念的鮮花和相片。
正面評價
這本日記的高度文學價值一直受世人重視。美國知名劇作家梅耶·萊文(Meyer Levin)曾以“有著嫓美長篇小說的張力”來形容安妮的寫作風格,並受到她的日記啟發和感動,在日記出版后不久,便與奧圖·法蘭克合作把日記內容改編為舞台劇。另外,著名美國詩人約翰·貝里曼(John Berryman)也曾表示,日記描寫的內容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態,而且“以細緻而充滿自信,簡約而不失真實地描述了一個孩子轉變為成人的心態。”

安妮小時候與母親、姐姐的合影
在日記的美國發行版中,
埃莉諾·羅斯福(即前美國總統羅斯福夫人)在序中寫道:“在我曾閱讀過的書籍中,這是其中一個對戰爭影響的描述最為現實和聰慧的記載之一”。前美國總統
約翰·肯尼迪在1961年一次演說中提到說:“在眾多於我們歷史重要關頭,站出來為人性尊嚴辯護的人當中,沒有誰的說話比安妮法蘭克更鏗鏘有力。”同年,一位蘇聯作家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urg)也認為,“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萬(猶太)人心聲的書,縱使這不是什麼雄壯偉大的史詩,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記。”
安妮也被認為是一個有高度寫作水平的作家和人道主義者,同時也被廣泛視為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以及迫害主義的一個象徵。希拉里·柯林頓(即前美國總統柯林頓夫人,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候選民主黨提名人) ,在她於1994年接受埃利·維瑟爾人道主義獎時的演說中,也提到安妮的日記“喚醒我們不要再作出愚蠢的岐視行為”(指當時於薩拉熱窩,索馬利蘭和盧安達的種族戰爭和屠殺)。

家人
在獲得安妮·弗蘭克基金頒授的人權獎后,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發表講話,他說在閱過安妮的日記后,“在當中獲得許多鼓勵”。他把自己對種族隔離的反抗喻為安妮對納粹的反抗,並以“因為這些信條都是完全錯誤的,也因為古往今來,它們都在被跟安妮·法蘭克相似的人挑戰,所以它們是必定會失敗的。”來把兩種信念連繫在一起。同樣地於1994年,前捷克總統
瓦茨拉夫·哈維爾在響應怎樣面對當時的東歐國家,在蘇聯解體后的政治與社會變化時,也回答說:“安妮·弗蘭克留給後人的精神至今仍然存在,並且對我們仍然具有重要意義。”藉此表示自己的理念。
義大利作家普利摩·利瓦伊(Primo Levi)曾經表示安妮·弗蘭克之所以被廣泛認為代表著在二戰中數以百萬計受害的民眾,是因為“接受安妮·弗蘭克的故事,比起要去接受那成千上萬與她一樣的受害者要來的容易。也許這樣比較好吧,人們總不能活在成千上萬悲慘故事的陰影下。”而奧地利作家瑪莉薩·穆勒(Melissa Müller)在她的撰寫的安妮弗蘭克傳記的後記中,也提到相似的想法,並且試圖消除公眾對“安妮·弗蘭克代表著六百萬納粹集中營受難者”的誤解。她寫道:“安妮的生命與死亡都是她的命運,而那六百萬受害者也有著自己的命運。所以她不能代表那六百萬被納粹奪去的性命,他們也有著自己與別不同的命運……但她的命運,依然使 我們明白大屠殺對猶太人的影響是如此的廣,如此的深遠。”
安妮的父親,奧圖·弗蘭克在餘生都致力於維護安妮留下的一切。他曾表示“這樣給我的感覺很奇怪。通常在正常的家庭關係里,都是子女承受著父母之名所帶來榮譽和負擔,而我卻恰好相反。”而他也重提了出版商認為日記何以如此暢銷的意見。“他們說,日記觸及的日常生活細節是如此的廣泛,致使幾乎每個讀者都 能在日記中找到觸動自己的共鳴。”著名的“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認為,安妮的日記大大提高了公眾,對那些在
紐倫堡審判中已被確認的屠殺罪行的注意和認識,因為“人們都認識這個女孩。人們都知道大屠殺對她的影響,這也是在我的家庭,在你的家庭也發生著的事,所以人們都能明白這個罪行的影響。”
於1999年6月,美國時代雜誌出版了一冊題為《TIME 100: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TIME 100:Heroes & Icons of the 20th century)的特別期刊,安妮·弗蘭克獲選為其中之一。編者羅傑·羅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對她的貢獻作出了這樣的評價:“安妮的日記燃起了所有人對她的熱情,她使人們認識到大屠殺、反猶太主義,也使人們認識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為現代世 界的精神象徵-不論是在受著各式各樣影響的個人精神道德,還是在堅定人類對生存的渴望,與對未來的憧憬上。”他同時表示,當人們敬重安妮的勇氣與實事求是的態度時,同時她對自身的分析能力與寫作能力亦使人欽佩,“她的聲譽所以能長存不朽,主要是因為她具有高度文學水平。不論什麼年齡來看,她都是一個水平極高的作家,能在當時殘酷的現實環境下寫出了如此優秀的作品。”
負面評價和訴訟
日記自20世紀50年代起受到公眾關注后,開始出現不斷的批評與質疑,也有著作申述這些批評,最早期的著作來自瑞典及挪威。在這些負面評價中,曾經有人質疑日記的作者不是安妮·弗蘭克,而是劇作家梅耶·萊文。
於1958年,當安妮的日記改編的舞台劇在維也納上映時,在席的西蒙·維森塔爾受到一班抗議者的滋擾。那些抗議者質疑安妮·弗蘭克是否實際上不存 在,並挑釁維森塔爾要求他找出當年逮捕安妮的軍官以茲證明。後來於1963年維森塔爾找到了當時的蓋世太保Karl Silberbauer,在與他的會談中, Silberbauer對當時的罪行直認不諱,並在一張被他逮捕的人的相片中認出了安妮·法蘭克。他並供認了整個逮捕過程,也記得在過程中曾翻倒了一個載 滿紙張的公文包。這些證詞後來全被其它目擊證人,包括奧圖·法蘭克予以證實。這次事件也平息了對安妮·法蘭克是否存在的質疑。
除此以外,有批評者提出了對作者新的質疑。批評者認為,安妮的日記實際是親猶太組織的宣傳品,而奧圖·法蘭克亦被指為騙子。於1959年,奧圖·法蘭克於德國呂貝克對一名曾為希特拉青年團成 員的教師Lothar Stielau興訟,控告該名教師在校報上詆毀日記為贗品,後來同時控告了在呂貝克一份報紙登信支持Stielau的Heinrich Buddegerg。開庭審訊后,法庭分析了日記的手稿,在1960年確認了日記筆跡與已知的安妮·弗蘭克筆跡相同,並確定日記為真品。法庭判決后, Stielau撤回本來的言論,而奧圖·弗蘭克也沒有繼續追究。
1976年,奧圖·法蘭克控告法蘭克福的Heinz Roth,指他印發詆毀日記為贗品的小冊子,法庭其後判決Heinz Roth被罰款500,000馬克及監禁6個月。Roth其後提出了上訴,但他於1978年去世,而在翌年上訴也被駁回。
同年,奧圖·法蘭克也對Ernst Römer提出了訴訟,指他印發一本名為《暢銷書安妮日記的謊言( The Diary of Anne Frank, Bestseller, A Lie)》的小冊子。此案在法庭審訊時,一個名為Edgar Geiss的人在庭上派發此本小冊子,結果他也被起訴。法庭其後判決Römer被罰款1,500馬克,而Geiss則被判監禁6個月。在上訴后刑期雖然獲得減少,但此次案件卻因為奧圖·法蘭克後來對刑期的再度上訴,超過了當地有關誹謗的法律條例範圍而結束。
在奧圖·弗蘭克於1980年死後,安妮的日記包括書信與分散的頁紙,按他的遺願被轉交予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研究所後來在1986年委託荷蘭司法部對日記進行司法科學鑒定。司法部分析了日記的筆跡並與過往案例作對比,證實筆跡脗合,而日記上的紙張,漿糊與墨跡亦被確認為與日記撰寫年代脗合,最後安妮的日記正式被荷蘭司法部確認為真跡。後來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綜合研究結果與原稿及其它資料,出版了所謂的“評論性版”。於1990年3月23日,德國漢堡地方法庭對此版的日記進行了確認。
1991年,兩位大屠殺否定派學者羅伯特·弗里森(Robert Faurisson)與 Siegfried Verbeke出版了一本名為 《安妮的日記:另一面接觸(The Diary of Anne Frank: A Critical Approach)》的著作。這本著作宣稱日記由奧圖·弗蘭克撰寫,並提出日記內容有不少矛盾,質疑躲藏在隱密之家的可能性,以及文章風格及文筆與同年齡的青少年有別等問題。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蘭克之家與位於
瑞士巴塞爾的安妮·法蘭克基金,在1993年12月就上述著作動用民事法,禁止該書在荷蘭的進一步印發。於1998年12月9日,阿姆斯特丹地方法庭按原告要求,禁止任何否定日記及其內容真實性的印刷品出版,違者將被罰款25,000荷蘭盾(約11350歐元)。

在寫日記的安妮
在1957年5月3日,一群阿姆斯特丹市民,包括奧圖·弗蘭克,成立了安妮·弗蘭克慈善會(the Anne Frank Stichting)以拯救有被拆卸危險的隱密之家(舊Opekta Works公司大樓),並把大樓改建為安妮之家博物館,於1960年5月3日向公眾開放。博物館由Opekta公司的貨倉與辦公室和隱密之家兩部分組成,所有的傢具都已經被移走,使訪客能自由移動。而一些前住客的個人物品則仍被保留,如一些安妮貼在牆上的影星照片、奧圖·弗蘭克在牆紙上標示女兒身高的部 分、還有一幅記錄著同盟國進 度的地圖,這些東西都仍然保存完好。在一間曾經是彼得居住的房間里,有一條通往旁邊樓房鄰居處的通道,也被慈善會買下來併入博物館。這些房屋都曾用作收藏 安妮的日記,以轉換的展覽區來展示當時納粹迫害的影響以及當代世界的反對種族岐視暴力。安妮之家至今已成為阿姆斯特丹一個重要旅遊景點,在2005年當年 接待了965,000名遊客。博物館亦提供了網上導覽予不能前來的公眾,也舉辦了多國流動展覽。直至2005年,已有32個國家舉行過展覽,分佈於歐洲、亞洲、北美洲及南美洲。
1963年,奧圖·弗蘭克與他的第二任妻子,Elfriede Geiringer-Markovits,成立了安妮弗蘭克基金會作為慈善基金,以瑞士巴塞爾為總部。基金會籌募捐助經費使博物館“看來好一點”。直至奧圖·法蘭克逝世,他在遺願中表示把日記的版權留給基金會,但附帶條款是把每年需在版權所得收入中撥出80,000瑞士法郎予他的繼承人,其餘收入則由基金管理員決定如何使用。1963年基金會使用這筆收入,每年定期捐助給一個名為“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計劃中以作醫療用途。基金會亦致力教育下一代反對種族歧視暴力,曾在2003年借出安妮的部分手稿,於美國大屠殺紀念館作公開展覽。在同年的年度報告中,基金會也指出它們於德國、以色列、印度、瑞士、英國及美國亦開展著同樣的計劃。

安妮·弗蘭克
安妮一家在1933年至1942年間曾經居住於荷蘭Merwedeplein區的一所房屋,於本世紀初仍為私人所有,直至一部電視紀錄片公 開才開始受到公眾關注。雖然長期沒有保護及維修,但這所房屋被一家荷蘭房屋公司收購后,房屋公司根據以往法蘭克一家的照片,與安妮在信件中對傢具環境等的 描述數據幫助下,成功恢復到1930年代的舊貌。在過程中,安妮之家博物館的Teresien da Silva與安妮的表弟Bernhard "Buddy" Elias亦提供了不少意見。該所房屋已於2005年重開,提供予部分因不同原因,而不能於原居地寫作的被選作家以作棲身之所。每名被選的作家都有一年期 限於屋內居留或工作。首名被選的作家是阿爾及利亞籍的小說作家El-Mahdi Acherchour。
2007年6月,安妮的表弟"Buddy" Elias捐贈了約25,000件家居文件予安妮之家博物館。這些文件中,包括了一些弗蘭克一家在德國與荷蘭拍下的照片,以及奧圖·弗蘭克於1945年把前妻與女兒於納粹集中營中死去的消息告知母親的信件。
以安妮·弗蘭克的生命、日記、作品為靈感,後世也創作了大量以她為參考,或以她為主題的文學、音樂、電視及其它媒體作品。
奧托·弗蘭克於奧斯威辛集中營拘留期間倖存下來,戰後他回到阿姆斯特丹,在那裡他得到梅普·吉斯及丈夫揚·吉斯的庇護,並試圖尋回他的家人。雖然他知道他的妻子艾迪特已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中死去,但他仍希望兩個女兒仍然活著。幾個星期後,他得知瑪戈與安妮也死了,他嘗試去確定跟安妮有關朋友的命運,並得知當中很多人都被殺。在荷蘭製片人威利·連和於1988年拍攝的電視紀錄片《安妮弗蘭克的最後七個月》中,他訪問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生還者有關弗蘭克家中女性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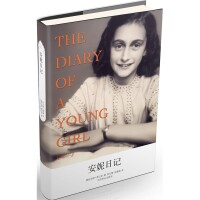
《安妮·弗蘭克日記》
安妮的日記由於公司女職員的保存而留了下來,之後公司的女職員又轉交給生存下來的奧圖·法蘭克,1947年安妮的日記便出版,成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奧圖在看過日記后,也表示從來也沒有想到安妮在日記中,對往日的生活狀況竟有著如此準確和良好的記載。基於安妮在生前曾多次提到自己的意願是成為作家,奧圖開始考慮把日記公開出版。在若干年後,當奧圖再次被問起對此事的感受時,他表示“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發現,.我從不知道她有這麼深刻的想法和感受,... 她從沒有表露過這些”。
開始時,安妮的日記都是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在裡頭強調了很多次她不容許任何人看她的日記。她聰明地形容了她的生活,她的家庭與同伴,他們的情況,同時又表明了自己希望寫小說出版的意向。在1944年春天,她聽到一個Gerrit Bolkestein做的電台廣播——他是一個荷蘭流亡政府的成員。他說當戰事結束后,他會籌組關於戰事荷蘭人民受壓迫的公共紀錄。他 也提起過出版信件和日記,所以安妮決定在那時交出她的日記。她開始修正她的作品,刪減某些部分,又重寫某些部分,希望終有一天可以出版。她原本的筆記本子已經用完了,開始寫另一本活頁簿。她為屋子裡的所有人起了假名,雲佩斯一家成為了賀文,比曹妮娜和彼得·雲丹,費茲飛化成為了艾拔·德素。奧圖·法蘭克用了稱為“A版本”的原日記,和稱為“B版本”的修改了的日記一起,出版了日記的初版。他拿走了幾篇文章,大多數是用不奉承的詞語形容他太太的,和一些形容 安妮對性的興趣的篇章。他恢復了他們一家的真實身份,但其它人依然沿用假名。
![安妮·弗蘭克[猶太大屠殺著名受害者]](https://i1.twwiki.net/cover/w200/m3/e/m3eb4bdcaf57e3d3b1354e49d35650105.jpg)
安妮·弗蘭克[猶太大屠殺著名受害者]
他把日記交給歷史學家安妮·羅美,她想出版日記的嘗試卻都不成功。然後她把日記交給丈夫,他從而寫了一篇關於日記的文章,叫“一個小孩的聲音”,於1946年4月3日刊在報紙上。他寫道:“日記結結巴巴地道出了一個小孩子的心聲,體現了法西斯主義的可怕,連紐倫堡審判都不及它。”他的文章引來了出版商的注意,在1947年,日記初版, 1950 年再版。美國的初版在1952年,書名稱為《安妮·弗蘭克:一個少女的日記》。在法國、德國、美國,日記的發行都大受歡迎;但英國卻是個例外,在1953 年便已停印。在日本,此書的發行極受注目及好評,初版賣出逾100,000本。而安妮·弗蘭克在當時的日本,也成為戰時受害的年輕一代的象徵人物。後來艾拔·赫吉把它改編成為戲劇,於1955年10月5日在紐約首次公演,後來贏了普立茲獎。1959年,日記被拍成電影,《安妮·弗蘭克的日記》 ,無論是評論還是票房都是非常正面。日子久了,日記的受歡迎程度也與日俱增,在很多學校,尤其是在美國,它被列入學校正規課程中,把安妮介紹給新一代的讀者。
1986年,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發表了所謂的“評論性版”日記。它包括了所有已知版本的比較,已修訂和未經修訂的都包含在內。它也包括了對日記真實性的討論,和附加的,有關這個家庭和日記的歷史資料。
1999年,安妮·弗蘭克基金的前主席和美國大屠殺紀念教育基金的主席瑞積(Cornelis Suijk),宣布他擁有被奧圖·弗蘭克在出版前拿走的五頁日記;瑞積說奧圖·弗蘭克在1980年臨終前把這幾頁都給了他。那幾頁,記下了安妮對父母關係緊張的婚姻的批評,和她母親對她的漠不關心。當瑞積打算賣出那五頁日記以替他的美國基金籌錢的時候,惹起過一番不小的爭議。而手稿的正式主人,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要求瑞積交出手稿。 2000年,荷蘭教育、文化及科學部同意捐出300000美元給瑞積的基金,2001年,手稿回到他們的手上。自此之後,五頁手稿都被收入日記的新版本中。
2021年11月24日,擔任編劇的電影《安妮日記》在法國上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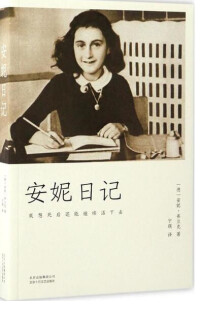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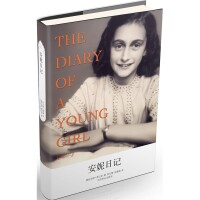
![安妮·弗蘭克[猶太大屠殺著名受害者]](https://i1.twwiki.net/cover/w200/m3/e/m3eb4bdcaf57e3d3b1354e49d3565010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