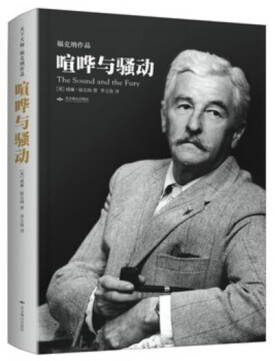共找到4條詞條名為喧嘩與騷動的結果 展開
喧嘩與騷動
福克納創作長篇小說
《喧嘩與騷動》(The Sound and the Fury)是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創作的長篇小說,創作於1929年。
該小說徠講述的是南方沒落地主康普生一家的家族悲劇。老康普生遊手好閒、嗜酒貪杯。其妻自私冷酷、怨天尤人。長子昆丁絕望地抱住南方所謂的舊傳統不放,因妹妹凱蒂風流成性、有辱南方淑女身份而愛恨交加,竟至溺水自殺。次子傑生冷酷貪婪,三子班吉則是個白痴,三十三歲時只有三歲小兒的智能。全通過這三個兒子的內心獨白,圍繞凱蒂的墮落展開,最後則由黑人女傭迪爾西對前三部分的“有限視角”做一補充。該作品採用了多角度的敘述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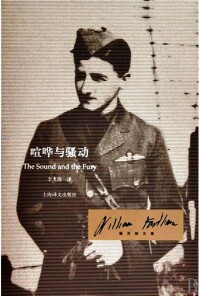
其他版本的《喧嘩與騷動》
康普太太自私冷酷,無病呻吟,總感到自己受氣吃虧,實際上是她在拖累、折磨全家人。她念念不忘南方大家閨秀的身份,以致僅僅成了一種“身份”的化身,而完全不具有作為母親與妻子應有的溫情,家中沒有一個人能從她那裡得到愛與溫暖。
女兒凱蒂可以說是全書的中心,雖然沒有以她的觀點為中心的單獨的一章,但書中一切人物的所作所為都與她息息相關。物極必反,從古板高傲、規矩極多的舊世家裡偏偏會出現浪蕩子女。用一位外國批評家的話來說,是:“太多的責任導致了不負責任。凱蒂從“南方女”的規約下衝出來,走過了頭,成了一個輕佻放蕩的女子。她與男子幽會,有了身孕,不得不與另一男子結婚。婚後丈夫發現隱情,拋棄了她。只得把私生女(也叫昆丁)寄養在母親家,自己到大城市去闖蕩。
哥哥昆丁和凱蒂兒時感情很好。作為沒落的莊園主階級的最後一代的代表者,一種沒落感始終追隨著昆丁。這個“簪纓之家”的孑遺極其驕傲,極其敏感,卻又極其孱弱(精神上、肉體上都是如此)。他偏偏又過分重視妹妹的貞操把它與門第的榮譽甚至自己生與死的問題聯繫在一起。凱蒂的遭遇一下子使他失去了精神平衡。就在妹妹結婚一個多月後,他投河自盡了。
關於《喧嘩與騷動》,福克納在1933年寫的一篇文章里說:“在這以前我寫了三部小說,輕鬆與愉悅的程度越來越少。那三部我足足推薦了三年,在此期間我把它往一家又一家的出版社投寄,懷著一種執拗而不斷破滅的希望,只想至少把它用掉的紙張與耗掉的時間的價值掙回來。這個希望最終也必定幻滅了,因為有一天突然像一扇門悄悄地咔噠一聲永遠關上,把我跟一切出版社的地址與書目隔絕了,於是我對自己說,此刻我可以寫了。此刻我可以不顧別的只管放開寫了......”
福克納是在1928年2月至10月寫成這部作品的。但糟糕的是,他原來的出版者又不願接受他的新作,幸而那裡的一個合伙人哈里森·史密斯獨具慧眼,願意讓自己剛參加進去新成立的一家公司出版。於是《喧嘩與騷動》這部小說在1929年10月7日由喬納森·凱普與哈里森·史密斯出版,發行量僅一千七百八十九冊。
班吉
《喧嘩與騷動》的開頭是由白痴的班吉敘述,時間是1928年4月7日,這天正好是他33歲的生日,但智力卻停留在3歲階段。他不會說話,只能用哭嚎表達自己的心情,極度地渲染了康普生家頹敗的氣氛。正如西方學者指出的,班吉首先不是白痴,而是人。由於班吉不受任何虛偽、世俗和功利的影響,他是最基本的人性的體現; 由於他只能索取,不能給予,對他的愛只能是無私和真誠的; 由於他是白痴,不能開口講話,人們以為他什麼都不懂,因此在他面前不需掩飾,直接展示出自己的本象。所以有評論家指出他實際上“是一面道德鏡子”,真實地反映周圍人的本性,或醜惡,或美好。不像隱形的中心人物凱蒂一樣,班吉出現在全書的主體四章中(附錄是時隔16年才添加的),所以在這個日趨落魄的貴族家庭中,父母、兄弟姐妹和傭人是如何對待他,以此讓讀者管窺南方社會落魄家庭及其滅亡的必然性。
徠凱蒂
在班吉這面鏡子里看到童年時候的凱蒂是一個純潔的、充滿愛心的、愛打抱不平的姐姐形象。步入青少年時候渴望追求愛情與幸福,但是由於沒有父母正確的引導,加上摯愛的兄弟(即班吉和昆丁)的阻攔失去愛情,自認有罪而走墮落的道路,為顧全家庭名聲無可奈何地嫁人。由此可見南方傳統的男性都希望和要求女性不要長大,要保持聖女的形象,如班吉在凱蒂使用香水,和男人親吻及失貞后都大聲哭嚎; 而昆丁更是無法忍受凱蒂的失貞,他向父親謊稱他同凱蒂發生了亂倫行為,不料被父親識破,他和凱蒂的情人達爾頓·艾密斯決鬥,在反對結婚無效后最終自殺。這種傳統壓抑婦女自然成長的觀念勢必引起自幼就有反抗精神的凱蒂的抗爭,她去尋找自己的愛情和幸福,但是最終無法抗拒來自親人的壓力,她妥協了,接受母親的安排跟一個自己並不愛的人結婚,不久就遭拋棄,只好忍痛割愛將女兒送回家,而自己卻無家可歸,淪落風塵。可見在傳統控制下的南方貴族家庭對婦女人性的摧殘,對青年一代的心靈的毀滅性影響。而且,凱蒂的失貞和淪落象徵了康普生家族玷污了的榮譽,從更深一層意義上講,象徵了美國南方社會的混亂與墮落。
昆丁
英語中,昆丁這一名字意為有勇氣。事實上,福克納筆下的那個昆丁一直也在努力扮演一個有勇氣的角色,他企圖超越現實,超越父親,努力捍衛自己家族的榮耀。在飽受巨大折磨的同時,昆丁也曾努力做出更有意義更積極的事迹,但由於缺乏膽量,他的種種企圖均以失敗告終。他想殺死凱蒂,自己的刀卻掉在地上;他想用亂倫的手段來“永遠監護她,讓她在永恆的烈火中保持白璧無瑕”,但這至多不過是“意念犯罪”,他根本做不到;他甚至與引誘凱蒂失貞的達爾頓決鬥,結果自己卻“像女孩子那樣暈了過去”;他步履維艱,執著地懷著南方人特有的眷戀之情和根深蒂固的信念去苦苦追索那些早已遠離的家族榮耀、純潔無暇的淑女觀和溫情脈脈的家族關係,然而殊不知,他所竭力追求的正是他的“地牢”。因此,他註定是失敗者,註定要承受厄運的鞭笞。
康普生夫婦
康普生夫婦對他們的兒子班吉漠不關心,康普生太太甚至覺得班吉是她的恥辱,是老天對她的懲罰。當班吉四歲時,她意識到班吉是個白痴后,馬上將他的名字由毛萊改為班吉明,因為毛萊是她弟弟的名字,她不想讓她的娘家蒙羞。她不僅不愛班吉,也不允許別人愛班吉。看到凱蒂抱著他,康普生太太說,“他太大了,你抱不動了。你不能再抱他了。這樣會影響你的脊背的。咱們這種人家的女子一向是為自己挺直的體態感到驕傲的。你想讓自己的模樣變得跟洗衣婆一樣嗎?”凱蒂還堅持要抱,她又說,“反正我不要別人抱他。都五歲了。不,不。別放在我膝上。讓他站直了。”班吉生日那天自己伸手去摸火被燙得哇哇大叫,康普生太太不僅不心痛,反而責怪迪爾西沒看好他,使她不得安生,看到迪爾西給班吉買的蛋糕,竟然說,“你是要用這種店裡買的蹩腳貨毒死他嗎?這就是你存心要乾的事。我連一分鐘的太平日子都沒法過。”——她非但不慶祝兒子的生日,還詛咒別人毒死他。
而康普生先生的虛無主義也給子女帶來不良影響。他性格軟弱,事業一無所成,家產殆盡,只能用酒精麻痹自己。所以當他把傳統價值觀念傳給孩子們時,同時又用自己的虛無主義破壞了它的基礎,使其在現實生活中失去意義。正是這樣一個缺乏愛,缺乏正確精神引導的家庭使得孩子們未能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未能直面現實生活,使得悲劇產生。在資本主義工商經濟的大環境下,這種傳統的南方種植園世家日趨分崩離析。
傑生
傑生從未關愛這個智障的弟弟,而且認為是個累贅,所以一有機會就甩掉這個包袱。他像他母親那樣誰都不愛,自私自利,而且損人不利己,報復心強,好面子,這一切正如小說題目所暗示的:他扭曲的人生充滿了喧嘩與憤怒,終了無所獲。福克納曾說: “依我看,從我的想象里產生出來的形象里,他是最最邪惡的一個。”但是,傑生的這種“邪惡”與他童年的孤獨、沒有得到應有的愛護和關懷以及受不平等對待等遭遇不無關係。小時候,昆丁和凱蒂都不跟他玩,父親不理會他,母親也只是口頭說他是唯一一個像她娘家巴斯康家的人。唯一愛他的大姆娣(奶奶)在他3歲時就去世了;家裡賣掉班吉的牧場給昆丁上哈佛和凱蒂辦婚禮后就沒錢送他上大學了;由於凱蒂的失貞,凱蒂的丈夫承諾給他的銀行職位也不了了之。所以,傳統因素較少的傑生就成為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投靠者,成為空虛的、沒有道德內涵的、自私、冷酷的實利主義者,可最終也免不了失敗的命運,淪為社會轉型期的犧牲品。
迪爾西
然而,黑女僕迪爾西卻自始至終都呵護著班吉,三十三年如一日照顧著他的吃喝拉撒,還時常喝令她的兒子和外孫照顧好班吉。在他生日當天,自己掏錢買蛋糕為班吉慶生,班吉燒傷了,趕緊給他上藥包紮。她稱班吉為“主的孩子”,在復活節當天,由於康普生一家人都不去教堂,她就帶著班吉去黑人教堂,認為“慈悲的上帝才不管他的信徒機靈還是愚魯呢”,希望可憐的班吉能得到拯救。
儘管迪爾西是一個忠心耿耿的黑人女傭形象,她仍然是一個正直無私、仁慈高尚而且有著堅定的道德原則的人。儘管是傭人,她卻敢於反對傑生的惡行,直斥他的冷酷無情。她信仰並身體力行基督教所頌揚的博愛與同情精神,頑強地支撐著日益敗落的康普生家庭。但是,在牧師虔誠的佈道中,她獲得啟示,說,“我看見了初,也看到了終。”這預示著康普生家族的解體。因為在復活節當天,康普生一家都在進行著與基督教無關的事情:傑生忙著追尋小昆丁,對一路上的信徒嗤之以鼻; 而康普生太太躺在床上,對擱在床邊的聖經都不曾觸摸;小昆丁帶著從舅舅家偷來的私房錢逃之夭夭。傳統的宗教道德信仰已變成虛無縹緲,甚至遭唾棄。康普生家庭的沒落、解體和死亡,部分原因是這一家都是沒有信仰的行屍走肉。
作為夫妻的康普生夫婦關係冷漠,相互鄙視。康普生先生對太太的嘲弄和羞辱可以從他當面對其弟弟毛萊的譏諷中看出,而康普生夫人則覺得自己出身高貴,嫁給家道敗落的康普生實在是太委屈了。兩人在管教孩子的問題上也總是意見不和,各持己見。康普生先生將祖傳的手錶連同時間是“一切希望與慾望的陵墓”的宿命論思想灌輸給了昆丁。正是父親的教誨使得昆丁時常感受到人生的絕望和前途的渺茫。對於班吉,康普生先生並沒有因為他心智不全而表現出更多的關愛和照顧。對於傑生,康普生先生採取的是冷落和漠視的態度。對於女兒凱蒂,康普生先生是比較偏愛的,卻忽視了對她的正確引導,任其隨意發展而不加管教。而作為母親的康普生夫人對孩子們缺乏最起碼的關心和愛心,從不為孩子們的幸福著想。四個孩子中除了傑生,她認為其他孩子“都不是我的親骨肉,與我一點關係也沒有”。她視智障的小兒子是上帝對她的懲罰,認為凱蒂從小就專門和她作對,相信昆丁的自殺是針對她的報復行為。昆丁在自殺前感嘆到“地牢是母親本人”。
在沒有愛與溫暖的家庭氣氛中生活的孩子們之間的關係充滿了矛盾和不和諧。幼年的傑生是父母冷戰的犧牲品。母親對傑生的偏愛造成他被其他孩子孤立的局面。當童年的凱蒂、昆丁和班吉一起玩耍時,傑生在遠一點的地方獨自待著。為了維護班吉的利益,凱蒂對傑生拳腳相加。在孤立環境中長大的傑生,缺少安全感和對他人的信任感,變得冷酷無情、憤世嫉俗。當家后的傑生對凱蒂的咒罵、譏諷和要挾是一種變本加厲的報復行為。在母愛缺失的家庭中。而這一系列問題所能導致的只有家族的沒落。
這種家族沒落的主題也是整個世界從傳統向現代轉型所必然產生的一個主題。福克納對“家族的沒落”這一可稱為現代小說的宏大敘事的具體處理方式更為複雜,就是說,同樣是處理“家族的沒落”這個世界級的大主。福克納的具體著眼點是他自己的,是打上了福克納的註冊商標的印記的,所以可能就是別人無法替代的。比如,福克納自己就曾說過《喧嘩與騷動》是一個關於“失落的天真”的故事。這主要是指小說中最核心的人物,家族的女兒凱蒂的墮落的故事。她只得把私生女寄養在母親家,自己到大城市去闖蕩”,所以福克納說:這本小說是“兩個墮落的女人,凱蒂和她的女兒的一出悲劇”。在這出悲劇中,福克納更關注的是家族,或者他的小說人物究竟具體“失落了什麼”。而所謂的“天真”,正是他具體關心的母題。也正是在這一點上,福克納匯入的,其實是美國文學自己的傳統。而福克納關懷“失落的天真”的主題,也正是從傳統的道德法則和秩序的角度看問題的,這表明了福克納的傳統的一面。但是福克納所說的“失落的天真”並不能概括《喧嘩與騷動》的全部主題。
美國學者一個叫俄康納的學者同時把這部小說當作“一個家族溫暖消逝,自尊和體諒蕩然無存的描繪來讀”。而進一步引申下去,《喧嘩與騷動》又是一個南方的故事,一個二十世紀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關於“現代”的故事。前面我們是把小說中的女兒凱蒂當作主角。我們可以說它是關於“失落的天真”的故事,如果把《喧嘩與騷動》當作一個以昆丁(凱蒂的哥哥、哈佛大學的學生,是個自殺身亡的人物)為主角的故事來看,《喧嘩與騷動》就成為一個對於現代主角的探討的小說,通過對昆丁內心流程的挖掘,來表達某種現代意識,因此,美國一評論家稱福克納是“迷路的現代人的神話”的發明者。在這個意義上,福克納豐富了二十世紀現代小說關於“現代”的構成圖景。這個現代是卡夫卡的現代,是普魯斯特的現代,是喬伊斯的現代,也是福克納的現代。每個人的現代景觀其實都不盡相同,但起碼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這些大師都表現了現代人的希望與恐懼,憂患和矛盾。而福克納的矛盾似乎比其他人來得更複雜。而且,讀福克納總帶給人一種陰鬱甚至痛苦的感受。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另一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繆在1955年稱讚福克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是我們時代唯一真正的悲劇作家。……他提供給我們一個古老的但永遠是新鮮的主題:盲人在他的命運與他的責任之間跌跌撞撞地朝前走,這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悲劇主題”。
從《喧嘩與騷動》中,可以還看到福克納對生活與歷史的高度的認識和概括能力。儘管他的作品顯得撲朔迷離,有時也的確如痴人說夢,但是實際上還是通過一個舊家庭的分崩離析和趨於死亡,真實地呈現了美國南方歷 史性變化的一個側面。可以看到,舊南方的確不可挽回地崩潰了,它的經濟基礎早已垮台,它的殘存的上層建築也搖搖欲墜。凱蒂的墮落,意味著南方道德法規的破產。班吉四肢發達,卻沒有思想的能力,昆丁思想複雜,偏偏喪失了行動的能力。另一個兄弟傑生眼睛里只看到錢,他乾脆拋棄了舊的價值標準。但是他的新的,也即是資產者們的價值標準,在作者筆下,又何嘗有什麼新興、向上的色彩?聯繫福克納別的更明確譴責“斯諾普斯主義”(也就是實利主義)的作品,有理由認為:《喧嘩與騷動》不僅提供了一幅南方地主家庭(擴大來說又是種植園經濟制度)解體的圖景,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有對資本主義價值標準的批判。
多角度敘述

康拉德
在《喧嘩與騷動》中,福克納讓三兄弟,班吉、昆丁與傑生各自講一遍自己的故事,隨後又自己用“全能角度”,以迪爾西為主線,講剩下的故事,小說出版十五年之後,福克納為馬爾科姆·考利編的《袖珍本福克納文集》寫了一個附錄,把康普生家的故事又作了一些補充。因此,福克納常常對人說,他把這個故事寫了五遍。當然,這五個部分並不是重複、雷同的,即使有相重疊之處,也是有意的。這五個部分像五片顏色、大小不同的玻璃,雜沓地放在一起,從而構成了一幅由單色與複色拼成的絢爛的圖案。
作為其中的敘述者之一,班吉(那個白痴)起到了較為重要的作用。“班吉的部分”發生的時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通過他,福克納渲染了康普生家頹敗的氣氛。另一方面,通過班吉腦中的印象,反映了康普生家那些孩子的童年。“昆丁的部分”發生在一九一〇年六月二日。這部分一方面交昆丁當天的所見所聞和他的活動,同時又通過他的思想活動,寫凱蒂的沉淪與昆丁自己的絕望。“傑生的部分”發生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這部分寫傑生當家后康普生家的情況,同時引進凱蒂的後代——小昆丁。至於“迪爾西的部分”,則是發生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復活節),它純粹寫當前的事:小昆丁的出走、傑生的狂怒與追尋以及象徵著滌罪與凈化的黑人教堂里的宗教活動。這樣看來,四個部分的敘述者出現的時序固然是錯亂的,不是由應該最早出場的丁先講,而是採用了“CABD”這樣的方式,但是他們所講的事倒是順著正常的時序,而且銜接得頗為緊密的。難怪美國詩人兼小說家康拉德·艾肯對《喧嘩與騷動》讚歎道:“這本小說有堅實的四個樂章的交響樂結構,也許要算福克納全部作品中製作得最精美的一本,是一本詹姆士喜歡稱為‘創作藝術’的毋庸置疑的傑作。錯綜複雜的結構銜接得天衣無縫,這是小說家奉為圭臬的小說——它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創作技巧的教科書……”
意識流
“意識流”是福克納採用的另一種手法。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中也常寫人物的內心活動,意識流與之不同之處是:一、它們彷彿從人物頭腦里涌流而出直接被作者錄下來,前面不冠以“他想”、“他自忖”之類的引導語;二、它們可以從這一思想活動跳到另一思想活動,不必有邏輯,也不必順時序;三、除了正常的思想活動之外,它們也包括潛意識、下意識這一類的意識活動。在《喧嘩與騷動》中,前三章就是用一個又一個的意識,來敘述故事與刻劃人物的。在敘述者的頭腦里,從一個思緒跳到另一個思緒,有時作者變換字體以提醒讀者,有時連字體也不變。但是如果細心閱讀,讀者還是能辨別來的,因為每一段里都包含著某種線索。另外,思緒的變換,也總有一些根據,如看到一樣東西,聽到一句話,聞到一種香味等等。據統計,在“昆丁的部分”里,這樣的“場景轉移”發生得最多,超過二百次;“班吉的部分”里也有一百多次。傳統的現實主義藝術,一般都是通過外表(社會、環境、家庭、居室、傢具、衣飾……)的描寫,逐漸深入到人物的內世界。福克納與別的一些作家卻採取了顛倒的程序。他首先提給讀者混沌迷亂的內心世界的沒有規律、邏輯的活動,然後逐步帶引讀者穿過層層迷霧,最終走到陽光底下明朗、清晰的客觀世界里來。這時,回過頭來一看,會對整幅圖景具有更深刻的印象與理解。
《喧嘩與騷動》的第四部分沒有用意識流手法,回到了傳統的第三人稱敘述法,這也是頗具匠心的。在文字風格上它也與前面不同,我們從第一段便見到了一種冷峻、客觀縝密與繁複的風格。在前面三部分里,見不到人物的外形,現在,人物的形影變得清晰,連周圍的環境、氣候、光線、亦莫不如此。文字的節奏也從容、舒緩,宛如一部樂曲表情標記為“Adagio lamentoso”(柔板,哀傷的)的“終曲”。這個部分是前三部分的平衡。前面的抽搐、痙攣與悸動,憤怒與仇恨,至此通過迪爾西這一形象描寫,變成寧靜與平和,宛如離開峻險山嶺的急流,進入平原,自然地日夜流淌。黑人老女傭迪爾西是家中唯一的健康力量。她的忠誠、堅韌、毅力與仁愛,特別是清醒的判斷和具有歷史意識的智慧,讓人感到踏實。這溫暖更具體地體現在她操勞的廚房,那裡連火焰都在歡樂的歌唱,而碗櫃高處掛著的掛鐘“在發出幾聲嗽喉嚨似的前奏前奏之後,它敲了五下。”在福克納筆下,迪爾西無疑是美國南方歷史的見證人,也是智慧的化身。小說中寫到了復活節,讓人想到作者是不是像暗示基督的復活。不過迪爾西所體現的非基督肉身的復活,而是體現了基督教本意的人性的復活。
神話模式
“神話模式”是福克納在創作《喧嘩與騷動》時所用的另一種手法。所謂“神話模式”,就是在創作一部文作品時,有意識地使其故事、人物、結構,大致與人們熟知的一個神話故事平行。如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就套用了荷馬史詩《奧德修紀》的神話模式,艾略特的《荒原》則套用了亞瑟王傳說中尋找聖杯的式。在《喧嘩與騷動》中,三、一、四章的標題分別為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至八日,這三天恰好是基督受難日到復活節。而第二章的一九一〇年六月二日在那一年又正好是基督聖體節的第八天。因此,康普生家歷史中的這四天都與基督受難的四個主要日子有關聯。不僅如此,從每一章的內容里,也都約可以找到與《聖經》中所記基督的遇大致平行之處。但是,正如喬伊斯用奧德修的英雄業績反襯斯蒂芬·德迪勒斯的軟弱無能一樣,福克納也是要以基督的莊嚴與神聖使康普生家的子孫顯得更加委瑣,而他們的自私、得不到、受挫、失敗、互相仇視,也說明了“現代人”違反了基督死前對門徒所作的“要你們彼此相愛”的教導。
福克納運用這樣的神話模式,除了給他的作品增添一層反諷色彩外,也有使他的故事從描寫南方一個家庭的日常瑣事中突破出來,成為一個探討人類命運問題的寓言的意思。
《喧嘩與騷動》是美國南方文學領軍人物威廉·福克納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是第一部為作者帶來盛譽的作品,也是作者的得意之作,也是福克納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也是福克納心血花得最多,他自己最喜愛的一部作品。該書在出版了多年之後,才因其複雜的結構和令人迷惑的內容而引起極大的關注。小說表現了福克納先進的寫作意識和創造性思維,成為批評家爭相研究的對象。評論家從不同的角度對該小說做了多方面的研究。
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福克納的人物就像面朝後坐在一輛賓士的汽車上,未來看不見,現在十分模糊,而過去看得很清楚。”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1897年9月25日-1962年7月6日),美國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意識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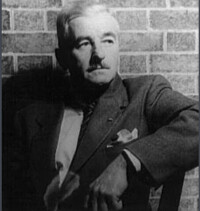 文學在美國的代表人物,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獲獎原因為“因為他對當代美國小說做出了強有力的和藝術上無與倫比的貢獻”。
文學在美國的代表人物,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獲獎原因為“因為他對當代美國小說做出了強有力的和藝術上無與倫比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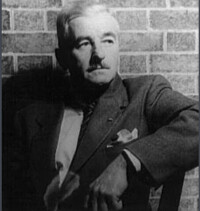
喧嘩與騷動作者
他一生共寫了19部長篇小說與120多篇短篇小說,其中15部長篇與絕大多數短篇的故事都發生在約克納帕塔法縣,稱為“約克納帕塔法世系”。其主要脈絡是這個縣傑弗生鎮及其郊區的屬於不同社會階層的若干個家族的幾代人的故事,時間從1800年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系中共600多個有名有姓的人物在各個長篇、短篇小說中穿插交替出現。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喧嘩與騷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