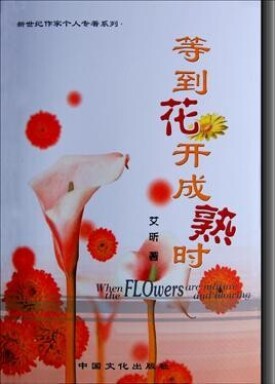等到花開成熟時
等到花開成熟時
文中男主人公以搞笑的方式登場,在對自己生活的陳述回憶中,將曾經的心情以花的物語來代替。主人公與靈兒的愛情與金濤等人的兄弟之情,無不帶給人感動,開頭幾章雖然不加修飾直白幽默的寫出了現實的生活,在看似荒誕的故事中,作者用幽默的伏筆埋下了沉重的包袱,此部作品被譽為80后冷傷感文學著作。讓你看後有一種不自覺地心痛!
序 在花開的那年,呱呱墜地
迷惘的雙眸,季候花開似夢的南國,溫柔旖旎的太陽每天在我左邊高高爬起來微笑,又在右邊沉重不舍地作別。
從此,月圓如詩,月缺如畫,那些在身邊發生的故事,那些陪伴我長大成熟的人,最後通通被深埋進了十九歲那個美好得讓人心碎的流年裡。
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一個良家婦女,就是我老媽。
夢見我的曾祖父在她面前正手腳並用地掰著西瓜狂啃,老媽“噔”一聲跪在他面前連磕了九個響頭,淚如泉湧地哀求這第四胎就保佑讓她生個男孩來著,因為前三胎都是接二連三的千金,老媽都給千金怕了。
曾祖父嘴裡堵塞著西瓜出不了聲,只有瞪大著眼對老媽一個勁地點頭。
老媽醒來后即刻感覺肚子發作,匆忙送入醫院后,從護士手裡抱出一個天生麗質的小男孩,那小男孩就是在我媽肚子里禁錮了十個月後悶得發慌硬闖出來的我。
可惡的是老媽根本沒有民主主義概念,竟然趁我尚未有任何發言權硬給我取下“點點”這個名字,理由如她正氣凜然地跟我解釋,說我乃是曾祖父那一點點頭才賜予我下凡的,所以經全家人一審通過,不許上訴,取名——易點點。
我從小就在黑暗陰影籠罩下艱難長大的。
我的童年極不童真。周圍的孩子們都不跟我玩,他們還總跟身邊的朋友對我指手劃腳說我是個超級大衰神,聽說當年抱我出來的那個年輕處女護士第二天被意外檢查出懷孕了,而且還是三胞胎來的。說誰跟我在一起誰倒霉。
哇靠!這是什麼理由啊!
真是天方夜潭!
那個護士懷孕關我屁事,我當時屁大的孩子連自個性別都還沒來得及探個究竟呢,我做個啥孽啊我?
我衰神?我衰神怎麼不見跟我親密無間的家人有事啊?
雖然在慶祝我滿月那天,順便也慶祝了我父母雙雙英勇下崗。
兩周歲時,天資國色的大姐被一“青蛙”給勾搭上了,但怎麼著他也不是一隻普通的青蛙,他有錢,是一隻鍍了金的青蛙王子來的呀。
我記得第一次咧嘴笑是在三歲的那年,那時二姐和三姐逗得我忍不住“咯咯”笑,見她們當時那麼高興,我便打鐵趁熱的對她們再狂笑多幾聲。
第二天,二姐和三姐在醫院被檢查出聽覺功能暫時性衰竭症。
從此,我家人一見我剛一裂嘴正準備露出天真的笑容來溶解這個冰冷無情的世界時,他們就很有默契的“嗖”一聲圍到我身邊,幾隻大手同時按在我的嘴巴上,好幾次差點把我給弄死過去了,我當時就在想,抗洪救災那會咋就不見你們這般英勇,難道我有比災難還恐怖嗎?
我媽也曾居安思危的安慰我說:“孩子啊,你別理外界的眼光怎樣,你始終都是媽的命根,媽愛你。你也要諒解一下,你媽我現在正芳年華月的,還不想那麼早就玩完,以後就千萬別對你媽笑了,啊?”
因為從小就遭人排斥,所以我的童年也就只有小說肯與我為伴了。
而且養成了個看小說的怪癖,習慣一行字一行字細細的看,邊想像著裡面角色的情感,腦際里彷彿身臨其描述的場境,嚼磨著每一句對白的味道,可能是一直孤獨導致感情變得異常細膩吧,時常隨著小說的主人翁悲喜情節而時刻牽動著情緒。
唉…真是墮落墮得不亦樂乎了。
可是,小草的生命力是頑強不屈的。
我在風風雨雨下依然長成個一米七五,帥氣陽光的年輕小夥子。回憶起過去一路走來的艱辛生長曆程,真是不容易啊……
人總是要向前看的,過往的就當發一場惡夢算了。
雖然我一直都是衰神在身邊庇佑著,可欣慰的是認識了同寢室的三個知己損友,與我在學海無涯里同舟共濟。還順手牽到幾片MM的芳心。
我阿彌陀佛!還算對得住曾祖父對老媽的那一個點頭把我帶到這世間來烏煙瘴氣一番嘍。
第三十九章 折萼
聽過花萼被折斷的脆音嗎?看過花萼折損在黃土的凄涼嗎?
桃花柳綠,草長鶯飛,在那個風清迷人的季節,花萼,是為了誰而堪折了?
“你們喝不喝可樂啊,我去買。”
“不會不好看吧?”小強的眼光透過玻璃鏡片急切地問我。
我皺著眉對他的臉好好琢磨了一陣,才搗搗頭真心地稱讚:“嗯,這雞滿帥的,起碼沒有禽流感。”
小強摘下那幅長型的黑邊眼鏡,閉上眼用兩隻手在額頭上輕輕按摩,徐徐地說:“我也不想戴眼鏡的,好麻煩,不過眼睛越來越模糊了,昨天去檢查,才知道有兩百多度了,唉,天妒英才啊。”
“嘿,英才?英勇的蠢才么?”
小強把手中的一本書直甩過來,被我接了個穩穩噹噹,我拍了拍那本厚厚的《化學研究》,笑著說:“幹嗎那麼拚命呀?”
“你是說那個嗎?”小強指著我手裡的書繼續說:“沒辦法呀,反正閑著也是閑著。哎,我看那些研究生特拽,心裡有些不順,所以我投入一點,以後也考出個研究生來,好在你們面前也拽一拽,讓心裡平衡平衡。”
“靠!說得像要升仙似的。”我很是不屑地打擊他:“就你這幅德性,還考研究生?那我還混什麼吃呀?不行,我也要投入到學習來了。”
說完坐下來翹起腿捧著本《化學研究》看。山仔半眯著眼一字一頓地對我說:“點點,你剛才不是說要請喝可樂么?學我健忘啊?”然後自己哈哈大笑了起來。我凝視著山仔那單純的的笑容,假如我忍心告訴他,說我前幾天陪文君去墮胎,而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不知道,他單純的笑容將會如何改變,抑或是從此殆失在了他的錦瑟年華里吧。
“點點,”山仔摩拳擦掌地不斷用舌頭舔嘴唇,笑眯眯地對我講:“我們好像好久沒那個了?”
我一聽這話馬上氣得跳起來大罵:“靠!你少說模糊不清的話好不好!人家不知情會以為我和你有什麼不尋常關係的,你小子是想說要喝酒是吧?要喝酒就說白了唄,什麼叫做這個那個的!”
山仔被我罵得委屈地低下頭嘀咕:“咱們都這麼熟悉了,用起暗號比較爽嘛。”
小強趴近我也摩拳擦掌的,抬了抬眉毛兩眼發光說:“是呀是呀,咱們是好久沒喝酒了。”
“去,”我鄙視地看著他們說:“瞧你們兩個那德性,提到酒份子上就像見了你們奶奶一樣親切,哎呀,廢話少跟你們說了,我下去搬一箱上來。”
說完嘿嘿笑地走出去。山仔卻在背後大聲叫喊:“點哥,就我們三個人了,不用買那麼多。”
我停住了腳步,心裡緩緩滋生出毛茸茸的感覺,而且越發地膨脹,鬱悶得快要窒息過去。然後又一步一步地蹀躞而去,隱隱約約聽到小強在細聲責怪山仔的語音。
當我奔跑到喘得不成樣子時我才停歇下來,邁著小步徐徐地走。
餘暉和煦地潲遍全身的每一寸肌膚,頂上的那片雲兒在悠閑舒展,老樹新樹鬱郁芊芊,把長草雀躍青翠的園地團圍得嚴密整齊,數以千計的鳥兒隱蔽在蔭綠的葉群里肆無忌憚地啁啾不息。
“聽說那個叫金濤的有錢公子哥因為愛滋病自殺死了。”
“那種人早就應該死了。”
“嘿,妒嫉他呀?是不是妒嫉他在學院泡了你的妞呀?”
“泡個屁!我去妒嫉個死人?老大,你說那小子會不會因為身邊的女人太多了,自己又是個性無能,所以自殺了。”
“哈,操你娘的,分析得真合我意。”
然後他們大笑著突然就僵硬了臉。我面無表情地直直站立在他們面前,風吹得乾淨的白襯衣扯裂般響,六雙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我。
那個頭髮弄得很花哨的大個子從草地上站起身,跋扈輕蔑地斜著臉看我,五官俊逸,只是滑潤的臉頰有道大煞風景的疤痕,細細長長卻不明顯,像似以前被尖刀劃過留下的。
他走近我,把兩隻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滿臉的譏嘲:“操你娘的我認識你,跟金濤住在同一狗窩上的對不?怎麼?聽得不服氣呀,我們這裡可有六個人,你敢動……”
我提起右腳對準大個子的肚子就使勁蹬過去,他防不勝防被我踹得退後了幾米遠,彎曲著腰捂住肚子痛得吡牙咧嘴,伊呀呀咒罵著:“操你大娘的,懂不懂規矩啊你,一句話都不說就動手,他媽的,讓你下半輩子跟輪椅一起過。”
然後五張凶神惡煞帶著有些譏嘲的臉立馬圍住我不斷地逼近,我站在原地臉上依然沒有情緒,心跳卻像剛跑完田徑比賽回來一樣竄個沒停。
媽的,今天豁出去了,頂多就是明年清明叫人燒多些冥紙給我。我使盡全身力氣,驀地就向最沿近的那張臉一拳掄過去,接著馬上回過頭把一個身材嬌小的一腳踹到樹下邊歇息去。
可是當我把右邊的人推倒下去,卻被左邊的人踹倒在地上。我爬起來捏緊拳頭揮向前邊的大個子,又被背後的人拉拽住了手臂,然後大個子像報血海深仇似的往我胸膛就一大拳直捶下去,那一瞬間我恍惚看到天光在泯滅,肋骨裂斷開似的痛。
我捫住胸口整個身體癱靠到了牆角匆促地喘氣,咬緊牙忍耐著裂肺的疼痛,冰冷的汗水不停的從額頭滲出來大顆大顆地滑落。
他們還一步步向我不斷地逼近著,臉上是陰森森的微笑,看來這幫沒人性的,真的想把我打到輪椅上去過日子了。
突然六個人像見到寶藏似的一齊向我沖跑過來,我閉上眼睛手忙腳亂地應付了一陣就在牆角蹲了下去,蜷曲著身子,兩隻手抱緊了整顆腦袋,雙膝擋護住胸前。
媽的,我想,反正就後背保不了了,要是喜歡就拿去練拳練到你良心過不去。想要把我打成殘廢?還不是一個容易了得的。
結果如我所願,從天而降的拳打腳踢如雨點一般“咚咚咚”快速頻繁地砸落到了我背上。
我埋著頭痛得不停地吡牙咧嘴,我知道要是再讓這幫殺千刀的砸背如敲鼓一樣擂下去,我一定得被他們打瓜過去的,可是現在全身又已經提不上一丁點兒力氣來反抗了。
於是我想到了三十六計,正琢磨著怎麼走為上策,拳頭就突然停止了擂背。
我手腳懈怠地癱躺在牆角,全身的骨骼像剛被人拆卸下來然後重裝上去的一樣渙散。
我呼出口氣,擦了把朦朧的眼才看清楚小強正跟那六個人渣在搏鬥,我刻不容緩地掙扎著站起來,閉上眼整個身子跳撲了過去。
睜開眼睛的時候見到有兩個被我壓在地上哀嚎,我稱心滿意地拍拍手爬起來轉過身,卻迎面一團黑壓壓擋住視線的拳頭狠掄了過來。
我猝不及防地被揍迎上臉,腳軟地後退了幾步接著一個趔趄,感覺天昏地轉的,眼前的一切暗朦了下來。
我一隻手托撐到了樹榦上,使勁地左右甩了甩頭,在這個時刻,我不能不清醒。
鼻子酸痛得很難受,於是我想用另一隻手揉揉鼻子忍住痛,卻沒想摸到了一手掌清稀的鼻血,低下頭看到原本潔凈的白襯衣,前襟已經被染紅透了的斑斕,粘乎著胸膛,血還在不停地從鼻子翕忍滴流下來。
我連忙用衣襟擦了下鼻子,抬起頭。
“啊~~~”一陣撕心裂肺的慘叫聲震裂了耳膜,數以千計的鳥只被恫嚇得紛紛應聲飛竄出密匝的葉群,嘰喳著愴涼地叫,匆促地在蒼穹四處悲鳴逃難。
我被眼前靜止無聲的畫面驚攝了魂,瞠目結舌的學生以我們為圓點,圍成了一圈密不透風的人牆。
躺在草地上掙扎的大個子頭髮亂蓬蓬的一團糟,兩隻手掌死死疊按住右眼,紅澄澄的鮮血從他的手掌下和指縫中不斷迅速地溢冒出來,身旁的長草被渲上了一大片斑駁的血紅,從草莖流進根部滋潤,歇力的兩隻腳在沒有方向地蹬上蹬下。
小強獃獃凝結了在原地,愣盯著草地上那一漬滲透入地面的鮮血,雙手還是緊緊抱住那顆尖利的硬石。
我即時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我嘶啞了聲音對小強大吼:“快放下石頭!快放下啊笨蛋,快走,快走啊~~~”
喊完鼻血就流進了嘴裡,又涌流了出來。
我想跑過去拉住小強逃離的,可是發抖的雙腿像被地上的藤條纏住了,一步也動彈不了。
忽然有幾隻強勁的大手把我的胳膊往背後拉直,壓住我的前身彎下腰。
然後兩個警察從小強後面的人群中擠出來,奔跑過去拽住小強的手臂反輾到腰后,接著壓倒在地上,發寒光的手銬冰涼地銬住了雙手。他們用手緊緊把小強的腦袋按貼在草地,翠嫩的小草從他眼前長出來。
他沒有抗拒被捕,他只是把貼緊草地的臉側翻過來,兩隻眼睛直直地看著我,眼神跟我一樣驚惶失措的悲哀。
周圍的喧嘩嘲哳我都淡漠得渾然不覺,在我的耳內一直回蕩的是那群老鴉掠飛過時的哇哇聲夾摻著小強悠長沉重的喘息……
第四十章 花,灰暗
你在雲上,我在雲下。你憂傷空濛的眼角噙含不住那一滴淚,在穹蒼晶瑩剔透地悠轉著墜落,濺碎在了我脆弱的心窩,滋潤了我的雙眼,從影子氤氳出來潮濕的灰暗,你是否也能夠感覺得到了呢?
全世界都在沉默,眼帘逃離不開寬長灰暗的四面空牆,孤寂老舊的長桌陪在我面前噤言等待,一盞老燈在頂上輕輕晃晃曳曳,頹廢落寞的燈線闌珊灑瀉下來,從此把灰暗凄涼的身影,用廉價的蠟筆描繪在了生活的空白紙張里。
我的喉嚨被東西卡噎得說不出一句話來。當出現在我眼前的小強,一身淀藍色的監獄制服,襤褸落拓地徐徐彳亍在我對面坐下來,懨懨地低下了頭,久沒梳理而塵膩的頭髮油漆漆蓋掩住蒼白的臉頰,遮蔽了凹陷空洞的兩隻眼睛,青黑的鬍渣子詵詵侵滿了乾裂的嘴唇邊的每一處毛孔。
當我看到這樣髁瘦沮喪的小強,我真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剛才在來探望的路上琢磨排序的台詞,剎那在腦際殞亡殆失。
我想到的只是,只是幾天前還在我面前兩眼發光,說要考個研究生在我們面前拽一拽的那個小強,那個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的小強。
我凝視著他的灰暗,心裡翻湧一陣一陣的難過。
我們就這樣,沉默地靜靜坐了很久很久,讓這個世界繼續寂靜踽涼下去。
小強緩緩抬起頭看著我,額前幾縷卷粘在一起的髮絲在獃滯無神的雙眸前輕盪。我看到了他滿臉的淚水在滑落,他壓低著嘶啞的聲音伴著哭腔跟我說:“我好難受,在這裡的每一天我都好難受,我想你們,我真的好想你們……”
然後他驀地在我面前趴了下去,哭泣得很大聲,哭得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對準了我的心臟直刺下去,抽出來再刺進去,直到血肉模糊,才把它扔棄到荒涼的天涯旮旯,讓它慢慢地掙扎顫抖,讓它慢慢地殘喘死掉。
當我走出大門的時候,我又回過頭去,看著那高高的樓廈。不知道在眼前的這個四四方方的世界,它的過去,現在,將來,到底會囚禁多少振翅欲飛的心呢?
陽光很是柔軟,我的眼卻有些疼痛感。
昀日像初嫁的新娘,躲匿在湛湛的雲層背面,露出半邊臉來偷窺這個不停在瞬息萬變的世界,兩隻蝴蝶繾綣繞圈從我仰著臉的眼前低低飛過,我突然覺得很美,很簡單的一種唯美。
於是我靠在街牆坐到地上來,依然仰著臉,獃獃地凝視著這片溫柔的天空。
街上紛紛擾擾的行人從我面前路過,他們都要一邊懷著各種表情斜低下頭來打量我。
我不管,我依然一臉的淡漠,就算他們路過會誤會地施捨下錢,我也不管,我只想一心品賞眼前的那一片美,而那些帶著奇異的目光匆匆從我面前走過的人,他們卻忽略了只要一抬頭就可以看到的這一片天空。
回到學院的時候,偌厚的雲層已經把太陽囫圇吞沒了,天灰暗得像就要壓塌下來一樣。
佳佳娉婷地佇立在宿舍樓下,高高的柱燈照下一個孤孤單單的影子在搖曳。我走近她,兩張臉瀰漫著的同樣是憂傷在瀲灧。
我努了努嘴,仰望上天空,尋找不到那片潔凈的雲朵,鳥群從眼前低低急速飛翔而過,我低下頭對佳佳說:“快下雨了,怎麼還不回去?”
“我在等你。”佳佳緩緩抬起頭,眼眸里彷彿永遠都是那片絲毫不起的漣漪的純情。
“嗯?”我頓了頓,彷彿想起了什麼,抿了一下嘴唇說:“喔。小強他,還好,嗯,判了三年……”
我的嘴唇還在繼續顫,連我自己都聽得出最後那句“判了三年”是抖摟著唇牙說出來的。
“哦,麻煩你記得幫我問候他一下。”好平淡的口氣,接受又突然變得有些慌亂,連說話也在斷隙:“我來是想問你,金濤……是這樣的,就是……我……就是其實我一直都在等,我一直都在等金濤到我面前說一次‘我還愛你’,在我心目中他不是什麼花花公子,他從來沒有對我說過‘我愛你’,在分手的那一天他很堅決,可是在他轉過身我就看到了,我看到了他的淚落到了地上……可是以後,我在等待的東西,他都給不到了,我……我不明白他為什麼那樣傻……”
傻?也許總能輕易把‘我愛你’掛在嘴邊的人,那才叫高明的吧?或許對他看來,‘我愛你’這三字從口裡說出來后的份量會變得縹緲沉重,因此他才會格外小心翼翼地去愛你。
他知道,他脫口而出的三個字,簡單透明,她卻會從此把它鑄鏨進心碑,一生一世永不漫漶。所以,他決定不在嘴上愛她,他把她包裹到心底處去愛了。
我平靜地聽佳佳倉促地說完話,然後低下頭咬了下嘴唇,才抬起臉看著她問:“佳佳,你想問我什麼?”
佳佳瞬時反而愣住了,接著兩隻眼睛也失去了光彩,低下臉在我面前輕輕搖了搖頭。
“那,我上去了,你也該回宿舍了。”說著我走過了她的身邊,嗅到悵然的氣息,我停住了腳步,呼出一口氣轉過身對著佳佳的背影問:“你的一個高中同學他喜歡了你六年,你知道嗎?”
佳佳的身影有了一些愕然的反應,然後只是背對著我搖頭。
“喔,”我又轉回身子,走了兩步又停了下來,狠狠扼了把手腕,心裡鬱悶得半死,然後背向著佳佳,把臉仰上天空,用很輕的語氣悠悠說:“你們分手的那一夜,我們都喝醉了,後來金濤躺在我身旁,他趴在我耳邊跟我說,”那一晚,滿地的玻璃瓶,他躺在地上潮紅的臉,趴在我耳邊醉醺醺說著斷斷續續的話,那些片段,串連成一截錄音帶,不斷地在我腦間掠播過,敘說著你我他的故事:“他說他真的喜歡他,他想,他真的想,畢業后娶你過門的。”
說完我再沒有回過頭就一步一步向樓梯走上去,一步比一步沉重。
走到寢室的時候,聽到了淅淅瀝瀝的碎音。我站在陽台俯望下去,到處籠罩著白茫茫的一片,燈照下孤單的影子還在繼續搖曳。
然後我看到她慢慢地蹲了下去,好像在電視里播放的慢鏡片,她的左手緊緊捏握住右手肘垂放在雙膝上,埋著頭抽泣,任雨滴打在她顫抖不停的雙肩,跟著周圍芊郁的花草潮濕在了一起。
我想送一支傘下去給她的,可是,她的另一片天空也許也在下雨呢。那麼,我的傘,無法足夠撐擋她甘霖滂沱的心雨,她就不需要了吧。
於是雨漸漸下得大了起來,迅速地從眼前墜落下去。孤單搖曳的影子跟著也漸漸朦朧了,最後被雨湮滅了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