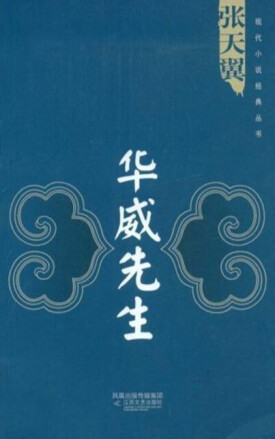華威先生
張天翼著短篇小說
《華威先生》是現代作家張天翼創作的一部短篇小說,發表於1938年第1卷第1期的《文藝陣地》半月刊上,后收入小說集《速寫三篇》。
國民黨官吏華威整天忙碌於開會、演說、吃飯,企圖操縱一切群眾活動。其所作所為遭到人們的鄙視和抵制,最後,他不得不為此感到害怕。
《華威先生》最大藝術特點是諷刺手法的運用,通過對人物言行的誇張達到嘲笑、鞭撻生活醜類的目的;但誇張而不失真實,幽默而不失嚴肅,表現了作者卓越的藝術才能。
華威先生是國民黨在文化界的卑鄙、腐朽、驕橫的反動人物,他擔任著難民救濟會、通俗文藝研究會、全省文化界抗敵總會等十來個委員的空銜。一個戰時保嬰會沒有找他,使他大吃一驚,他用恫嚇威脅的手段,終於達到目的,又做了戰時保嬰會的委員,他不做抗日工作,卻整天忙於酒肉應酬,拉攏關係,進行著卑鄙無恥的反動活動。他去參加開會,總是遲到、早退。在開會時,他借口還要去參加另外的會,隨時打斷主席的報告,自已站起來就講話,他的話都是:內容貧乏、重複羅嗦,叫人厭煩的空洞說教。
有一次,他講演沒有人聽,派了兩個青年去拖幾個人來聽,結果連被派去拖人的人也一去不復返了,使得華威先生大發雷霆。後來,他質問那兩個青年,兩個青年毫不懼怕地頂撞了他。華威先生氣得渾身發抖,吹鬍子瞪眼睛地大罵“渾蛋”,並且恫嚇他們要小心。可是真正抗日的人民跨過他,象跨過絆腳石一樣,繼續去做抗日工作。
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抗日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變得激烈起來,其鬥爭也日趨尖銳。一方面,人民群眾的抗日激情高漲,另一方面,國民黨統治區地方的軍政界的頭目卻害怕人民動員起來。當時作者在長沙搞文化界的統一戰線工作,對後者的情況是比較熟悉的。“文化界抗敵後援會”有三個部長,部長都是民主人士,後來國民黨要求來爭領導,要爭作部長,當了部長又不幹抗日的事,鬥爭很尖銳。那時茅盾主編《文藝陣地》,向作者要稿子,作者有感於此,創作了《華威先生》。
華威先生
這是一個掛抗戰招牌、到處監視人民、拚命搶奪抗日統一戰線領導權、對抗戰工作包而不辦、華而不實的國民黨地方文化官員的典型形象。他挾公文皮包、執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叨雪茄煙、坐包車,表明他有著半土半洋的紳士風度且頗有來頭和權勢:戴結婚戒指,稱妻子為“密司黃”,說明他趨附時尚,以新派人物自居;拿著雪茄煙的無名指微彎、與高高翹著的小指構成一朵蘭花圖樣,意味其善於孤芳自賞;坐包車搶路、跑得車圈的鋼絲閃亮,下車時尤愛踏鈴,到會場門口稍作他立,而後看著天花板走進去,坐下后又點煙又看錶,寫出了他的行動的忙迫及其愛出風頭、抖威風、擺架子的傲態。對熟人,他故作謙恭,讓人稱他“威弟”或“阿威”,對下級,他飛揚跋扈、霸氣十足;口稱不當主席,又點名推舉主席,還命令主席在兩分鐘內報告完;他颳了兩分鐘洋火之後又打斷主席的話搶先發表意見;那每會必講的“認定一個領導中心”論,成了他掛在嘴邊的口頭語,將其充當國民黨一黨專權的吹鼓手的黨棍本質一語道破。他忙於赴會和演講,忙於監視、探聽消息向劉主任“聯絡”、“彙報”,忙於赴宴或宴請別人;忙於鑽營,到處插手攫取“領導”頭街。而四忙歸到底是一忙:抓權。
華威權迷心竅、官欲奇盛,卻又色厲內荏、惶恐不安。為炫耀和擴大手中的權力,他對待抗日民眾極盡壓制威脅之能事,必然引發了相應的抵制與反抗。難民救濟會裡的人見他來了,不是拉長了臉,就是握緊拳頭瞪圓眼睛,做出一副準備決鬥的姿態。華威的演講沒有人肯聽,連被他派去拉人來聽的人自已也不去。抗日青年不買他的賬,難民救濟會裡的一個長頭髮青年還當面揭穿他的說謊。學生們舉辦“日本問題座談會”不通知他,他得知后暴跳如雷,以“秘密行動”、追查“背景”相恐嚇,兩個學生樣的人也“動了火”,毫不客氣地對之反唇相譏。儘管他大罵“混蛋!”“媽的!”叫嚷“你們小心,你們…...”卻醜態盡出;牙咬著,唇顫抖,嘴巴痛苦地抽得歪著,以至5分鐘后抬起頭來,還“害怕地環顧四周”,發出“現在的青年怎麼辦”的長嘆。他喝酒、罵人、打碎茶杯,恰正暴露出其空虛、矛盾、慌亂、感懼的內心隱秘。
《華威先生》刻畫了一個“包而不辦”,名義上為抗戰奔波、實際上到處參會搶權的文化官僚形象,暴露了在全民抗戰的熱情下潛藏的黨派狹隘利益和個人私利之爭,具有一定的時代典型性。作品緊緊抓住華威先生的“忙”和“講”的言行表現,運用誇張和對比等手法,辛辣地揭露了那些“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只對限制和控制抗日工作的“領導”感興趣,而對加強和促進抗日的實際工作不感興趣的國民黨政客。
橫斷面式選材
作品不寫人物的出身經歷,也不敘述故事情節,而只截取生活的幾個橫斷面,凸現他性格中最顯著的特徵和外觀的形態,表現相對靜止的人生相。作品僅攝取他參加三個會議的片斷便把他既驕橫又虛偽的性格特點表現出來了。參加難民救濟會時,他的“態度很莊嚴,用一種從容的步子走進去”,“很客氣地坐在一個冷角落裡”,退出會場時,“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挾,瞧著天花板點點頭,挺著肚子走了出去”,擺出一副居高臨下,唯我獨尊的架勢。到達通俗文藝研究會會場時,他發現未等到他駕到就已開會,很不高興,發了幾句“要認定一個領導中心”的議論就立即退席。趕到文化界抗戰總會會議室,因遲到了就擺出一副謙恭的樣子,但坐下后,卻與別人談論昨晚喝酒的事。當他聽說有個座談會沒有通知他時,火冒三丈揚言要追查政治背景。他那種要包攬一切而又包而不辦的無賴相,以及既驕橫又虛偽的性格特點也就暴露無遺了。
對照中進行刻畫
作品把華威的自命不凡、不可一世與人們對他的反感、憎惡以及他表面的崇高、謙恭與內心的卑下、偏狹構成矛盾,進行對照,刻劃他性格。比如他外表總假裝很謙虛,連主席都不肯當,但實際上他的手伸得特別長,什麼事都要管,連戰時保嬰會這樣純屬婦女的工作,他都要插手。參加難民救濟會時,他耀武揚威、自鳴得意,但與會者一看見他來就噁心。他到處抓權,鼓吹“一個領導中心”、實際上誰也沒有把他放在眼裡,他表面上裝模作樣,道貌岸然,實際上不學無術,庸俗卑劣。
漫畫式誇張
作品以漫畫式的誇張,突出他的“忙”,忙於開會,忙於發言,忙於打進一切抗日組織。他的包車跑得“象閃電一樣快”,還說“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覺的制度。”他的忙,只是到處誇誇其談地兜售“一個領導中心”的反動貨色,只是為了攫取一切“會”的領導權,只是干擾、限制群眾的正當抗日活動。這樣,他的“忙”,就成了“破壞”,他活動得越積極,其破壞性就越大。
結構緊湊完整
作品在選材上花了很多篇幅放在華威先生開會上,他一個會接一個會地開,節奏越來越快給讀者造成一個他對抗日真是非常熱心的印象,但到作品結尾時,情節陡地一轉,當幾個青年真正參加了抗日的會議時,他反而大為光火。這個結尾著墨不多,卻異常有力,把華威的醜惡本質揭露出來。通過第三者“我”的眼睛,把華威在會上、會後、公開場會與家庭及他本人的自我評價與旁人的看法統統組成了一個整體,使結構更為緊湊、完整。
諷刺性的語言
徠不論是敘事狀物,或者是描繪人物的神情姿態,以至一言一笑,作家都十分注意遣詞用句的準確、鮮明、生動,往往在樸實中見匠心,於明快中露機趣。他善於大詞小用、庄詞諧用,賦予常態的語言以奇譎的色彩和深長的意味,往往令人忍俊不禁。如小說開頭,寫華威故作親近、謙和之態,讓“我”不要叫他“先生”,應當叫他“威弟”或“阿威”,這種親戚之間的稱呼本屬區區小事,可作家寫道:“把這件事交涉過了以後,他立刻戴上了帽.....”這“交涉”二字就妙不可言,準確而又風趣,十分切合華威的身份和性格。作家還擅長於使用熱辣辣的誇張語言,故作驚人之筆,或者有意地重複使用某些語言,加強挪揄的色彩和力度,從而給讀者留下更為深刻難忘的印象。如描繪華威驅車赴會的惶急狀態:“掏出表來看一看,他那一臉豐滿的肌肉立刻緊張了起來。眉毛皺著,嘴唇使勁撮著,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斂到臉上似的。”寫華威進人和退出會議場所的姿態時,又重複使用“瞧著天花板點點頭”這樣神氣活現的詞句,等等。這些都是出色的例子。但是,小說中運用得最成功的還數那極富於諷刺意味的個性化的人物語言,也就是華威先生的語言。他在任何場合都不忘高唱“要認定一個領導中心”、“要在這一個領導中心領導之下”團結、統一起來的老調子,辭令總是那麼乾巴僵硬,令人生厭;但在私下與沆瀣一氣的同僚搗鼓吃喝和太太之類的事兒時,他卻變得那麼心口如一,痛快淋漓。在大庭廣眾之中,當著青年們的面,他是那麼莊重威嚴,一再恭維大家工作都很努力和熱心,表示“我很感謝你們”;可是,當他在家裡聽到有的青年竟不告訴他而去參加了“日本問題座談會”,就像觸動了他那最敏感而又最脆弱的神經,頓時暴跳起來,咬牙切齒,破口大罵,什麼“媽的!”“混蛋!”種種粗野難聽的詞兒都使出來了。華威先生這些色調豐富、諧趣橫生的個性化的語言,猶如一面燭照幽微的鏡子,把他那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言行不一、虛偽透頂的醜惡嘴臉和靈魂,絲毫不爽地映照出來了,使他無可遁其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