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福特
美國作家
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於1944年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傑克遜市(Jackson,Mississippi)﹐自幼常居傑克遜和阿肯色州的小石城(Little Rock,Arkansas)﹐在公立學校上學﹐后赴密歇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加利福尼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和華盛頓大學法學院(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就讀。創作了《體育記者》(The Sportswriter)﹑《野性生活》(Wildlife)和《獨立紀念日》(Independence Day)等5部長篇小說﹐另出版《石泉》(Rock Spring)和《多重罪惡》(A Multitude of Sins)等3本短篇小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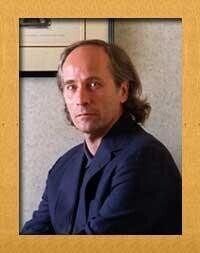
理查德·福特
還獲得普利策小說獎(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筆會/福克納小說獎(PEN/Faulkner Award for Fiction)和筆會/馬拉默德短篇小說獎(PEN/Malamud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the Short Story)。
各種長短篇小說已被翻譯成23種文字﹐曾榮獲法國文學藝術獎(Ordre des Artes et des Lettres)。福特現居新奧爾良(New Orleans)﹐妻子克里斯蒂娜‧福特(Kristina Ford)。
不言而喻﹐這其實是一個可以反反覆覆爭辯不休的問題﹐可謂文學界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一樁疑案。如果推而廣之﹐問問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身為俄羅斯人對契訶夫(Chekhov) 有哪些影響﹖身為女性對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 有哪些影響﹖身為一名高不盈尺的水手﹐波佩耶(Popeye)為何如此鼎鼎大名﹖他終於知道問題的答案﹐而且見解精到﹕"我就是我。我是什麼﹐就是什麼"。
為破解這個邏輯難題﹐我不想囿於成說﹐需另劈蹊徑尋求答案。這通常是小說家的功課﹕超越表像挖掘新意﹐開創令人耳目一新的認知﹐豐富已知的總體現實﹐砸開我們內心封凍的海面﹐不論你對達到新的境界有什麼設想。
首先有兩種命題方式需要當即排除﹐因為這兩種方式都不特指美國。本文標題提出的問題是﹐"身為美國人對我的寫作有哪些影響﹖"有人可能會說﹕"身為美國人意味著我想寫什麼就寫什麼﹐而我的確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故言之成理。"但我如果在丹麥﹑加拿大或英國﹐是否也能如此﹐從而同為所述諸國人氏﹖這個推論適用於美國﹐但並非特指美國。其次﹐身為美國人可能造就了我的作家生涯﹐為我的事業打上了不可磨滅的烙印﹐但與其它一些國家相比﹐美國不一定能使我成為一名更受歡迎的作家。世界文學史已經敘述了這一點。依我之見﹐我如果是法國人﹐可能更為成功。
我不記得我什麼時候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是美國人。6歲向國旗宣誓效忠。18歲登記服兵役。20歲加入海軍陸戰隊。但我可以肯定﹐早在這一切發生之前﹐我非常清楚我首先是密西西比州的南方人﹐更確切地說是傑克遜人﹐是來自阿肯色州雙親的兒子﹐他們並非密西西比州本地人﹐與我略有不同。當然﹐所有這些獨特的地方性均以我是一名美國人為前提﹐因為合眾國﹐作為一個國家及其代表的原則已蘊涵了這一切。因此﹐對於我本人和我的作品﹐我可能認為具有南方人典型特徵之處﹐廣義而言也反映了我身為美國人的屬性。
20世紀四五十年代﹐我在密西西比州長大成人﹐當時人們對於南方應效忠整個美利堅合眾國一事顯然態度曖昧。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已成過去﹐但往事還不算久遠。我認識的一位遠親當年就在珍珠港(我的家人在晚飯時談到過這件事)。朝鮮戰爭仍在進行。大多數南方人感到﹐共產主義即使還沒有危害到我們自己的全部屬性﹐也已經對我們的國家安全造成了威脅。我父母投了票。羅斯福(Roosevelt)和杜魯門(Truman)先後擔任美國總統。我曾宣誓效忠。美國屬於我們﹐我們也屬於美國──至少是為了保護它﹐捍衛它。
然而﹐還有其它重要的社會政治問題﹐特別是種族﹑選舉權﹑機會均等﹑保障人人享有美國給予的一切以及美國拔新領異的"聯邦主義"等問題。"聯邦主義"是美國憲法的基石﹐各地稱之為"州的權力"。人們或許認為很多南方人寧願另覓祖國﹐完全歸屬於其它某個國家﹕很多白人會嚮往南非或巴拉圭﹐黑人則屬意法國或瑞典。不論在這些事關國計民生的問題上站在哪一邊﹐身為一個美國人﹐服膺美國提倡的有關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理想﹐不免會遭遇波濤起伏﹐面臨不和諧的氣氛和種種爭議﹐有時還可能危害健康。
自覺承認自己的國民歸屬﹐認同自己的屬性﹐顯然只是有所歸屬的一種體現。實際上﹐對於我們的歸屬問題﹐美國人歷來在很多方面都視之為理所當然﹐從而可更專心致志地享受這種歸屬結出的累累果實。我國共和制政體的一個內在目標是﹐勉勵大家關心自己作為公民應如何身體力行﹐哪怕是不經意的行為﹐不必太注意公民身份包含的機制與原理。因此﹐國民歸屬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為了達到個人自由這個目標的一種方式。
但對我而言﹐從1950年到1962年在密西西比州﹐在南方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做一名美國人﹐承認自己的國民歸屬﹐意味著完全(絕非不經意地)被捲入一個就美國公民問題進行公開辯論的翻騰起伏的大旋渦﹐人們情緒激昂﹐眾說紛紜。這場辯論的核心問題是﹕當我的出生國看來想壓制我認為我擁有的最基本的﹑絕不可剝奪的個人權利的時候﹐我應如何看待自己歸屬於這個國家的問題﹖主張種族隔離的白人認為﹐這個權利意味著他們有權隔離與自己不同型式的人﹐彼此不相往來﹔黑人和主張取消種族隔離的白人則針鋒相對﹐他們認為這個權利允許人們不受拘束地自由行動﹐隨心所欲地與別人交往﹐凡此種種都不必擔心受到傷害。在這場激風暴雨中﹐圍繞著這個問題出現了被稱為"美國民權運動"的長期辯論﹐很多人為爭取正義與權利獻出了生命﹐但正義與權利最終得以實現﹐儘管可能未臻完美。
判斷任何一種態度﹑人物﹑行為﹑品德﹑經歷或信念是否具有"典型的美國特徵"﹐總令我頗費躊躇。我在國外時﹐某些讀過我的作品的人問我﹐某一篇故事是否具有典型的美國特徵﹐我竟一時語塞。然後我說﹕如果乘直升飛機飛越美國某城郊的上空﹐看見一位頭戴餡餅式便帽的男人在草坪上刈草。這當然應該是一位典型的美國人。但他究竟是什麼人﹖(我們以為我們知道答案。)我們走近一看﹐輕輕摘掉他頭上的帽子﹐才發現他是巴基斯坦裔﹐一位移民﹐也可能看見一名第三代迦納裔或華裔美國人。按照他的人生軌跡﹐他在這一天出現在這個城鎮的這塊草坪上﹐不僅打破了大多數有關典型性的概念﹐而且揭示了不合傳統的特質往往被淡化和排除的傾向。由此可見﹐個性證明了共性的不可靠。這正是大量文學名篇力求敘述的一點﹕貼得越近﹐看得越清。我們本應如此。
50年代我在密西西比州長大成人的經歷是否比這位巴基斯坦移民的生活更具有典型的美國特徵﹐這當然還有待討論。但我和他一樣﹐都是美國人。我們的經歷都是在美國的生活體驗﹐或者有一部份發生在美國﹕跌宕起伏(就我而言)﹑公民身份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國民歸屬與造成隔閡的地方主義。所有這些都不完全地融入一個宏大的政治理想。這個理想在大量包容的同時﹐儘可能避免人們受到壓制和束縛。(也許我應當承認﹐我和這位移民擁有的共同點比我想象的還要多。)
或許應該更確切地說﹐我的生活經歷可能通過什麼方式引導我進行創作﹐因為從人類想象的一個介面向另一個介面追尋文學表現形式演進的軌跡﹐從萬般隨意和單憑感覺的一面跨越到(故事)成型的一面﹐這個過程全靠臆測﹐常常似是而非。無庸諱言﹐我本人沒有能力區分我的意圖和我取得的實際結果﹐同時我希望通過我的作品"證明"一種影響的存在﹐而且我從作者的角度對作品的全部理解與讀者的解讀也有區別──所有這些都使我無法從最客觀的角度﹐或者以最有說服力的方式對自己進行評價。
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給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的信中寫道﹕"小說家告訴讀者以質疑問難的方式了解這個世界......在以不容置辯的一定之規為圭臬的(極權)社會﹐小說就喪失了生命力。"因此﹐與我的美國經歷(絕不屬於極權﹐但聚訟紛紜﹐盤根錯節﹐顯得撲朔迷離﹐廣泛多樣﹐不和諧的狀態往往到了引發軒然大波的地步)一脈相承﹐我始終力求創作的故事和小說能證實人們在身處危困﹑不和諧的環境和面臨責難而飽受煎熬時展現的人類本性──尋求愛情的人們期盼兩情相悅﹑心心相印﹐彼此能給予體貼和慰藉﹐結果卻轉眼成空﹔父子意殷殷﹐母子情切切﹐但中間橫亘著誤解的鴻溝﹐無法盡遂人願﹐既難以找到確切的方式表達親情﹐又為了當面向對方說出必須要說的話頗費躊躇。這一幕幕情景沸沸揚揚﹐已成水火不容﹑恩怨難息之勢﹐其中還包含著不為人知的隱情。我從中體會到美國人經歷了哪些變故﹕民權運動和越戰﹐都伴有家庭解體的現像﹔麥卡錫大清洗﹐鑄成國家的分化﹔大蕭條以後的歲月﹐然後是世界大戰爆發和50年代的繁榮局面誕生。
其次﹐與我在美國生長的經歷相呼應﹐我遵循需要和自由的原則進行創作﹐描述各種與我不同類別的人物(如婦女﹑其它種族和國籍的人﹑兒童)﹐嘗試回答我作為美國公民面臨的特定的根本性問題﹕為什麼我們如此千差萬別﹐彼此又如此相像﹖我寫了一些小說﹐希望這種朦朧狀態能令人們感到可以承受﹐饒有情趣﹐甚至賞心悅目。
我還體驗了通過個人日常生活展示的細緻入微的政治。正是在這樣的日常生活中﹐在自成一統的小家庭範圍內﹐在一個美國小城鎮﹐在遠離權力中心和公眾輿論的地方﹐我第一次看見是非竟如此明斷。事實上﹐我在不可能預作籌劃的某一個時刻﹐僅僅受好奇心的驅使﹐離開作為我寫作主題的南方﹐設想向更多的美國讀者介紹我帶有地方色彩的思考﹐同時試圖以整個國家為我寫作的背景﹐甚至更希望以此作為寫作的題材。
最後──在這一點上我無需推測是誰影響了誰──作為一名作家﹐我始終相信可以美國為背景﹐描述對人類具有普遍意義的種種事件和行動﹐探究其中的動機和道義後果﹐從地球上任何一個角度觀察都可以了解其重要性。美國的人文歷程﹐即使不能成為世界其它地區效仿的典範﹐至少可資借鏡﹐耐人尋味。
歸納自己所受的種種影響往往令人頭腦發熱﹐狂妄自大到不著邊際的地步。但我覺得﹐我現在得到的結果令我感慨萬分。如果這麼多年來我沒有受到這些影響的話﹐我或我的作品可能會截然不同。當然﹐我也完全不可能成為現在的我。從等式一邊去掉關鍵的一項﹐原來的等式就不復存在。波佩耶若是一名飛行員或一名債券交易員﹐就不是我們喜愛的波佩耶了。
今天﹐車臣有一位作家可能也在寫......談車臣對他的作品產生的影響。他正在寫我寫過的同樣題材﹐或更值得寫的題材。我覺得很高興。如果說所有這些年﹐身為一個美國人能讓我發現﹐我與從未謀面的某人有著相似之處﹐相互間有某些關聯﹐能讓我領略文學最寶貴的財富﹐那麼作為一名美國人﹐同時也作為一名作家﹐僅此己使我受益匪淺。
斯科特‧菲茨傑拉德(F.Scot Fitzgerald)﹐1896~1940﹐美國小說家
J.D.賽林傑等(J.D. Salinger)﹐1919~﹐美國小說家
邁克爾‧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1944~﹐美國電影演員
布魯克倫(Brooklyn)﹐紐約市內一區
弗蘭克‧格雷(Frank Gehry)﹐1929~﹐美國建築師﹐1989年獲普立茲克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
星空迷航記(Star Trek)﹐美國科學幻想電視系列片﹐1966年由全國廣播公司(NBC)首播﹐后被改編成電影
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國作家
馬洛(Marlow)﹐康拉德的作品《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主人公
羅賓遜‧傑弗斯(Robinson Jeffers)﹐1887~1962﹐美國詩人
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國小說家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美國小說家
弗羅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美國詩人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美國小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