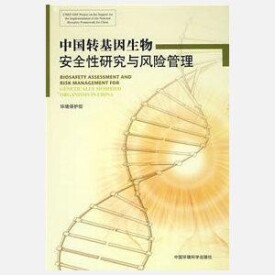轉基因生物安全
轉基因生物安全
隨著轉基因技術的發展,轉基因生物安全問題在國內外已經引起極大的關注,不同領域的專家都從自己的專業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很多研究,積累了豐富的文獻。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態學、科技倫理、環境科學等方面,主要通過技術層面來分析轉基因生物的安全性問題。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一致認為,生物安全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它對於人類社會的深遠影響已經超過人們的預期,原來那種希望僅僅依*科學技術的完善來解決人們對生物安全的疑慮和不安的想法已經顯得過於簡單。
中國出現了一系列涉及到轉基因生物及其產品的案件和糾紛,如雀巢轉基因食品標識糾紛,美國轉基因大豆進口許可證風波 等,還有如今沸沸揚揚的轉基因稻米市場化爭議,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意識到生物安全法律問題研究的重要性,在生物安全立法、管理體制等方面作了很多開創性的研究工作,但是與國外的研究現狀相比,我國對生物安全的法學理論研究滯後於實踐的狀況比較嚴重。因此在生物安全法律規制的框架構建上缺乏足夠的法學理論支撐。就現有的極少量相關研究成果而言,大都出自生物技術專家之手,而非出自法律專家。從採取的研究方式來看,長期以來僅僅引進和介紹國外相關研究成果,研究範圍狹窄,層次相對單薄,沒有建立起獨立和成熟的轉基因生物安全法律研究框架和法學理論。
作為轉基因生物安全法律問題研究的邏輯起點,轉基因生物安全的概念界定是一個核心問題和工作基礎。筆者有感於國內學者對轉基因生物安全概念理解的不一致,結合轉基因生物安全問題的科技背景和轉基因生物安全問題的演變,試圖對轉基因生物安全的概念作一梳理和探究。
“轉基因生物”一詞的最初來源是英語“Transgenic Organisms”,因為在上世紀70年代,重組脫氧核糖核酸技術(rDNA)剛開始應用於動植物育種的時候,常規的做法是將外源目的基因轉入生物體內,使其得到表達,因而在早期的英語文獻中,這種移植了外源基因的生物被形象地稱為“transgenic Organisms”,即“轉基因生物”。但隨著分子生物技術的不斷發展,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科學家們能夠在不導入外源基因的情況下,通過對生物體本身遺傳物質的加工、敲除、屏蔽等方法也能改變生物體的遺傳特性,獲得人們希望得到的性狀。在此類情形下,沒有轉入外源基因,嚴格說就不能再稱為轉基因,稱為“基因修飾”更加合適和全面,因此現在開始用“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簡稱GMO)”,即“基因修飾生物”,來代替早期的“Transgenic Organisms”。因此,我們所指的“轉基因生物”,其概念已經為“基因修飾生物”所涵蓋。但因為“轉基因”一詞已經普遍為人們接受,而且外源基因導入仍然是分子生物技術在作物育種領域中所採用的主要方法之一,“轉基因生物”一詞就沿用至今。基於此,本文繼續沿用“轉基因”一詞,不過是在“基因修飾生物”的意義上加以使用。
早在1956年,Crick和Watson對生物遺傳物質的結構的揭示極大地促進了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到1968年,美國科學家Paul Berg成功地將兩段沒有遺傳相關性的DNA片段連接,引起生物學界的轟動,該科學家也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隨後,他試圖開展將這段重組脫氧核糖核酸(rDNA)導入真核生物細胞核的實驗,由於實驗採用的DNA來源於一種非常危險的病毒,一旦DNA片段在真核細胞內恢復了生物活性,後果不堪設想,此時,有同行意識到該實驗的危險性,向他發出了警告,Paul Berg在仔細斟酌后暫時放棄了這項可能再度讓他問鼎諾貝爾獎的實驗。而在1972年,生物學家Boyer從大腸桿菌中提取了一種限制性內切酶,命名為EcoRⅠ酶,這種酶能夠在特定編碼區域將DNA鏈切斷,這使得不同遺傳物質之間的重組變得愈加可行。在這種情況下,科學家們再次考慮到生物實驗的安全性問題,並且於1975年召開了著名的Asilomar會議,專門討論生物安全問題。
在Asilomar會議召開后不久,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就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專門針對生物安全的規範性文件,即《NIH實驗室操作規則》。在《NIH實驗室操作規則》中,第一次提到生物安全(biosafety)的概念,可以說,以後生物安全概念的變動和發展,都是基於這一概念。但是要注意的是,此處的生物安全是指“為了使病原微生物在實驗室受到安全控制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A series of procedures in the laboratory to ensure that pathogenic microbes are safely contained)。可見,就生物安全問題的起源來說,有兩個基本要素:其一,生物安全與生物技術緊密相連,如果沒有現代分子生物技術的發展,沒有對遺傳物質在物種間進行轉移的科技能力,就不會有生物安全問題的出現;其二,生物安全是基於轉基因生物及其產品而導致的確定或不確定的潛在風險。綜合上文對轉基因生物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到,《NIH實驗室操作規則》對生物安全概念的界定,主要針對的是轉基因生物,所調控的是一種狹義的生物安全,即將病源性微生物控制在實驗室內的安全使用。
在我國法學界,什麼是生物安全?不同的學者有各自不同的解釋。如有的學者認為,“生物安全,是指生物的正常生存和發展以及人類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人類的生物技術活動和其他開發利用活動侵害和損害的狀態” ;有的學者認為,“生物安全是指生物種群的生存發展處於不受人類不當活動干擾、侵害、損害、威脅的正常狀態……所謂人類不當活動是指違背自然生態規律的人類活動,包括開發、利用生物資源的生產活動、交易活動和技術活動” ,等等。這些概念的界定是否準確?是否具備了法律上的特徵?
正如很多其它科技發展帶來的法律問題一樣,對生物安全概念的界定,不能脫離生物安全問題的科技背景,否則就不能準確找到法律層面的切入點。正如前文所述,生物安全的最初概念可以等同於轉基因生物安全的概念,但是隨著生物安全被人們重視的程度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問題被歸入到生物安全的範疇中去。比如外來生物入侵,這是一個傳統的生態危害問題,而且已經為人們認識到了,但是在轉基因生物的生態危險性尚未顯現以前,沒有人把生物入侵看成是生物安全問題。即便現在看來,轉基因生物安全問題還是生物安全的主要方面,當前在調整生物安全過程中體現的一系列原則,如“審慎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實質等同性原則(substantial equivalence)”,“事先知情同意(Advance Informed Agreement)”等都是在調整和規範轉基因生物安全的過程中被強調和研究的。
而值得進一步考慮的是,從上文所引的國內兩種代表性觀點看,似乎“生物安全”一詞中的“生物”是作為被保護的對象來說的,使其保持在一個不被“干擾、侵害、損害、威脅”的狀態。但事實並非如此。從生物安全概念的起源來看,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知道這裡的“生物”指的不是“需要保護的生態環境內的生物”,而恰恰是“能夠引起不安全狀態的病原生物”;所謂的“安全”則是指對採取措施使得這類危險的生物被控制在“安全”狀態而言的。如果不明確這一點,就會對生物安全作擴大的解釋。與生物技術無關的人類活動,比如濫捕野生動物、過度砍伐等行為,即使是產生了對生物界的危害,也不應被納入生物安全的範疇。
《NIH實驗室操作規則》第一次提出生物安全的概念,但如果生物安全概念只停留在這個層面上,轉基因生物停留在實驗室里而沒有產業化的價值和意義,那麼所謂的轉基因生物安全法律問題無非是一些實驗室的操作規範而已,法律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會微乎其微。
實際上,隨著農業綠色革命的風起雲湧,傳統的農業栽培和育種模式的潛力已經挖掘怠盡,日益精細的耕作和大量的農藥、化肥投入使得原本已經脆弱不堪的生態環境遭到進一步的惡化,同時世界日益增長的人口又使得溫飽問題的解決雪上加霜。此時,人們認識到生物科技對於農業的運用所能帶來的巨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對以上問題的緩解作出貢獻。農業產業的獨特生產特性使得轉基因生物獲得了極大的應用前景,尤其在一些氣候惡劣、病蟲頻發的地域,轉基因作物顯現出傳統作物所難以企及的優勢,市場化推進速度驚人。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在1996至2004年的九年期間,全球累加的轉基因作物價值為240億美元。專家預測,2005年,全球轉基因作物(僅指官方登記認可的,不包括非法栽培的轉基因作物)的價值預計將超過50億美元一年。而全球全部轉基因生物產品(包括農作物、藥品等)總產值從1984年來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至2003年,已經達到450億美元之巨。這也是生物安全研究的主要對象恰恰是轉基因農業作物的根源。
轉基因生物技術在很大程度上能對農業生產產生很大的促動,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現代生物技術可以將無關聯的生物品種,包括植物、動物和微生物中的遺傳材料相互轉移(並且可以指定要轉移的基因),產生出新型的植物、動物和微生物。因此技術本身還是存在一些不能確證但卻危害巨大的隱患,包括對生態環境和公眾健康的威脅。在生態方面,如果轉基因作物的外源基因向親緣野生種轉移,就會污染到整個種子資源基因庫。1997年,人們在玉米的原產地—墨西哥山區的野生玉米內檢測到轉基因成分,但轉基因玉米的栽培地卻是在離山區幾百里之遙的美國境內。人們由此覺得轉基因生物的負面生態影響必須得到重視。在食品健康方面,人們擔心轉入了其它基因的作物含有對人體不利的成分。尤其是美國王斑蝶(Monarch butterfly)事件 和英國普斯陶教授(Arpad Pusztai)的轉基因土豆毒性研究報告 的發布,更加使人們對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的安全性問題充滿了憂慮。
這種利益和風險之間的衝突必然會大大促進生物安全概念的發展。生物安全已經不再僅僅是實驗室內的一種安全操作規則,而是演變成為政治、經濟、倫理、法律諸方面相膠合的綜合性問題,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被極大地擴展了。可以看到,生物安全又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它所涉及的具體內容有一定的時空範圍,又隨自然界的演進、社會和經濟活動的變化及科學技術的發展而變化。
從國際法的層面上來看,第一次提出生物安全問題的是1990年制定的《生物多樣性公約》。該公約是從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角度來理解生物安全的。在術語一章中沒有為生物安全作出定義,而是把生物安全和外來生物入侵、惡意生物資源勘探等活動一樣作為危害到生物多樣性的一種原因而加以關注,它的內容還是十分單一,很大程度上是對生態風險的強調。但在2000年根據公約制定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中,生物安全的概念就得到極大的拓展,雖然《議定書》也沒有給出生物安全的確切概念,但在《議定書》的目標中提到,“本議定書……協助確保在安全轉移、處理和使用憑藉現代生物技術獲得的、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可持續使用產生不利影響的改性活生物體領域內採取充分的保護措施,同時顧及對人類健康所構成的風險並特別側重越境轉移問題” ;在“術語解釋”中,“現代生物技術”被定義為包括兩種技術,“其一,試管核酸技術,包括重新組合的脫氧核糖核酸(DNA)和把核酸直接注入細胞或細胞器;其二是指超出生物分類學科的細胞融合,此類技術可克服自然生理繁殖或重新組合障礙,且並非傳統育種和選種中所使用的技術” ;“改性活生物體”是指“任何具有憑藉現代生物技術獲得的遺傳材料新異組合的活生物體”。可見,國際法上對生物安全的概念界定,主要規範的還是與生物技術緊密相關的轉基因生物,但議定書對生物安全產生最深影響的,是將生物安全的內容和範圍由實驗室擴展到更廣的範圍。根據議定書,生物安全涉及到GMOs越境轉移的程序、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國家間生物安全信息資料交換、GMO損害的責任與賠償 等方面。在這裡,轉基因生物安全是一個系統的概念,即從實驗室研究到產業化生產,從技術研發到經濟活動,從個人安全到國家安全,都涉及到生物安全性問題。
總之,轉基因生物安全首先是一個科學的概念,轉基因生物從實驗室到栽培實驗地,到大田,到食品加工廠,到超級市場,到我們的餐桌上,隨著消費者離轉基因生物及其產品的距離越來越近,在這各個過程中,生物安全涉及到實驗室安全、項目審批、大田栽培風險評估、市場准入、運輸隔離、食品標籤等一系列問題。而在法律的視野中,轉基因生物安全包括著兩個層面的安全:其一是生態和健康上的風險防範。因為“科學不確定性”的存在,使得法律對轉基因生物的風險規制努力只能是“防範”而非“根除”隱患;其二,是指一旦轉基因生物造成了損害,法律是否加以救濟,提供怎麼樣的法律框架予以救濟。這也是生物安全的另一個方面,是法律框架內的安全。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轉基因生物安全概念,“轉基因生物安全,是指為使轉基因生物及其產品在研究、開發、生產、運輸、銷售、消費等過程中受到安全控制、防範其對生態和人類健康產生危害、以及救濟轉基因生物所造成的危害、損害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的總和”。相應地,調整和規範其中每一個過程中產生的法律關係的法律,其總和也就構成了轉基因生物安全法。
王延光.生命倫理與生物技術及生物安全研討會綜述.哲學動態,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