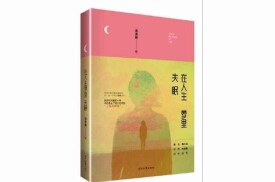在人生夢裡失眠
在人生夢裡失眠
作家、詩人、畫家沈亦然心靈力作,野夫、葛紅兵、葉開、李亞偉傾情推薦
故事簡介:
周莉一直對自己從事的每天8小時B超室暗室工作感覺壓抑。尤其覺察到逐漸加深的職業感使她對生命存在和死亡的認知正慢慢走向麻木和漠視。在自我覺醒的掙扎中,她接觸到了蟬城一個宣揚自由奔放的寫作群體,開始辭職北漂。
北漂過程中,與賈加苦戀一年後,周莉發現壯志未酬、終日喜歡苦思冥想、易怒嬗變、悲觀厭世所致性無能的賈加與她的焦慮和恐懼完全不同,無奈分道揚鑣,回到各自的世界。
七年過去,周莉再一次與蟬城聚會時結識的林一塵相遇,倆人走到了一起。但林一塵卻一直在周莉和留法女友王小鶴之間徘徊。同時,王小鶴也在國內的林一塵和法國的索德之間游弋不決。長久苦悶無著落的情感生活也使林一塵逐漸成為一個對情感無法承擔責任的愛無能者。
錯綜複雜的情感糾葛像北京城濃厚的霧霾,謎一樣,讓周莉怎麼也明確不了方向。一場似乎等待已久的嚴重車禍終於使周莉明白,她所尋覓和追逐的生活景象只不過都是意念存在時一場幻象,如賈加最初告訴她的:生命是沒有意義的,只有尋找生命意義答案的過程才是有意義的。
沈亦然,作家、詩人、畫家,1979年生,安徽馬鞍山人。做過醫生,辭職後分別在《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工作過。2003年開始創作小說、詩歌,作品多次發表在《芙蓉》 《 》 《 》等文學期刊。2013年起定居北京宋庄,在創作詩歌、小說的同時,也從事水墨、油畫的創作。2015年出版長篇小說《 》。
“人生失眠症”,是現時代我們每個人都能隱隱約約切身體驗到的一種迷失感極重的孤絕精神狀態,“存在卻又無法定義”。沈亦然第一次在這本作品里以生活事件形式提了出來,可見學醫出身的她,始終沒有放棄解剖這個時代我們正面臨的社會癥結。無論是用手術刀,還是用筆。
——野夫
沈亦然用平實敘述的語言尖銳而又深刻地展現了我們所處這個時代無以逃遁的“人生失眠症”問題,就是在經濟、科技快速發展大背景下,個人精神世界里逐漸散失的“施愛能力”。這是這個時代所面臨的極其嚴峻及待解決的問題,不可忽視。
——葉開
沈亦然可謂一個真正懂得女人心理的女性作家,她不僅認同女性在情愛世界里要相信愛,保持永不放棄的炙熱追求精神,更警示女性在情愛生活中遭遇焦慮、疑惑、失去時,一定要保持清醒,自我救贖。
——葛紅兵
沈亦然十分厲害,是一個擁有極高智慧的作家。她總會用非常簡單、平實的語言解決我們一直迷惑、無法澄清的宏大問題,比如世界觀、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根源等等,她輕易地以殊途同歸的方法論將這些問題剖析清晰。讀完,非常過癮。
——李亞偉
前言:引子
引子
“2011年11月11日,深夜11點11分左右,北京東南六環外出京方向的高速公路上發生了一場極其嚴重的車禍。一輛紅色小轎車撞上一輛黃色‘現代’計程車,將計程車頂到高速公路左側護欄后,紅色小轎車自己又急速轉方向準備跨越三個車道。跨越途中,被中間車道的一輛隨後而上的大貨車頂飛,直接撞上了公路右側護欄。護欄沒有斷裂,被撞成巨大的‘C’形。紅色小轎車車頭、車體徹底碎裂,車主不幸遇難。”
在這場車禍中,我正是紅色小轎車中那個遇難的人,所以,很不幸,那晚,我死了。
我的生命在十個“1”,一萬年才遇一回的這個特殊的日子裡(2011年11月11日深夜11點11分),用高速公路的鋼鐵護欄畫上了一個圓圓的句號。
我死在了那場車禍的警燈閃爍不止中,像一隻被拍死的蚊子,突然結束了氣焰囂張的“嗡嗡”聲,寂靜無聲地躺在一片光亮里。
我已死亡這個事實是等我清醒后,才真正得到了確認。
車禍的肇事者是我,屬於酒後駕車。
當時,我的死狀不是相當慘,幾乎沒有血跡,斜躺在駕駛座位上的樣子像正沉睡在夢鄉,對夢中之物充滿了依戀,死活不想醒來。
只是,令人悲傷的是,躺在那裡,除了遠處兩個尚未發現我的警察,我孤零零的,身邊沒有任何人。
雖然我已停止了呼吸,可我腦海中還一直反反覆復地叨念著一些人的名字。濃烈的酒精和食物一直包圍著這些名字,忽隱忽現,顫抖不息。我一邊叨念,一邊反覆辨認,強烈地渴望立刻能找出一直令我激動不安的那幾個字。
我著急地在那些名字的森林裡穿梭。後來,又有一股熱乎乎的血像漲潮的巨浪從我後腦拍了過來,以至於我躺在那裡,腦海里一直還是一團糨糊似的起起伏伏,胡亂顫抖。
我並不知道我已經死了,僅僅是感覺很累。腦袋裡沉重得令我很想扶著一把椅子坐下來。我渴望能睡進一個非常窄小幽暗的房間。只要我能坐在那裡好好地、安心地喘息,我也會逐漸平靜。不管房間有多大,我希望它能擁有一扇可以透進光來的小窗口,哪怕裝在屋頂上,幾束太陽光微弱地從窗戶外面照進來,像幾個未經世的小孩子朝裡面好奇探望的小腦袋。我會友好地抬起頭,在陽光中展露微笑,朝他們做鬼臉並眨眼睛。這樣,我就已經覺得,真舒坦……
可是,我卻死了。
我是真的一點兒都不想離開,也是真的還想最後再看一眼……
我知道,在我念出一些人的名字時,我的嘴唇一直在顫抖……
第一章你為什麼不出來會會朋友呢?
大約七年前,一個偶然的巧合,我知道了蟬城一個文藝群體的存在,並且有意識地接近了他們。
我的工作具體是操作一台通過粘滿黏稠耦合劑的探頭,探查人體腹腔內部臟器有無疾患。
每個白天的八小時,我都必須待在一個暗室里。這樣的生活,周而復始,可能會一直這麼幹下去,並且可能會註定永無止境。因為我時常聽見旁人跟我母親攀談,她們不管是一起從菜市場回來,還是偶爾同時路過水果攤,都不無羨慕地說:“還是你女兒好啊,有一份旱澇保收的事業單位工作。”
實際上,沒人能感覺出我的內心有多苦。我從事的這項工作是怎樣的枯燥無味,整個工作流程機械得像某個早已設定好了的電腦程序。除了最初兩個月略感新鮮,之後,工作完全變成了按部就班的程序化。平時,我極少去看清探頭下面那個連接在身體上的面孔,幾乎從來不看。我接過他們手裡遞過來的申請單,瞄一眼需要探查的身體部位,就指示他們躺下去。他們一個接一個,躺在我操縱的這台機器旁邊的那張簡易木床上,也是躺進了我這個小小暗室里的黑暗深處。
我很少關心躺下去的那個人究竟長的什麼樣。他們的面孔對我來說,一點兒都不重要,並且,假使有一瞬間,我對躺下去的那個人產生了片刻的好奇,事後,我自己都會為這一瞬間感到驚訝。
我所要做的,僅僅是從那些肉體中,從那些噴著熱氣、有節律地蠕動著的腸、胃、肝、脾、腎等臟器中找到那些隱藏其內的寄居者、異生物——它們都是一些怪物——那些成熟的,或正處於萌芽狀態的毒瘤、嗜血鬼們。
很多人都認為我從事的是一份非常光榮而又了不起的職業——像一名雄赳赳、氣昂昂的人民警察勘探著他們的軀體——這樣的虛榮有時確實讓我感覺到了些許快樂,但是非常短暫。因為事實上,我並不能保護他們。等我從超聲波探頭下看清楚那些異生物的模樣后,我只能站在遠處,成為一個束手無策的旁觀者。雖然,我每天都能體驗到為他人排憂解難,找到他們身體痛苦的根源,告知他們,然後接受他們感恩戴德的致謝。
但我十分清楚,更多的時候,我感覺到的是恐懼和崩潰。我發覺自己同時也扮演了一位審判長的角色——當你發現到了那些禍害生命的腫瘤、癌症細胞后,你就從一個醫生變成了守候地獄之門的判官,你手中緊握的長筆輕輕一勾,毫不留情地就宣判了他們的死期,眼睜睜地計算著他們生命的期限。這個時候,他們只能是驚慌又迷惑不甘地抹著眼淚,默默地離開。
他們無法抗爭,只能緘默地接受你給予他們的宣判。
我望著他們血水流盡、皮肉消失、化為骷髏。
我日復一日地清清爽爽地觀望著那些血、糞便、尿液、腐爛的食物,它們在我眼皮底下一浪一浪地起伏、鼓動著。光潔、華美的表皮下以及肉體內部最骯髒的部分被我一覽無餘。
我焦慮不安,我總是在想,我完了!我已經徹底完蛋了。
我的一生似乎只能如此。我唯有在黑暗中自言自語。如花的青春,我只能這樣日復一日地待在這個黑屋子裡,守著這台既不能動,又不能說話的機器,終生與它為伴!就這樣一天一天地等下來,等到皮膚鬆弛、頭髮發白、牙齒脫落、肌肉萎縮,等到像我母親、像我奶奶、像我早已死去的曾祖母那樣老態龍鍾,坐在門檻上,悄無聲息地死去。最後被我鍾愛的那些親戚,被其他一些人,甚至我在這個世界上,從無打過交道的陌生人,塞進我這個黑屋子斜後方的太平間里。
每回想到這兒,我渾身的雞皮疙瘩就頃刻間豎起,開始直打冷戰。接下來,連續幾天,我都無以逃遁地置身在這種極其低落的情緒里。
我時常掀起暗室的窗帘,看雪花、看雨滴、看諸多的廢紙、塑料袋、落葉被或大或小的風颳起,漫天飛舞。我只能喝一口茶,對著它們發獃。它們絲毫不會感動我,也絲毫打攪不了我。我與它們身處兩個世界,厚厚的玻璃窗戶隔離並有效地保護著我們彼此,互不干涉!我摸不著它們,它們也妄想能侵犯我。
我的身邊沒有風,沒有雨,也沒有雪花,連空氣都是稀缺的。我的生命就此停頓在窗帘背後,被熱鬧的街道和匆忙的行人毫不察覺和漠視的黑暗裡。
“你為什麼不出來會會朋友呢?”趙大強對我說。
我很驚訝。
“是的,我們都是你朋友。”
趙大強繼續在QQ上跟我說。我被他說懵了,卻又十分溫暖和心動。
“我們肯定很快就能成為朋友。”他十分自信地跟我說。
“你可以寫作,來參加這個月底我們這裡舉辦的文學聚會吧,我介紹你認識一些你原本早該結識的朋友,他們就在你身邊,我幫你搭上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