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3條詞條名為朱啟平的結果 展開
- 原《大公報》記者
- 福建省泉州市副市長
- 2012年度北京師大“感動師大”人物
朱啟平
原《大公報》記者
朱啟平(1915.11~1993),原名朱祥麟,祖籍浙江海鹽,1915年11月生於上海,1933年南京金陵中學畢業,考入北平燕京大學醫學預科。一二九運動爆發,為參加學生運動,他棄醫改讀新聞,七七事變后,他輟學南下,輾轉到重慶,先後在《新蜀報》和《國民公報》工作,1940年秋加入重慶《大公報》。1945年9月2日,朱啟平作為《大公報》駐太平洋戰區隨軍記者,在“密蘇里”號戰艦上,目睹了中國和其他反法西斯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儀式的全過程。他當即寫長篇通訊《落日》並發表,反響強烈,這是報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儀式通訊類作品的“狀元之作”。

美軍密蘇里號戰艦上的日軍投降儀式
1945年9月2日,朱啟平作為《大公報》駐太平洋戰區隨軍記者,在“密蘇里”號戰艦上,目睹了中國和其他反法西斯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儀式的全過程。他當即寫長篇通訊《落日》並發表,反響強烈,這是報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儀式通訊類作品的“狀元之作”。
《落日》結合現場報道,表現出中國人民戰勝強敵的民族自豪感,揭示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偉大意義,提醒人們展望前景,激起歷史責任感和危機感,是一篇能振奮民族精神和民眾意志的好文章,是報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儀式通訊類作品的“狀元之作”——此文現已編入高中語文教材;由於他在二戰中國際大局報道和對日作戰報道方面的成就,他被譽為“《大公報》繼范長江之後的又一個傑出記者。”
抗戰勝利后,朱啟平奉派赴美國任駐美特派員兼駐聯合國記者,其間寫了《大戶人家辦喜事——共和黨第24屆代表大會》等不少精彩的通訊。 1949年大陸解放前夕,雖然他的兩個弟弟均在台灣政界和商界身居要職,他卻毅然偕妻子經香港回國迎接解放。
新中國成立后,朱啟平參加創辦每日《英文參考消息》。1951 年7月,他自願報名參加赴朝慰問團,在戰火中採訪停戰談判。美軍飛機多次襲擊代表團駐地,大部分記者都撤離了,朱啟平冒著生命危險一直在朝鮮堅持到了1953年7月27日停戰協定最終簽字的那一刻。
從朝鮮回國后,他任香港大公報駐京記者。反右運動中,朱啟平被打成右派,被遣送至北大荒勞改農場。1960年經廖承志提名,朱啟平調到解放軍外國語學院教外語。及至“文革”,他這‘摘帽右派’又被揪斗,慘遭迫害。
1978年,朱啟平調到香港《大公報》任編輯部副主任,次年右派問題得到平反改正。1979年他隨中國代表團訪問西歐四國,憑弔戴高樂墓,撰寫了《偉大的平凡》一文,文筆優美,意義深遠,一時為人們所傳誦。
1985年退休,1990年移居美國加利福尼亞,1993年末病逝家中。
晚年朱啟平回顧自己新聞生涯,對年輕同業寄予殷切希望。
“一筆在手,胸中要有億萬人民”——傑出的戰地記者朱啟平
《大公報》記者朱啟平的名字或許對很多人來說是陌生的,但是他筆下記錄的一頁頁歷史風雲卻時常被提起。
正當他準備升入協和醫學院就讀之際,一·二九運動爆發。
由於醫學預科功課繁重,又要忙於參加學生運動,為了多爭取些課餘時間,朱啟平改讀了新聞。七七事變后,日寇佔領北平,他輟學南下,後轉到復旦大學。之後,他輾轉到了重慶,先後在《新蜀報》和《國民公報》工作兩年。
1940年秋加入重慶《大公報》,先任夜班編輯,不久被派往昆明,採訪滇緬公路通車新聞,一年後返回重慶任外勤記者。
抗戰烽火中朱啟平耳聞目睹了敵人的殘暴和同胞的苦難,從一個熱血青年成長為一名優秀新聞記者。1939年5月3、4兩天日寇對重慶大轟炸,朱啟平親眼看到轟炸過後慘象。
轟炸過後重慶各報也損失慘重,不得不停刊改出聯合版,由《時事新報》編印,各報輪流派人編報。朱啟平也參加了這一工作,第一晚就輪到他在小樓上編稿,就在樓下的院子里,工兵正在挖一枚入土而沒有爆炸的炸彈。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要說心神安泰那是假的,但是,前方將士浴血奮戰,我們連承擔這一點風險也不行嗎?”
“誰也沒有把握炸彈一定不炸,然而編輯、排字等員工,個個都認真工作。敵機的殘暴,不能使重慶無報!”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抗戰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形成。朱啟平一直關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1944年盟軍開始反攻,他向報社領導胡政之建議派記者採訪世界各大戰區,他自薦到美國太平洋艦隊當隨軍記者。胡政之同意了他的要求。
戰爭是慘烈的,戰地記者不是戰士,卻承擔著和戰士同樣甚至更大的危險。臨行之前,朱啟平特地到重慶和父母辭行。去車站的路上,他一步一回首,心如刀割,不知能否生還。他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寫道:“對日寇的瘋狂要有足夠的估計,作為一個到美國艦隊中當隨軍記者的中國人,自己的言行無可避免地隨時隨地地被人認為是國家的代表,特別是在生死關頭上,我決心在採訪任何戰鬥中不落在美國戰友的後面。”
1945 年3月他從重慶乘美軍用飛機飛越喜馬拉雅山,經印度加爾各答、澳洲達爾文,4月5日到達關島,隨太平洋艦隊進入戰區採訪。4月20 日當美軍登陸殲滅日軍時,他從關島飛到沖繩逗留兩周採訪新聞。一次乘吉普車去前線,一隻腳剛下車,另一隻腳還在車上時,一枚彈片飛來,正好擊中他剛剛離開的座位,摸之猶燙。如果晚起一兩秒鐘,彈片正好直貫胸腹。戰火瀰漫,想也不想,也不看第二眼,立刻下車。沖繩之戰激烈時,他就住在機場旁的一頂帳篷里,夜間敵機來襲,只好貼卧在行軍床旁的地上,聽天由命。子彈在身邊掃過,著地時泥土騰起,如同暴雨。當時根本無法構築任何防禦工事,只好擠進山腳下的石築墳墓中暫避,聽著石案上骨灰瓶的搖動聲入眠。對於自己在戰場出生入死的經歷,在新聞中他很少提及,他的觀點是:“到戰場採訪,工作第一,生命第二”,“讀者要知道的是戰況,不是個人的洋相。”
在這期間他寫下了《硫磺地獄》、《沖繩激戰》、《塞班行》、《琉球新面目》等許多出色的戰地通訊。他還曾跟隨美國航空母艦“泰康提羅加”號出航一個月,與戰士們同吃同住,目睹戰機從航空母艦上起飛、出擊、返航、降落,以及年輕的戰士們英勇獻身的精神,撰寫了長篇通訊《鷹揚大海》。這是當時唯一一篇中國記者采寫的反映美國航空母艦的報道。

中外記者團51年8月15日在開城駐地合影留念
朱啟平晚年病重時和老友陸鏗談及當年寫作情況時說:“在密蘇里號軍艦上,有各國記者參加受降儀式。我想我必須以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中國人的感情來寫好這篇報道。”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落日》的字裡行間流露出濃烈的愛國之情和歷史責任感,打動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也因此成為永垂史冊的經典:
“這簽字洗凈了中華民族七十年來的奇恥大辱。這一幕,簡單、莊嚴、肅穆,永誌不忘。”
日本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都是中國人民的熟人,當時在我們的國土上不可一世,曾幾何時,現在在這裡重逢了。”
“全體簽字畢,麥克阿瑟和各國首席代表離場,退入將領指揮室,看錶是九時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製造瀋陽事件,隨即侵佔東北;一九三三年又強迫我們和偽滿通車,從關外開往北平的列車,到站時間也正好是九點十八分。現在十四年過去了,沒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這個時刻,在東京灣簽字投降了,天網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謂歟!”
勝利固然可喜可賀,但是更可貴的是在勝利時刻仍然保持清醒頭腦。記者的憂患意識和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在此刻表現出來。“我們別忘了百萬將士流血成仁,千萬民眾流血犧牲,勝利雖最後到來,代價卻十分重大。我們的國勢猶弱,問題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團結,才能保持和發揚這個勝利成果。否則,我們將無面目對子孫後輩講述這一段光榮歷史了。”
49年後,朱啟平在國際新聞局參加創辦每日《英文參考消息》。緊張的工作,微薄的收入,絲毫沒有影響他投身新中國建設的熱情。1951 年參加赴朝慰問團,美軍飛機多次襲擊代表團駐地,朱啟平直到1953年7月27日停戰協定最終簽字的那一刻。
從朝鮮回國后,他任香港大公報駐京記者。1957年因對新聞業務問題提了幾條意見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遣送黑龍江省東部虎林縣,修大壩、燒炭,食馬肉,經常看見抬出死人,真可謂“九死一生”。直到1960年經廖承志提名,朱啟平調到解放軍外國語學院教外語。及至“文革”,他這‘摘帽右派’又被揪斗……
晚年朱啟平回顧自己新聞生涯,對年輕同業寄予殷切希望。他說:“作為記者,一筆在手,胸中要有億萬人民,萬不得已時,可以不寫,不能打誑。”“當記者,最要緊的,是盡心為讀者提供最好、最真誠的服務,不說假話,不炫耀自己,始終不渝,要做到這一點極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一顆熾熱的為讀者服務的心是第一位的,文字水平,包括寫特寫,自然越高越好,但是是第二位的。”其中體現出來的敬業精神和人生境界,直到今天仍是新聞工作者追求的崇高目標。
太平洋戰爭中,他成為活躍一時的隨軍記者;1945年9月2日在“密蘇里”號上舉行的日本受降儀式中,朱啟平就是三名中國記者其中之一,發回的長篇通訊《落日》傳誦一時,被公認為“狀元之作”,後來還被列為大學新聞系教材。其後他又任駐美特派員兼聯合國記者,赴朝鮮戰地採訪,通訊享譽海內外。
老新聞人嚴秀先生1997年讀到遲來結集出版的《朱啟平新聞通訊選》,就發自內心地讚許說:“朱啟平的新聞之所以值得長久保存,關鍵在於兩個字:眼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投降簽字儀式定於1945年9月2日上午九時在美國海軍“密蘇里”號戰艦上舉行。日本的投降儀式分明在上午,為什麼題目叫落日?這裡有象徵意義,曾經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今天終於在世界人民面前低頭簽字投降,如同日落西山一樣;日本侵略者當年侵略他國,其以“旭日東升”自喻的國旗,令人望而生惡,今天,它的“墜落”不僅大快人心,且透出作者的嘲諷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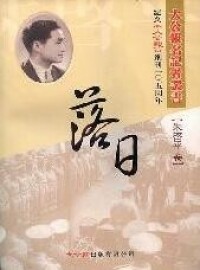
《落日》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時十分,我在日本東京灣內美國超級戰艦「密蘇里」號上,離日本簽降代表約兩三丈的地方,目睹他們代表日本簽字,向聯合國投降。
這簽字,洗凈了中華民族七十年來的奇恥大辱。這一幕,簡單、莊嚴、肅穆,永誌不忘。
天剛破曉,大家便開始準備。我是在七點多鐘隨同記者團從另一艘軍艦乘小艇登上「密蘇里」號的。「密蘇里」號艦的主甲板有兩三個足球場大,但這時也顯得小了。走動不開。到處都是密密簇簇排列著身穿卡嘰制服、持槍肅立的陸戰隊士兵,軍衣潔白、摺痕猶在、滿臉笑容的水兵,往來互相招呼的軍官以及二百多名各國記者。灰色的艦身油漆一新,十六英寸口徑的大炮,斜指天空。這天天陰,灰雲四罩,海風輕拂。海面上艦船如林,飄揚著美國國旗。艙面上人影密集,都在向「密蘇里」號艦注視著。小艇往來疾駛如奔馬,艇后白浪如練,摩托聲如猛獸怒吼,幾乎都是載著各國官兵來「密蘇里」號艦參加典禮的。陸地看不清楚,躺在遠遠的早霧中。
簽字場所
簽字的地方在戰艦右側將領指揮室外的上層甲板上。簽字用的桌子,原來準備向英艦「喬治五世」號借一張古色古香的木案,因為太小,臨時換用本艦士官室一張吃飯用的長方桌子,上面鋪著綠呢布。桌子橫放在甲板中心偏右下角,每邊放一把椅子,桌旁設有四五個擴音器,播音時可直通美國。將領指揮室外門的玻璃櫃門,如同裝飾著織綿畫一般,裝著一面有著十三花條、三十一顆星、長六十五英寸、闊六十二英寸的陳舊的美國國旗。這面旗還是九十二年前,首次來日通商的美將佩里攜至日本,在日本上空飄揚過。現在,旗的位置正下視簽字桌。桌子靠里的一面是聯合國簽字代表團站立的地方,靠外的留給日本代表排列。桌前左方將排列美國五十位高級海軍將領,右方排列五十位高級陸軍將領。桌后架起一個小平台,給拍電影和拍照片的攝影記者們專用。其餘四周都是記者們的天下,大炮的炮座上、將領指揮室的上面和各槍炮的底座上,都被記者們佔住了。我站在一座在二十厘米口徑的機關槍上臨時搭起的木台上,離開簽字桌約兩三丈遠。在主甲板的右前方、緊靠舷梯出入口的地方,排列著水兵樂隊和陸戰隊榮譽儀仗隊,口上又排列著一小隊精神飽滿、體格強壯的水兵。
白馬故事
八點多鐘,記者們都依照預先規定的位置站好了。海爾賽將軍是美國第三艦隊的指揮官,「密蘇里」號是他的旗艦,因此從來客的立場講,他是主人。這時他正笑吟吟地站在出入口,和登艦的高級將領們一個個握手寒暄。之後,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將軍到了,海爾賽將軍陪著這位上司走入將領指揮室,艦上升起尼米茲的五星將旗。海爾賽以前曾在向記者的一次談話中說過這樣一件事:他看中了日本天皇閱兵時騎的那匹白馬。他說,想等擊敗日本之後,騎上這匹名駒,參加美軍在東京街頭遊行行列。他還說,已經有人在美國國內定製了一副白銀馬鞍,準備到那時贈他使用。一個中士也從千裡外寫信給他,送他一副馬刺,並且希望自己能在那時扶他上馬。我還想起,第三艦隊在掃蕩日本沿海時,突然風傳「密蘇里」號上正在蓋馬廄。現在,馬廄沒有蓋,銀駒未渡海,但日本代表卻登艦簽字投降來了。
樂隊不斷奏樂,將領們不斷到來。文字記者眼耳傾注四方,手不停地作筆記。攝影記者更是千姿百態,或立或跪,相機對準各處鏡頭,搶拍下這最有意義的時刻。這時候,大家都羨慕四五個蘇聯攝影記者,其中兩個身穿紅軍制服,仗著不懂英語,在艦上到處跑,任意照相。可是我們這些記者因為事先有令,只能站在原定地點,聽候英語命令,無法隨意挪動。這時,上層甲板上的人漸漸多了,都是美國高級將領,他們滿臉歡喜,說說笑笑。我還從來沒有見過在這樣一塊小地方聚集這麼多的高級軍官。
代表到來
八點半,樂聲大起,一位軍官宣布,聯合國簽字代表團到。他們是乘驅逐艦從橫濱動身來的。頃刻間,從主甲板大炮後走出一列衣著殊異的人。第一個是中國代表徐永昌將軍,他穿著一身潔凈的嘩嘰軍服,左胸上兩行勛綬,向在場迎接的美國軍官舉手還禮后,拾級登梯走至上層甲板上。隨後,英國、蘇聯、澳洲、加拿大、法國、荷蘭、紐西蘭的代表也陸續上來了。這時,記者大忙,上層甲板上成了一個熱鬧的外交應酬場所。一時間,中國話、英國話、發音語調略有不同的美國英語以及法國話、荷蘭話、俄國話,起伏交流,笑聲不絕。身移影動時,只見中國代表身穿深灰黃軍服;英國代表穿全身白色的短袖、短褲制服,並穿著長襪;蘇聯代表中的陸軍身穿淡綠棕色制服,褲管上還鑲有長長的紅條,海軍則穿海藍色制服;法國代表本來穿著雨衣,攜一根手杖,這時也卸衣去杖,露出一身淡黃卡嘰制服;澳洲代表的軍帽上還圍有紅邊……真是五光十色,目不暇接。
八時五十分,樂聲又響徹上空,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到。他也是坐驅逐艦從橫濱來的。尼米茲在艦面上迎接他,陪他進入位於上層甲板的將領指揮室休息。艦上升起他的五星將旗,和尼米茲的將旗並列。軍艦的主桅杆上,這時飄起一面美國國旗。
上層甲板上熱鬧的外交場面漸漸結束了。聯合國代表團在簽字桌靠里的一面列隊靜立。以徐永昌將軍為首的五十位海軍將領和五十位陸軍將領,也分別排列在預先安排好的位置上。這時有人說,日本代表團將到。我急急翹首望去,只見一艘小艇正向軍艦右舷鐵梯駛來。不久,一位美國軍官領先,日本人隨後,陸續從出入口來到主甲板。入口處那一小隊水兵向美國軍官敬禮后,即放下手立正。樂隊寂然。日本代表團外相重光葵在前,臂上掛著手杖,一條真腿一條假腿,走起路來一蹺一拐,登梯時有人扶他。他頭上戴著大禮帽,身穿大禮服,登上上層甲板就把帽子除了。梅津美治郎隨後,一身軍服,重步而行,他們一共十一個人,到上層甲板后,即在簽字桌向外的一面,面對桌子列成三行,和聯合國代表團隔桌而立。這時,全艦靜悄悄一無聲息,只有高懸的旗幟傳來被海風吹拂的微微的獵獵聲。重光一腿失於淞滬戰爭后,一次在上海虹口閱兵時,被一位朝鮮志士尹奉告投擲一枚炸彈炸斷。梅津是前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著名的《何梅協定》日方簽訂人。他們都是中國人民的熟人,當年在我們的國土上不可一世,曾幾何時,現在在這裡重逢了。
儀式開始
九時整,麥克阿瑟和尼米茲、海爾賽走出將領指揮室。麥克阿瑟走到擴音機前,尼米茲則站到徐永昌將軍的右面,立於第一名代表的位置。海爾賽列入海軍將領組,站在首位。麥克阿瑟執講稿在手,極清晰、極莊嚴、一個字一個字對著擴音機宣讀。日本代表團肅立靜聽。麥克阿瑟讀到最後,昂首向日本代表團說:「我現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國大本營的代表,在投降書上指定的地方簽字。」他說完后,一個日本人走到桌前,審視那兩份像大書夾一樣白紙黑字的投降書,證明無誤,然後又折回入隊。重光葵掙紮上前行近簽字桌,除帽放在桌上,斜身入椅,倚杖椅邊,除手套,執投降書看了約一分鐘,才從衣袋裡取出一支自來水筆,在兩份投降書上分別簽了字。梅津美治郎隨即也簽了字。他簽字時沒有入座,右手除手套,立著欠身執筆簽字。這時是九時十分,軍艦上層傳來一聲輕快的笑聲,原來是幾個毛頭小夥子水兵,其中一個正伸臂點著下面的梅津,在又說又笑。但是,在全艦莊嚴肅穆的氣氛下,他們很快也不出聲了。
麥克阿瑟繼續宣布:「盟國最高統帥現在代表和日本作戰各國簽字。」接著回身邀請魏銳德將軍和潘西藩將軍陪同簽字。魏是菲律賓失守前最後抗拒日軍的美軍將領,潘是新加坡淪陷時英軍的指揮官。兩人步出行列,向麥克阿瑟敬禮后立在他身後。麥克阿瑟坐在椅子上,掏出筆簽字。才寫一點,便轉身把筆送給魏銳德。魏銳德掏出第二支筆給他,寫了一點又送給潘西藩。他一共享了六支筆簽字。簽完字后,回到擴音器前說:「美利堅合眾國代表現在簽字。」這時,尼米茲步出行列,他請海爾賽將軍和西門將軍陪同簽字。這兩人是他的左右手。海、西兩人出列后,尼米茲入座簽字,簽完字,就各歸原位。麥克阿瑟接著又宣布:「中華民國代表現在簽字。」徐永昌步至桌前,由王之陪同簽字。這時我轉眼看看日本代表,他們像木頭人一樣站立在那裡。之後,英、蘇、澳、加、法、荷等國代表在麥克阿瑟宣布到自己時,先後出列向麥克阿瑟敬禮后,請人陪同簽字。陪同的人澳洲最多,有四個,荷蘭、紐西蘭最少,各一人。各國代表在簽字時的態度以美國最安閑,中國最嚴肅,英國最歡愉,蘇聯最威武。荷蘭代表在簽字前,曾和麥克阿瑟商量過。全體簽字畢,麥克阿瑟和各國首席代表離場,退入將領指揮室,看錶是九點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製造瀋陽事件,隨即侵佔東北;一九三三年又強迫我們和偽滿通車,從關外開往北平的列車,到站時間也正好是九點十八分。現在十四年過去了。沒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這個時刻,在東京灣簽字投降了,天網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謂歟!
投降書髒了
按預定程序,日本代表應該隨即取了他們那一份投降書(另一份由盟國保存)離場,但是他們還是站在那裡。麥克阿瑟的參謀長蘇賽蘭將軍本來是負責把那份投降書交給日方的,這時他卻站在簽字桌旁,板著臉和日本人說話,似乎在商量什麼。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麼事,記者們議論紛紛。後來看見蘇賽蘭在投降書上拿筆寫了半晌,日本人才點頭把那份投降書取去。事後得知,原來是加拿大代表在日本那份投降書上簽字時簽低了一格,佔了法國簽字的位置,法國代表順著簽錯了地方,隨後的各國代表跟著也都簽錯了,荷蘭代表首先發現這錯誤,所以才和麥克阿瑟商量。蘇賽蘭後來用筆依著規定的簽字地方予以更正,旁邊附上自己的簽字作為證明。倒霉的日本人,連份投降書也不是乾乾淨淨的。
日本代表團順著來路下艦,上小艇離去。在他們還沒有離艦時,十一架超級堡壘排列成整齊的隊形,飛到「密蘇里」號上空,隨著又是幾批超級堡壘飛過。
機聲中,我正在數架數時,只見後面黑影簇簇,蔽空而來,那都是從航空母艦上起飛的飛機,一批接一批,密密麻麻,不知有多少架,頃刻間都到了上空,然後向東京方向飛去。大戰中空軍將士厥功甚偉,理應有此榮譽,以這樣浩浩蕩蕩的陣勢,參加敵人的投降典禮。
我聽見臨近甲板上一個不到二十歲滿臉孩子氣的水手,鄭重其事地對他的同伴說:「今天這一幕,我將來可以講給孫子孫女聽。」
這水兵的話是對的,我們將來也要講給子孫聽,代代相傳。可是,我們別忘了百萬將士流血成仁,千萬民眾流血犧牲,勝利雖最後到來,代價卻十分重大。我們的國勢猶弱,問題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團結,才能保持和發揚這個勝利成果。否則,我們將無面目對子孫後輩講述這一段光榮歷史了。舊恥已湔雪,中國應新生。
(1945年9月3日寫於橫須賀港中軍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