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小煒
施小煒
施徠小煒(1957年—)早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日本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后留校任教。后留學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日本文學研究科,並執教於日本大學文理學部。經他翻譯的村上春樹的《當我談跑步時談些什麼》,以及日本著名女作家川上弘美的《老師的提包》等多部譯著,獲得了讀者廣泛好評。也是村上春樹新作《1Q84》第一二三部的譯者。
求學生涯
施小煒,1957年出生,他很喜歡中國古體詩,曾是他尊敬的老師楊烈先生組織的餃子詩社的成員,楊先生去世時,施小煒還專門寫了一首古體詩悼念。
1989年至2007年,施小煒都住在日本,先是留學,後來留在日本大學里任教,主教比較文學,對芥川龍之介等作家的研究很受肯定。

施小煒
譯著村上作品
自2009年在非常低調的情況下接手《1Q84》中文本翻譯任務以來,施小煒連續奮戰7個月,除了大學教職的正常工作以外,他的幾乎全部業餘時間都撲在了這部小說翻譯上,全力以赴,不敢稍懈。
代價也是痛苦的,翻譯過程中腰痛發作,持續三周,只能仰卧在床上,將電腦放在肚子上繼續翻譯。“這是翻譯中最苦的時候。”施小煒說。至於翻譯中耗費的巨大腦力,施小煒自述“每一頁都是挑戰。所謂敝帚自珍,希望每一頁都能讓我滿意。”但同時他又表示:“我是一個‘文學翻譯否定論’者,儘管我自己作一些文學翻譯。這是我曾再三表示過的觀點:文學翻譯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營生。
基於三大理由:一是文學作品的不可翻譯性(原本的文學性,是在翻譯中失去的東西。翻譯能夠傳遞事實,卻無法傳遞文學性,只能向讀者提供文學性的代用品)。二是譯本的不確定性。三是翻譯的必需性。概言之,文學翻譯是不可能的,卻是必要的。而翻譯中的最大挑戰,恐怕就在於如何尋覓譯者自以為是的最佳代用品了。”
翻譯界新星
從翻譯“海選”中拔得頭籌接下翻譯村上春樹《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后,資深教授施小煒一下子成了日語翻譯界引人注目的“新星”,尤其是一場關於村上春樹“專屬譯者”翻譯水準優劣之爭的興起,令他多少有些無奈。接手《1Q84》,對他來說,似是水到渠成,唯儘力譯出滿意作品而已。讀者問他會不會成為林少華后的村上新的御用譯者?施小煒答:“也許還會再譯幾本村上作品。但是‘御用譯者’云云,非吾所願也——首先這個詞就不喜歡。比起一枝獨秀,我更欣賞並支持百花齊放,並願意躬體力行。”

《1Q84》Book1
詮釋解讀《1Q84》
村上春樹曾多次提到“想寫綜合小說”,他舉出的實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據他自己稱,所謂綜合小說就是“將種種世界觀、種種視角糅合為一體,使之相互糾纏盤根錯節,以期浮現出某種新的世界觀來”。
徠《1Q84》就是這樣一部“綜合小說”。這體現在作品的多面性上。貫穿小說的第一主線是男女主人公天吾與青豆的愛情,曲曲折折峰迴路轉,而最終只怕逃不脫“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窠臼,於是我們也許可以將它當做戀愛小說來讀;第二主線則是村上本人也曾親歷過的戰後日本知識界的思想演化史,波瀾壯闊驚心動魄,人們又不妨將它作為思想小說來讀;而在處理副線時,作者不迴避性主題,且寫來坦誠,可能會有人感到作品不無情愛小說的側面;在故事的講述上卻又導入了推理解謎的手法,寫得津津有味,於是我們則又可以把它當做懸念小說來讀。
另外,可以從私文學和公文學的角度去理解。比如村上早期的《且聽風吟》就是一個純粹的私文學作品。徹底割斷與這個社會的關係,都是在私人層面跟周圍人發生關係,跟社會完全脫節。這是日本近代文學的一大特點。
《1Q84》的重要性在於:天吾受到某一個公司的僱用,為那個公司常年工作,是很自由的人,隨時可能被解僱,也隨時可能他自己辭職,這就是私人的層面;他改寫《空氣》,影響了社會,而不僅僅是影響自己個人層面或者周邊私人關係層面,使得這部小說更有社會意義。可以說,在《1Q84》中,私文學與公文學成功地對接,村上文學又一次實現了華麗的“變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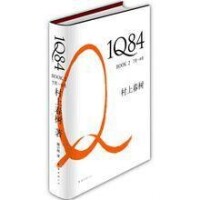
《1Q84》Book2
《1Q84》是部反《1984》的小說
我認為《1Q84》是一部思想小說。
止庵曾經說過,《1Q84》是對《1984》 的致敬。但是,他反對類型化的致敬,要注意到兩者的不同之處。他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一致。
《1Q84》當然是致敬,但是致敬不等於模仿。不妨說《1Q84》是一部反《1984》的小說,它在許多方面都體現出這種特徵。儘管它作了種種偽裝,實際上,它體現了對意識形態操縱個人現實的一種批判。
“小小人”就是意識形態,是意識形態的形象化。這和《1984》不同。
《1984》直奔主題,非常寫實,把一個已經極權化的社會展示給你看。
《1Q84》則不同,它裡面的極權社會是存在於講述人的口中,沒有被直接呈現。“先驅”等於深田保,就是老大哥。深田保所控制的意識形態,就是“小小人”。他最終也想擺脫這種意識形態,擺脫小小人,他擺脫的辦法只有死。青豆去刺殺他的時候覺得很奇怪,因為她發現深田保知道她要來刺殺自己,並且歡迎她來刺殺自己。村上春樹用魔幻的方式把意識形態形象化了,它不再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它變成一種人的形狀,這種人很小,藏在每個人的體內。意識形態存在於我們身體之內。
《1984》裡面,老大哥要控制人類,只有靠折磨他們等一些外在的手段。而小小人存在於我們的體內,要消滅這種意識形態,就必須靠我們自己殺死自己。這是它的可怕之處,也是《1Q84》超越《1984》的地方。
村上春樹的小說綜合了很多東西,是一種綜合小說,讀言情小說、讀奇幻小說、讀思想小說的讀者都可以在他的小說裡面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他隱藏得很深,很多年輕人沒有讀懂村上春樹。
他的作品還呈現出一種共同性,雖然他自己已經61歲了,但是他筆下的人物永遠是年輕人。他的主人公不會跟著他一起“與齡俱進”,長大變老。他有句格言,寫在他的自行車車身上,叫做“到死都是十八歲”,這是加拿大的歌手寫的一首歌。
村上是否歐美化
大家都說村上春樹是非常美國化或者歐化的日本作家,其實他書里常寫的法國葡萄酒等等在日本很普通,在學生食堂就會賣這些東西。傳統日本的早飯是一碗米飯,一碗味增湯,一個生雞蛋。但更多的普通人早上恐怕還是會烤一個麵包,喝杯紅茶,也是非常西化。
西方文化早已融入了日本社會,甚至可以說早已成為現代日本文化的一個構成部分。如不理解這一部分,就無法全面理解當今的日本和日本人。因此與其說是村上春樹“美國化”了,不如將句子的主語換作“整個日本社會”方才更符合實情。喝牛奶未必就會變牛,吃魚也未必就會變魚。村上未必因此就變成了“美國化”了的小說家。

《1Q84》Book3
譯著求真求實
我以為,任何一部譯著,都無非是譯者自身風格與原著風格鬥爭妥協的結果。每個譯者,只要他自己也寫點東西,大約都會有著自己的文體風格,至少是表達習慣,要求譯者完全拋卻自己的文體風格或者表達習慣,百分之百地再現原著的風格,雖然十分地理想,但其實是不可能實現的。譯者不可能殺死自己,以凸顯原著風格;譯者的自身風格總會在不知不覺間偶露崢嶸。譯者至多只能無限地接近原著風格。
最愛《且聽風吟》
《且聽風吟》。日本批評家川本三郎說過這樣的話:任何一個小說家,都絕難超越他的處女作——大意如此,現下手頭沒有原文,未經核對。我覺得在村上的這部處女作中,他後來探討的許多主題,都有所預示。
駁斥孩子不宜的說法
在日本,暢銷書中也有您說的“淺俗讀物”,可並不僅僅只有“淺俗讀物”才能暢銷。非常希望早日看到在我們中國,能夠多一些非“淺俗讀物”的暢銷。
據我理解,日本的作家們似乎有一種傾向:將性視為“人”與別的生物至為根本的區別所在。在眾多生物中,獨有人的性是截然不同於它的。一般而言,人以外的動物們的性大抵僅僅為繁殖後代、延續物種而存在,而人的性則遠為複雜。所以性的描寫,在他們而言,乃是深入人之本質的切入口。
村上的性描寫,儘管坦誠,卻很潔凈。他是將它作為人這一自然存在的自然一面來描寫,我以為。寫人而絕口不提及性,也許便難稱全面,難稱自然,難稱“綜合”吧。
家長們不用擔心。這部作品你說花哨也好,偽裝也好,它歸根結底是寫一個純潔的故事,一對少男少女在10歲的時候,彼此間產生了某種情愫,在20年中兩人始終不曾忘記對方,最後經過種種曲折走到一起。應該說,這是一個純潔的故事。
村上春樹的性描寫,應當說還是乾淨的。我覺得,如果我們連《金瓶梅》都能夠接受的話,便沒有理由不能接受村上春樹。

施小煒
村上春樹 《當我談跑步時談些什麼》。
村上春樹 《1Q84》第一、二、三部。
村上春樹 《天黑以後》
日本著名女作家川上弘美的《老師的提包》等多部譯著。
村上春樹 《沒有色彩的多崎造和他的巡禮之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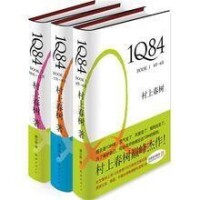
《1Q84》三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