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拉可汗
柴拉可汗
專輯中文名: 柴拉可汗
歌手: 李建復
音樂風格: 流行

圖
資源格式: APE
發行時間: 1981年
地區: 台灣
語言: 普通話
那是唱片公司買斷作品的年代,幾位年輕的音樂人好友,包括當時最受歡迎的民歌手蔡琴和李建復,搶手的製作人李壽全等人,自組天水樂集,他們主張從創作到演唱一以貫之,不假他人,不受商業箝制,完完全全,對自己,對大眾負責,被視為離經叛道,卻也交出兩張精采萬分的作品:《柴拉可汗》和《一千個春天》。二十五年後,兩張作品的復刻版現在以32bit/96k Remaster重新問世!
《天水》這兩張專輯的精神內涵或許承襲著中國現代民歌的脈絡,但就音樂形式而言,它們骨子裡是不折不扣的搖滾樂。李壽全早在新格時期替王海玲、李建複製作專輯的時候,就偷渡過一些搖滾的元素到民歌專輯里,但直到加入天水,他才真正能夠擺脫羈絆、大展身手。
李壽全迷戀的是七○年代alan parsons Project、Moody Blues、Yes、SUPERTRAMP、Pink Floyd等等前衛搖滾樂團的概念式專輯(concept album),當年一般的專輯只是把一堆歌曲湊在一起,很少有人思考整張專輯內在的聆聽邏輯或者概念的連貫,音樂製作人也很少和編曲溝通。李壽全算是當時第一個以整張專輯的規格去思考,並且對編曲很有想法的製作人。他在《龍的傳人》專輯與陳志遠初步嘗試這種製作編曲配合的方式,到了《天水》的兩張專輯,李壽全終於可以再把這樣的理想向前推進一大步:這兩張唱片的核心,分別是《柴拉可汗》和「細說從頭》這兩個組曲。兩者風格殊異,但同樣大膽。
長達十一分鐘的《柴拉可汗》交響詩組曲,是李壽全受到Chris De Burgh的"Crusader"專輯啟發,乃決定做一首結合演奏曲與口白橋段的長篇敘事詩,並且把故事背景設定在11世紀的蒙古平原。當時才22歲的靳鐵章發揮想像力,把李壽全的故事寫成六段式的長曲,並且特意用了一些中東式的音階來表現塞外風情。陳揚一口氣擔下了這樁史無前例的編曲《大工程》據蘇來回憶,陳揚必須先用鋼琴編出一個模型,再把整個架構建立起來,根本是在創作交響樂。現在你再叫陳揚做這樣的事,我想他也不願意幹了。同樣才22歲的李建復,聲嗓正是巔峰狀態,標題曲《柴拉可汗》的高音完全難不倒他,清亮的歌喉幾乎壓過了戰鼓喧天的器樂。一曲《別離》唱得盪氣迴腸、卻絕無半分匠氣流氣,真是一整個時代的絕響。
《一千個春天》專輯中的《細說從頭》組曲,則是和《柴拉可汗》相呼應的嘗試。《柴拉可汗》是一氣呵成的長曲,《細說從頭》則刻意讓六首歌各自有獨立的面貌,分散在唱片的AB兩面。這套由蘇來和許乃勝合作的組曲,在精神上與雲門的《薪傳》呼應,企圖用六首歌描繪出先民渡海來台、落地生根、世代傳承的歷史。六首作品曲勢起伏、風格殊異,又要能夠創造內在的連貫性。李壽全說,這其實也帶著"Rock Opera"(搖滾歌劇)的味道。
說到李建復的這張專輯,不能不提及“天水樂集”,這個現在聽來有些陌生的名字,在風起雲湧的民歌時代可是一塊響噹噹的牌子。當時由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像李建復、蔡琴、蘇來、李壽全組成,他們希望能脫離版權制度的束縛,自立門戶,做出最好的音樂。以“龍的傳人”成名的民歌手李建復和他的朋友們都希望在已漸漸成為千篇一律的民歌中開闢一條新的路線,突破老的形象。
於是《柴拉可汗》這張圍繞中國情節的概念唱片問世了。主題曲《柴拉可汗》竟由組曲的形式出現,由《序曲》開始,然後著名演員郎雄娓娓道來“柴拉可汗”的故事,再接《塞外》,李建復鏗鏘地演唱《柴拉可汗》,《別離》,《征戰》《尾聲》,整整七個段落,大漠、黃沙、英雄、射鵰,長達11分鐘,一氣呵成,宛如一部小的交響詩,聽下來非常過癮。據說編曲的陳揚完成此首作品的編曲,就再也不願接像這樣的工作了。
另一首取材《水滸傳》的《武松打虎》,不僅運用了京劇中的鑼鼓點作為過場,而且也把一些西方流行音樂元素融了進去,展現了醉酒、上山,打虎的整個過程,那個好漢武松的形象被活脫脫地表現了出來。這種創作不但在當時是很大的革新,就是現在聽來都不乏其前衛之處。
天水樂集的成員稱自己為傻子,他們認為也許只有傻子才會作這樣的音樂。《傻子的理想》正是紀念他們對音樂的追求與夢想。其實他們的理想很簡單,是《漁樵問答》中那種“採菊東離下”的浪漫,是《天水流長》中的古風古韻。那是一段黃金歲月,而《柴拉可汗》正是鑄造了那個理想年代的經典之作。
台灣百佳專輯的評選中《柴拉可汗》排在第40位,但是口碑只是口碑,李建復在推出2張專輯后,銷量的慘淡,音樂的實驗性不太被接受,現實的環境最終讓“天水樂集”解散,但留下的《柴拉可汗》,《一千個春天》兩張專輯都成了樂壇的經典。而“天水樂集”作為第一個音樂工作室對日後的唱片界也起著無比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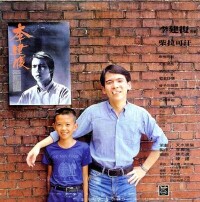
《柴拉可汗》
天水樂集策劃/李壽全製作/陳揚、陳志遠編曲
民歌末期“力挽狂瀾”的經典鉅作
1981 年原始母帶 32bit/96k Remaster,發燒級爆棚音質
收錄全新出土“謝幕曲”珍貴 Demo 與伴奏版本
精心重現原始專輯內容,收錄珍貴歷史圖文資料
天水樂集成員親撰回顧感言、樂評人馬世芳 8000 字專文導聆
那是唱片公司買斷作品的年代,幾位年輕的音樂人好友,包括當時最受歡迎的民歌手蔡琴和李建復,搶手的製作人李壽全等人,自組“天水樂集”,他們主張“從創作到演唱一以貫之,不假他人,不受商業箝制,完完全全,對自己,對大眾負責”,被視為離經叛道,卻也在民歌風潮的末期以“力挽狂瀾”的氣魄推出兩張重量級專輯:“柴拉可汗”和“一千個春天”,卻因“走得太遠”,作品“叫好不叫座”,成為民歌時代最終、也是最悲壯的經典。
二十多年來,《柴拉可汗》和《一千個春天》早已絕版,成為行家眼中的珍寶,原版黑膠唱片市價高達數千元。2005年,“天水樂集”的六位老朋友決定重新出版這兩張專輯,兩張作品的復刻版現在以 32bit/96k Remaster 重新問世!替曾經擁有的青春年代,重新實現那樁“傻子的理想”。
天水樂集的時代背景:
1980 年冬,幾個搞音樂的年輕人,經常在新生南路的“紫藤廬”煮茶清談。其中有寫歌的、有唱歌的、也有搞製作的,都是二十歲出頭的熱血青年。聊到唱片公司如何“欺負”年輕人,不禁同仇敵愾、愈談愈激動。最後,大家決定一起豁出去、乾脆脫離唱片公司體制,以獨立創作人的身分“大幹一票”,“天水樂集”就此誕生。他們年紀雖小,卻個個大有來頭:蔡琴和李建復是當時最受歡迎、備受景仰的民歌手,李壽全是“新格”旗下最搶手的製作人,蘇來、許乃勝、靳鐵章都是才華橫溢的詞曲作者。他們信心滿滿,以為光憑這群人的才華、誠意和勇氣,就一定能夠橫掃樂壇、再造新氣象。
對於當時唱片界不合理的情況,蘇來寫道:“著作權賣斷,歌者因公司門戶不能自由演唱喜愛的歌,是一種阻礙進步的行為。欲求突破,只有從根本上入手。那就是組成團體,從創作到演唱一以貫之,不假他人,不受商業箝制,完完全全,對自己,對大眾負責。”這段豪氣干雲的宣言,當年竟被視為“離經叛道”、“忘恩負義”。如今詞曲版權不賣斷、唱片公司用“版稅”方式和音樂人拆帳,都早已成為“常識”,然而回首當年,著作權法還沒通過,侯德健寫“龍的傳人”只拿了三千塊,李建復錄一張專輯也只有兩三萬的酬勞,唱片賣得再好,也與他們無關。對照暢銷專輯動輒創下十幾萬張的市場紀錄,難怪他們悒鬱不平。
那是“雲門舞集”、“蘭陵劇坊”、“雅音小集”先後在舞台上掀起熱潮的時代,出版界“漢聲雜誌”崛起,高信疆主編“人間副刊”,報導文學方興未艾,鄉土論戰餘溫未退。新的啟蒙年代,彷彿就在伸手可及之處。也是在那陣子,台美斷交,人心惶惶,“莊敬自強”口號震天價響。“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大逮捕和軍法大審吸引著全國的注目,政治氣氛悄悄開始鬆動。台灣經濟持續“起飛”,服務業人口漸漸追上製造業人口。
從七十年代中期,楊弦創作“中國現代民歌”、李雙澤喊出“唱自己的歌”口號以來,“西學中用”、“文化傳承”一直都是青年創作歌謠的重要課題‐‐“唱自己的歌”這個口號背後,原本就有著強烈的國族意識。而七十年代“鄉土意識”的萌芽,又讓這樣的思考有了更豐富的樣貌。“天水樂集”的作品充滿故土中國的文化意象,音樂形式則揉合了西洋搖滾、古典音樂和傳統戲曲的風格,或可視為“中國現代民歌”這個脈絡經過數年洗禮,吸收了豐富的製作、創作與市場實戰經驗之後,形式與內容臻於圓熟的典範。這反映了那個世代知識青年的思惟,也和“雲門”、“蘭陵”呼應,在“橫的移植”與“縱的繼承”之間努力尋找新的出路。
幸或不幸,“一千個春天”和“柴拉可汗”竟也成為“民歌”風潮末期,企圖“挽狂瀾於既倒”的最後經典。這場轟轟烈烈的音樂大夢,許是“走得太快太遠”,聽眾不如想像中捧場。他們原本打算出三張系列專輯,分別是李建復個人專輯、李建復和蔡琴的合輯、以及蔡琴個人專輯。但前兩張的銷量不如預期,規劃中的第三張也就一直沒做出來。加上李建復入伍服役、許乃勝赴日留學,大家意興闌珊,“天水”僅僅維持了一年多便結束了。這兩張專輯總共花掉了 240 萬的製作費,在當時是相當驚人的規格。投資發行的“四海唱片”,最後並沒有回本:“專輯賣得不夠好,害四海沒賺到錢,所以第三張我們也不好意思再做了。”李壽全苦笑著說。 “天水”解散不久,金韻獎停辦、海山唱片結束營業,市面上跟風抄襲、粗製濫造、標榜“民歌”的作品到處泛濫,“民歌沒落”之說甚囂塵上。新生代的滾石唱片與飛碟唱片相繼成立,以強勁的“企劃導向”方式替唱片界帶來一番新氣象,開展了台灣流行音樂的“后民歌”時代。“天水”的起落,正好處在“前浪”待退、“後浪”初興的交匯點。“天水”集結音樂人才獨立製作專輯、先爭取“百分之百的音樂製作自主權”,再找發行公司合作出版的模式,替八十年代末期林立的“音樂工作室”樹立了最早的榜樣。這樣的合作方式,讓音樂人的想法得以不受唱片公司的無謂干預,也間接促成了後來台灣流行音樂百花齊放的榮景。而版權和版稅的觀念,之後也透過許多音樂人奔走串連而成為共識,“強迫賣斷”的劣習不再,證明“天水”當初的堅持確實值得。
天水樂集的音樂:細聽這兩張專輯
“天水”這兩張專輯的精神內涵或許承襲著“中國現代民歌”的脈絡,但就音樂形式而言,它們骨子裡是不折不扣的搖滾樂。李壽全早在新格時期替王海玲、李建複製作專輯的時候,就“偷渡”過一些搖滾的元素到民歌專輯里,但直到加入“天水”,他才真正能夠擺脫羈絆、大展身手。
陳揚再度接下這樁編曲的大工程,並且用了跟“柴拉可汗”完全不同的風格:且聽“古厝”開場那段一分多鐘的鋼琴前奏,一絲腥氣也無,沉鬱悠遠,層層遞進,再徐徐引入李建復和蔡琴的歌聲,不愧大師手筆。“陳揚在學校主修鋼琴和打擊樂器,對這兩種樂器有很獨到的想法,”李壽全回憶道:“當時‘天水’有幾首比較實驗性、比較‘怪’的歌,我就交給陳揚去編,其他想做出某些特定風格的歌,就讓陳志遠來處理。他們兩個人的工作習慣很不一樣,但是都非常有才華!”
我們在“細說從頭”組曲確實可以感受到陳揚的野心:“我的鋤頭扛在肩”瀟灑如雨珠的鋼琴、“搖搖童謠”晶瑩剔透的鍵盤前奏,都是不落俗套的示範。“白浪滔滔向前航”拳拳到肉的大鼓打得漂亮,“歡喜慶豐年”後段的鑼鼓鐃鈸則是把“武松打虎”最末的那段實驗更進一步,整曲管弦齊鳴、電吉他熱火朝天,堪稱台灣搖滾樂錄音的里程碑。放眼當時樂壇,恐怕只有次年羅大佑遠赴日本錄製的“之乎者也”堪與並論。
李建復在“武松打虎”中把他的聲腔潛力發揮到極限,演唱表情之豐富、之“戲劇化”,恐怕是他演唱生涯空前絕後的嘗試。作曲的蘇來在這首歌用了驚人的 14 度音階,恐怕也只有李建復能夠駕馭這樣難唱的作品。陳揚的編曲更是令人咋舌:先是用琵琶和木吉他密密交疊、模擬林里風聲,繼而引進京劇武場的鑼鼓,象徵“打虎”的橋段,再以熱烈的搖滾吉他作結,最後更神來一筆,拉進一段民間喜慶音樂的嗩吶鐃鈸,創造英雄凱旋的熱鬧情境。李壽全說:“我們那時候對於要如何呈現‘打虎’傷透腦筋,後來想到京戲里抽象的舞台,也會用音樂去象徵一些東西,就請樂師來錄一段武場的鑼鼓,完全保留京戲的元素,只有陳揚墊了一點鋼琴。曲子最後的節慶音樂,表示武松凱旋歸來。錄音的時候我們幾個都下去一起敲敲打打,很熱鬧。”這首歌徹底實現了“百分之百創作自主權”的理想,前衛勇猛的曲式,如今聆聽,仍然足以讓後輩汗顏。
光從“柴拉可汗”開場曲“漁樵問答”就能感受到“天水”不受拘限的才情:游正彥行雲流水的藍調吉他和梆笛呼應交響,象徵漁夫和樵夫的對話。中國式的旋律竟然和藍調吉他搭得天衣無縫,值得向編曲的陳志遠脫帽致敬。“你可以想像樵夫砍竹子做了一支笛子,那漁夫的釣魚線就是吉他弦吧!”李壽全笑著說:“陳志遠自己也是練吉他出身,很想玩玩看 Blues 的東西,於是由他告訴 Masa (游正彥) 自己想要的彈法,兩個人合作,才能把它錄得這麼好。”
在那個沒有電腦取樣技術的年代,陳志遠在“寒山斜陽”的前奏用電子合成器手工“創造”出撞鐘的聲效,並且做出了李壽全想要的類似 Alan Parsons Project 的鍵盤音色和空間縱深:“陳志遠全憑想像,用 Roland JP-8 先做出‘金屬’的音色,再做出‘木頭’的音色,然後把兩種混在一起,就是‘木槌撞鐘’的聲音,結果非常逼真,實在很厲害!”
又如“傻子的理想”,是一首 New Wave 風格的搖滾樂,恐怕很多人都不記得李建復竟然唱過這種“搖滾巨星”風格的歌。李壽全說:“那時候很少人做這種搖滾的東西,陳志遠用 sequencer (編曲機) 去做了一段鋪底的音色,但當年還沒有數位的 Sequencer 可以設定,只有類比式的,你得一直跟著拍子按按按,才能做出這種效果。”蘇來和李壽全合作的歌詞,就是當時“天水”的自許:“大家不肯做的/我們來擔當”,這股理直氣壯的熱情和勇氣,驅動著這些“傻子”,做出了動人的成績。
此外,當然不能忘記“天水流長”這首“主題曲”。當初大家就是因為聽到靳鐵章寫的這首歌,才決定採用“天水樂集”這個名字,多少也有“尋根以明志”的意味。靳鐵章的作品多半有著雄渾的風格,這首歌細膩中不失壯闊,短短的篇幅中,李建復高亢的聲嗓和壯麗的弦樂,把格局拉得極為開闊,使這首短歌一點都不顯得“小”,功力了得,堪稱極品。
梁弘志的“跟我說愛我”是“天水”兩張專輯中唯一不是由六位成員創作的歌曲。這首歌是當時同名電影的主題曲,李壽全取得同意,把它收錄在新專輯的開場。梁弘志的第一首作品“恰似你的溫柔”在前一年由蔡琴唱紅,開創了兩人的音樂生命。他們合作的“讀你”、“抉擇”,也都是膾炙人口的經典。許是上一張故意把主打歌“天水流長”放在 B 面的作法證明“行不通”,這次他們做了一點點妥協,把“賣相最好”的歌推到最前面來。“跟我說愛我”果然大受歡迎,成為“天水”兩張專輯中最紅的歌,專輯也跟著沾光,銷售成績略勝一籌。
“意映卿卿”從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發展出來,用另一種角度重寫每個人都在課本里讀過的故事,凄惻悲壯,是當年“大時代”精神的又一展現,也可看作蔡琴“秋瑾”的姊妹篇。平心而論,當年那些充滿國族意識的歌曲如“龍的傳人”、“中華之愛”、“天水流長”,儘管事過境遷,仍然有著澄澈動人的力量,並不像當年欽定的“凈化歌曲”與時代同朽,關鍵就在這些青年創作人誠摯、純良的用心。有趣的是,當時這首歌數度送審、皆未獲新聞局通過,理由大約是“革命先烈家屬故事,他人不宜妄作文章”云云,令人哭笑不得。
“長途旅行”的編曲只用了鍵盤和電吉他作骨幹,貝斯輕輕鋪底,李壽全幽幽吹著口琴,完全沒有用到節奏樂器,創造出氤氳朦朧的空間感,很有“城市民謠”的味道,在當時是十分新鮮的嘗試,不禁讓人聯想到五年後李壽全在個人專輯“八又二分之一”的編曲方式。
專輯結束曲“謝幕曲”一語成讖,結果真的變成“天水”的最後一首歌。“謝幕曲”旋律非常美麗,當時大家都認為它有主打歌的實力,可惜這麼美的歌,當年並沒有傳唱開來。蘇來回憶“謝幕曲”是“命題作文”,原本就打算放在專輯的最後:“這首歌是為蔡琴量身打造的,寫的時候一邊想像她會怎麼唱,配合她的音域來寫旋律。”
在這次復刻版的製作過程中,蘇來找到塵封多年的兩卷盤帶:一卷是“謝幕曲”的伴奏帶,一卷是他在 1980 年10月27日自彈自唱的 Demo,包括若干至今未曾發表的作品。“當時我的工作習慣是,只要作好一批歌,就會去敦化南路的三雅錄音室,花一個下午把它們錄下來。”蘇來說:“後來蔡琴在錄音間唱‘謝幕曲’的時候,我們又做了一些調整,所以唱片里的版本和 Demo 的旋律有一點不同。”這兩卷母帶都是用 7.5 吋電台專用盤帶錄製。我們從母帶轉錄成數位格式之後,選出“謝幕曲”的兩種版本,重做母帶後期處理,放在“一千個春天”專輯最後,作為珍貴的史料參考。它們都是初次發表的“新出土”版本。
撫今追昔,回顧天水樂集:
就“替音樂人爭取版稅權益、替創作爭取自由空間”的理想來說,“天水”這兩張專輯確實達成了目標。可惜環境險惡,這群年輕人也沒想到進一步成立什麼正式組織,“天水樂集”既非公司、亦非人民團體,一旦成員星散,便形同解散了。回顧那段歷史,他們是這麼說的:
靳鐵章:“天水樂集對樂界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工作室’的發軔,那在當時被視為是大逆不道的行為,唱片公司認為我們忘恩負義,但是‘版稅’的概念從這裡開始,我想這是個里程碑。其實當初是有點不自量力,但那時候嘗試組曲的東西,背後的精神是希望流行音樂能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試著想做一些有深度和廣度的作品,雖然青澀,但我們的的確確做了嘗試。”
蘇來:“我們當時想的是‘放到世界樂壇上,什麼是代表我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們走的是一個中國風的路線,可惜的是做了兩張唱片之後就無以為繼,理想還是不敵現實。可是現在再看那時候做的事,還是很開心。因為我們大概是台灣流行音樂裡面第一個敢用 Production House 的型態去跟唱片公司談、勇於打破原來的規範、原來的惡勢力。”
李建復:“坦白講我和蔡琴當時都算滿紅的,我們希望藉著在歌壇上的地位來突破一些現況,所以透過‘天水樂集’這個工作室形態的組合做出一些作品來,再跟唱片公司談條件。除此之外,也希望能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東西,不受商業的影響。這當然是很理想化的,事實上有點不知天高地厚。我們可能忽略掉我們畢竟還是在做流行音樂,一般的聽眾,尤其是跟我們一起長大、聽民歌的聽眾,可能還沒有脫離聽民歌的習慣,而新成長的青少年可能沒有辦法一下子接受這麼新的東西,所以坦白講,那時候要不是有一兩首很好聽的歌的話,那兩張唱片不容易賣得很好。”
李壽全:“我們最初的動機、理想都沒有錯,只是時間比較早,理念沒有辦法繼續下去,可能我們裡面還是少一個生意人。當時太年輕了,覺得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沒有考慮很多跟商業上的配合。不過我們也沒有後悔,或者懷疑當初做這些東西值不值得,至少現在有人提到這兩張唱片,都覺得我們做得很好。那時候的精神,是沒有辦法再去尋找回來的。”
蔡琴在 1981 年底“天水”成軍將近周年的時候,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幾句話,或許可以作為這樁“傻子的理想”最好的註腳:為什麼不把一切留給時間來證明呢?不能長久留傳的就是無法長存,它自然會有個分曉的。我們只是想找尋自己的根啊!
關於 2005 年復刻版母帶:
為了這次復刻版的發行,我們輾轉連絡上“四海”唱片的廖干元先生,並且得知 1981 年混音完成的四卷 1/4 吋母帶都還完整留存,外盒上,李壽全 24 年前的筆跡歷歷在目。感謝廖先生慷慨出借這批母帶,我們在錄音室用所能找到最好的類比式盤帶機,把原始母帶輸出轉換成 32-bit/96kz 的數位格式,並且參考 1981 年的原版黑膠唱片,替整張專輯的音場、聲頻、音量、乃至歌曲播放的轉速,都做了憚精竭慮的校正與調整,李壽全本人也親自參與了這次復刻版母帶的重新處理,希望能讓這批歷史錄音,呈現出最細緻、最完整的聲效。我們相信,其中的用心,您會聽得到。
“天水樂集”成立於1980年,由六個熱愛音樂的年輕人合組而成。這六個年輕人甫自大專畢業,在音樂領域中各有各的專長,且皆才華洋溢,為當時校園民歌風潮中的佼佼者。其中,李壽全為策劃及執行製作人,蘇來、許乃勝、靳鐵章負責詞曲的創作,而蔡琴、李建復優越的嗓音則早為大眾熟悉。此外,當時負責為“天水樂集”作品編曲的是陳揚、陳志遠二大編曲家,這使得“天水樂集”作品水準更向上提升不少。而事實上儘管該樂集在製作了二張專輯之後便解散,但這僅有的二張專輯卻成為民歌末期試圖力挽狂瀾的經典;縱然在歷史意義上敵不過同時期蘇芮、羅大佑的黑色革命,但誠懇、紮實又不失創意的內容仍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今天聽起來依舊韻味無窮。而當年篤信“理想”與“現實”可以并行不悖的這六個年輕人,亦為今日普遍化的“音樂工作室”開了示範的先聲。
《柴拉可汗》除了作為“天水樂集”的初啼之外,它另一個音樂史上重要的意義在於其已具雛形的“專輯整體概念”,換言之,即西方音樂中所謂的“Concept Album”。整張專輯的風格非常一致,無論在詞意曲風上都蘊涵濃厚的中國味,從《漁樵問答》、《寒山斜陽》到《天水流長》、《古城夢回》,首首都象極了水墨淋漓、氣韻酣暢的中國山水畫。
除了上述歌曲外,這張唱片的重頭戲,同時也是最大的突破,在於《武松打虎》及《柴拉可汗組曲》,這兩首曲子的故事性皆相當濃厚,而陳揚的編曲使得故事的氛圍能夠鮮明地環繞在聽者四周,功不可沒。《武松打虎》的特色在於曲子中段“打虎”的部分不用文字描述,而以音樂作象徵性的表達。在當時電子合成樂器尚未普遍之際,傳統鑼鼓樂器所呈現出的效果便如同國劇中的“馬鞭”一般,雅緻別具且提供了廣大的想象空間。而李建復的歌聲亦表現了相當大的戲劇性,對於如何詮釋武松這位打虎英雄的心境作了不少努力。
較之《武松打虎》,《柴拉可汗組曲》的主題更龐大、結構也更完整。其用組曲的形式來鋪陳情節,使得一首首的曲子猶如電影中一幕幕動人的畫面,在光影流轉間娓娓說著蒙古高原上流傳不盡的英雄爭戰、兒女情長。這種做法在當時是項很大的創新與突破。“一直到現在,聽起來都還頗前衛的。”陶曉清回憶著說。
而在“天水樂集”製作的下一張專輯《一千個春天》中,他們又再度實驗了組曲的其他可能性,《細說從頭組曲》中的六首曲子可以各自獨立欣賞,而合起來又呈現了薪傳的大主題,且還有時間順序,亦是不錯的作品。
面對今日流行樂壇盛行的翻譯抄襲,當年“天水樂集”的這群年輕人對音樂的熱忱、理念及勇於實驗的創造力該是他們透過這二張專輯遺留給我們最珍貴的寶藏。就如同陳揚所說:“那時候我們可以為它連續開會個三、四天,對音樂編排方式,還有怎麼去詮釋一個蒙古的東西……,完全沒有禁忌,盡量發揮想象力……”就是這樣一種忠實於音樂、忠實於自己的態度,使他們做出了如此優秀耐聽的歌曲。而同樣身為所謂社會良知的大學生的我們,或許可以藉此反省自己,拿出勇氣及創意在各自的領域裡,發出真誠的聲音。
01. 漁樵問答
02. 寒山斜陽
03. 武松打虎
04. 歌者抒懷
05. 傻子的理想
06. 天水流長
07. 古城夢迴
08. 柴拉可汗︰序曲(音樂)
09. 柴拉可汗︰塞外
10. 柴拉可汗︰柴拉可汗
11. 柴拉可汗︰別離
12. 柴拉可汗︰征戰(音樂)
13. 柴拉可汗︰尾聲
